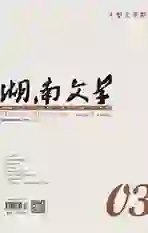我们幸福之时,别有他名
2019-04-21李翊云许玲
[美国]李翊云 许玲
李翊云,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出生于北京,现居美国。李翊云坚持用英文写作。主要作品有《千年敬祈》《金童玉女》《漂泊者》等,已经被翻译成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日语等十几种语言。《千年敬祈》获得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李翊云屡次入选英美“最佳青年作家”名单,如《格兰塔》杂志的“二十一位最佳美国青年小说家”和《纽约客》杂志的“二十位四十岁以下的作家”名单。二○一○年,麦克阿瑟基金会颁给她奖金高达五十万美元的“麦克阿瑟天才奖”。李翊云也成为继哈金之后,美国文坛上第二位以英语(非母语)写作获得成功的华裔作家。此文发表于《纽约客》杂志二○一八年第十期。
“办丧人就来了”,当嘉玉和克里斯按响门铃的时候,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对讲机中传来。他们在门廊上站了一分钟又一分钟。于是,嘉玉和克里斯便在两把柳条椅上坐下,两人中间是摆着黄菊的小圆桌。这是一个万里无云的日子,天空异常蔚蓝,一对松鼠在草坪上互相追逐,一些鸟儿隐藏在没有褪色的树叶间放声啁啾,这是它们对太过安静的邻里进行的一场抗议游戏。嘉玉想,兴许所有莎士比亚剧的真正背景,都处在这样一间无墙的等候室:人生是通往死亡的前厅。
四个月之后,她觉得那个念头,不过是自己刻意戏剧化,毫无意义的想法。她以后还能和谁谈论莎士比亚呢,她最后一次读莎士比亚,是在北京一所读大学时,攻读现在对她来说,几乎没什么价值的英语专业。现在,她想起埃文死后那一段阳光普照的日子,突然意识到她和艾里斯在对讲机听到的女声本尊,无论第一次还是之后的拜访中都没有现身过。殡仪馆里没有前台。每次那扇门开,只有办丧人出来和他们握手。嘉玉第一次打电话时,这个说话温和的男人在询问了埃文的出生日期后,说了一句话:“哦,天哪。”
对讲机里的声音,是属于连姓名牌都不需要的接待员,她也不用日以继夜的面对面接待客户。当然,如果没有死神的指令,没有谁会愿意踏进这所房子。在以往的所有场合中,嘉玉从来没有注意过一个前台接待,但是这个从未相遇过,不知长相的女人却拒绝沦为一个平庸的前台接待。死亡也不应如此庸庸碌碌,然而,其本身就是一种徒劳的抗议。这一点是她读了篇有关青少年惊人自杀数据的时文后意识到的。
死亡带来新的生活轨迹,哀痛的亲友团加入治丧,收到亲友确认出席葬礼的信,给内奥米小心翼翼地打电话。这个威斯康星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葬礼过后,她开始拒绝父母接近她的生活。这种全然陌生的,令人脆弱崩溃的日程让她想起人生的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它是祖父送给她的五岁生日礼物,对于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来说,它是一个奢侈品。不过,令人沮丧的是,她的小手指要拨到电台,收听时长半小时的午后学龄前节目也确实不容易。就算成功了,不过几分钟,表盘的指针就从正确频道上溜走了,关于狐狸小偷和派对狗熊的歌曲变成了静电的沙沙声。
那个怀抱收音机的小孩怎么就变成了如今的中年妇女,她依然无法将人生拨盘到正确的状态。有时,她将车停在车库前,却没法按下按钮打开库门。有时,她不明目的,不知疲倦地打扫房子,或者切洋葱时突然泪如雨下,直到菜板上一片透明的水洼。她为什么会在车库门止步不前,让洋葱浸泡在她的眼泪里,答案显而易见,一切反常或不反常的行动和感觉,都网罗在那柄名曰悲伤的伞下。
悲伤?悲伤是什么?一天早上,嘉玉睁开眼睛,对着天花板说:“悲伤,我不知道你是谁,所以请你不要假装知道我是谁。”
她和克里斯在丧礼结束后就恢复了上班,嘉玉在邻近城镇的一所公立大学管理文化交流项目,而克里斯是当地一家医院的医疗工程部门负责人。起初两人都在痛苦中挣扎,克里斯几次在工作中请假,嘉玉躲在女厕所里,一连哭了两天,可是他们仍然坚持着,在世人面前让自己看起来很坚强。嘉玉在第一次霜冻前整理了花园,种下了秋球茎,克里斯给灌溉系统做冬天来临前的防御。他们一起从路边摊买南瓜,和往常一样,依然是买的四个。两人每天都发短信给内奥米,知道她冰冷的面具后面有一颗和他们一样受伤的心。过了一段时间,内奥米态度变得柔和了许多,同意回家过感恩节。
在他们心里,能让他们坚持下去不是这种故作的坚忍,而是对现实失败的一种妥协。工作日结束时,他们中的一个会觉得不能坚持,心理几近瘫痪,他们俩会轮流进入这种状态,另一个人就会开车去附近的一个公园。在那里,他们只是一对在黄昏中散步的中年夫妻,黄昏来得一天比一天早,在日子站在了十一月的边上,他们已经是在黑暗中散步了。
“可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中的一个人在散步中打破沉默。
“为什么是他呢?”
“我一点也没有看出迹象,你呢?”
“没有,我以为是青春期。”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以为青春期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场艰难而又必经的考试。”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通过。”
“如今,当一个年轻人真难。”
“比我们那时要难多了,不是吗?”
“我看报纸上,很多研究人员都是这样说。”
“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他早上还在说他的游泳比赛呢,他看起来很兴奋的样子。”
“他談论考驾照时也是如此,他过生日那天一大早,我就准备带他去车管所。我正准备打电话给学校,说他预约了医生。”
“你觉得是学校里发生了什么吗?”
“没有一个朋友知道究竟怎么回事……”
“你不是以为他有很多朋友吗?”
“他拥有快乐的童年……”
“我们的确给了他一个快乐的童年,不是吗?”
“他自己这样说。”
“内奥米也这样说。”
“到底是哪里出了岔子?”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不知道真相是多么痛苦”
“这实在是太痛苦。”
“这是最痛苦的,不是吗?”
如果在五十年前,嘉玉和克里斯在这个美国中西部小镇可能会引人侧目。而如今,尽管克里斯母亲在婚礼上反复念叨这是难以置信的奇迹,一位玉米地里长大的小伙和一位北京胡同姑娘结婚,过上和邻居差不多的居家日子,已经不算个事儿了。
到今年夏天,他们的婚姻已经走过十九年,他们渡过那些磕绊,如所有婚姻都会出现的那样。他们一起努力去经营踏实的生活,用爱和拥有的常识去抚育内奥米和埃文。如此非常之事是怎么找上他们,并将他们牢牢困住,嘉玉想,他们如此平凡,对生活并无野心,默默无闻。一个孩子死了,这应该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事,是希腊悲剧或苦情电影中的事。一只蚂蚁被雷劈中的机率有多大,幸存的蚂蚁要背负多少创伤,让自己努力生存下去?
嘉玉在她的电脑建立了一个表格。她的家人、亲戚、邻居、熟人——她试图列出她所遇见过的亡故之人,她记下她还能想起的,每个人的生卒年份和死亡原因。 在她记不清的地方,被她标满了句号。虽然她可以查讣告,找到一些被她丢失的信息。可是她就是想挑战自己的记忆力,如果那些走了的人,还有那么一件或者两件事存在于她的脑海里,他们就没有被遗忘,就不会沦为一个泛泛而平庸的死者。
例如,艾琳·威尔森,嘉玉婚礼上最老的宾客之一。“我的表兄”威尔森太太在婚礼上对嘉玉说,“他在中国是一个传教士。”
“什么时候的事?”嘉玉问道。
“一八九一年。” 威尔森太太说。
“我的祖父出生于那一年。”嘉玉说。
“这是多么巧!我的表兄死于那一年。他在山东省住了两个月,然后掉了脑袋。”威尔森太太将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脖子上说。
“噢,天啦!”嘉玉说,我很抱歉。
“得了,你不需要道歉。”这个老女人笑着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告诉你,我最喜欢碰到谁——我的姑姥姥萨莉,她从邻居那里偷了五只绵羊,这在当时是能送上绞刑架的罪,但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她得到了宽恕。”
回忆这些故去的人,决不像在回忆之路上故地重游一样,回忆之路,嘉玉对自己说,多怪的短语,只有条理清晰的大脑才能想出个所以然。回忆,它并不是沿着一条插着岁月木桩的林荫道上散步,回忆是干草垛,想在里面找一个故事,结果你会得到一百个故事,但是没有一个是完整的。
故事不断涌现出来。想到埃文时会让她分心,尽管思念本身毫无用处,想念埃文本身也是一种错误的说法。想,就是回忆,是一种追溯行为。可是埃文一直都在这里:在她精心尝试新食谱的周末时光里,在她将插着花朵的花瓶摆满缺少色彩的房间里,在她为了稍微缓解心痛,放的冥想软件空洞的声音里。
电子表格在她的电脑上一直开着。每一个名字,不仅只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比如,文姐的丈夫和文姐,文姐是她在北京的邻居家中最小的女儿,比她大十四岁。文姐和一个警察开始约会时,每个周日早晨,嘉玉都会在胡同口处等他,看到他骑着摩托车的身影出现,就会往回跑,大声喊道,他来啦!他来啦!丝毫不在乎文姐其实已经站在院子里,也能听到摩托车引擎的声音,仿佛她是那一只给婚姻提前报喜的喜鹊。
五十岁,肝癌。当嘉玉在男人名字旁边打出这些字时,想像不出他成为老男人的样子。有一次,他和文姐带着嘉玉去兜风,她坐在警车的侧斗里,手紧紧抓着前面的金属栏杆,仰着头看着他们:她穿着杏黄色的连衣裙,而他穿着白色的制服。“我们幸福之时,别有他名”。嘉玉想起自己还是学生时读过的这句话,尽管她已经记不起上下文。一对沉浸在爱河中的年轻人,一个只想见证这场爱情故事的孩子——结果,他们都成了什么样?一个死去的男人,一个寡妇,一个丧子的母亲。
但嘉玉并不是第一个失去孩子的父母。她不断提醒自己。还有她的表妹敏,她的孩子在不到两岁时死于白血病。这个孩子已经从她的记忆里褪色,虽然她知道如果打开一本旧相册,她还能找到她的照片。许多亲戚都为她的离去流过泪,但是现在又有多少人能讲述关于那个小女孩的故事呢?敏丧女之后又生了一个孩子,一个健康的男孩。有一次,一位重男轻女的姑妈对嘉玉的母亲说,应该积极地看待整件事情,因为孩子的死为小弟弟腾出了地方。这个姑妈说过,独生子女政策肯定不能改变,所以有时生个女儿,反倒是个坏消息。
还有儿时伙伴莺莺,在她们进入不同的小学前是非常要好的玩伴。她们的母亲一起在北京第二聋哑学校教书,她们下午在等待妈妈下班的时间里,一起在学校的操坪上玩耍。莺莺比嘉玉小一岁,是个胆小的姑娘,嘉玉喜欢把毛毛虫藏在火柴盒里或把甲壳虫放到她手背上来戏弄她。莺莺会吓得哭起来,嘉玉便去安慰她,两个人很快合好。她们旁若无人,自始至终假装看不到将她们包围的学生,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都是由政府供养的寄宿生,那些孩子比她们年纪大得多,有些快二十岁了,准备在学徒期满就离开学校了。
嘉玉现在想来,她们俩都带有点表演的意味。她想着法子让莺莺哭,而莺莺也乐于接受这种机会,来制造一些喧哗而让她们显得与其他学生不一样。他们中的一些孩子会围着她俩站成一个半圈,表情严肃地凝视着她们,互相做着手势比划着手语,嘉玉得知他们正在谈论她和她的朋友,这使她很兴奋。她們不需要手势的交流无法越过她们站着的中心,她和莺莺也无法进入这个半圆组成的无声世界。
一年前,嘉玉的母亲打电话告诉她莺莺死了,死于卵巢癌,四十三岁,她的女儿刚进入中学。嘉玉不能想像童年玩伴成了躺在棺材里的女人。一个母亲失去了孩子,一个孩子失去了母亲,这两者看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也许,悲伤无非是令人难以置信。
第一场雪下下来,融化了,然后是第二场雪,在这之后,她实在没有理由再将这一切继续算下去。邻居们装上了圣诞灯,屋檐下蓝白相间的冰锥,橙色和红色的灯泡闪烁着,勾勒出常青树的轮廊。一只鹿在前院拉着雪橇,天使张着宽大的翅膀吹着喇叭。这个世界并非新造,也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它会再次成为这个新的世界。也许,悲伤不过是认识到假象不再。
“把房子装饰下会让我们很难过吗?”有一天晚上,他们把车子停在未亮灯的房前,嘉玉问道。
“要是不装饰,我们会不会更悲伤?”
“你认为埃文会希望我们怎么做?”
“我不知道,我无法抉择。”
“我也是。”
圣诞树怎么弄?嘉玉绣的有他们名字的四只袜子怎么弄?平安夜是否还去埃里克森太太家里?埃里克森太太的孙女和埃文的生日相差一天,因为不同病因,两人住在相邻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里。后来,埃里克森太太认了埃文为干孙子,他们和埃里森太太的大家庭一起渡过了十五个圣诞节。他们大肆吃着烤火腿、扇形土豆和香脆薄饼,然后大家在埃里森太太的钢琴伴奏下,一起唱圣诞颂歌。这是一架年代久远的竖式钢琴,为了迎接这场节目,它每年都需调一次音
每一个问题都从开始走向了死胡同。嘉玉觉得某一天,她和克里斯会对视一下,然后毫不犹豫地开车去挑一棵树回来。克里斯会装上灯,嘉玉会整理长袜子,包括埃文的,将它们放在壁炉上。当埃里克森太太发出邀请时,他们会问是否需要带锅贴,这是他们在聚会中一贯的贡献,他们将和以前一样,一如既往地做那些事情。“永远”是一个不可信的词,再说,除了遵守“一如既往”的法则,还能做什么呢?在一个难免犯错的人生中,这是一条既不更好也不更差的路。
表格停止了更新,痛楚却未得到缓解。一个人将死亡的知识可以写到枯竭,丧子之痛却缠绵无绝。如果嘉玉开始重新列出活着的、健康并且幸福的人的清单,也许她能写个更长的单子,但是,诸多的死亡例子也不能制造出痛丧一子的有效解药,再多的生命对她又有何不同?
嘉玉突然意识到,埃文可能某天也会进入另一个人的名单。这种想法既没有安慰她,却也没有给她增添困扰。表格里还有华,一个在毕业前一年自杀的高中同学。还有嘉玉幼儿园时期朋友的父亲,他在两年前的一个晚上,在退休合唱团的彩排结束后自杀了。嘉玉高中时从没和华说过话,朋友的父亲戴着黑框眼镜,她能记起的就那么多了。
尽管如此,她还是经常会翻出电子表格,试图回忆更多的瞬间,更多的细节。有时,一个新的名字会突然出现,她很惊讶,仿佛死者正在耐心地等待着她去找回他们。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被称作“英勇奶奶”的老妇人独自一人住在隔壁的小巷里,她是一个农民党派,她去世后,报纸也证实了这一点。这张报纸上还印有“英勇的女孩”的照片——她在战争期间的昵称——当时她还是十几岁的少女模样,剪着短发,肩膀上扛着卡宾枪,两把没鞘的匕首随意地插在腰带上。三年级的时候,嘉玉和她最好的朋友策划了一场为期一年的比赛,比赛内容包括做好事,他们决定每天去看“英勇奶奶”,打扫她的房子,帮她做跑腿的差事,准备简单的饭菜,听她追忆战争时期那些传奇的故事。他们来的前两次,她挥手把他们赶走了,当他们一意坚持时,她动用了扫帚将他们轰了出去。她告诫说,如果他们敢再出现,她就把她们视为老革命家的骚扰者报告给学校。噢,此等羞辱,这般不公,嘉玉现在回想起,那種感觉,这是这么久以来,她第一次想冲动得大笑。她还记得,在遭到“英勇奶奶”威胁的第二天,她和她的朋友挖了十条蚯蚓,把它们扔进了老太太的院子里。
噢,重温年轻和不败的岁月是多么有趣啊!
或是回忆一下那些寿终正寝的老年人和他们功成名就的生活。在清单的所有人中,嘉玉经常回想起她外祖父。他长寿幸福,一百零一岁才过世。对妻子而言,他是个好丈夫,对八个子女而言,是个好父亲,对所有孙辈而言,都是慈祥和公平的。敏的小姑娘死时,他没哭,但此后每个曾孙辈出生,他都送一把银制的长寿锁,坠饰上一边刻着“长命百岁”,另一边刻着“富有、幸运、平安、祥和”,以保护他们脆弱的生命。
晚年丧妻后,他会花掉部分时间在每个子女家轮住,也会自己旅行,有时会造访已经成家的孙辈。因为嘉玉的母亲是兄弟姊妹中最小的,她家经常在八月接待外祖父。外祖父在她家最多呆几周,他不允许自己成为一个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
嘉玉心想,她外祖父孑然一身的生活,理应成为一条美好的记忆之路。他在嘉玉家小住的时候,恰逢她的暑假时光,她陪外祖父早晨慢跑,晚上遛弯,还去北京的很多宫殿城墙和公园远足郊游。
即使此刻她还坐在电脑前,只要循着那条不变的轨迹,她依然能够追忆起那个颐和园、那座紫禁城:从圆亭到八角亭,从石拱桥到木拱桥,从睡莲盛开的锦鲤池到只有锦鲤的池塘。在最热的日子里,他们就待在家里,坐在院子里的槐树荫下,外祖父自己从一个凉在水盆中的锡壶里倒茶,嘉玉在低垂的树枝上找槐蚕。外祖父送给她的晶体管收音机放低了音量,当他们懒得再拨表盘时,就让它放着静电音。有时外祖父会打个盹,只有这时,嘉玉才会拿出他给她的一个钢镚儿,去买个冰棍儿。
每年外祖父到访前的夏天,母亲都会边打扫屋子,边自言自语。她说,来一次少一次了。他这把年纪,你永远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在聋哑学校教了一些年学后,她养成了把所思所想大声说出来的习惯,忘了世界还能听得到她的声音。
嘉玉全都听到了。一个较敏感的孩子可能会担心这些睡不着觉,关切地看着外祖父的每一个动作。但他毫无身体欠佳的迹象。一两天后,很难不去相信,他将会长生不老呢。
槐树下,一切看起来都井井有条。嘉玉是个普通孩子,很容易满足,外祖父拥有美好的人生。生活感觉就应该如此,每一代人都会在生命该结束的时候安详而去。可埃文的死扰乱了这种秩序,这让嘉玉感到不安,如果她认为埃文理所应当会像她祖父一样幸福长寿,她能否避免重蹈覆辙轻信所有这一切都是正常的?
后来,她的名单又多了两个连姓名都不知道的人,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她们的出现,让嘉玉感到震惊,以至于认为自己已经很脆弱的心脏不再是体内的一个稳定器官。之后的几天里,她恍恍惚惚,在已不真切的记忆中惶恐不安,如同发掘着童年的遗迹,那些记忆碎片像一块块风化的小骨头,一碰就碎,灰尘飞扬。
有一天傍晚,她和外祖父散步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女人和她的两个女儿。大的和嘉玉年纪相仿,小的还坐在竹推车里。对,是两个女孩和一辆竹推车没错,嘉玉确定了这段记忆。当嘉玉的祖父和女孩们的母亲坐在附近的长凳上时,她和大点的孩子便轮流推着它。嘉玉在那年早春已经满了五岁,她随身带着晶体管收音机。几周来陪她玩耍的小女孩想看她的收音机,嘉玉给她看开关键、调频旋钮和音量键,还有拔出来可折叠的天线,她们假装是鱼竿,在她们的游戏中,婴儿推车中的女孩,就是她们要钓的鱼。小女孩举起手来哭,可是她们就是让她够不着天线的末端。嘉玉现在还记得,两姐妹的锅盖发型。而她自己穿着最喜欢的,绣着向日葵褶边的黄色无袖裙。
后来,小女孩和推车消失了,就在同一个夏天。嘉玉记不住具体哪天了。她记得有一天,她和小姐姐爬上人工湖旁边的一块石头,就在那个湖边小姐姐说她妹妹死了,但没说怎么死的。没有小妹妹当鱼,嘉玉和小姐姐那天没有玩游戏。嘉玉记忆中,她们坐在石头上听广播,小心地拿着收音机不让它掉下去,嘉玉看见女孩的妈妈和嘉玉的祖父坐在长椅上。不知那个女人跟他讲述这个消息有没有流泪?外祖父是不是尽量保持着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女子之间的合宜距离,却想着将她的手放进自己的手心里?
暴风雨很到了她家。这是嘉玉唯一一次看到母亲失去了温和的脾气,对着外祖父发火。不可能,她对外祖父咆哮。疯了吗,她也大吼那个女人,她大叫大喊,他这么大年纪的人,和一个可以做他孙女的年轻女人在一起,人们会怎么想?
嘉玉现在分析,他应该不只是想给这个女人经济支持,他可以不让任何人知道就给她钱。他是否说要结婚?还是打算以不那么传统的关系相处?他曾设想过要改变鳏夫的生活,只是出于憐悯一个丧偶了的寡妇和失去孩子的母亲,抑或出于对一个在他生命即将拉下帷幕时,照亮了整个夏天的女人的爱,抑或是众多子孙也无法慰及到的孤独?嘉玉不敢回答这些问题。如果一个答案让逝者成了另一个人,那么回答是没有必要的。
事后的那年夏天风平浪静,此后也是如此。一如既往,嘉玉和他的外祖父照样四处溜达,却再也没碰到那个女人和她还活着的那个女儿。几年后,这个女生转学到嘉玉的学校。嘉玉立马认出她来了,但这个女儿看起来不记得嘉玉了。故事的结局是这个女孩的母亲也死了,这个女孩现在与她的表舅和表舅妈住在一起,表舅妈是她母亲的一个表亲。这对夫妇给她取了一个新名字,嘉玉现在还记得。虽然回忆总是很吝啬,却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打开了闸门。现在女孩的名字是两个字,叫舒畅,意思是“幸福和无忧无虑”。 收养女孩儿的夫妇俩肯定对她寄予了希望。嘉玉意识到她从来不曾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女孩以前的名字了,那个还是那位母亲的女儿时用的名字。
嘉玉的祖父在她上大学时去世了。直到那时,她才知道他在祖母前还有一任妻子。他们唯一的儿子还是婴儿时死于白喉,而那个妻子自杀了。这个消息知道得太晚,被嘉玉当作远古的历史尘封了,直到现在,嘉玉才能想像出外祖父曾经的三口之家。如果说生命是死亡的前厅,那么死亡也是其他生命的前厅。她想起了人造湖边的岩石上,她和女孩看着长凳上的男人和女人。她孩子的死亡,让嘉玉再一次悼念她的祖父。这一次,他是一位埋葬了他妻子和老婆的年轻男人。尽管她不能说,这种哀思来得太晚。然而,真正的悲伤始于不相信,而终结于别处,它从来都不会太晚。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