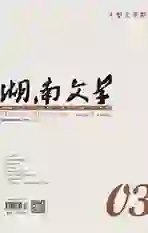穿过街河口(外一篇)
2019-04-21查建中
查建中
我的样子很狼狈。左手端个搪瓷脸盆,里面是漱口杯、牙膏牙刷和一块肥皂,稍一晃动,脸盆和杯子就撞得“叮当”乱响。右手提只网兜,里面塞几件衣服。最有特色的是背在背上的被褥。那包单用日本尿素袋拼接而成。许多“尿素”“株式会社”“净含量46%”的字样被折叠在一起,变成“会尿”“46%株”等莫名其妙的组合。
我要去的地方是一条两百吨排水量的木驳船,全称叫做:岳阳帆船运输社一大队一组。那里将是我进入社会的第一个起点,也是我初中毕业被待业两年后走向新生活的出发地。但我却找不到它在哪里。
大队童秘书叹了口气:我送你去吧。说完接过我手里的网兜走出大队部。
大队部在街河口,是一条和这座城市一样古老的小街。与其说是街,不如说是座码头更准确。街长不过两百米,一直往西延伸到水边。街面随着湖水的涨落延长或缩短。冬季枯水时街面可以一直伸到湖中心,而到夏天时湖水可以涨到大队部的门口。水最大时小划子能一直划到街河口与南正街交汇的十字路口。
街河口是岳阳城连接洞庭湖西岸最重要的客货两用码头。每天有数十条船靠泊。那些船在这里卸下一群群走亲访友、赶街贩运的人,或是卸下一堆堆西瓜、柑橘、红薯、黄豆等农副产品,还有肉猪、家禽、鲜蛋等,再装上返程的人群和日杂百货、农具、烟酒糖之类的用品远驶而去。小街上一天到晚人来人往,推车的、挑担的、过磅称重的。人们肩扛手抬,人声鼎沸。加上鸡鸣、狗吠、猪哼哼,把这个叫做街河口的地方搅得声名远播,在湘北地区几乎无人不晓。
来往的人一多,自然做生意的就多。街两边几乎全是店鋪。最具特色的店铺有两类。一类是杂货铺,里面专卖船舶用品。桐油、石膏、贮麻、帆索、缆绳、油布。还有两丈长的挽篙,杂木制作的船桨……光顾这类店铺的全是头扎罗布手巾,裤脚卷起老高,把薄扇大的一双赤脚踏得路面“叭叭”响的船拐子。另一类是铁匠铺,门前必有几只大铁锚。铺子里面的墙上挂满了葫芦、马钉、刮刨、粗细不一的铁链,类似古代兵器“戈”的挽篙头,以及其他一些稀奇古怪的船上专用铁器。铁匠铺里面少不了一炉火,一铁砧。炉火在风箱的鼓动下耀出白色的火光。铁匠从火光中钳出一块烧红的铁置于砧上,大锤小锤开始此起彼伏,火星四溅,“叮当叮当”的节奏从街头漫向街尾,有极好的韵律。
我在大队部参加了一个星期的“水运知识培训班”,休息时就溜到街上四处转悠,对这条街渐渐熟悉起来。街对面有一个小酒馆,炒菜的炉灶就摆在门外。有酒客来了,那厨师就当街操作,自然把厨房里十八般武艺格外地卖弄出来,只听锅碗瓢勺一片响,颠勺时炒锅里的热油和着菜肴一起翻飞,火焰腾起老高,诱人的香味便慢慢浓洌起来。许多年后,吃了不少山珍海味却还是忘不了那街边小酒馆的香味。也许是当年一直没有尝到过那小酒馆里的味道所致吧。
而街河口有一样美食我却尝过,是用小蒸钵酿制的甜酒。卖甜酒的老汉每天挑一担食盒,里面大约有几十钵甜酒,五分钱一钵。老汉从来不高声叫卖,只把手中两块竹片打出花样翻新的声响,在满街的喧嚣中独具一格。那声音带着酒香和清甜,具有极强的侵略性。
所有的店铺里用水都是直接从湖里面挑。这种体力活一般是男人做,只有铁匠铺的女人长年挑水。那女子个头高挑,属于苗条型。挑水时裤腿挽到膝盖上,这样就可以站在水里直接用水桶舀水。铁匠女人挑着一担水从街上走过时,细碎步,水蛇腰,水桶随着步伐起伏忽闪,胸脯也随着步伐起伏忽闪。那水桶里面的水漾出一圈圈细纹却不溢出一滴。这时,西斜的阳光在铁匠女人身前拉出长长的影子,满湖的水在身后闪闪烁烁。她一路忽闪过去,整条街都痴了。
穿过街河口,有一条坡巷通往鱼巷子。巷子内清一色的麻石地面。石面光洁如镜,透露出岁月的悠远。这条与街河口齐名的鱼巷子现在却腥臭无比,我心里一阵阵翻涌,却强忍着不敢吱声,因为童秘书正高声大气地和每一个熟悉的渔民打着招呼,还不时在某一个鱼摊前停下,揭开渔篓看看,然后开骂:狗日的黑了心,这鱼都死了几天了还拿来卖,不怕你老婆生个崽没屁眼呀!那“狗日的”也回骂:我是缺了德呢,昨天老婆生了,我回去一看,小崽子怎么长了一脸的麻子。“狗日的”一脸坏笑地盯着童秘书脸上的麻子。童秘书会意,哈哈大笑,和卖鱼的笑成了一堆。看得出童秘书是个极随和的人,听说为人特仗义,肯帮忙,在这一带有着极好的人缘。
好不容易穿过那些腥臭,我们来到高高的码头上。洞庭湖扑面而来,正是枯水时节,水不大。风从水面拂过,远处有大大小小的风帆在波澜不惊的湖中鼓风而行。天很蓝,有一堆一堆的白云漂浮。极远处的君山在阳光的背景里成为一张剪影。湖边泊满了各色各样的船。,童秘书指着那一大片渔划子对我说,要吃鱼只有到那些划子上去买。那些划子上都有一个活舱,里面的水和湖水相通。那舱里捞上来的鱼都是活蹦乱跳的。直接用清水煮,放点盐,什么佐料都不要,保证鲜掉你的下巴。
童秘书的清水煮鱼秘诀,在我后来十几年的水手生涯中曾经无数次地使用过,果然是人间第一美味。不过这办法现在不能用了,那些在池塘里用饲料养出来的鱼,任你是国宴大厨也做不出那种鲜美来。
沿着渔巷子的石阶下到湖滩。顺湖滩向北远远地可以看见一大片木排,在木排的外面停靠着几艘木驳船,我们必须走过这片湖滩才能到达那里。湖滩上有三三两两的人群走过,一看那古铜色的皮肤和蒲扇一样的大脚就知道,都是风浪里讨生计的人。偶尔有个把女人,小心翼翼地跟在一个男人的后面,沧海桑田的脸上也看不出真实年龄,不过走路的身态倒是婀娜多姿。
风不大,但也能掀起一层层细浪从湖心飘过来,冲向岸边。前面的浪刚退,后面的浪又迎头冲上来,两股水流冲撞到一起,卷起一线白色的浪花。如此地周而复始,在水与岸的交际处形成一条白线,断断续续逶迤而去,北不见头南不见尾。波浪沿岸洒落斑斑驳驳的漂浮物,一蓬蓑草,几片乱木,半只烂球鞋,空酒瓶,破木箱,还有一只小凳子,四条腿只剩下一条腿。这些乱七八糟的漂浮物躺在天地之间,是不是正在回忆各自的故事呢?比如那只球鞋,曾经穿在什么样的脚上,它走过城市宽阔的大街吗,走过乡间泥泞的小道吗,它是否在某一间私密的小屋听过主人喁喁的情话,是否偷偷踩过某只女式的鞋?如今,它漂落在天地间的某一片湖滩边,是永远搁浅在这里,还是要随着下一个浪头继续开始新的漂泊,就那么随波逐流漫无目的,直到腐烂,直到化作一堆尘埃。
忽然穿过一片沙滩,细腻的沙粒在波浪的冲刷下平整如镜。阳光下闪闪烁烁的光点是沙粒们破碎的灵魂还是思想的片断,它们从遥远的高山上被水流带到这里,是不是还在寻找皈依的故园呢?我一边走着一边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着。童秘书看我一脸凝重,满腹心思,也不多话。只有此起彼伏的脚步声忽轻忽重地淹没在岸边轻轻的浪花声里。
小心点,我们要上木排了。童秘书的声音忽然响起,吓得我一激灵。抬头,一大队一组已经清晰可见啦。
见习水手
是一个舱室。大约七八个平方米,高两米。靠后舱壁有一张用几块船板搭成的简陋的床,没有桌子,没有凳子,也没有窗户。床铺前方两米处的舱顶有一个八十公分见方的开口,顺着口子下的楼梯爬上去就可以出舱。这是房间唯一的出口兼采光口。我把被褥在床上铺好,躺上去试了试。头正好顶着船舷,隔着五公分厚的船板就是湖水,可以清晰地听见水在船板外流过的唰唰声。船舱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桐油味,这是一种被浓缩了的自然的气息,有森林的味道。如果这气息再淡一点应该就变成了芳香。桐油是天然的油脂,是木船用来防腐防漏的最佳材料。实际上我们这艘木驳船上所有的木制品包括水桶、脚盆全部都用桐油涂过,所以整艘船都笼罩在桐油的气息里。
我从床上坐起来,头有些发懵,一时竟不知身在何处。我的“豪宅”就位于船的最前部,叫着闷头。舱顶的外面叫铺头。铺头上有绞锚关、系缆桩,最前端伸出浪头的部分是鸡公头,上面吊着三百斤重的主锚。铺头是水手们最主要的作业场地。抛锚、起锚、系缆、撑篙,向拖轮递送和解除连接钢缆,和邻船相互搭帮的作业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水手们扯皮打架,搏力较技的许多故事也都是在这里上演。
正发愣,外面有人叫喊:新来的学生伢子弄完吗?组长回来了叫你去。喊我的人好像姓蒋,三十五六岁,个头不上一米五,凸起的嘴唇下两颗包不住的大暴牙最引人注目。我赶紧爬出舱随他往船尾走。不料他一把拉住我,指着舱口对我说,舱口必须时刻都关着。他告诉我舱盖有两层,下面一层木格子盖板通过滑动开闭。人在舱里时只需拉上格子盖板,既透光又通气。人出去或者铺头上要作业时必须把外面一层木盖扣好。他一边为我示范一边解释,如果舱盖不及时盖上,有人过时不小心踏空肯定会出伤亡事故,那可不得了!我听着一阵后怕。这时看他那两颗大暴牙似乎没有那么扎眼了。
组长姓侯,年龄在五十岁上下。人们称他会爹(kuai dia)。个子也不高,偏矮。不过身板比蒋师傅壮实多了,隔着冬衣也能感觉到那对臂膀的力量。侯组长坐着,我站着。他不动声色地盯着我足足有分把钟,让我觉得时间突然变得无比漫长。
家里什么成分?他突然开了口。
下中农。
父亲是做什么的?
省航运局干部。
二十一种人吧?
……嗯。
刚才是不是你在那边的木排上喊救命?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一组是靠泊在木材公司的一片木排外面,要上船必须从这片上千平方米的排上走过来。大片的木排则是由一小块一小块木排联结在一起的。我第一次行走在這些又圆又滑,欲沉欲浮的木头上,心中战战兢兢,犹犹豫豫。一个不小心,两块木排突然裂开,裂缝越来越大。我一脚蹬一块小排,腿越劈越开,不由惊得大呼小叫。走在前面的童秘书回头见我窘态,转身把联结两块木排中间的篾缆往上一提,两块排悄然合拢。那边,有人在哈哈大笑。
幸好侯组长没有继续问下去。显然他对我的情况已经摸得十分清楚。我父亲刚从单位关押二十一种人的学习班放出来,正在航运局的码头上拉着板车改造思想呢。
侯组长开始介绍一组的情况。他手里捏着一把小壶,一边喝着一边挺自豪地说着。
一组共有两艘木驳船。每艘满载排水量为两百吨。是全社最大的两艘无动力货船。船长约四十米,宽六米,满载吃水深两米。船分前后两个货舱。船尾有舵舱兼卧室兼餐厅兼厨房。有两个封闭的吊铺,其中一个是侯组长夫妻休息兼做爱处。船舱建在舱面之上,又称梢楼。高约二点八米,面积大概不超过二十个平方米。全组算上我共有十人。一号驳六人,二号驳四人。我在一号驳,不算正劳力,侯的老婆专管做饭。所以两艘船的人手分配是基本均衡的。
侯组长分配给我的工作内容是每天和两位师傅用吊水桶提水冲洗铺头和船两边走人的跑干,冲完再用拖把抹干水渍。两个货舱的盖板也要抹干净。早晚各一次。至于舵舱内就不用我们管,那是他们俩口子的范围。船舶受载前我要和师傅们把货舱的盖板揭开码好。把货舱的底板一一铺好。上货时,我的任务是在跳板前发筹(一种小竹牌,用以计量搬运工人装货的数量,也是他们用来结算的凭证)。但是我们一般习惯把这种小竹牌叫做“欢喜”,发“欢喜”而不是发“愁”,无非是讨个好彩头。我要学习的内容也很多。如笨重货和散装货的受载卸载顺序各有不同,泡装货的堆码更有技巧。航行时怎样下腰舱察看底舱渗水,怎样用唧筒泵排水。怎样扎拖把,打绳结,系缆绳,怎样给船体抹桐油。甚至怎样走路怎样上跳板都要从头学起。不一而足。
侯组长警告我,三个月内不许到铺头上作业,不许独自驾驶脚划子,不许在行船的时候用吊桶到船外提水。我在心里开始咒骂这老小子,心中发恨同时也暗暗担心,看来就算我已经沦落到船拐子了还是躲不开革命群众警惕的监视。想到这里,心情突然沮丧之极。我心不在焉地听着,目光却落在侯组长身后挂着的一叠日历上。最前面一页是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日,农历鼠年二月初六,春分(申时)。我看不清那个“鼠”字,身体不由自主凑上前去。侯组长往后一仰,双手已作势横在胸前。这时我突然嗅到一股酒味,原来侯组长手里捏着的壶里装的不是茶水而是酒。我对侯组长笑笑,我想看看你壶装的是什么,原来果然是酒。他的脸色一松随即又紧张地双手捂紧酒壶,你不许偷我的酒喝!我瞥见他说这话时蒋师傅脸上有一丝诡异的笑意一闪而过。一时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只口中“嗯,嗯”地应着。
晚上七点钟开批林批孔的批判会。侯组长最后用一个开会通知结束了和我的谈话。我暗吁一口气,告辞转身出了舵舱。却听见蒋师傅在里面起了高腔。
又开什么会,都批了大半年了还批?
这是政治任务,上面布置的。
二号驳还在湘阴卸载,半组人怎么开?
也要开。
花麻子和老马都上岸去了。
已经通知他们。
我不管,晚上我要回去看崽。
说得好听,看崽!怕是欠着路没搞得吧。我看你迟早要死在堂客的胯里。好吧好吧,只开一个小时,散会就让你回去。
蒋师傅如获大赦,一脸春风地出来领着我开始洗船。
早春天日短。太阳已经开始西斜,阳光泛出红色。湖面虽然比丰水期缩小了许多,却反而更加闹腾。各式各样的船舶往来穿梭,汽笛声声。远处归帆拉出长长的侧影,如劳作中的剪叶蚁,悄无声息地滑过水面,船尾的浪痕隐约可见。数只小鱼划子在来来往往行驶的船舶之间穿来绕去,让人看得心惊胆战。那渔人却不在乎,只把两叶桨打得上下翻飞,驾着那小划子像鸟入丛林般随心随意,还不忘向过往的大船招手示意,兜售刚刚捕获的鲜鱼。太阳这时已经像一枚巨大的蛋黄,漂浮在天边的云层之中摇摇欲坠。有水鸟腾起,排着整齐的队列掠过天际。春色已浓,这大概是最后一批北归的候鸟。
我笨拙地完成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水手的作业。在春分这一天成为一名见习水手。不过,晚上还有一个批判会在等着呢。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