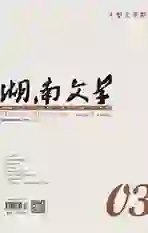活在鼎丰的人间
2019-04-21陈甲元
陈甲元
一
时令一过,已是初冬。就丰城而言,这是一年里难得的冷暖相宜的好日子:气温在十到二十度之间,早晚温差不大,起大风的时候少,太阳不烈。即使有雨,也不会长久。这样的天气,满城人受天气的影响,温和,谦让,知书达理。不像这前后的时节,要么暴烈,要么冷酷!这表现和丰城的位置和气候确实有关系:丰城位于江边,这之前的夏秋,太阳火辣、江水滚烫,拉高了丰城的气温;之后的深冬,江风呼啸、江水寒凉,有时还会结冰。夜深人静的时候,寒风呼啸着从江城的高楼上空猎猎吹过,让丰城市民从发肤到内心对冬天都有着具体细微的感受。
公司在丰城东北一角,在仁智大厦的十二层。当初选址的时候,一重考虑是大厦周边是已成气候的行业商业圈;二重考虑是此地离岳母家、离自己的新家近,方便适用。时间老人是魔术师手中的神奇魔法棒,挥舞比划的瞬间,八年时间就过去了,从八年前的小陈到现在的陈总,从当初的良好青年到现在小女孩眼中的大叔,时间对躯体的侵袭是传染,扩散得厉害。
下午去仓库的时候,本可以出公司大门直接右转,再在第五个红绿灯路口左转,左转后直行一点五公里再左转上坡即到,但前天坐电梯下楼,看到大厦新换电梯暂未拆卸的木框上被建筑工人涂写在上面的“生活,生下来,活下去!”的涂鸦后,这盘踞心头的八个汉字在今天下午就产生了奇异和强大的魔力,牵引我走向另一条可达仓库的路:出大门后左转,行驶一公里左右后右转上坡,上坡后连续弯路,在弯路两公里处再插横上坡即到。这样,虽然远了一公里,但在连续弯路的中间三百米平坦地段的右边,能见到那一簇灰扑扑的工厂老房子,见到三栋用作冷库的大仓库,见到水泥砂石地的宽阔的鼎丰大院前坪,坪里停满挂着吉字、粤字、赣字、辽字等开头牌照的大货车,有长相如北方大馒头的东北汉子攀着货车的曲针形扶手跑到门口右侧的鼎丰商店买方便面泡水吃;能见到冷库当头工人们晃动的身影;冷库靠门口这头,住户花花绿绿晾在铁丝上的衣服;能看到不愿和子女住市中心的李娭毑房子前面墨绿的盆栽,运气好的时候,看得到盆栽里碗状的大红花灿烂开放。
这里是鼎丰大院,我身心的一部分,我生命里某些东西留在了这里。隔得久了,就像有某种隐疾复发,只有鼎丰的空气,空气里夹杂着鱼腥(冷库里放做熟食的小鱼仔较多,据说鱼仔来自越南,也有更远的来自印度洋畔的莫桑比克,鱼仔气味浓烈)的气味才是此类隐疾的对症良药。
二
鼎丰的命运是和岳母一家人尤其是和岳母一生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岳父的老家在鼎丰往东二十公里的一个叫白云的地方,岳母虽然不高,但长得灵秀聪颖。后来当好事的老婆问岳母为什么当初选择和没钱的岳父结婚时,岳母坦诚当时七挑八选,年龄大了,可供选择的只有娘家山区附近的几个青年,所以当亲戚做媒把岳父介绍他时,虽然觉得岳父家贫,但有地域好、年轻的岳父长相好两方面优势时,她权衡之后还是答应了求婚的要求。白云是塅里,人烟稠密,岳母在生下老婆一岁后,省里选址白云修机场,在选择补偿现金或安排工作时,岳母做主选择了后者,洗脚上岸,和同村邻村的农人一样,糠箩跳到米箩里,做了鼎丰汽车配件厂的工人。
据老婆讲,她的童年是相当幸福的,当时的工人地位高、福利好,生活条件远远高于当地居民。她们上学时经常有零食带着,羡煞了周边农家的孩子,厂里有固定工资,家里有单车,寒暑有福利,家里的绿豆,白糖,瓷缸存货都不少。岳母也在搬到鼎丰第三年后,产下了舅子小明,衣食红火,儿女双全,日子过得舒坦。然世上的事,仿佛注定了起起落落,厂子兴旺了几年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放开,效益开始滑坡,到后来,竟被厂长偷偷签字卖给第三方。岳母的能耐就是在接下来的和第三方打官司和省轻工业局协调的事故中凸显的,当年正是岳母带队,带着鼎丰院子里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一百多号人在省轻工业局大院吃住一个星期,与第三方打了将一年的持久战后,终于将鼎丰所在土地的产权争取了过来。
和老婆结婚后,在鼎丰院子里走走,能感觉到岳母在大院里受到的尊敬,邻居们有什么事都喜欢请她到家里坐坐,或者直接上岳母家門,就一些具体事情征求岳母的意见。有雨有闲的日子,岳母喜欢戴上老花镜,将红绿两个有了年份的本本拿出来,犀利的眼神不时透过镜片折射到手拿遥控想看电视的我身上,岳母总是先酝了酝神,叹了口长气,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唉!千辛万苦搞得鼎丰的房产证件,不容易!当年虎子也真猛,直接蹿上去,把轻工业局食堂那一大钵白米饭直接倒在了地上。两个房产相关证件下面,是一本黑色封面的圣经,蘸点口水,打开折痕明显、颜色泛黄的圣经里页后,岳母又抬起头,悠悠地说:真是人心不古啊,陈二龙,自家院子里的人,竟然带着外人给鼎丰下套,将租金压低,租期拉长还不说,将厂房改成仓库后不兑现承诺办房产证还不肯赔钱,直接将仓库搞成了非法建筑,这样搞下去,只能法庭上见了。都是院子里的人,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呢?这样的场景我见过几次,都是在雨天,氤氲的雨雾总是拥挤着,奔涌着往我和岳母坐着的客厅里灌,每一次,望着身形瘦削的岳母,望着她沧桑的面容,我的亲切感陡然升腾,在心底里,我感觉她就是我的亲生母亲。
三
陈二龙是鼎丰出身,已经发了财的人。陈二龙和我一个姓,都是陈家人,出生地也和我一样,深山老林的山沟沟。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了鼎丰汽配厂。人灵泛,和岳母一家关系一直较好,即使后来到了和陈二龙是股东之一的鼎丰仓库租赁方打官司的份上,人情来往也一直没断。他的发迹和他的妹郎有关系,他妹郎从区委书记一直做到丰城政法委书记的高位,陈二龙也慢慢从鼎丰所在地的大丰区市场管委会的办事员,科长,副主任到离开体制后现在的身价上亿。和老婆结婚的第一年,我考虑到老婆的生活圈子在丰城,决心到丰城发展,前几年,人生地不熟的丰城,摔打得我鼻青脸肿几近绝望,期间,岳母为了我的工作着落帮我多次想过办法,如找在东北做菌子生意的姨表叔;找在政法频道做制片人的信主的姐妹;找在丰城做包工头的姑爷,这其中也包括后来被岳母说成不是好人的陈二龙。岳母做了拿手的清蒸鳊鱼、红烧排骨、刀切牛肉、老姜炖鸡请陈二龙吃晚饭,陈二龙翻着我带给他的在报纸上发过的文章和获过文学奖的证书,抽出省报纸副刊金奖的那个本本说,这个有点用。然后慢条斯理的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局促着回答说我的长处是写点东西,看陈叔能不能帮忙谋个和文字有关的差事。后来他打电话要我去市中心离火车站不远的一个叫博达的广告公司人事经理处做了个试卷,再后来回信说我的卷子做得还行,但那边待遇很低,只怕不蛮合适。接下来老家的父亲身患肺癌,需人照顾,岳母和我都没再向陈二龙提工作的事。
虎子和岳父母一样,也是洗脚上岸的农民,但早没了农民的淳朴忠厚,有的是戾气和横蛮。在厂子垮掉后,借钱和老婆一起开了个饭店,惨淡经营两年后,时来运转,自己煎猪油,自己熏腊肉,小菜要乡下亲戚特供,慢慢将生意做大了起来,据说一年纯利润不少于两百万,有了钱的虎子在院里横冲直撞,如上了岸的螃蟹。看得出来,正直的岳母在院子里的很多事情上和虎子并不和,可能,现在的鼎丰已不是从前的鼎丰,现在的虎子也不是从前的虎子。
当然也有不变的。比如邻居廖行叔,永远都是微微笑着,一副亲切谦和的模样,他和老婆都是就近汽车制造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带着一个腿有点瘸的宝贝女儿,据说女儿的腿病治愈的几率在百分之五左右,廖行叔一家的中心就是赚钱,治病,每年带女儿去北京协和医院两趟,生活过得隐忍、平静、从容,心底埋着春天嫩芽孢般的希望。还有日饮酒不少于一斤的唐叔、喜欢打麻将喜欢去洗脚城钓妹子的龙叔、五十岁了喜欢化妆、打扮得像三十岁少妇、把歌唱得如原声般风情万种的柳姨。当时还没瘫痪的兼搞大院卫生的岳父,每次我的面包车刚进门,他就跑着去帮我找停车的地方。岳父国字脸,身形高大,一百八九十斤的体重,长得一表人才,可惜当年家贫,读书太少,要不然,命运将会是另外的安排。
四
活泉堂高高的塔尖,巍峨的十字架,典型的西方建筑,门口有个小院,有一棵四人才能环抱的大香樟,堂内的地板和木椅是棕黄色的,窗帘浅黄,有浅蓝的树叶状的花纹、以马内利四个血红的大字进门即可看到,大字左下方是用于讲经的杉木讲台,油漆成闪亮的黄色;右下角是一台折叠式钢琴,温和悠扬的圣歌的伴奏声就从这架神圣的钢琴流出。
星期天礼拜,岳母经常会要求老婆,蒙蒙和我参加。蒙蒙很幸福,是在主祷词、圣经和圣歌声中长大的孩子,小小双眼中有天使般的圣洁可爱的光泽。梁牧师、徐牧师、就近小区的赵娭毑、院子里的杨姨、唐叔、周边的邹妈、吴伯、小敏、阿根……神愛世人,不论身份职业,富裕贫穷,大家常聚一起,讲圣经,唱圣歌,背主祷词;万象节搞大型活动,圣诞节唱歌跳舞,联欢聚餐,为家人,为世界祈福,也为鼎丰大院虔诚祈祷。
开始的时候,我不习惯皈依上帝的岳母,也不是很认可院子里信神的子民,我来自山村,我信仰的更多的是村后山的真人,他在世时是医术精湛治病救人的医生,死后封神;我信仰的是山村稻田深处河畔柳树下的土地爷爷,慈祥和接地气,护佑着一片乡土。但后来深入了解后,我觉得一片土地长出水稻,麦子和苞谷,一片土地肯定也长出真人、佛祖和和基督,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也是需要的。虽然基督是外来的,但只要这样一种信仰,是为善,为和谐,为内心的安宁和幸福,我们是应当包容的。
晚饭后,我带蒙蒙散步,牵着她如嫩芽般的小手,望着活泉堂高高的塔尖和香樟的一团墨绿,我会想,就现在的情况看,鼎丰院子里大部分人是并不富裕的,都干些普通的自食其力的活,比如岳父,他是搞水电的,比如胡点叔,他是开出租的,比如廖行叔,他是做工厂流水线的,比如龙双叔,他是液化气搞安装的。他们,我身边这些人,望着丰城周围开着豪车,带着美女,带着金链,吼着流行歌曲,嚼着槟榔的土豪,他们的内心会失衡吗?晚上会因深深的失落而失眠吗?
《新约·马太福音》里说:“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是上帝的正话反说呢?还是全能的神,一瞬间的糊涂?
五
如果有一位林神,我想她肯定记得我,记得陪伴了她足足三年的我、老婆和蒙蒙。林子不大,属省畜牧兽医所的绿化区,里面种了香樟、杜英和乌桕,紧靠岳母家我和老婆孩子的住房。我的新房是按揭房,二年后交房、分期首付的,一来位置理想;二来经济压力小,可以边赚钱边供着,因此,就落下了和林子三年的缘分。
林神肯定注意到了,当时有一个还算年轻的,面容清秀倦怠,显得心事重重的青年总是把油漆窗框上的窗玻璃打开,睁大眼睛,透过墨绿色的防蚊窗纱,望着林子里香樟粗大的树干、树干下种满狗牙根的草地,草地上飞舞的白色和彩色的蝴蝶。有时候,蝴蝶会飘飞着,落到青年胸前的窗台上,青年认真地、安静地看着白羽黑点的蝴蝶,内心的心事又加重了一层。房子不大,夏天有些闷热,隔壁林子蝉的叫声总是激越苍凉、生动诠释一个季节的真谛。冬天,会有北风呼啸着,打着旋、搅动地上的枯叶,在青年身前飞舞着。林神也不会忘记有那么几次,房间的灯光晕染,青年趴在面容姣好,身形苗条的年轻妻子身上,努力晃着他健壮有力的腰,床板噗噗作响。有几次,床上的被子腾挪扑闪一阵后,青年安静下来,趴在妻子雪饱满雪白的胸前呜呜咽咽、低声咆哮如受伤的小兽……这时候,林神总是轻轻地,悄悄地,怜爱地、沉默地看着这一切,她似乎懂得青年的艰难和疲倦,懂得这样一个小朋友,它内心所有的风暴和洗礼。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更愿意青年像她怀抱中幸福的野花。
借住岳父家的第二年秋天,岳父从畜牧所打新鲜牛奶回来,边给蒙蒙兑牛奶边说,隔壁林子里的树可能要砍掉,建一栋两层科研小楼,我听了心里一沉,难过的感受瞬间爬上了心头。好在第二年、第三年过去,直到我离开林子搬到自己买的新房后,蓊蓊郁郁的林子一直都维持着现状,没有改变。
我曾在丰城日报的副刊上写过一篇林子的文章。我是这么写的:无限风情的小树林,她是我的亲人,是我的爱,是生命中永恒的臂弯,是我童年时梦寐以求的美丽星座,是我的领悟和福祉。
六
我把车停在了鼎丰的前坪,或许是冬天来了,任何事物看上去都萧瑟一些,或者又过了一段时间,鼎丰本身已陈旧了,虽然各省牌照的货车还是将院子停得满满当当,上货下货时搬运工弄出的声响还是哐当哐当,虽然扑鼻的鱼腥味还是那么浓烈。
坪里没有其他人,只有高龄八十几的开的士的胡点叔的老妈在打盹晒太阳,她年纪大了,反应不灵敏,院子里车子进出多,对我的到来她没有半点反应。我想起几年前,她推着坐在轮椅上老伴胡嗲嗲在院子里缓缓散步的情景,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正是午后,虎子开的饭店也已冷清,食客们都已饱食散去,他的饭店没有招牌,装修简陋,土黄色长条形的塑胶门帘挡着,我看不清里面。虽然连招牌都没有,但听说饭店生意这些年还是出奇的好。仅仅几年过去,鼎丰对我的感觉就打了很大的折扣,仿佛我是一个陌生人,闯进了一个和我从来没有过瓜葛的地方,我自由来去,没人在乎我的欢喜和忧伤。
和岳父他们住一起时,岳父曾眉飞色舞的鼓励我说,鼎丰很快征收了,征收了就给你买个奥迪,还给你点钱花,现在岳父住在市里的新房里,坐在特制的轮椅上总是提醒我带老家那种口感较好的发饼给他,说是饿了的时候,就啃上一口,再很少跟我提征收的事。想想,即使现在征收了,赔了几百万,对轮椅上的他也意义不大了。岳母还在为鼎丰的利益和冷库承租方打着官司,三年了,对方一直找人协调,拖延,迟迟没有判决,各中原因,颇为微妙,大家心知肚明,却又无可奈何。鬓角白发丛生、上了年纪的岳母一次次奔跑在去法庭的路上,肯定会想起当年去轻工业大院的往事,肯定也会有湿漉漉的泪漫上她日益浑浊的老眼。姐妹中,和岳母关系最好的赵娭毑去了加拿大女儿那边定居,据说经常来电话,和岳母交流上帝的思想和意旨,只是电话越来越少;我整日忙于商务,只有在某些特别的时刻才会想起鼎丰,尽管仅仅隔着几公里的距离。也许,不管怎样,几十年后,我,岳母,赵娭毑,鼎丰大院的居民,身边来去匆匆的亲友,最终的结局都会和大院眼前胡点叔的老妈一样,像天空中隐隐飘荡着主的叮咛一样,一切将归于平静,世间繁华将冲淡我心。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