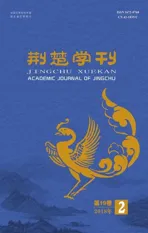《常谭搜》收词及雅俗论阐微
2018-06-19王开文
王开文
(荆楚理工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荆门 448000)
汉语字典的编撰历史悠久,从《说文解字》《字林》《玉篇》,到《康熙字典》,几千年,伴随读书人一路走来。词典,虽然地位稍逊,其编撰历史也源远流长,通常分为两个流派:一是雅类,成书于西汉的《尔雅》开始,到三国时魏国《广雅》,再至明清的《骈雅》《通雅》《比雅》《叠雅》为一条发展线索;一是方言、俗语类,从两汉的《方言》《通俗文》到明清的《俚言解》《雅俗稽言》《通俗编》等等。
明清时期,汉语俗语词典蓬勃发展,仅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明清俗语辞书集成》就收录20种之多。它们收词有多有少,体例也各不相同。其中首次从语体上对词汇进行分类的是《常谭搜》。周荐先生认为,“《常谭搜》较之他前后的学者所纂辑的类似俗语类工具书是前进了一步的,那就是它把语汇分作了雅、俗两类。词语之有雅、俗之分,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千百年来的无数的文人雅士,或许早有人意识到了这一事实,但却从未有人动手将其分别开来。易本烺不但意识到了这一语言事实,而且亲自动手尝试性地为词语作了雅、俗的分类,不能不让人由衷地敬佩。”[1]400确实,在此书面世二百多年前,张存绅历时30年写成,刊行于明朝天启三年(1623年)的《雅俗稽言》就注意到词语的雅、俗之别,其“自序”论该书“雅俗并收,今古兼摭”,可惜正文编排词语并无雅俗之分。
对明清辞书研究,人们于《常谈搜》注意很少,主要原因是该书原版“用粗劣纸印刷,字面多有不清之处”[2]424。该书又缺乏雅俗分类的相关说明,这些使得人们只注意到该书的雅俗词汇分类事实,而雅俗分类标准却一直不明就里。周荐先生试图从词语来源的典籍类别、构成词语的字数多寡等方面厘清分类线索,结果仍是无解,“《常谭搜》在雅类词语和俗类词语分类的标准上,显然存在着较大的任意性、随意性。”[1]396
其实,细读该书,雅俗词语的分类还是有章可循,本文将对其收词和雅俗词划分作一探索。
一、《常谭搜》书名解说
该书是清朝道光年间举人,京山(今湖北京山县)人易本烺所著。后由其子易崇直等校订,于易本烺殁后次年,即同治三年(1864年),在湖北京山付梓出版。《常谭搜》共四卷,收字、词和熟语共计1348条,词条的解释极少,而是一一指出它们的出处来源。该书卷一、卷二为雅类,分别有472条和194条;卷三、卷四为俗类,前者有295条,后者有387条。雅类、俗类所收条目的数量大体相当。
辞书名之“常谈”非易氏首创,宋代无名氏有《释常谈》,明代周梦暘《常谈考误》;或名之“常语”,如稍迟出现的清人郑志鸿编著的《常语寻源》。
《常谭搜》原名为“常谭”。“谭”字,《说文解字》未收,通“谈”。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孚部》里解释,“谈,语也。字亦作谭。《庄子·则阳》:“夫子何不谭我于王?”陆德明注释“谭,本亦作谈。”成玄英疏:“谭,犹称说也。”[3]
所以,“谭”与“谈”是异体字,如《天方夜谭》又作《天方夜谈》。“”与“搜”是古今字。两组字音义皆同。因此该书被名之《常谭搜》,或《常谈搜》、《常谈叜》等,甚至有讹变为《常语搜》,如《明清俗语辞书集成》里既是,从而失其本真。
二、《常谭搜》收“词”属性考查
如前所述,该书收词较丰富,计1300多条,来源多样,因为现在被归为“明清俗语词典”类,所以常遭误解,认为它收录的词语是民间俗语,或贩夫走卒之每日常谈的口语词。实际上,该书收词几乎都有书面典籍依据,且以书面语为主,现略加说明:
首先,该书收录不是口语词、方言词,而是书面词语。这从该书前言所述的编写目的可以看出。《常谭搜·弁语》“余习举业时,流览诸籍及制艺、试贴、各家注释,有所蒐(即”搜”字,笔者注)引,即笔之于编,并参互补益,以自省览,兼示子姪,俾知作文不可一字不知来历。”[2]425也就是说,该书汇集的词语,来自于书籍,服务于作文,书面语也好,口语也好,方言也好,只要用之于文章,皆可收录,书面性是这些词语的根本特征。
书中词语绝大多数都有准确的典籍出处,文言词如“帡幪《法言》(笔者注,词条后为该书列出的来源,下同)、丁艰《尔雅·释诂》”,典故如“黄卷《宋祁笔记》、太平有象《唐书》、声价《后汉书》”,人物名号如“名工(今人赞人所作之佳曰名工,见《考工记》注)、‘老泉为子瞻号’《七修类槁》,古今口头词语,也是典籍所载,如“眼睛‘韩愈诗’、张三李四《朱子类语》、月亮(‘李益诗’,今人遂呼月为月亮)”,诗文中词语,两字的如“奉陪”(杜牧诗)、“光降、娇客”(东坡诗)、“眼睛”(韩愈诗),三字的,“科松枝”(白居易诗)、“三三径”(杨堇诗),四字的多为短语或小句,如“自今以后”(杜诗)、“是何道理”(卢仝诗),四字以上,整句收录的,如“布衣暖,菜羹香,诗书滋味长。”(韦丹诗)、“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杜诗);联语词,即拼合典籍中两词为一语,如“谐臣媚子”(谐臣出《唐书》,媚子出《诗经·秦风》)、四通八达(四通五达出《史记》,七通八达出《五灯会元》),截断词,即截取典籍中词语的一部分构成的词,如“祝发”(祝发文身见《谷梁传》),源于典籍、流行民间的谚语格言,如“天下事,常八九不如意《通鉴》、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管子》、慈不掌兵,义不掌财(《陈龙川集·喻夏卿墓志》),明代杨慎所辑《古今谚》收有此语。“人遗子金满籝,不如教子惟一经”《汉书》等等。
其次,该书收录的词语,明辨字词的正确书写和准确出处,有时也参考历代字典。如“壹贰叁肆伍等字(见《正字通》,《康熙字典》有‘捌、柒、陆、玖、拾’)、幺(以幺称人,见《说文解字》)、等(俗以候为等。案,《篇海》,‘等,候也。’);辨别词义类,书中标之曰“误释”类,如“县官”《史记》。其本是皇帝的称谓,如《史记·绛侯世家》有“盗买县官器”之语,索隐:“县官谓天子也。”《周礼·夏官》“王畿内县即国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6]再如“果然”(《宋书》,《庄子》中义异),确实,《宋书·王曾》“传帝问曾,曾曰:‘河决奏未至,第民间妖言尔,不足虑也。’已而果然。”“果然”是“结果确实如此”的意思。《庄子·逍遥游》中“适莽苍者,三飧而反,腹犹果然。”“果然”是吃饱喝足、腹部隆起的样子。两者语义差别显著;有辨别异体词的,如“马头(见《晋书》,今为‘码头’)、卷属(《史记》中原作‘婘属’)”;辨正书写的,如《常谭搜·弁语》里说,“寡二少双”常被误作“少二寡双”;有明辨词、语出处的,如“春水满四泽四句”(顾长康诗,后人误入陶彭泽集中)。所以,字、词的书写正确,是该书的重点内容。明辨出处,也是为了读者了解语源,理解词义,正确使用和书写。
其三,该书收录的条目不仅有“词”,有“语”,条目的单位更有字,有诗,有句,甚至是字、词的说明。
收录的单字,往往是因为该字的特殊义项,或考证该字起源。如“甫”(《七修类稿》“表德用甫字者,起自荆公,当时多效之。然甫字亦止用于字内,后人乃于字之下亦用之”),《七修类稿》里有“‘表德皆连甫,花书尽带圈’之说”。荆公即王安石,字介甫。后人取字时以“甫”为美称。再如“睡”(此字始见于《史记·商君传》)。再者“貌”(俗呼‘无’曰‘冒’字,非;以为‘没’者亦非。考《异物汇编》,‘狗缨国有兽名貌,善遁入人室中偷食,已,大叫。人觅之,即不见矣。故至今吴俗空拳戏小儿,已而开拳曰:‘貌’。按,此‘貌’字之由来也。),这里“貌”的义项是“没有了”,属于特殊义项;熟语里,有成语,如“画饼充饥”《三国志》、“坐吃山崩”(元曲)、“想入非非”《楞严经》、“同病相怜”《吴越春秋》,惯用语如“打秋风”《野获篇》、“抱佛脚”(张世南《宦游纪闻》),谚语如“人善人欺天不欺”(元人曲),“娇儿不孝,娇狗上灶”《史记》,“谷怕胎里风,人怕老来穷”《陈后山丛谈》,“外孙多似舅”《容斋随笔》等。有作文类熟语,如“结上文”《尧典正义》、“别字白字”《后汉书》、“押韵”《文献通考》,等等。
所收条目还有一类既不是词,也不是语,而是列举一类字,或对某字词的意义说明。如“乎哉矣也”《文心雕龙》,是一组文言虚词列举;“自谦云敝者”《左》,是说明“敝”字表自谦的用法;“称天子曰上”(《史记》裴骃“集解”),是对“上”一个义项的说明。还有民俗中专有名称,如“四喜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俗传为“四喜诗”。案,已见于洪迈《容斋随笔》)。“打油腔”(《南部新书》有胡钉铰、张打油二人,皆能为诗。《升庵外集》载张打油“雪诗”,即俚俗所传“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也。),即今天所谓“打油诗”。等等。
三、《常谭搜》雅俗分类探赜
雅、俗词语分类编排是《常谈搜》的首创,这对后世编撰辞书的语体区分有着筚路蓝缕之功。
词语雅、俗之分由来已久,这是汉族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使然。
白兆麟先生认为,“地域阻隔,习俗不同,就会造成言语的分歧,写在书面上即形成异字同义或同字异义的复杂现象。应当指出,这里所说的‘雅’和‘俗’,都有两种相对的不同涵义:一是指古代的‘华夏通语’和‘方言殊语’;一是指先秦时期形成某种格式的‘文言词语’与东汉以后民间使用的‘俚俗词语’。”[7]就是说,雅俗之分,一是异地——共同语言和方言,一是异体——语体不同。因为《常谭搜》编写目的在指导作文,所以易氏雅俗所指显然是后者。
雅语是先秦时汉族的标准语,是以中原语音、词汇为标准的民族共同语;雅词就是标准语里的词语。于根元先生指出,“雅通夏,雅言就是夏言。指的是中原地区的方言。雅又解释为常、正,雅言可以说是当时的共同语。”[8]雅言是权威、标准的汉语,是书面语的指南。
俗是通俗。温端政先生的解释是,“‘俗语’作为语汇单位的名称,以较强的生命力流传至今,其他同义名称,如‘鄙语’、‘俗谚’、‘里语’、‘俗话’、‘常言’等,或者已经消失,或者使用频率不高。……俗语定义为:汉语语汇里为群众所创造、并在群众口语中流传,具有口语性和通俗性的语言单位[9]。
容易看出,易氏“雅词”是书面语,“俗词”是口语。但是,该书几乎所有词、语都注明其典籍来源,加大了人们对该书的雅俗分类标准判定的难度。其实,这正反映了易氏的辨正、动态语言观——传世典籍中有书面语词,也有口语词;古代典籍中书面词语,可能成为后世的日常口语词;反之,古代口语词可能不断地补充到后世的书面词语词汇里。《常谈搜》里“雅类”词语一般是说明出处,而“俗类”词语的说明中一般则有标记,或暗示标记,具体如下:
(一)俗类词语标记
1.词条解释说明里标明是俚言俗语的
标明是“谚”语的,如“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玉堂闲话》所引谚语)、“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鹤林玉露》引谚)、“生吞活剥”(刘肃《大唐新语》“谚曰”)、“祸至心灵”(《史照通鉴疏》引谚)等。
标明是“俚”语的,如“鲫溜”(语本于俚俗)、“闲事莫管”(《苕溪渔隐丛话》,“世间俚语往往极有理者,如‘闲事莫管’。”)、“不中”(俚语以不可为不中)。
标明是方言的,如“君子不夺人所好”(《指月录》赵州语)、“竖起脊梁”(《指月录》道川语)、“叔侄”(《颜氏家训》曰“兄弟之子,北土多呼为侄。)、“妯娌”(《汉书》颜师古注,“古谓之娣姒,今关中俗呼为先后,吴楚呼之为妯娌。”)、“毛病”(荆南之人语)、“铁汉”(《该闻録》李遵宜握兵,江淮人号铁汉。)
标明是“俗”语的,如“行止”(俗谓德行曰行止)、“搭船”(唐·廖融《梦仙谣》,“拟就张骞搭汉槎”,今俗谓搭船)、“打秋风”(俗以自远干求曰打秋风)、“外后日”(俗语耳)、“敹衣裳”(今俗呼缝补曰敹)“张冠李戴”(《留青日札》俗谚云,张公帽掇在李公头上)、“罗隐说破”(今俗称事有前定者为罗绮秀才说破事)。
标明是“今人语”的,如“信士”(今人出财布施曰信士)、“柴米油盐酱醋茶”(今人谓之开门七事)、“秀才不出屋,能知天下事”(今俗语)。
标明是“鄙”语或近乎鄙语的,如“娇儿不孝,娇狗上灶”(今鄙语曰,娇子不孝)。
标明词义是日常口语词的,如“卖弄”(《后汉书》作招权市恩解,与后世作夸翊意者不同。)即“卖弄”作为俗语,是“夸耀、炫耀”的意思。“有”(俗以贫富为穷有。)
2.词语出处标明是俚言俗语的
出自于古、今口语的,如“冬烘”(唐人言)、“肥酒大肉”(吾乡俗语)
指明出自俗语辞典的,如“岳丈为泰山”《雅俗稽言》、“无恙”、“交代”《风俗通》、“恭敬不如从命”、“人心不足蛇吞象”《通俗编》。
出于语录体书籍的,如“小底”《晋公谈录》、“生姜树上生”《程伊子语录》等等。
出自典籍人物话语的,如“逢场作戏”(邓隐峰语,见《传灯录》)、“改头换面”(《五灯会元》元宗杲谓张无垢)、“金玉满堂”(欧阳修会老堂口占)、“千万千万”(《旧五代史》太祖遗命有“千万千万,莫忘朕言”之语)、“大喜”(《战国策》公孙戍曰)、“糊涂”(《宋史》太宗曰:“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传灯录》船子和尚语)
因此,元曲和“歌行”等类题材文章,口头传唱特征显著,其所用词语,几乎都列入了俗类。元曲一般不注明具体篇目。如“口快心直”(元人曲)、“啾啾唧唧”杜甫《狂歌行》等。
3.词义内容上暗示是俚言俗语的
曲有高雅,谓阳春白雪;也有通俗,称下里巴人。民国时期,高雅为“绅谈”,通俗为“街谈”。因此,事涉底层人民的生活生产,普通人的生老病死等用词多为通俗。此类多为叙述性语、句,说明某个道理或事理具体如:
关涉农事、农时的,如“大富由命,小富由勤”(唐·宋尚宫《女论语》)、“早起三朝当一工”《宋楼钥诗》、“雨揽雪,无休歇”(娄元礼《田家五行》),等等。
关涉持家、育子的,如“养儿代老,积谷防饥”(《琵琶曲》、《陔余从考》)、“闲时办,急时用”(《苏佑逌旃琐言》)、“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监戒录》王凡夫诗)
关涉劝善的,如“阴地不如心地”(《癸辛杂志》倪文节语)
关涉迷信果报的,如“命里有时终须有”(《潘子真诗话》)、“财与命相连”(支允坚《异林》“常言财与命连”)、“恶人自有恶人磨”(见元曲)、“举头三尺有神明”(徐铉语,见《南唐书》)
关涉为人处世的,如“蝼蚁尚且偷生”(元·马致远曲)、“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元人曲)
粗俗詈骂语的,如“白日鬼”(《刘跂暇日记》,“宋时指贼人曰白日鬼。诞谩者,亦曰白日鬼。”)、“酒囊饭袋”(《金楼子》祢衡云,‘荀彧可与强言,余皆酒瓮饭囊’……时谓之酒囊饭袋。)
4.用字通俗、浅白的是俚言俗语
“驼子压直了人吃了亏”《百喻经》、“偷食猫儿改不了性”(东坡《杂纂二续》)、“真个有天没日头”(宋神童诗)。又见今存明·郎瑛《七修续稿·俗语本诗句》。“没巴鼻”(苏长公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使奸邪”)。《后山诗话》“有意头,没把鼻,皆俗语也。”又见于《通俗编》。“头不梳,面不洗”(《五灯会元》僧问慧颐,“如何是无缝塔中人?”颞举语云云。)此语收入《通俗编》,并注“此语为俚俗童谣”。等等。
(二)雅类词语特征
雅类词就是书面性强,出处上,一般出自经、史、子部典籍。出自经部的如“权舆”《诗》、“激发”《考工记》、“吉祥善事”《易》等;出自史部最多,如“芝宇”《唐书》、“国色”《公羊传》、“公家言”《南史》、“画饼充饥”《三国志》等;出自子部的如“达人”《鹖冠子》、“刍茭”《慎子》、“后来居上”《文子》等;还有极少来自字典的,如“寒酸”《正字通》等。
内容上,与俗类词相反,主要是读书、文章,科举、功名,政治、治国等语义场的词、语。如“字眼”《沧浪诗话》、“涂鸦”《卢仝诗》、“承上文”《左传》、“贫者士之常”《沧浪诗话》、“字眼”《列子》;“科第”《汉书》、“八秩”《礼》;“军政”《春秋内传》、“王道本乎人情”《通俗编》、“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宋书》、“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汉书》。此外含典的列入雅类,数量颇多,如“城府”《晋纪总论》、“松封五大夫”《汉官仪》等等。
用字上,典雅,甚至古奥,如“嗤点”《晋纪总论》、“擘画”《淮南子》、“矞皇”《太元经》、“伏惟”(汉乐府)、“胶庠”(张说诗)。等等。
(三)雅、俗词抽样考查
一般地说,不同类型的作品,其语体特征总体上是明确的。如经部多古奥、典雅,收词多入雅类;语录、歌谣、元曲等用词浅显、通俗,其词多收入俗类。
但是,《常谭搜》的雅俗分类,从典籍来源上探索,价值不大。同一典籍里的词语,有收入雅类,也有收入俗类,这在《常谈搜》里不胜枚举,因为,口语词和书面语词交织在典籍中,书面作品如人物话语中可能常常是口语体,包含大量口语词;相反,口语中,如演说,因其严肃性,事先多拟草稿,可能包含大量书面词语,典籍也是如此。
下面以该书所收《庄子》里词语和无具体典籍出处的词语为例,说明雅俗之别。
《庄子》词语,雅类收录31条,俗类收录6条。详见表1

表1 《庄子》词语收录表
“不敢当”,三字格,近乎惯用语,是日常语,故列入俗类。易氏之前《通俗编》,稍后的《越谚》皆收录也是佐证。
“生熟”,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司马云,生脍也;一云,生熟谓好恶也”。或解释为“布帛饮食”。该词今收入《汉语方言大词典》。易氏认为该词是先秦时方言词。
“骑缝”,该条释文“《庄子》缘督以为经,谓中两闲而立。俗所谓骑缝也。”注明是“俗”。
“安当处顺”,本于“《庄子》‘安时而处顺’”,该词是作者变通而成。
“见笑大方、不近人情”两词应为易氏时代日常口语词,用字浅显,是列俗类。易氏之前《通俗编》,其后《俚语徵实》皆收录可证。值得注意的是,“贻笑大方”源于该词,因用字古奥,明清典籍使用甚广也不为当时俗语辞典收录,尽管它宋代已出现,宋·韩拙《山水纯全集》“去古逾远,贻笑于大方之家也。”[10]该成语现作为雅类的书面语——成语,固定为“贻笑大方”。
这说明,易氏判定俗词依据是,该词是否为当时口语常用词;是否已编入俚语俗言辞典;用字是否浅显等等。
再看,无具体典籍来源的词语,雅类收14条,俗类15条。详见“表2”

表2 无具体典籍来源的词语
上表中,雅类词语有三种:
一是含典、意义古奥的,如“市井、点睛、如坐针毡”含典;古奥的多引经典或大儒解释,如“幺”引《说文解字》,“后裔”引朱熹说,“诅祝”引孔颖达说,“市井”引张守节说,“点睛”引《康熙字典》。
二是联语、化用,都有确切的典籍来源,如“及锋而试”,“及锋”见《史记》,“而试”未详;“秉钧当轴”,“秉钧”见《诗经》,“当轴”见《前汉书》;“谐臣媚子”,“谐臣”见《唐书》,“媚子”出“秦风”(即《诗经》);“光天化日”,“光天”出《尚书》,“化日”出《潜夫论》。
三是治学科举类词、语,如“尺牍”(今人以书函为尺牍)、“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涉及《尚书》《大学》;“时文”则是科举制度中专门术语,即八股文。
俗类则多说明是古今时语、传闻、口头成语或方言。“婴儿、枭首、落地”三词,易氏一一作解,“女幼者曰婴,男幼者曰儿,今欠分别矣”,“人初生曰落地”。“枭首,百劳名”是候鸟,关涉农时,其传说也有劝善之义。“闲月忙月”或跟农时有关,故为俗词。
四、总结
《常谈搜》收词丰富,给后世辞典及读者提供了准确的语源线索;其中雅俗分类,实时记录了当时词语的书面使用情况,既开启了汉语词汇语体分类的先河,为后来辞书的语体分类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也为考查汉语词语的历时雅俗变迁提供材料。
词语的雅俗之分,反应了词语的口语性和书面语性这组对立语体特征。由于雅、俗词语在书面作品中的交融和历时转变,雅俗分类标准也较复杂,易氏主要从词语的来源、社会使用典雅与通俗、词语语义领域、用字的古奥与浅显等角度加以分门别类。尽管有些难以截然划分,如同是连绵词,“伶利”是俗词,是书说明“韵书称人颖敏曰伶利。案,苏子由与人书则作灵利字,亦作伶俐。”而“徘徊”(出楚语)、“囫囵”《朱子语录》却为雅词。究其缘由,“灵利”口语性强,且字形不定,《字汇》也视其为方言;相与之反,“徘徊”字形固定,语出《庄子》,为《广韵》《玉篇》《康熙字典》收录,较为典雅,故列雅类。“伶俐、徘徊”这种语体之分,今天犹然。“囫囵”,《通俗编》言“鹘沦”,引《天瑞篇》作“浑沦”,本当列俗类,却因《常谈搜》该词条前含典的雅词“囫囵吞枣”而连带列入雅类。此外,易氏在依据自己的雅俗标准分类时,也受到当时已有字典、词典的影响,或者说,有时以它们为参考。以之对比之前《通俗编》、之后《俚语徵实》等辞书,不难发现这种一脉相承的特点。
参考文献:
[1] 周荐.词汇学词典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 长泽规矩也.明清俗语辞书集成[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 郭庆藩.庄子集释[M].中华书局,1961:876.
[4]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K].武汉,成都: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433.
[5] 俞樾.春在堂全书(第2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566.
[6] 王俊良.中国历代国家管理辞典[K].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874.
[7] 白兆麟.新著训诂学引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43.
[8] 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M].太原:书海出版社,1996:65.
[9] 温端政.汉语语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72-73.
[10] 田忠侠.辞源考订[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