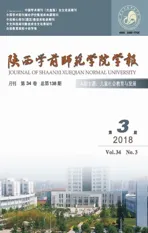振兴一带一路 盛唐文化先行
——第三届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研讨会述评
2018-04-02黄彦震雒晓辉尚宝珠
黄彦震,雒晓辉,尚宝珠
(1.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陕西西安 710100;2.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
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世界四大古都之一,长期以来是国内外盛唐文化研究的重镇。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自成立以来,即把盛唐文化研究作为学会的主攻方向,在文化强省的战略下,整合西安市多家学术机构,积极推动盛唐文化研究,为当代中国树立文化自信提供理论支撑和历史借鉴。盛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巅峰,其重要价值早已为世界所认同。在此背景下,2016年12月17日,第三届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行,与会专家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学术观点。
一、唐代新史料的运用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在全国各地陆陆续续发现了大量唐代的墓志。西安作为唐代的都城,墓志更是屡屡被发现,这为隋唐史的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新史料[1]。西北大学贾志刚教授的报告《唐代宦官问题札记——以出土宦官受谴贬陵墓志为中心》,就《姜子荣墓志》为例并以《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载的其在长安犯错而被贬守陵的史料依据,对墓志的真伪进行了考证。唐代的宦官给我们的整体印象是专权跋扈、贪婪奸诈,但由于唐后期宦官不仅形成了以宣徽使为首的庶务使职系统、枢密使为首的政务使职系统,而且还形成了以中尉为首的典军使职系统,加之地方监戎的监军等,宦官的势力可谓是达到了顶峰[2],其专权擅政、废立君主的事情累见于史乘,但就其管理和处置的制度、事件却是少之又少。贾志刚根据大量现出土的宦官墓志探讨了宦官惩罚性管理的具体内容,宦官犯错后的处罚等问题。名目很多,有派陵、派边及配南牙等,派陵与派边相比要轻,派陵与派南衙相比又较重。对派陵行为做了细致的考察,并将派陵行为与唐律中的徒刑、流刑相比较,其结论是派陵基本上是遵守唐律的规定,但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它既不属于徒刑也不属于流刑,而是居于二者之间。墓志主姜子荣之前应该是属于左神策军系统的,但在犯错后仍然作配陵的处罚,可见唐代后期对宦官的惩罚性管理措施还是有的。特别是在中唐以后,宦官政治下,以贬陵为特色的管理制度对约束左右军和飞龙厩等宦官损民害佃的情况无能为力,故宦官任使左右神策军也成为影响左右军存在基础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无论如何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一味姑息。即使在宦官专权擅政的时代,宦官管理仍是有章可循的。
陕西师范大学拜根兴教授根据多年从事唐与新罗、百济、高句丽关系的研究经验,以出土的多方有关唐与三韩的墓志为课题,作了题为《石刻墓志史料所见七世纪中叶唐与百济关系——以新发现的唐人军将墓志史料为中心》的报告。以23方与百济有关的墓志为前提,采集史事、结合正史,分析研究了已征行军兵员的来源、赴百济的唐人军将的招募(兵募)以及随从将领的推荐选拔等一系列军事行为。又通过其他如行军元帅可以把自己熟悉的将领推荐自己的中高等部将,平定百济后的州府设置以及经营朝鲜半岛数十年等问题进一步分析了唐为了征服百济、高句丽等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文章以战争中中下层军将的牺牲为着眼点,越来越重视小人物的研究,这是唐史研究进步的体现。
自从金石之学在宋代兴起以来,使用碑铭来核验禅宗的传法谱系就被历代学者所沿用。陕西师范大学葛洲子做了《唐宋禅师传记书写的虚与实——从荆门玉泉皓长老塔说起》的报告。自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敦煌文献的广泛应用,利用不同的文本去修正、恢复被虚构的禅宗历史,成为了禅宗史研究得重要途径之一。在面对禅宗相关文献中的事实与杜撰、神话与历史时,应多方面的、广博的依据材料去判别“禅宗史的真历史与假历史”。葛洲子以“荆门玉泉皓长老塔”为中心视角,广泛地考察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和研究禅宗史的独到理论和方法。
近几十年来,敦煌文书资料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学者们通过与正史资料结合从而解析敦煌文书解决了许多过去悬而不决的问题。陕西师范大学李宗俊教授做了《甘州回鹘可汗上奏后梁的两份表本及相关史事考》的报告,认为敦煌文书P.3931两份《表本》均为甘州回鹘可汗上奏给后梁太祖朱温的。且同一次出使草拟的两个稿本,上书时间大约在开平二年(908)到乾化元年(911)之间,正值回鹘西迁,诸部分离之际,急需中原王朝的颁赐册立,以在回鹘诸部中树立权威与正统地位。作为外交文书,两份《表本》语言含蓄委婉,但又绵里藏针、掷地有声地表达了当时甘州回鹘的政治诉求。通过节度文书,可知上奏者的身份就是入居甘州的首任回鹘可汗“大圣天可汗”或称“天睦可汗”。
二、长安的建筑与交通
唐代历史久远,盛唐物质文化至今保存下来的十分珍贵。西安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张全民研究员的报告《隋唐长安城安仁坊探古》对安仁坊作了全面的探究。“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安仁坊作为棋局的一格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是隋唐长安城的一处著名里坊,唐代于坊内西北隅立荐福寺浮图院。宏伟壮丽的长安城随着唐王朝的灭亡变成一片废墟,安仁坊的隋唐遗迹大多已湮没于地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隋唐长安城遗址展开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安仁坊地下文物遗迹得以发现。张全民判定出安仁坊在现代西安城市中的准确位置,对安仁坊和荐福寺地下文物遗迹的发现情况作了概括总结,其中有一些是首次公布。
有唐一代,佛道二教,此起彼伏。其中佛教的起伏尤大,但总体上佛教势力在唐朝仍有着巨大的发展。唐都长安虽称不上“四百八十寺”,但也是刹宇云布[3]。为了保证西安市在城市建设的同时,更好地保护这座千年文化古都,对于大量寺观遗迹旧址的研究仍然是极具现实意义的。陕西师范大学介永强教授的报告《唐都长安庄严寺与西安市木塔寺公园》,对今西安市高新区科技六路之南的木塔寺公园进行了研究,提出它是在古代木塔寺遗址的基础上建成的带有古遗址保护性质的现代中式园林。木塔寺始建于隋文帝仁寿三年(603),是隋文帝为独孤皇后所建,初名禅定寺,寺中有木塔“高三百三十尺”,“举国崇盛,莫有高者”。唐武德元年(618),禅定寺改名为大庄严寺。庄严寺位于隋唐长安城西南隅,是隋唐时期著名的皇家寺院,因而成为唐武宗“会昌灭佛”运动中长安城中得以保留的4座佛寺之一。会昌六年(846),庄严寺更名为圣寿寺。唐末战乱兵燹,长安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圣寿寺亦未能幸免。然而,由于庄严寺在隋唐时期的重要地位,宋人宋敏求《长安志》和元人骆天骧《类编长安志》都对其有简略记述,仍然称作大庄严寺。清代嘉庆《长安县志》记载,庄严寺“俗谓之木塔寺”。由此可知,至迟在清朝乾嘉时期,庄严寺因原寺中有“高三百三十尺”的木塔而在民间被称为“木塔寺”。清初康熙年间,木塔寺经过两次修葺,稍具规模。可是,好景不长,在清朝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中,木塔寺再遭兵燹,废毁殆尽。历史上的木塔寺早已灰飞烟灭,如今木塔寺公园却在原址拔地而起。抚今追昔,透过历史的长廊回望,我们依然可以看见木塔寺在古都长安熠熠生辉。
唐代长安作为首都,其交通可谓是四通八达,其中越南山的商於古道是长安通往南阳和荆襄的主要交通要路,亦称做“商山——武关道”。刘邦降破崤关入屯灞上、先项羽一步迫降子婴于咸阳走的就是此路。陕西历史博物馆梁子研究员的报告《唐代的商於古道》,分析了商於古道在唐朝时的地位和作用。商於古道是唐代关中通向东南的交通要路,尤其是在唐中后期中原叛乱、河朔连兵、汴渠漕路阻梗之时,更加凸显了其价值。东南入供之赋,皆溯汉沔至丹水,而后与商於道转至京师长安。唐代亦称此路为“贡道”,并多次修筑。唐人王贞白诗云“商山名利路,夜亦有行人”,故此道又被戏称为“名利路”。
三、唐代传世文献的整理与考证
对传世文献的精心筛选、排比、钩沉仍是盛唐文化研究不可忽视的工作。通过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体系去分析解读传世文献,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精髓,是历史研究的中国气派。玄武门政变是多年来唐史学界关注的话题。西北大学李军教授以北门禁军为对象、以对常何的考察为中心做了《北门禁军与武德九年玄武门政变之关系考辨——以常何为中心的考察》的报告。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了旨在夺取最高权力的玄武门政变。世民之所以能在太极宫内设伏,以及建成在接到宫内示警的情况下仍坚持入宫,恐均与此际在北门禁军任职的常何无关。虽然世民在政变前曾通过常何收买禁军中的豪杰之士,但我们并未发现有常何及北门禁军曾参与政变筹划过程的直接证据。从玄武门政变的具体实施步骤看,北门禁军也只是参与了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并非是决定事变走向的关键力量。如果将记载常何生平事迹的碑文与高宗朝制作的玄武门政变功臣的石刻文献进行对比,也可证明常何或与玄武门之变并没有太大的关联。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穆渭生教授的报告《唐杨贵妃“度道,入宫”时间、原因新考订》通过对传世史料的钩沉、梳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杨贵妃的入宫时间进行了又一次的考订。他指出,在考证杨贵妃入宫时间问题时,应该注意到史料产生的时间排比以及对史料的重新关注和解析,使其符合常情和伦理。关于杨贵妃的入宫时间,陈寅恪先生曾有文章考证并推断是开元二十八年,此后学术界也大多认可、并相沿不疑。而穆渭生教授重新考证了陈寅恪先生作为结果论据的宋代乐史《杨太真外传》,发现其中错误较多,而且成书时间也比陈鸿《长恨歌传》等书目较晚,故而开元二十八年的时间截点不太可取。再者,从感情伦理看,寿王从小被宁王抚养长大,宁王视寿王若亲子,而唐玄宗对自己的大哥宁王更是无比的尊重,故而穆教授认为玄宗度杨贵妃入道至少是在宁王去世之后,也就是开元二十九年以后。穆教授认为杨贵妃在开元二十九年后是有过真正的入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寿王与杨玉环成亲多年,但杨贵妃始终无所出,这应该是其入道的最主要原因,故而穆教授将杨贵妃的度道、入宫又向后推迟了一两年,即天宝二年或天宝三年左右。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黄彦震副教授将穆渭生教授的报告延展评介其新著《盛唐长安的国家乐伎与乐舞》(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指出该书把乐伎与乐舞纳入国家治理层面考量,将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来透视盛唐的国家治理能力[4]。
四、唐代文化遗存的搜集与研究
文化遗存的搜集需要长期的注视,并利用遗存与文献的结合进行研究。西安碑林博物馆王其祎研究员的报告《欧阳询的书法新世界》对欧阳询书法作了详细研究。长期以来,学者们都是依据存世的一些碑刻和墨迹整理研究,自宋代以后很少再有新的发现。直到近半个世纪随着大量石刻文献的出土,才令人惊喜的发现了一片欧阳询书法的新世界。自20世纪七十年代在旬邑县出土了贞观十一年凌烟阁功臣侯君集的母亲《窦娘子墓志》以后,近十余年间在长安地区又相继出土了五种极有可能是欧阳询楷书“真身”的墓志铭,依次为:贞观八年《李誉墓志》、贞观八年《翟天德墓志》、贞观十年《王女节墓志》、贞观十四年《邓通夫人任氏墓志》和贞观十五年《丘师墓志》。通过对以上五种新出土墓志做书法与人事关系的考察,不仅可以揭示隋唐年间都城流行的新体楷书的领袖人物确是以欧阳询为代表这一问题,而且能够看出其书体的影响亦颇见深巨,而这种影响也是南朝士人所带来的文化因素融合到书法流变上的反映。这种楷书体式上的流变更成为了影响整个唐代乃至于千百年来的主流风尚。另外也可印证两个问题:一是欧阳询的卒年与享龄还是应以张怀瓘《书断》所记“以贞观十五年卒,年八十五”为准;二是历来未澄清的《皇甫诞碑》的书刻年份,从笔法与结构来看最接近于前述贞观八年至贞观十五年的五种新出土墓志,以及今存昭陵的贞观十一年《温彦博碑》,因此或可推断其刻立时间也应在贞观八年到十五年之间,而非清人王澍所说的“定当是高祖时书”。同时,这些新墓志也无疑成为了研究欧阳询晚年书法面貌最重要的素材。
陕西历史博物馆张维慎研究员的报告《试论唐墓壁画中侍女所持“丁”字形杖的用途》探讨了唐墓壁画中侍女所持“丁”字形杖的用途。绘有侍女手持“丁”字形杖壁画的唐墓共有8座,其中五座在太原附近(即太原市董茹庄唐代壁画墓、太原市金胜村第6号唐代壁画墓、太原市金胜村第4号唐代壁画墓、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太原市第337号唐代壁画墓),3座陪葬于长安以西的太宗昭陵(即李震墓、新城公主墓、长乐公主墓)。这8座墓墓主所处的时代,主要在唐初至高宗、武周时期。在初唐至高宗、武周时期,统治者上层鉴赏书画成风。当时书画的立轴,称为障(包括画障、图障、软障等)。上层统治者在鉴赏立轴(挂轴)书画时,其展示方式最少有三种:一是让人用“丁”字形障竿或鸦叉(丫叉)悬挑立轴书画直接展示;二是在曲江盛会或贵族的宴会上,以“丁”字形障竿或鸦叉悬挑立轴书画挂于架子上来展示;三是让侍女用“丁”字形障竿或鸦叉把书画立轴悬挑起来挂在庑殿的横梁上来展示,这在公主墓或高等级墓壁画中多有反映。
陕西历史博物馆杨效俊研究员的报告《隋唐敦煌地区佛舍利崇拜》综合利用敦煌文书、壁画及文献资料,发现敦煌地区隋唐佛舍利崇拜具有时代上的连续性、制度上和长安统一性的特点。敦煌地区佛舍利崇拜的两个重要时期是隋代和武周时期,反映了都城长安佛舍利崇拜制度对敦煌的直接影响。敦煌地区佛舍利崇拜所依据多种涅槃经典同时并存,综合运用但仍可见从隋代至晚唐,昙无谶所译《大般涅槃经》一直是敦煌地区涅槃经变所依经典,从武周时期开始《大般涅槃经后分》逐渐成为主要经典。以武周时期为中心,形成了适合敦煌莫高窟石窟寺建筑和艺术特色的独特的佛舍利崇拜系统,包括中心柱洞窟、涅槃变相、涅槃与弥勒佛的共存关系等舍利崇拜建筑和图像程序。通过对比敦煌和长安地区舍利崇拜的经典制度,可见敦煌地区隋唐佛舍利崇拜的地域特点,即敦煌地区佛舍利崇拜传统和长安传入新的制度方面的融合性。敦煌地区呈现出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佛舍利崇拜面貌。这种地域特点正是由于敦煌所处的丝绸之路要道的重要地理位置和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社会面貌所决定的。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关于女皇帝武则天的形象,唐代以来曾有一些绘画作品传世,但这些画作多为画家想像之作,故差别甚大,莫衷一是。王双怀教授作了《武则天“真容”考》的报告,解读了现存武则天的各种石像、画像和雕像等,以求能够恢复武则天的真实面容。相传洛阳龙门卢舍那佛像是根据武则天的原型雕凿的,广元皇泽寺所存佛像被认为是武则天“真容”。这些传说并非空穴来风,但一直没有得到证实。最近,英藏鎏金仕女银像面世。这尊银像头部有五只鎏金凤凰,颈部佩戴牡丹纹项饰,与广元皇泽寺所藏武则天石刻“真容”颇为相似,也符合文献所载武则天“方额广颐”、“龙目凤颈”、“奇像月偃”的某些特征。故这尊银像很可能是武则天的“真容”。广元皇泽寺石刻反映的是武则天晚年当“金轮”皇帝的形象,而这尊银像则可能是对她“太后”形象的写照。
总之,本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对西安在“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中起到促进作用,既给我们带来文化思考,也是三秦大地的现实需要。振兴一带一路,盛唐文化先行,西安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进程中,已经将包容开放的盛唐文化作为自己的名片,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1] 胡戟,荣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
[2] 贺忠.唐代宦官使职制度研究述评[J].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8).
[3]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M].李健超,增订.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4] 黄彦震.“一带一路”文化研究的新成果——简评《盛唐长安的国家乐伎与乐舞》[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