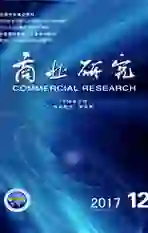基于农地区域类型差异的农村土地确权模式研究
2018-01-25孙德超曹志立
孙德超+曹志立
内容提要:应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必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确权是“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础性工作。当前我国农村土地确权政策的落实面临诸多阻碍,地方执行困难重重、执行效果不佳,为此,需要综合考量中央、地方和农民在农村土地确权中各自秉持的目标和寄托的诉求,并根据不同地域特点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别化的执行方案。本文以人地关系和农地升值潜力两个要素为维度,以农业区域为载体将我国划分为四种农地区域类型:东北“平原区”、西北“荒地区”、西南“碎地区”、东南“城郊区”,在具体考察不同农地区域基本特征和经营现状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依据现状确权确地、调整土地后确权确利、调整土地后确权确地、依据现状确股确利四种农地确权模式,以期对不同农地区域农业经营成本的降低和规模经营的实现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地区域;类型差异;农村土地确权;政策执行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7)12-0001-10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是发展农业农村经营的基础性制度条件,而我国农村正在组织实施的土地确权工作对于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具有基础性意义。目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以下简称“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意义已经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可,包括有效提高土地长期投入、促进土地市场化流转、维护农民权益等[1-3]。农业部2009年开展首批工作试点,2012年出台统一的正式规程,2013年扩大整省推进范围。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提出“围绕正确处理农民和土地关系这一改革主线,科学界定‘三权内涵、权利边界及相互关系,逐步建立规范高效的‘三权运行机制,不断健全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发展”,这为农村土地确权的工作基础、核心要义和目标图景指明了要求。
从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情况看,农村土地确权政策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顺畅,落实成效有限,有的地方政策执行进度远远落后于国家预定的期限和目标,有的地方积极性偏低。根据实际的基层调研和对现实问题的考察,地方政府对待农村土地确权政策的态度和执行行为迥然不同,在这其中,积极冒进者存在,消极懈怠者亦有[4]。更有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因为农村土地确权政策的落实,出现了“相互推诿”的现象,致使政策无法彻底落实,执行周期延长。
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政策本身所需的外部支持不足,如存在一些政策与法律的冲突,需要国家法律层面的完善[5];地方政府面临着资金压力、人员不足、宣传不到位等问题,需要加大各方面的投入力度[6];此外,传统惯习构建的农民产权认知,与政府确权实践之间存在着不适应性和冲突[7]。另一方面,也源于政策执行方式的匮乏,地方政府还没有找到适合于本地的土地确权工作方法和实践路径。关于这一问题,即如何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相关研究已经展开了探讨。有学者提出农地产权的地方安排中应当遵循的规范性问题。姚洋认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其实是地方条件(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地方差异)的函数,而这种具有地方差异的农地制度创新,内在地遵循着资源配置的高效性、社会保障的兜底性和土地分配的公平性原则[8]。这表明,农村土地确权的地方创新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也为实践操作提供了可资判断的参照标准。需要注意的是,农地确权政策实践内含着国家强制“赋权”与乡村社会反制力量之间的互斥,因此,实际地权结构的形成特别需要考虑民众的诉求[9-10]。有学者探讨了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开展方式。于建嵘和石凤友指出,“按现有人口以及土地占有状况确认土地权利”是共识性且符合法律政策规定的方式[11]。而且,地方政府为贯彻落实土地确权政策开展了多样化的尝试与探索,积累了诸多经验。例如,满足了农民自主产权交易与低成本产权整合两项功能、对承包权确权不确界的“虚拟确权”模式[12],将经营权委托给村集体的“确权确股不确地”模式[13]。有研究指出,单一的确权确地方式可能会损害承包方、经营方和集体的利益,需要适时采取“确权不确地”的方式给予调整并跟进配套措施[14]。
总结现有关于农村土地确权方式选择的研究,已经在两个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方面,基于既有经典产权理论的延伸,指出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安排受到两方面力量的形塑,也即由国家主导、源自于经济学倡导的以产权明晰化和流动自由化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以及社会建构逻辑主导下的基于公平分配和不确定性的农地产权合約格局[15],这决定了我国的农地确权既要兼顾市场效率,也要遵循农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有关农地确权方式的地方探索得到了有效的关注,理论界对实践中形成的昆山模式、南海模式等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综上,无论是基于规范理论的原则性探讨,还是极具地方发展特色的个案分析,已有研究对农地确权的实践指导意义仍然有限,地方政府在选择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时,应该基于何种原则、做出何种恰当并具有区分性和针对性的决策方案,仍然并不明晰。
本文尝试从中观层面,对宏观的理论争论和微观的实践经验进行整合,并在更大范围内对地方政府如何针对不同情境、采取不同的土地确权方式进行探讨。具体而言:第一,明晰农地确权政策中不同主体的目标诉求。不同诉求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张力,这些基于单一立场的目标张力和矛盾,仅仅凭借倡导“兼顾市场效率和农民生存”的原则是难以调和的,将其置于不同农地区域类型的背景之下,则可以被分解进而逐个解决。第二,考察农地确权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人地关系和农地升值潜力。第三,梳理不同区域类型(东北“平原区”、西北“荒地区”、西南“碎地区”、东南“城郊区”)农地经营的基本特征。第四,基于“类型-模式”的逻辑,综合不同农地区域类型下各方主体利益诉求的突出表现形式和具体呈现方式,研究不同农地区域类型下土地确权实践面临的核心问题,以不同农地区域类型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特征为基础,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的农业经济发展格局,探讨出适合各自实情的最佳确权实践路径。endprint
二、农村土地确权政策:目标定位与影响因素
农村土地确权,是指由政府农业部门查清耕地和“四荒地”等农村承包土地地块的面积和空间位置,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空间位置不明、登记簿不健全等问题,把承包地块、面积、承包合同全面落实到户,核准并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赋予农民更加充分明晰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能。目前,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实践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片面性立场和单一化的认知体系,突出体现在对于是否确立土地私有权利、该坚持集体规模化或者小农经营等类似的“二元”争论上。实际上,对于农村土地确权政策的制度设计和基层实践,一方面,国家给予基层政府一定的政策调整和变通空间,而不是“一刀切”地只允许一种工作思路和模式;另一方面,这种调整和变通,也要控制在具备一定合理性且可供選择的范围内,避免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确权和农业发展模式引导过程中出现“竞相跟风”的非理性行为或者“图省事”的不作为现象。在回答如何更好地选择农村土地确权方式、提升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上,需要明确政策本身的目标定位,以及可能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因素,这样,才能因地制宜地选择确权实践的有效方式,为不同主体的目标实现提供最佳路径。
(一)农村土地确权政策的目标定位
农村土地确权政策本身应解决的问题和应有的定位,也即政府开展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初衷和农村发展的客观需求,是衡量政策设计能否达到目标的指标,也是选择具体土地确权实践方式与发展路径的标准。
首先,就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而言,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4年11月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农村土地确权的目的是“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最终实现“地,要从农户手中有序流转出来;人,要往城镇有序转移出去”[16]。具体而言,一是要形成基于完整要素市场的土地有序流转格局。为此,国家逐步放开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贷款,其目标是以工商资本来撬动农地市场、带动农村土地“生金”。二是要促进新型主体带动下的农地规模经营。国家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心,是走企业主导的“大”农业和产业化道路。从中央“一号文件”的表述看,2013年提出“培育壮大龙头企业,组建大型企业集团”,2014年提出“加快发展现代种业和农业机械化”,2015年提出“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2016年提出“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体系建设”,2017年提出“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突出了以高新科技为支撑的农业企业在生产环节的主体地位。根本而言,农村土地确权工作需要服务于上述国家发展战略。
其次,就基层政府而言,农村土地确权政策的有效落实,必须考虑其对于政策执行者的实际意涵。根据财政部2015年1月印发的《中央财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中央对农村土地确权经费的分级配套和专款专用进行严格的监管,使得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并不能给基层政府和干部带来直接的资金收益[17]。相反,农村土地确权易引发民众间矛盾,带来社会不稳,使基层干部工作的政治风险变高,存在“三怕”(即怕确权工作会引起农村长期积累的矛盾集中发生,怕确权工作会给今后征地工作增加难度,怕确权工作会对原来已经获得流转土地经营权的经营者造成影响)的现象[18]。2016年4月,农业部等四部委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注重发挥农民群众和乡村干部的主体作用,充分依托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等渠道,妥善将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19]。因此,基层政府更加看重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有效地减少民众因土地纠纷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维护基层社会稳定。
再次,就农民层面的农业生产而言,基于个体理性的农民期望提高农地经营收入,降低经营土地的风险,获得持续性收益。对于单个耕种者而言,他们迫切需要减轻耕作难度和降低成本,例如,有效减少农村土地的细碎化程度,实现连片耕种,通过更为便利的农田灌溉和机耕道路等集体基础设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对于家庭农场或农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者而言,需要降低农村土地流转交易的成本,尽可能地减少由于土地权利分散和固化带来的那些拒绝合作的“敲竹杠”者,也即“不怕饿死的钉子户”[20]。因此,理论层面上农村土地确权带来的产权明晰效益,其实际价值对农民而言并不明显。
(二)我国农村土地确权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
农村土地确权政策目标的多元化以及有关农地经营格局的争论,决定了基于单一立场的政策设计和理论探讨无助于该政策在实践层面的贯彻落实。考察不同农地类型和区域农业经营方式的特点,我们认为,人地关系和农地升值潜力两大因素,影响了包括国家农业发展战略、农民农业生产需求和基层确权纠纷矛盾控制在内的农村土地确权目标的实现。
首先,农业生产发展需要考虑生产主体和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也即人地关系,涉及人均耕地面积、人地比例等。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时强调,“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21]。中国的人地矛盾状况,直接决定了“地能否流转出来、人能否走进城里”,人地比例提高和人地分离,将有效地推动农地经营发展。农村土地确权中的“多地”问题,在人地资源均衡程度不同的地区处理起来的办法就会不同。在中国当前农村生产经营背景下,人地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与土地“细碎化”相关,影响农民经营农地的便利程度。人地关系缓和、人均面积大的农村,单块土地面积较大,规模经营较易实现。对于基层政府而言,农村土地确权实践中的问题纠纷多少和工作量大小,与人地关系紧张程度联系紧密。如东北地区,人均耕地面积较大,实测面积多于合同面积的“多地”问题较为普遍,而其“少地”问题相较于人地关系紧张的东南地区而言较少,化解难度也较小。
其次,农地的升值潜力,制约着土地利用方式、农作物选择和农业经营规模等,是影响农地经营决策的重要因素。农地价值及其升值潜力,一般受制于自然条件和地理区位两大影响因素。前者既包括耕地质量对土地产出能力的影响,也包括地形地貌等因素对农业生产的边际成本高低的制约;后者意味着土地用于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变化,也即在作物种类结构调整和土地用途转化中所带来的价值提升。基于此,反观当前我国农村土地确权政策的目标定位,不难发现,农村土地确权在不同的农地升值潜力背景下面临的外在约束条件有所差异,农地升值潜力会影响政策推进的效度。研究发现,由于不同质量的农地收益不同,导致高质量农田流转困难[22]。就国家层面而言,具备区位优势的农地因用途转化而升值,能够有效地促进工商资本进入和土地流转市场的活跃度,也会压缩农地规模经营的发展空间。对于农民而言,农地升值潜力越大,也就越能提高收入。然而,当土地升值扩大到大范围群体中,会迅速增加以“敲竹杠”为目的的拒绝合作者,不利于规模经营的实现,随之而来的争地夺利行为,将给基层政府的土地确权工作带来较大的压力。endprint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从人地关系和农地升值潜力两个维度,将农地划分为四种类型(见图1)。考虑到这种简化了的抽象概念和类型的现实参考意义有限,为了认识的形象化、直观化和易于理解,我们将农地的二维特征与农业地理区域的主要特点相结合,实现农地类型与农业区域划分的有效结合,使每一种农地类型的特点在某一典型区域中更加突出,使有关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和经营实践的探讨更具现实指导意义。例如,东北地区人少地多,人均土地面积大,进行集约化生产的成本低,规模经营较易实现,属于人少地多、农地升值潜力大的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城镇化水平高、人口密集、经济发展水平高,农地寸土寸金,属于人多地少、农地升值潜力大的类型;依次类推。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每一区域内所有的农地类型仅为单一类型,如在东北“平原區”中心城市的周边农村,会面临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土地扩张的需求,需要解决与东南“城郊区”类似的问题。出于学术研究中对研究对象和问题的概念化处理和应有的抽象化共识,在此舍弃每种类型内部所具有的多种情形,不再对区域内农地类型的情况作进一步讨论。
三、不同农地区域类型农业经营的基本特征
(一)东北“平原区”
作为“人地关系舒缓、农地升值潜力大”的东北“平原区”,人均耕地面积约为南方省份的15-25倍(见表1)。在耕地质量上,根据2014年农业部《关于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的公报》,东北地区耕地质量等级前三的比例在全国八个农业区中最高,而质量最差的三个等级的耕地比例最低[23]。在土地承包经营格局方面,调研中发现,新一轮土地确权过程中,东北地区农村的“多地”问题较为突出。“二轮”承包以来,由于延包工作不规范、荒地开垦以及农业税时代“大亩分地、小亩报税”的做法,导致目前家庭承包土地面积普遍多于原承包合同面积。例如,吉林省国土“二调”面积比农业部门的二轮承包面积多出近75%;在走访某边远山区县的过程中发现,平均每个村新开垦的“册外地”要多出400多亩。对于这些多出来的“灰色土地”,应该由谁拥有、拥有多大比例、收益归谁等问题,不仅在农民中颇有争议,也成为基层政府开展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主要忧虑。
东北“平原区”作为国家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区域内农作物同质化、粮食商品化、耕作机械化和农民职业化程度均较高。然而,该地区农业企业发展和工商资本带动规模经营的情况并不乐观,国有计划经济色彩浓重,私营经济体和市场竞争环境发育还不充分,以简单初加工为主的小型农业企业仍占多数。2015年,东北三省销售收入超亿元的龙头企业与湖北省数量大体持平,而且,龙头企业融资能力和意愿不足,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者的数量不到50[24]。由于本地工商企业发展和运作动力不足、外地资本进入少,加之人均耕地面积大,粮食种植便利,因此,分散个体所得收益较好,耕种意愿较强,农业经营主体中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较多,而以工商资本带动农地规模经营则显不足。
(二)西北“荒地区”
西北地区人少地多,但在自然条件限制下农地升值潜力不足,属于“人地关系舒缓、农地升值潜力小”的类型。甘肃、陕西等省份的人均耕地面积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但地区内耕地的地力较差,黄土高原区的土壤贫瘠、养分缺乏、水土流失严重,甘肃、新疆垦区水资源缺乏、沙漠化严重。西北地区的土地沙化和荒漠化严重、分布地域较广,仅甘肃、内蒙古两省区的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就占全国的301%[25]。 “荒地”不仅体现在自然条件下土地质量不高、环境恶化,更体现在人为弃耕导致大量耕地荒芜。
在此条件下,农户为增加收入而广种薄收,甚至开垦荒沙地来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加剧了水土流失和环境恶化的程度,使农业生产效益和农地升值潜力进一步缩减[26]。农业生产成本较高、产出偏低,使得农户生计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下降,以人口外流和青壮年劳动力转移为特征的农村“空心化”问题较为严重。农村土地经营主体渐趋老龄化,耕种能力低,进一步加剧了土地抛荒的趋势。与此同时,公共服务供给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区别对待,使得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要地的问题在本轮土地确权中较为突出,农民对于原本抛荒弃耕的土地仍然不放。
在农业经营方面,西北“荒地区”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农业经营方式必须有效发掘其地区优势并回避劣势。传统分散式地依靠个体家庭从事粮食种植,无法有效地提升农民收益,也无助于国家农业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虽然国家倡导并力促节水农业,为西北农村开展节水技术推广提供了有效的支撑,农民也具有节水意识,但实际上,大部分地区仍然采用漫灌、渠灌等粗放方式,而没有采用滴管、日光温室等更加节水的技术[27]。本地区农业企业的发展表明,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需要依靠具有雄厚资金和实力的企业或政府,借助其在基础设施建设、先进的种养技术引进和生态改造等方面的投入,为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和经营提供重要支撑。
(三)西南“碎地区”
西南地区人口多,山区地形分割,导致连片的耕作区域较少,属于典型的“人地关系紧张、农地升值潜力小”的类型。该区域人均山地面积大,但人均耕地面积较小。例如,云南省人均山地面积位居全国第一,但耕作区域内存在大量不宜耕作的大坡度土地,坡度大于25°的不适宜耕种的陡坡地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是全国水平的3-4倍。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为了实现公平分地、让每家都有地可种,往往按照好坏搭配、分级切块的原则,导致承包地严重的碎片化,西南地区一些县市平均每个承包户有10到20多块地[28]。受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的限制,以及长期分散的土地经营格局的影响,对农业生产开展有效的规划整合较为困难,农地升值空间有限。
在农民之间、地块之间、农民与地块之间关系紧张的人地格局下,土地稀缺性和人口压力加剧了该地区农业发展受到有限土地资源约束的程度,其规模化经营也更加受制于人地关系的影响。有学者指出了农地细碎化的负面作用,如造成农村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配置的低效,提高农业机械的使用成本,损害农户的生产效率等[29-30] 。而且,细碎化不利于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农村公共资源的利用,甚至导致为争夺公共品如水利设施而爆发冲突[31]。零碎地块加大了该区域土地确权工作的财政投入,使勘察实测和帐地比对的工作成本较高。进一步而言,真正成为本地区农村土地确权工作难点的是,随着过多地块和复杂边界确认而产生的矛盾和纠纷。土地碎片化不仅使农业发展更多地依靠密集的劳动,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经营的规模化。endprint
(四)东南“城郊区”
东南城郊地区人口集聚,耕地资源有限,城市周边地区的耕地质量、区位条件均较好,人均耕地面积在四类区域中最小,属于“人地关系紧张、农地升值潜力大”的类型。较高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不断扩张的城市建设用地需求,不仅压缩了城市周边的农地面积,加剧了原本紧张的人地关系,也使得城郊区域的农村耕地面临开发殆尽的局面。便捷的交通和优越的区位条件,提升了农村土地这一稀缺资源的价值。对于“城郊区”的农村土地,无论是经济作物种植还是建设土地征用,往往会给集体和承包户带来较大的收益。
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可以带来长期收益递增和边际成本降低,优势区位条件带来农业生产的高附加值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个体经营成本,使得人多地少的現实背景下土地碎片化和经营分散化的问题仍然存在。一方面,较高的土地价值加剧了农村土地确权过程中矛盾纠纷的产生,争地要地现象突出,如因长时间的土地租用、征占而造成土地归属不明的,土地整理或流转条件下土地的长期集中耕种方式导致界限模糊等,农户承包地的边界难以明确,为了确地而确权将产生高额的确权成本。另一方面,土地收益的提高增加了农地流转和集中经营的难度,区域内农地规模化经营的需求难以满足。一部分集体组织成员要求逐年提高土地承包费用、不愿流转土地或调整土地位置,造成土地无法实现流转的现象大量存在,严重制约了农地规模化经营的进程[32]。
四、基于农地区域类型差异的农村土地确权模式选择
从发展趋势看,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根本归宿,也即本轮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重要目标在于,形成便于个体农户耕种的土地承包格局、激发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内在动力、减少农地产权登记和交易成本。根据人地关系和农地升值潜力划分的四种农地区域类型,其农地经营格局和土地确权工作面临的问题各异。归纳起来,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否调整土地;第二,是否需要严格确地。前者的“调整”并非个人的增减地,而是对细碎土地的集体性整合,有助于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后者的“确地”,意味着将四至位置清晰的集体土地固定到每个承包户,确保承包地的实际勘界结果精确,地块信息和证书一一对应。实际上,调地和确地面临着不同的现实需要和操作成本,据此,我们对是否调整土地和严格确地进行区分,提出农村土地确权的四种模式(见图2),为降低不同地区农地确权成本、实现规模经营提供助益。
(一)依据现状确权确地模式
依据现状确权确地模式,是以原二轮承包合同为基础,对当前农村承包地的现状不作调整,严格坚持“确权确地为主,确权到户到地”。这一模式能切实落实为农民“颁铁证、确实权”的目标,确保农民承包土地四至清楚、边界清晰,也符合中央提出的开展农地确权工作的基本要求。该模式适合于农民对土地存在一定的依赖和耕种需求、农民耕种负担较小,土地确权依据清晰、土地争议纠纷调解难度小的地区。
东北“平原区”地广人稀,是非近郊的商品粮主产地,适宜大面积粮食作物种植,农民对于土地经营有较高的认可和依赖。正常的家庭劳动力,配备小型农机,可以充分发挥劳力、农地和农业机械等要素的效率,获得较高的农业经营收入。其一,确权确地能够充分确保土地在此类农村地区的家庭收入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重要作用。对于实践中存在的大量多地问题,按照国家要求,以村集体协商讨论的办法处理。例如,有的地方采取集体讨论合理的多地比例、对不合理的“多地”进行适当收费的办法,受到农民的广泛认可。在强化农户承包地权益的同时,该模式为农民进城但无法定居或者返乡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极大地降低了社会矛盾和风险触发的可能性。其二,确权确地为平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服务社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规模经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目前农民对土地还存在依赖,规模化经营面临困难,但随着城镇化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在机械化耕作便利地区,确权确地可以在不改变农户土地承包权的条件下为农户提供粮食生产的全程服务,这种农业社会服务市场化将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如黑龙江的“阿城模式”,以“不动地、不调地、不收地”的方式登记承包地,在“一村一策”集体讨论的基础上退还非法机动地、收回开荒地,实现了精准确权、推动了规模经营[33]。
(二)调整土地后确权确利模式
调整土地后确权确利模式,以原二轮承包面积为基础,将土地面积分配到各家各户,但不将具体承包地的边界四至确权给个人。该模式通过村组层面的土地大面积整合来促进集体合作经营,实现收益上的成员共享。同时,预留部分连片耕地,允许个人向集体申请耕种。该模式明确保障了农户的土地承包资格和权利,形式上实现了“个人+集体”的土地经营权运作模式,适合于人地关系较为舒缓、土地收益对农民收入贡献较小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较小,农业经营更需要依靠高度集约、规模统筹来实现发展。
调整土地后确权确利模式对于解决西北“荒地”区农业生产面临的土地效力低和农民耕种意愿不强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按照承包面积确权,可以有效地保护个体农户应有的土地权益。一方面,集体预留部分适于耕作的土地,在有限的范围内根据农户申请,交由农户耕种,确保部分依靠土地经营生存和发展的农户需求;另一方面,对于个体经营效益低或会导致环境恶化的不适合分散耕种的土地,可以统一收归集体或政府进行绿化改造或经济林建设。在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务农提供发展空间的同时,也能有效地破解农村空心化带来的土地撂荒问题。其二,调整土地后确权确利,为进一步推动土地流转提供了便利条件。作为国家“严格按照水资源配置总量,控制灌溉发展规模”的节水农业重点发展地区,西北“荒地区”的农业生产需要依靠基础设施投入和科技支持。个体分散化经营的效率较低,需要依靠拥有雄厚实力的企业的大量前期投入,通过对单位产出低或需要较大资金和设施投入的土地进行整治,实现规模化经营,以降低科技和基础设施投入的生产边际成本。其三,确利的方式,为集体合作经营,企业带动农地经营过程中农户参与,以及双方利益联结机制的形成提供了产权制度基础。如宁夏平罗县以二轮承包为基础,探索以承包地自愿有偿退出和农村老人以“三资”股权收益来获得收入、缴纳养老保险和置换养老服务的办法,以这种承包地的再调整和利益分配模式,有效地解决了村庄空心化和老龄化带来的土地闲置困境[34]。endprint
(三)调整土地后确权确地模式
调整土地后确权确地模式,是对村组集体发包的土地,按照集体民主和农户自愿的原则,积极推动土地调整置换,以提高家庭土地集中率,实现“小田并大田”;或者将土地整体集中整合后,重新按户连片发包,完成土地调整后,再将土地按照边界四至与面积逐户登记。其目标是实现农户承包土地集中连片,解决农户耕种不便利、市场流转或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该模式的适用范围较广,不仅适用于那些农户具有较强调整土地意愿的地区,也适用于一般的人多地少地区。
调整土地后确权确地模式对于西南“碎地区”的土地确权工作以及未来的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一,该模式有效地实现了碎地整合工作,能够在农民权益明晰的前提下提高集体土地的整合率,高效地完成农村的土地确权和碎地整治任务,有效地减少确权实践中农户土地的零散分布带来的土地实测、村组会议讨论等基层工作量。其二,该模式能够将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工作“提前”。目前,土地整治和土地流转被认为是解决农地碎片化的两种主要途径,然而,单一依靠外部力量(即政府)的整治和市场机制的流转方式,表现出治理碎片化和失灵[35]。实际上,西南地区过于碎片化的土地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流转,而借助土地产权登记来实现碎地整合,为农地的规模经营和流转市场培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现实中,调整土地后确权确地模式在许多地方都有成功的典范,如四川省成都市,实行调整土地的方案和意见由村民会议自行协商确定,尊重群众调地的意愿和协议,明确交地条件,即可实施“调地确权”。
(四)依据现状确股确利模式
依据现状确股确利模式,是指在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确地到村或组,统一对集体土地面积进行股权份额量化,以人口或农户为单位来明确承包资格、实际承包地股权及收益比例。该模式不是对承包地而是对土地这一产权客体的价值进行界定和划分,实现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割,将土地实际占有权、经营权和部分处置权委托给集体。一般适用于人地关系紧张、承包地无法精确分割,或者确权到户成本过高,尤其是长期实行土地集体经营的地区。
依据现状确股确利模式,能够为东南“城郊区”解决土地确权和农地经营面临的诸多问题。其一,实现农地产权界定的清晰化和高效化。在有效地减少确权确地的边界纠纷和多地少地矛盾的同时,股权分割的方式使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经营权转让和承包权退出更加便捷顺畅,确保了农户承包权长久的稳定性和分配的相对公平性。其二,实现农地经营权行使方式的灵活化。确股确利的方式实质上是保留农户的收益权,而将用益物权的使用和处置权利等委托给集体行使,在完成土地确权的同时,实现了农户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将原本分散于农户手中的土地集中起来并置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资源配置效益的最大化,放活经营权,促进集体规模经营和土地流转。其三,便于实现集体统筹管理。土地潜在升值空间较大,容易促使個人选择机会主义行为,个体农户有较强的动机为一己私利采取“敲竹杠”的行为,不利于集体利益最大化。确股确利模式能够有效地降低此类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确保土地经营的规模效益得以充分发挥。实践中,珠三角、江浙等地区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如广东的“南海模式”采取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实现集体内的股份合作经营,形成“以权入股,按股分红”的格局,在保障农户承包权益的同时,也推动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壮大[36]。
五、余论:农地类型、土地确权与农地经营发展策略选择
农村土地确权不应该仅是概念,应当回应农民的需要[37]。农村土地确权方式的选择,关乎未来不同地区农村土地经营模式和经济业态的形成;土地确权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农地产权格局也将影响农地经营发展的方向和成效。根据中央精神,农地“三权分置”的基础是“稳定承包权”,核心是“放活经营权”。在此前提下,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在稳定承包权的基础上,如何有效地放活经营权,使承包权的稳定服务于经营权的使用,探索形成土地流转、托管、入股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局面。
目前,就我国现代农业体系而言,农业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和经营体系等千差万别,不同地区的农地生产经营定位出现分化,如东北地区户均承包面积较大,流转土地主要从事粮食生产,而广东、海南等省70%以上的流转土地均用于非粮作物种植,流转到企业的耕地比例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38]。在此条件下,稳定农户承包权的基础作用毋庸置疑。但更为重要的是,针对当前不同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现状和问题,应在土地产权界定的过程中给予什么样的产权结构安排及何种方向的引导,以更好地服务于包括个体农户在内的经营主体的农业生产活动。为了实现多种形式并存的农业经营格局,需要在农地区域类型差异的背景下,积极探讨土地确权与农地经营方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考量土地确权如何服务于包括土地流转、新型主体培育和农业信贷担保在内的农业发展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国家提出“三权分置”的基本要求和原则①。
第一,区域类型差异下的农村土地流转引导。影响农村土地流转的因素较为复杂,包括土地实际产出效益、土地产权的不完全性和不稳定性、土地的“收益-需求”因素等。从土地流转的动力或土地要素市场形成的内因看,农村的人地关系及土地升值潜力,不仅影响了当前农村实际土地承包格局和土地确权工作,而且左右着规模土地流转得以开展的条件和范围,是土地流转市场形成和政府引导中应该关注的重要因素。在区域类型差异下进行农地流转分析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如东北地区,许多承包户维持着家庭经营,在耕作便利的条件下,个体自发流转不断增多,因此,确权确地能够稳定农户产权、保障劳动收益。然而,单一的粮食生产并不足以吸引工商资本进入,土地流转更多维持在村庄熟人之间。在此条件下,以代耕或托管形式为代表的农业生产服务社会化过程更加符合农民的需求,应成为土地流转形式探索的重心。东南“城郊区”的土地流转中,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明显,以实现土地信息共享为目标的农地交易平台在土地流转市场建设中尤为重要。endprint
第二,区域类型差异下的农地经营主体培育。当前,我国农地经营主体随着流转市场的逐渐放开和活跃而异军突起并呈现出分化的趋势,如传统小农、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等。然而,这种分化在不同地区之间并不是均质的。针对不同地域的农地经营主体培育也要有所区分,因地施策。如西北“荒地区”的农业发展需要以农业企业和合作社等作为主要经营者带动农户经营,西南“碎地区”的自然条件则允许农户个体经营,但二者都需要一定的土地整合。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常常存在发展规模不大、盈利能力不足、提高股农收入作用有限、农户参与度不高等问题,此类地区不宜倚重农地股份合作模式[39]。在政府引导土地调整后进行确权,既能有效地保障农户权益,也可以解决土地的细碎化问题,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至关重要。
第三,区域类型差异下农地规模经营的保障体系建设。近年来,在促进农业产业发展、提高对农地规模经营主体的保障能力方面,国家不断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例如,国务院2016年10月印发的《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提出,“健全覆盖全国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立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的监督考核和风险防控机制。稳妥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对稳粮增收作用大的高标准农田、先进装备、设施农业、加工流通贷款予以财政贴息支持”。实际上,由于农地类型及其经营模式不同,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生产融资活动和信贷需求也有较大差异。如东北地区大部分农村,农户家庭自营或生产服务外包托管的形式较多,他们对银行贷款的需求较小,推广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政策的实际效果有限。调研中发现,位于东北平原区的吉林省东部某县市,家庭农场的“农地贷”总额不足全部农场总投资额的1/10;相比而言,西北“荒地区”的农业企业或合作社的生产性融资需求较大,更需要由政策性担保公司或政府财政资金作担保,以降低银行的融资风险。
综上,在推进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农村土地确权政策的落实并非简单地“毕其功于一役”,而是需要满足政策参与主体的预期目标和发展需求。有效的办法应该是针对不同类型农地区域的特征,有侧重地在个体分散经营和适度规模经营之间平衡,以实现对农村土地确权和农地经营发展工作的通力统筹。
注释: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要求,“充分考虑各地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差异,鼓励进行符合实际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总结形成适合不同地区的‘三权分置具体路径和办法”。
参考文献:
[1] 姚洋.农地制度与农业绩效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1998(6):3-12.
[2] 南方农村报记者专访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N].南方农村报,2013-11-23.
[3] 厉以宁.談谈产权改革的若干问题[N].北京日报,2013-12-02.
[4] 曹志立.农村土地确权政策执行差异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5] 陈文学,高圣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视野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困境与出路[J].学术探索,2010(3):19-24.
[6] 丁琳琳,孟庆国.农村土地确权羁绊及对策:赣省调查[J].改革,2015(3):56-64.
[7] 王毅杰,刘海健.农地产权的地方化实践逻辑——基于Q村土地确权风波的考察[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52-58.
[8] 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00(2):54-65.
[9] 吴毅,陈颀.农地制度变革的路径、空间与界限——“赋权-限权”下行动互构的视角[J].社会学研究,2015(5):36-62.
[10]钱龙,洪名勇.农地产权是“有意的制度模糊”吗——兼论土地确权的路径选择[J].经济学家,2015(8):24-29.
[11]于建嵘,石凤友.关于当前我国农村土地确权的几个重要问题[J].东南学术,2012(4):4-11.
[12]夏柱智.虚拟确权:农地流转制度创新[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89-96.
[13]张雷,高名姿,陈东平.产权视角下确权确股不确地政策实施原因、农户意愿与对策——以昆山市为例[J].农村经济,2015(10):39-44.
[14]郎秀云.确权确地之下的新人地矛盾——兼与于建嵘、贺雪峰教授商榷[J].探索与争鸣,2015(9):44-48.
[15]曹正汉.产权的社会建构逻辑——从博弈论的观点评中国社会学家的产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8(1):200-216.
[16]韩长赋.明确总体要求 确保工作质量 积极稳妥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J].农村经营管理,2015(3):6-9.
[17]财政部网站.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EB/OL].[2015-01-28].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wengao/wg2015/wg201504/201509/t20150916_1458683.html.
[18]黄业斌.农村土地确权存在的主要问题[J].行政管理改革,2016(1):33-36.
[19]农业部网站.农业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有关工作的通知[EB/OL].[2016-04-22].http://www.moa.gov.cn/govpublic/NCJJTZ/201604/t20160422_5104469.htm.endprint
[20]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204.
[21]新华网.习近平:加大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力度[EB/OL].[2016-04-28].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8/c_1118763826.htm.
[22]孙云奋,齐春宇.农地类型差异与农地流转困境分析——以山东省为例[J].农村经济,2012(1):40-44.
[23]农业部网站.关于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的公报[EB/OL].[2014-12-17].http://www.moa.gov.cn/govpublic/ZZYGLS/201412/t20141217_4297895.htm.
[24]朱宇,张新颖.中国东北地区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09-110.
[25]国家林业局网站.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EB/OL].[2015-12-29].http://www.forestry.gov.cn/main/69/content-831684.html.
[26]国土资源部网站.陕西榆林演绎荒沙地造田传奇[EB/OL].[2012-12-27].http://www.mlr.gov.cn/xwdt/dfdt/201211/t20121127_1160225.htm.
[27]梁植睿等.甘肃省民勤县农业节水灌溉技术传播的困境与出路[J].农学学报,2012(9):36-40.
[28]邓俐.承包地碎片化阻碍农村土地流转[N].农民日报,2014-04-14(001).
[29]谭淑豪,曲福田,尼克·哈瑞柯.土地细碎化的成因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3(6):24-30.
[30]田传浩,陈宏辉,贾生华.农地市场对耕地零碎化的影响——理论与来自苏浙鲁的经验[J].经济学(季刊),2005,4(3):769-784.
[31]桂华.组织与合作:论中国基层治理二难困境——从农田水利治理谈起[J].社会科学,2010(11):68-77.
[32]程渭山.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新常态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调研报告[J].新农村,2016(1):5-8.
[33]赵鲲,罗鹏,谭智心.精准确权激发农业发展活力[N].农民日报,2015-11-06(001).
[34]陈志强,宋晓意.盘活“沉睡”土地资产 平罗农村改革为全国“蹚路”[N].新消息报,2015-03-09(05).
[35]王山,奉公.中国农地细碎化及其整体性治理问题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16(1):17-22.
[36]张霞,欧阳柳依. “确权到人”变“确权到户” 南海修正土地魔方[N].南方周末,2015-04-24.
[37]贺雪峰.农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的由来、逻辑与出路[J].思想战线,2015,(5):75-80.
[38]刘守英.中国农地权属与经营方式的变化[N].中国经济时报,2016-02-19(010).
[39]诸培新,仲天泽,钦国华.经济欠发达地区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研究——以江苏省宿迁市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5(7):103-108+168.
Abstract: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and implement the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roposed by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it is essential to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s and deepen 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system. The right confirmation of rural land is the basic work of “developing a variety of forms of moderate scale management and cultivating a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At pres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policies of right confirmation of rural land is faced with many obstacles, such as difficulties in local implementation and poor effect of execution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goals and demands of the center, localities and farmers in right confirmation of rural land, and put forward targeted and differentiated implementation plan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Taking hu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rural land appreciation potential as two dimensions, and taking agricultural region as carrier,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of agricultural regions: “plain area” in Northeast China, “barren area” in Northwest China, “broken area” in Southwest China and “suburb area” in Southeast China. 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ng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management status of different rural land area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types of right confirmation of rural land model: confirming the right and land according to present situations, confirming the right and benefit after the adjustment of land, confirming the right and land after the adjustment of land, and confirming the stock and benefit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ducing agricultural operation cost and realizing scale operation in different rural land areas.
Key words:rural land area; type difference; right confirmation of rural l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責任编辑:李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