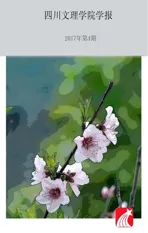司马元稹笔下的通州风土人情
2017-07-21陈正平
陈正平
(四川文理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四川达州635000)
司马元稹笔下的通州风土人情
陈正平
(四川文理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四川达州635000)
唐元和十年闰六月至十四年正月,大诗人元稹在通州(今四川达州市)做了三年半的司马。作为贬谪闲官,他“闲诞无事,遂专力于诗章”。在他的诗文中,有不少是状写通州的地理环境、社会现状、虫蛇猛兽、食货物产和民俗风情的。这些描写染上了他个人的感情色彩,流露了他独特的通州情怀,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当年的“通州印象”。
元稹;通州;风土人情
唐元和十年(815)春,元稹(779—831)自唐州还长安,三月二十五日再贬谪为通州(今四川达州市)司马。三月三十日,元稹在陕西沣西(今陕西户县)告别好友白居易等人,“一身骑马向通州”,[1]432一路延宕,闰六月才到通州。至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初离开,元稹在通州做了三年半的司马。他自谓“闲诞无事,遂专力于诗章”,将自己在通州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创作了古讽、乐府、近体诗180余首和少量的实用文。这些诗文中有不少是状写通州的地理环境、社会现状、虫蛇猛兽、食货物产和民俗风情的。《旧唐书》称元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写景抒情,自能沁人心脾。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言:“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2]作为一个政治上失意的贬谪闲官,作为一个从京城放逐到偏远山乡的“外地人”,元稹以独特的视角看通州,笔下的通州必然染上了个人的感情色彩,流露了他独特的通州情怀,但它毕竟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当年的“通州印象”。
一、元稹笔下的通州概貌
元和十年,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告诉如胶似漆的好友白居易说:“授通州之初,有习通之孰者曰:通之地,湿垫卑褊,人土稀少,近荒扎死亡过半,邑无吏,市无货,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计粒而食。大有虎貘虵虺之患,小有蟆蚋浮尘蜘蛛蛒蜂之类,皆能钻啮肌肤,使人疮痏。夏多阴霪,秋为痢疟,地无医巫药石,万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虑。”[3]元稹尚未到通州,就听说了通州艰难窘迫的生存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现状的恶劣,使元稹长叹:“夫何以仆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也如此,其所诣之忧险又复如此”!实际上,通州的环境还不至于使人难以生存,司马官也不至于计粒而食。白居易《与微之书》中就说过:“司马之俸虽不多,量入俭用,亦可自给,身衣口食,且免求人。”[1]92
元稹到通州后,又将自己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情况,向白居易去信作了描述。白居易在《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中,[4]342以诗的形式复述了元稹去信的部分内容:“来信子细说通州,州在山根峡岸头;四面千重火云合,中间一道瘴江流。虫蛇白昼拦官道,蚊蟆黄昏扑郡楼”;“匼匝巅山万仞余,人家应似甑中居”;“人稀地僻医巫少,夏旱秋霖瘴疟多”。这里概述了通州的地理环境:城在大山脚下的峡谷里,四面的山是红的,像火云一样围合着,州河从山间流过。州河的湿气常使恶性疟疾流行,所以元稹将州河称为不祥的“瘴江”。四面高山万仞,人们好像居住在被湿热熏蒸的甑子中。元稹概括通州气候特征,用得最多的是一个“瘴”字,如“通州炎瘴地”“瘴塞巴山”“瘴窟”“瘴毒”“瘴疟”“瘴气”“瘴色”“瘴云”“瘴烟”。通州的湿热使元稹染上疟疾。元稹不能适应“巴地湿如吴”“通宵但云雾”“三冬有电连春雨,九月无霜尽火云”。宋人乐史在《太平寰宇记·通川县》中有关于州河水流向的描述:“东关水东北自石鼓县界流入,经县南一百六十步,西南流入三冈县界”。又言:“古城山在县西五里,山四面绝崖”,“凤凰山在县西北五里,山形象凤翅,掩映州城”。[5]石城山指塔陀的龙爪山,可见,唐宋时的通州(达州)城建在距今龙爪山、凤凰山五里的州河边(今南门河口一带)。
唐代通州属山南西道(治所设于兴元府,即今陕西汉中),通州治所在今达州市区,管辖通川(今达川、通川区)、三冈、石鼓、永睦、阆英(以上四县后来被废除)、东乡(今宣汉县)、巴渠(今渠县)、新宁(今开江县)八县。关于通州的人口、幅员面积,元稹在《告畲三阳神文》中指出:“通之盛时,户四万室,耕稼骈致,谣讴涌溢。廛闲珠玉,楼稚丹漆。孝顺子孙,廉能吏卒”。这是通州的鼎盛时期有四万户人家。后来因为“政式不虔,人用不谧”,而至饥馑因仍,盗贼蜂起,百姓流走它乡,“万不存一”。元稹在通州时,“居才二百室,幅员六千里之地”(《告畲竹山神文》)。通州成了地广人稀,“邑无吏,市无货,百姓茹草木”的下州。
元稹在《见乐天诗》中云:“通州到日日平西,江馆无人虎印泥。”元稹下榻的“江馆”,据考证在今达州老城大东街黄龙寺一带。在《酬乐天雨后见忆》中又有“渐入黄泥渐到州”的句子,可见元稹是由今达城西外,经“黄泥碥”而到大东街。“虫蛇白昼拦官道,蚊蟆黄昏扑郡楼。”江馆空寂无人,黄泥路上有虎的脚印,可见其当年的荒凉卑褊。
二、元稹笔下通州的虫蛇猛兽
元稹到通州后不久,就作了《虫豸诗》七篇共二十一首。在诗的序中有言:“通之地,丛秽卑褊,蒸瘴阴郁,焰为虫蛇,备有辛螫。蛇之毒百,而鼻褰者尤之。虻之辈亦百,而虻、蟆、浮尘、蜘蛛、蚁子、蛒蜂之类,最甚害人。其土民具能攻其所毒,亦往往合于方籍。不知者,遭辄死。”他对通州阴郁潮湿的气候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四面高山,荒草杂树丛生,一条“瘴江”生湿,人们如生活在甑子中,湿热重,容易生病。这些恶劣的自然环境恰恰宜于毒蛇猛兽生存。通州的“土民”在长期与自然界的斗争中,总结出了经验教训,能以民间医药和方术“攻其所毒”,与虫蛇猛兽共存的环境里,自有其相生相克之术。元稹描述这些虫蛇特性的目的,在于“尽药石之所宜”,意在为民除害造福。
他首先写《巴蛇》三首。言“巴之蛇百类,其大,蟒”。民众常以雄黄烟熏以攻击或趋避。当今民众亦有在端午前后,喝雄黄酒,燃放“黄烟”以避虫蛇的习俗。巴蛇的传说起自远古时期。被鲁迅称为“古之巫书”的《山海经》的《大北方经》中言:“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6][7]《海内南经》又言:“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巴”字:“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象形。”巴蛇其实就是一种很大的蟒蛇,在远古时期凶猛地活跃在巴地。童恩正在《古代的巴蜀》中认为:“在历史记载中,巴既作为族名,又作为地名。”[8]“巴”这种名称的由来,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中就有以虫、蛇之属来解释的。元稹在写给白居易的诗中多次提到巴蛇:“君避海鲸惊浪里,我随巴蟒瘴烟中”“三千里外巴蛇穴,四十年来司马官”。可见当时在通州巴蛇还是随处可见。
巴蛇通常盘曲在洞穴里,在洞穴下面的巢穴里,有一种很大的“蛒蜂”,巴人俗称“牛蛒蜂”,其毒性数倍于其它蜂类和蛇蝎,“微遭断手足,厚毒破心胸”,螫人必死,“土人”常以巫术来医治蜂毒。
“巴蜘蛛大而毒。其毒者,身边数寸。”这种毒蜘蛛暗藏杀机,不仅攻击人类致死,而且还伤及竹柏,吞噬虫蛾。
“巴蚁众而善攻栾栋,往往木容完具,而心节朽坏。”通州偏湿热,宜于白蚂蚁繁殖,虽小而危害巨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元稹提醒州民注意,以免酿成灾祸。
元稹在诗中常常提到通州的“蚊蟆”,“蟆,蚊类也,其实黑而小”。元稹认为“蚊蟆与浮尘,皆巴蛇鳞中之细虫耳。故啮人成疮,夏秋不愈”。巴人常以柏树枝叶、苦蒿烟熏,或用麝香驱除,被咬伤后则用楸树叶捣成泥膏来敷疮治疗。
元稹在《虻》的小序中写道:“巴山谷间,春秋常雨……雨则多虻,道路群飞,噬马牛血及蹄角,且暮尤极繁多。”虻是一种昆虫,体长椭圆形,生活在田野杂草中,雌虻吸人和动物的血液,啮人肌肤,剧痛难忍,“无疗术”。
“通州到日日平西,江馆无人虎印泥。”元稹刚到通州,看到“江馆”外面的泥地上,就留下了虎的足迹。在《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中,元稹又写道:“茅檐屋舍竹篱州,虎怕偏蹄蛇两头”。二句诗下面有自注:“通州,元和二年,偏蹄虎害人,比之白额。两头蛇处处皆有之也。”“偏蹄虎”和“两头蛇”处处可见,夜里还时时听到虎啸声,令人心生恐怖。偏蹄虎似白额虎一样凶残,两头蛇并非长了两个头,而是头尾长得极像,便于自我保护,该蛇常倒着爬行,以便受攻击时用头部反击。古人认为两头蛇是怪异的不祥物。元稹还在诗中写道:“满身沙虱无防处,独脚山魈不奈何。”山魈别名鬼狒狒,常嬉戏于丛林及岩石间,体型粗壮,长约60—70厘米,雄性可重25公斤,它长有鬼魅似的面孔,长脸,鼻梁鲜红,颌下有一撮山羊胡须。牙齿长而尖锐,爪子锋利。成年山魈性格暴躁,凶猛好斗,敢于和狮子搏击。山魈是民间传说中的山怪、山精、恶鬼。《抱朴子·登涉篇》云:“山精形如小儿,独足向后,夜喜犯人,名曰魈。”
三、元稹笔下的通州民俗风情
元稹在诗文中描述了通州人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民俗。通州幅员虽有六千里地,但山高路险,“平地才应一顷余”,基本上还是采用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田畴付火罢耕锄”“田仰畲刀少用牛”“米涩畲田不解鉏(锄)”,诗中多次提到“畲田”的原始耕种方式:砍烧草木为灰,以灰为肥,候雨种植,收成很薄,民众生活艰辛,“刺史以下,计粒而食”“百姓茹草木”。这种生产方式不独通州所有,凡地广人稀的山区峡谷地带,均停留在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上,直到近代。通州所产的稻谷品种亦不佳,米味苦涩,不如中原的米好吃。

《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盛产桑蚕、棉麻等经济作物。元稹在《酬乐天得稹所寄苎丝布白轻庸,制成衣服,以诗报之》中写白居易送元稹簟席,元稹也将一段通州特产的白丝绸和一段绿花麻丝面料寄给了白居易:“苎薄绨轻共一封”。巴人所织的布,在当时相当有名。《说文》:“賨,南蛮赋也。”至唐代,依然保持了以绢布代俸禄的传统,賨布、賨人,皆因此而得名。“市井无钱论尺丈”“寅年篱下多逢虎,亥日沙头始卖鱼”,讲的是通州原始的交易民俗:物品、鸡禽等买卖不用秤称,论个数,比长短。寅年、亥日,是说通州场镇三天一次集市,逢寅、巳、申、亥为赶场日。这些交易习俗至今尚存。
“椎髻抛巾帼”,是说通州人的发髻象椎形,妇女用长丝巾包头。这种头饰装束是巴蜀各地共有的。《蜀王本纪》载:蜀人椎髻,左袏。男女用布或丝绸包头(俗称包帕子)的习俗沿袭到当代。“芒屩泅牛妇,丫头荡浆夫。”屩,草鞋,通州人善以稻草、苎麻编织草鞋,穿草鞋的习俗也沿袭至当代。
通州人的居住民俗是怎样的呢?“茅檐屋舍竹篱州”“阁栏都大似巢居”,元稹自注:“巴人多在山坡架木为居,自号阁栏头也”“江郭船添店,山城木竖郛”,亦指江上以船为店,通州城外的巴人大都在山坡上架木为室,“不础、不柱”。这反映了巴人建房“无论是选址、布局和构成,都善于利用自然条件,体现因地制宜、因山造势、沿河构屋及因材致用的节约和营建思路”。[9]这种“阁栏”可能是一种依山坡而建的矮小的吊脚楼或窝棚,因陋就简,以竹木为构架,不挖筑地基,不用梁柱,茅檐冬暖夏凉,矮小是为了避风。
巴人信巫重鬼,好祭祀。元稹诗中有“犷俗诚堪惮,妖神甚可虞”的句子,指巴人大多信奉巫觋,看病靠“巫医药石”,原始迷信顽固地长期留存。至今民间尚有“(喜)鹊鸣吉,(乌)鸦鸣凶”的吉凶观念。相关节日活动,如“春社”、“秋社”,把赖以生存的土地神格化为土地神,《太平寰宇记》云:“巴人之风俗皆重田神”,修庙塑像以祭祀。通州各地有不少的“龙王庙”“土地庙”,通州城里有著名的“黄龙寺”“会仙桥”,反映农耕文化的特点:希望借助各路神仙保一方风调雨顺,佑四邻畜旺人兴。元稹代理州务的半年多时间里,就带领官员和州民,以“清酒庶羞”,祭祀三阳神二次,竹山神一次,祈求神灵呼风唤雨,保通州政通人和,民众丰衣足食。人们总以为有灵魂、鬼神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和自然界的一切,求神力以补人力之不足。这种原始宗教观念根深蒂固。
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言巴人“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10]元稹“世居河南”,通州的风俗人情令他十分困惑,在《遣行十首》之九中他写道:“见说巴风俗,都无汉性情。猿声芦管调、羌笛竹鸡声”“夷音啼似笑,蛮语迷相呼”“舞态翻鸜鹆,歌词咽鹧鸪”。感觉巴人说话像谜一样难猜,唱歌像鹧鸪鸟叫,显然他听不懂通州蛮人的说话和歌舞。“入衙官吏声疑鸟”,在衙门里他听不懂官吏们的“鸟语”,地方官吏和巴人也听不懂他的河南话,语言交流就成了问题。“巴风俗”和中原的“汉性情”差异也很大,使他难以适应。
通州人劳苦并快乐着。《华阳国志·巴志》载:“巴人劲勇,俗喜歌舞。”《太平寰宇记》说巴渠人“不解丝竹”“其民俗聚会则击鼓踏木牙,唱竹枝歌为乐”。唐诗人于鹄《巴女谣》写道:“巴女骑牛唱竹枝,藕丝菱叶傍江时”,这是何等悠闲美妙的画面。宋人《溪蛮丛笑》载:巴人“死亡群聚歌舞,舞则联手踏地为节,名曰踏歌。”巴人的竹枝歌用词俚俗,质朴率真,多用比兴手法,蕴双关语,它“集辞、声、乐、舞一体,‘歌者扬袂睢舞’,舞者执竹枝,击节踏歌,铿锵作响,伴奏者或击小鼓或吹短笛,和而乐之”。[11]巴人竹枝歌咏风俗,歌民情,曲调新鲜活泼,韵律和谐婉转,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现实生活气息,有论者称“巴渝竹枝词,诗之国风,辞之九歌也”。元稹受其影响,也作过竹枝歌,白居易称其调苦词苦,可惜未能传世。
四、元稹的通州情怀
白居易在写给元稹的诗中,有两句对元稹的处境作了绝好的概括:“通州海内恓惶地,司马人间冗长官”。[4]358元稹在诗中称“黄泉便是通州路”,到通州后,又自谓“染瘴危重”“疟病将死”“病疟二年”“垂死病中”“十年谪宦,备极凄惶”。当时的通州乃海内蛮荒之地,常为官员贬放之所。司马位居刺史、别驾、长史之后,通州作为下州,司马从九品,当时已成一种冗员散职。如白居易在《江州司马厅记》中所言:司马“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元稹在《通州》一诗中描述了他的生活情状:“平生欲得山中住,天与通州绕郡山。睡到日西无一事,月储三万买教闲。”在诗文冠绝的唐代,元稹在通州扮演的是一位居闲职享薄禄的诗人角色,他一生最有代表性的诗歌理论和诗作(包括长诗《连昌宫词》),大都是在通州完成的。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元稹“自元和十年六月至十二年冬,皆在山南西道区域”。[12]68山南西道治所设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管辖今陕西汉中、四川东部、重庆西部地区,通州即在山南西道管辖区,元稹染病危重,通州又缺少“巫医药石”,自然去了道府兴元,又得贵人相助:权德舆(759—818),字载之,唐代政治家、文学家,曾拜相,后出为山南西道节度史,他对元稹十分关照。元稹以治病、养病为名请假到兴元府,得到了权德舆等人的庇护。元稹作通州司马三年零七个月,在兴元(今汉中)养病就有两年多。
作为诗人,元稹在通州是孤独的。本来巴人“俗喜歌舞”,无论男女老幼,均能踏歌唱竹枝。元稹有诗云:“橹划动摇妨作梦,巴童指点笑吟诗。”刘禹锡《竹枝词》之二云:“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于鹄《巴女谣》云:“巴女骑牛唱竹枝。”元稹刚到通州的“江馆”,就看到白居易的诗被题写到墙壁、柱头上。可见通州的文化氛围还不错,不乏民间歌手和诗歌爱好者。或许是由于语言不通难以交流,或许在通州知音难觅,元稹在《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的序中说:“通之人莫可言诗者,唯妻淑在旁知状”。
元稹在兴元(汉中)府见到涪州(今重庆涪陵)刺史的女儿裴淑(字柔之),一见钟情。由节度使权德舆做媒,元和十一年(816)春,37岁的元稹赴涪州结婚,裴淑成为元的继室。裴淑“贤明有礼”“稍知文墨”,[12]106与元稹“琴瑟相和”,是元稹身边的最大安慰。
自谓“苦境万般”“常在闲处,无所役用”的元稹,其志趣在与千里之外的好友白居易,讨论诗歌主张和不断的诗歌酬唱。《唐才子传》言:“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合之多,勿逾二公者”。[13]元白曾主张政治改革,诗歌方面又倡导和参加了新乐府运动,推崇杜甫,“寓意古题,刺美见事”“不虚为文”。元稹在通州所作的二十多首乐府诗,反映现实的面相当广阔,其作用和影响都不容忽视。元稹在通州大量的诗作是酬和赠答以及“遣病”“遣行”之什,诗中常有病愁怨叹之声。白居易在《与微之书》中说,元稹病时“上报疾状,次叙病心,终论平生交分”。元稹在通州水土不服,得疟疾是真,但“病心”却是他愁苦的根源,遣悲怀,枉凝眉,通州成了放逐他的伤心地。正如《旧唐书·元稹传》所言:“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惋。”
元和十三年(818)四月,通州刺史李实病死,元稹“以司马权知州务”,即代理通州刺史,使他的仕途有了转机,开始振作起来。在离开通州前的七个月里,他发动、组织通州人砍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乃劝州人,大课芟铚”,在南外“开山三十里”。
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元稹离开通州,迁虢州长史,“三月十一日,与白居易及弟白行简,相遇于峡口,停舟夷陵(今湖北宜昌市),留三日而别”。[4]358离开通州后,元稹在他的诗文中再也没有提起过通州。
[1] 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25.
[3]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13.
[4] 白居易诗选[M].顾启仓,周汝昌,选注.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
[5] 太平寰宇记:卷137[M].北京:中华书局,2008:1.
[6] 鲁 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9.
[7] 山海经[M].袁 珂,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3.
[8]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6.
[9] 陈正平.中华民俗文化论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393.
[10]华阳国志[M].刘 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28.
[11]陈正平.巴渠民间文学与民俗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142.
[1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3]辛文房.唐才子传:元稹[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95.
[责任编辑 范 藻]
About Local Customs and Practices in Tongzhou from the Writings by Sima Yuanzhen
CHEN Zhengping
(Literature and Media School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Dazhou Sichuan 635000, China)
From the second June in the tenth year to the fourteenth year of Yuanhe in Tang Dynasty, the famous poet Yuan Zhen had been appointed “Sima” (a name of the highest rank of military officer) for three and a half years in Tongzhou (now Dazhou, Sichuan province). He was relegated and had no important things to deal with, so he “devoted himself to writings”. His poems have a lot of descriptions about the geography, society, animals, food and customs in Tongzhou, which presents his feelings and gives us the impressions about Tongshou at that time.
Yuan Zheng; Tongzhou; custom and practice
2017-03-17
陈正平(1948—),男,四川平昌人。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与民俗学研究。
G127
A
1674-5248(2017)04-002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