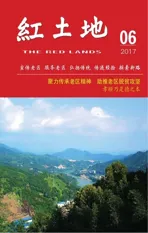古代广布法令与法家法治
2017-01-25
古代广布法令与法家法治
法家在古代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流派,而由于其对“严刑酷罚”的偏好,对趋利避害人性的尖锐剖析,又使得它在历史上饱受争议,甚至如秦之商鞅,“中于谗诽也二千年”。以现代法治的观念看,法家之法治,尤其是以商鞅为代表的“秦制”,确实与法治有所不同,法治是以法律为最高权威,而“秦制”尊君主之最高权威,故君主可以变更法律。此外,以秦为代表的法家法治包含有极端严苛的色彩、工具化的运用,都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去甚远。
然而,抛开个别法家人物的重刑倾向,及法治之内在标准的争议不谈,仅就治理技术及效能而言,法家的一些思想的确有可取之处,这就包含法家对广布法令、以法宣教大众的重视,它成为法家推动法治的重要基础。
何以需要广布法令
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法家不只考虑设计一套有效的制度,更关注“行法之术”,也就是如何使法律制度在政治统治中发挥实际作用。法家要求广布法令,让百姓皆知法令条文,就是着眼于提高法治的实效。
广布法令之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子产及赵鞅的“铸刑鼎”,将法律条文铸在铜鼎上,就是要让天下百姓皆知法令的内容,同时这一公布的方式亦极其庄重,充分体现了法律之威严。战国时,吴起变法,同样首先要求“申明法令”,自上而下地宣传普及律令。为了增强广布法令的效果,吴起还采取了类似商鞅“徙木立信”的办法,他先将一车辕移到北门之外,发布法令说:“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韩非子·内储说上》)有人将车辕搬运至南门外,果然获得了赏赐。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早期法家不仅广布了法令,更是使其法治取信于民。
法家倡导广布法令,是基于对人性的考量,避免“不教而诛”。尽管“教化”主要是儒家的思想,但法家也赞同教化的作用,只是其倡导教化的内容是法令。管子认为行法之前,应该先开导人民,使他们能知法而遵守之。《管子·权修》中说:“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即是说,申明宪令是获得大治、减少犯罪的基础。法家认识到,不止要向百姓申明法令,法令本身还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只有稳定和一贯的法令制度,才能获得百姓的信服,而欲使其获得教导与信服,又需要先从法律条文的公布开始,《管子·法法》曰:“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因此,广布法令必须与以信施法结合起来,做到信赏信罚,“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同样的,“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管子反复说明的是信赏信罚之重要性,而要做到赏罚分明,首先需要百姓或兵士知法,故广布法令成为行法的前提。
法家通过广布法令,是要树立其所欲求的行为规范,实现统治的目标。法家哲学基于对社会人性的敏锐观察,成为“一套操控人的行为系统”。先秦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终极目标,广布法令以行法治,也正是要为百姓树立行为指南,进而通过“农战”服务于富强之目标。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这就要求以法令引导民众趋向农战,“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者之农也。”国家的法律制度必须要以农战为指引,确立激励百姓的赏罚制度,才能导向富强之目标。而建立了农战之法,就必须让民众依法而行,使天下的官吏百姓都知道法令内容。普通百姓知法,了解遵法的益处,就能够安于农耕、勇于战斗;官吏知道民众知法令,“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官民都能知法遵法,“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法治所欲求的国家富强就能够实现。
当然,不可否认,法家要求广布法令,也与其对法律认识的局限性相关。韩非集先秦法家之大成,提出了法、术、势之说,与相对隐秘、不欲人见的“术、势”不同,“法莫如显”,“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只有将法广布于百姓,才能发挥法的作用,“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韩非子·难三》)换言之,一国之法令本来就是用来“御民”的,百姓当然需要知道其内容,进而才能有所遵从。法家倡导一刑、一教,以“燔诗书”配合“明法令”,实际上也是要统一民众的思想,服务于农战的目的,而将人自身的价值工具化。这种内在指向专制的法律观,当然与现代法治精神凿枘不合,但法律本身的公开性、普及性,又与现代法治的要求并行不悖。
如何能够广布法令
法家不仅详细论述了广布法令的必要性,更从施行法令、推动法治的角度,提出了广布法令的诸多途径,通过建立法令宣传普及制度、强化各级官吏宣教法律义务等方式,有效地促进了广布法令目标的达成。
通过建立法令普及制度,使法令宣教规范化。商鞅特别重视法律制度的宣传普及,让民众知晓法律是实行法治的必要前提,为普及法律,建立“主法令之吏”讲读法令的制度,官吏必须先学习熟悉法令,再向民众广泛讲读普及,“主法令之吏有迁徙物故,辄使学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序,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不中程,为法令以罪之。”官吏对法律的说明解释,百姓对法令的学读,必须准确到一字一句,不得任意删改,“有敢剟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商君书·定分》)
秦国基本遵循了商鞅广布法令之思想,要求全体臣民学法、知法,明确规定官吏必须“明习法令”,传世的“秦简”中有“凡良吏,明法律令;恶吏,不明法律令”。在官吏带领学读法令的制度下,官吏须率先学习法令,再向普通百姓广为传达,这不仅加速了法令的传播普及,更保证着法令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使法令能在更广的范围中得以贯彻和施行。
建立强制性的法令学读普及制度,亦为后代所沿袭。明初朱元璋制定“大诰”三编,在颁布之初就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加一等”,鼓励百姓学习法令。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又下诏广布“大诰”,“法司只依律与大诰议罪”,并令各级学校讲授大诰,科举考试考大诰,乡民集会宣讲大诰。
要求“以吏为师”,设置法令宣教官员,强化官吏的法律宣教义务。商鞅专门设置负责法令普及的法官法吏“以为天下师”。具体方法为,“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比秦一法官。郡、县、诸侯一受赍来之法令,学并问所谓。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商君书·定分》)此“法官”之设,实际上类似于普遍的建立法律宣教及法律顾问制度。
先秦时代造纸印刷技术尚未出现,法令传播极为困难,刻在铜鼎或竹简上的法令,很难广布于民间,普通百姓大多又不识字,自行学习理解法令几乎不可能。是故,设置专门讲授法令的“法官”,为百姓解释法令、说明法令,才能使他们知晓法令并依法行事。官吏普法又有特定要求,行使普法职责的“法官”自己需要全面、深入的掌握法律法令,当新法律制定后,宣传法令的官吏必须先学习。“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谓也,皆以吏民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即普法要遵循特定的步骤,普法之后,还要考核实际效果,否则要受到惩罚。普通百姓知法、用法,不仅有助于形成尊法、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更能督促官吏依法而行,形成官民互相制约的效果,故商鞅提出,“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只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官吏不敢恣意滥用权力虐民,百姓知道了法令,自己也不敢犯法,最终达到法治的目标。
法家不只要求一般性的普法,更注重通过司法个案的处理普及法令。通过司法审判普及法令,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西周时,召公在处理民间纠纷时,为了方便老百姓打官司,便采取巡行乡邑的办法,到老百姓当中去就地审理,据说这种方法很受老百姓欢迎。召公巡行乡间审判,自然不只是处理某起个案,实际也是一次普法宣传,发挥着宣示法令的作用,帮助周围群众从真实的审判中获得法令知识。提倡“以刑去刑”的商鞅非常重视个案的法令宣示意义,在论述“壹刑”时,特意引用了晋文公的故事:为了让天下百姓都知晓法令,有次晋文公将所有的诸侯大夫召集在侍千宫,颠颉来晚了,官吏请示文公如何处置,文公回答说:“按法律办吧。”执法官于是当场腰斩了颠颉并且示众,这下晋国的百姓都知道了晋国的法令,并且了解了晋文公执法以信的决心。商鞅本人也有类似的例子,他在秦国行法之初,发生太子犯法之事,虽然最终因太子有君主之尊,只是象征性地处罚了其师傅公子虔等人,但是效果仍十分显著,不仅新法令得到了广布,法令之权威也立刻得以树立,“秦人皆趋令”。
通过司法个案审理传播法令的经验,也为后世所沿袭。明清州县对诉讼采取“教谕式的调解”,尽管嵌入了自身基于情理的判断,但“教谕”本身也是通过个案向百姓传播法令的方式。
法家法令广布的现实意义
普法宣传之于现代法治的意义自不必赘言,但检视当代中国普法实际,却又存在着某些缺陷与不足。普通百姓,甚至个别领导干部,对于普法工作敷衍了事,普法的效果难以保证。整个普法工作也较缺乏统筹性、规范性的制度体系,这些问题都制约了普法的实效。回顾法家广布法令的历史经验,虽然带有特定的时代印记,但仍不乏一定的现实价值。
法律的宣传普及需要建立科学完备的制度。宣传法律、学习法律不能作一般性的要求,对法律知识的普及学习应该纳入强制性制度规范,对法律学习的内容、普法的效果与质量,应该作出详细的规定。对不同社会职业群体,或者文化程度不同的公民,应该要求学习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常识;普法学习后,要进行严格的考核,确保法律学习普及的效果,避免普法学习形式化。
法律的宣传普及应该更好发挥“法律人”的作用。这里的“法律人”,不仅是指专门以法律为业的人,还包括肩负着推动国家法治建设责任的法律“担纲者”,即各级政府官员。各级政府官员,首先需要认识到普法、学法之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性,不仅要以身作则了解法律、学习法律,还应该做好法律的宣传普及工作。行政执法官员,特别是基层一线的执法人员,更应该在日常工作中做好宣传法律、解释法律的工作,否则,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官群体作为法律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律宣传普及中具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法官们的普法宣传,不应该止步于法庭,或局限于具体案件的当事人,而需要充分利用巡回审判、下乡调解、诉讼执行等工作时机,将法律知识、法治精神带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而生动鲜活的现实案例,更能让百姓直观地熟悉法律知识、理解法律原理。只有让更多的普通百姓了解法律、熟悉法律,进而提高依法保护权利的意识,增强尊法、守法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才可能产生法治中国的原动力。
(摘自2017年3月17日《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