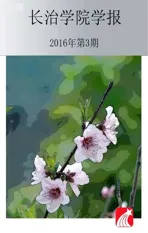顾欢《夷夏论》与宋齐之际的夷夏之争
2016-10-10许栋许敏
许栋,许敏
(1.太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山西太原030600;2.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顾欢《夷夏论》与宋齐之际的夷夏之争
许栋1,许敏2
(1.太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山西太原030600;2.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顾欢所著《夷夏论》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佛教基本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教之间的异同,是佛道之争发展到较高阶段的表现。该《论》出现后,佛道二教学者围绕顾欢所论述的问题,对佛道间的同异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不仅使二教间的差别愈发明了,而且也对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对佛道二教的发展以及中国古代三教合一思想体系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顾欢;《夷夏论》;夷夏之争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在我国内地传播初期,虽然在宗教形式上依附于道家方术,思想上积极吸取儒、道学说中与之相关的内容,极力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但并未因此而同化于儒、道二家,仍保留着自己固有的宗教思想和修行仪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汉译佛经数量的增加以及质量不断提高,人们对佛教认识的逐渐深入,佛教与儒、道之间的差异愈发明显,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了,从而引起了与道教在宗教地位及利益上的一系列争论。其中教义上的优劣、正邪、本末是二者争论的重要内容,而这些理论的争论中,顾欢的《夷夏论》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一、《夷夏论》的主要内容
顾欢,字景怡,一字玄平,吴郡盐官人。曾师从豫章雷次宗,学习玄学、儒学等。后因其母亲亡故,而隐居于剡县之天台山,聚徒讲学,受业者常近百人。晚年“节服食……事黄老道,解阴阳书,为术多效验。”公元483年,顾欢卒,时年六十四岁。顾欢一生,学兼儒、道,虽口不善辩,而著述颇丰,有《黄雀赋》、《三名论》一卷、《夷夏论》两卷等,是一位学术造诣深厚,有着“卓越成就和特色的思想家”。[1]
顾欢所处的时代,佛、道二教在我国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方面,佛教在我国内地经过几百年的传播,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佛教义理也逐渐与儒家思想相结合,更加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需要,在当时的上层建筑中占有着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道教经过寇谦之、陆静修等人的改革,并不断吸收儒家和佛教的思想和仪式,以一种更为成熟的宗教形式出现,越来越与统治阶级的伦理相接近。但是,由于佛、道二教“立教既异”,所以在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二者在教义及宗教利益上产生了种种矛盾。鉴于这一局面,特别是当时佛、道二教信徒经常互争高下的情形,宋明帝泰始三年(公元467年)顾欢著《夷夏论》以“辨是与非”,拉开了宋齐之际佛、道二教之间旷日持久的夷夏之争的帷幕[2]159。
据《隋书·经籍志》等史料记载,《夷夏论》共两卷。但因该《论》现已不存,故本文仅据《南齐书·顾欢传》中的有关记载,对该《论》的主要内容进行简单介绍。《夷夏论》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佛、道二教同源
顾欢在《夷夏论》的开始便提出应该通过分析二教圣典,以“寻二教之源”,来辨别佛、道之间的是与非[3]931。他根据《玄妙内篇》中的相关记载和佛教《法华经》、《无量寿经》、《瑞应本起经》中释迦累劫乃成佛,而在其成佛之前曾“为国师道士、儒林之宗”[4]931的内容。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师道士,无过老、庄,儒林之宗,孰出周、孔”之说,得出“若孔、老非佛,谁则当之”的观点。既然佛、道二教,教主相同,那么它们根本理论也就基本一致了。所以顾欢说:“二经所说,如合符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二教之道同源。
(二)二教之俗各异
顾欢认为佛、道二教之源虽然相同,但在“济天下”、“周万物”的过程中,因二者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出现了“其入不同,其俗必异”的情形。在论述这一问题时,顾欢首先比较了华夷在语言、服饰及礼俗等方面的差异。他说:“端委搢绅,诸华之容;剪发旷衣,群夷之服……教华而华言,化夷而夷语。”[5]931认为夷夏之间,虽所传之道同源,但因地域的不同,二者的习俗也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是难以逾越的。虽然佛、道二教都可以“齐乎达化”,但因夷夏之别,各自适用的范围也有所不同。所以,顾欢认为佛教徒“下弃妻拏,上废宗祀”,“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虽“道固符合矣”但与华夏风俗“大乖”,只有土生土长的道教才是适合华夏之俗的宗教,才是济度华夏民众的舟车。
接着,顾欢进一步对佛、道二教的特点及其与华、夷民众性格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顾欢从佛经和道经,内容的繁、简、博、精及基本教义的幽、显入手,对二教的特点进行了比较。指出虽然佛、道二教“在名则反,在实则合。”但因夷、夏民众在性格上的差异,佛、道适用的范围并不相同。华人之性格“谦弱”、“精”、“明”适合“精”、“显”、“抑”的道教来引导,而佛教“博”、“华”、“引”,为本性“夸强”、“粗”、“昧”的强犷之胡人所崇信,与华夏民族之性格并不相宜。
在该《论》的最后,顾欢以匠人造器来譬喻佛道二教之源同俗异。指出华夏、西戎“器既殊用,教亦异施”,故佛、道有着不同的适用范围,“佛非东华之道”而道则“非西戎之法”,故就华夏之俗而言,道教优于佛教,此即顾欢所谓的“优劣之分”大略在兹之说[6]932。
综上所述,顾欢在《夷夏论》中,虽然标榜同佛道之二法,但实际上是将道教置于佛教之上。而其用来衡量佛、道二教的标准则是我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他认为,土生土长的道教是一种在华夏民族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宗教,在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环境方面,明显优于佛教。而佛教则同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所构筑中国伦理道德及风俗习惯相悖,不适合在中国传播。所以,顾欢的《夷夏论》一出,便受到来自佛教方面的猛烈抨击,引起了当时思想界关于因果报应及形神之争后的又一次大的争论。
二、双方争论的焦点
顾欢的《夷夏论》发表之后,佛教信徒并不示弱,纷纷撰文就佛、道二教的“夷夏”问题同顾欢展开辩论,相关的文章主要收录于《弘明集》及《南齐书》中。据记载,这次辩论的参加者有司徒袁粲等人,他们围绕着佛、道二教的先后、同异、适夏、优劣等问题对顾欢进行了驳斥。
(一)佛、道的先后问题
关于佛、道二教先后的争论由来已久,而这一争论的关键在于是否承认“老子化胡”之说。佛教在传入我国内地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道家而传播的,所以“老子化胡”之说并未引起早期佛教徒的质疑。但魏晋时期,随着汉译佛典的增加及佛教影响的不断扩大,佛教的独立性越来越强,“老子化胡”说也愈来愈多的受到来自佛教徒的批判,成为佛、道二教争论的一个焦点。所以,当顾欢在《夷夏论》中重申“老子化胡”说,并以此为依据认为道教先于佛教而存在的观点提出之后,立即受到明僧绍等人激烈地驳斥。
如明僧绍就从质疑顾欢《夷夏论》中所依佛、道经典的角度出发,对顾欢的道先佛后之说进行了批驳。他指出,传统道家思想主要体现在“老氏二经(即《德经》和《道经》)”中,《庄子·内篇》则是对《道德经》的引申和发挥。老庄学说的基本内容是“得一尽虚”、“不务常变”、“安时处顺”,并无《玄妙内篇》中所讲的“形变之奇”、“入口剖腋”之说[7]37。而且顾欢在引用佛教经典时,也曲解了佛典的内容。并没有真正达到“寻二教之源”的目的,其道先佛后一说之荒谬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佛、道的同异问题
上文提到,佛教刚传入我国之时,为了便于传教,不仅在宗教形式上依附于黄老道术,而且佛经翻译时为了便于国人理解也多用“无为”、“非身”等道家术语,佛、道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魏晋时期,随着佛教的发展佛教独立的要求越来越强,所以当顾欢在二教同源的基础上,提出“道则佛也,佛则道也”的观点时,受到了奉佛者的驳斥。
袁粲针对顾欢之说,提出“孔、老、释迦,其人或同,观方设教,其道必异。”[8]933他认为儒、道以入世为本,而佛教则以出世为宗,二者之意趣不同。而且佛教以涅槃为最终目标,而道教则以仙化为最高境界,二者之追求也有着很大的差异,所以佛、道“符合之唱”,为顾欢的“自由臆说”,与二教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僧人惠通则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对顾欢的佛、道相同之说进行了批判。惠通认为道教中,除《道德经》外,其余经典都为“淆杂并荒谬之说”。他不仅否定“老子化胡说”,而且认为孔、老即为净光童子和迦叶,都是释迦的弟子,为释迦所遣,来华宣德示物,其学说则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做了铺垫。
(三)佛教是否适夏的问题
佛教适夏的问题,也就是佛教是否适于华夏之俗,能否在中国流传的问题。这是当时佛、道二教争论的中心问题。在《夷夏论》中,顾欢认为“佛道二教,虽齐乎达化,”但因夷夏之俗不同,故二者之“道必异,”“佛非东华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鱼鸟异渊,永不相关。”[9]934而奉佛者则认为夷夏之俗并无差异。
袁粲认为佛教的“膝行”、“踞坐”、“绕行”之仪,在中国古代就曾出现过,而非顾欢所说的西戎习俗,所以佛教与华夏之俗并无差异。而且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只有出家人才“服貌必变”,“清信之士”仍“容衣不改”,出家人改变服貌的做法,也只是对道的遵从,并非对西戎习俗的崇尚,不会因此而出现以夷变夏的情形,所以佛教适宜在中国流传。
(四)佛、道二教的优劣问题
宋齐之际,佛、道二教的夷夏之争,最终归结为对佛、道二教之优劣的判定。而顾欢在《夷夏论》中“优老劣释”的态度,也受到了奉佛者的驳斥。
僧人惠通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对二教的优劣进行了比较。惠通在《驳顾道士〈夷夏论〉》一文中,运用老子思想来批判道教的成生不老之说。他用老子“天地所以长久者,以其不自生也,夫忘生者生存,存生者必死”之说,批评道教“断粮以修仙术……服食以祈年长”的行为,与老子“以身为大患”的思想相乖。特别是道教徒“佩紫箓以为妙术”、“士女无分,闺门混乱”的宗教仪式,带有原始巫术的色彩,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相悖。而且东晋以道教为号召的孙恩起义,也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使“墟邑有痛切之悲,路陌有罹苦之怨。”[10]47上而佛家则可以立国安民,有助于维护统治。故佛道之优劣,也就不言而喻了。
综上所述,南朝宋齐之际的夷夏之争,是当时佛、道二教之间的一次大辩论。在这次辩论中,顾欢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为标准,对佛教种种与中华习俗不符的地方进行了批判,而当时奉佛的学者、官员、僧人则从各个角度对顾欢的非难进行了回击。通过这次辩论,人们对佛、道二教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二者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此次夷夏之争以分辨二教之优劣而结束,标志着佛、道二教的夷夏之争重点,已经转移到对佛、道二教是否有利于统治的争论了。
三、此次争论的影响
(一)对佛教的影响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内地后,便面临着如何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由于佛教是一种产生于印度文化中的宗教,其基本教义和宗教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如何缩小这种差异,是佛教在中国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汉魏之际,佛教依附于黄老道术传播,影响较小,所以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并不明显。魏晋南北朝时,随着佛教势力的不断发展,其在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独立性也不断增强,从而引发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激烈争论。但此时的佛教,在中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虽其表现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较大差异,但其内涵因受中国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已基本一致了,故而即使反佛一方也称“佛道实贵,故戒业可遵。”[11]934通过这次争论,不仅使佛、道二教之间的区别更加明显,佛教所独有的特色得以彰显,而且也使佛教徒认识到了佛教在适应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不足之处,为佛教进一步中国化指明了方向。
(二)对道教的影响
道教是我国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中国文化的根柢[12]353,在我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早期道教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巫术,特别是其半军事、半行政的到团组织形式以及力图建立一种政教合一体制的社会构想,与主流政治权力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从而使其成为一种非主流的并与皇权发生过激烈冲突的宗教。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内部已经深刻地认识到,道教如果要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避免同主流文化及官方的冲突,所以寇谦之、陆静修等人对道教进行了不断地改革,不仅逐渐泯灭道教对世俗事务的干预,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越来越靠近士大夫的伦理道德取向。在此背景下,此次夷夏之争中,奉佛者对道教教义、修行方式及组织形式的激烈批判,使道教徒进一步认识到本宗教的不足和缺点,对道教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对社会思想的影响
西汉武帝时,儒家思想在我国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到了东汉末年,儒家经学日趋繁琐,不能提出更高层次的哲学思想来回答时代的课题。所以,当时的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先秦朱子学说,特别是老庄学说,并在老庄学说和儒家思想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玄学,试图从哲学的层面对当时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给以解决的方案,但其实际效果并不明显。玄学的流行却为佛教基本义理与我国传统文化内涵的结合提供了契机。两晋之际,我国流行的佛教般若学与玄学在义理上有较多相近之处,般若学必须借助玄学才可能为当时的士人所接受。而般若学在哲学思辨方面不仅远远高于传统儒学,而且也较玄学更为系统,可以在中国传统的宗法文化体系下,成为儒家学说的有益补充,满足了当时民众多层次的精神需求。因此,玄学与般若学的合流,不仅可以为民众提供安神立命的精神归宿,而且也可以安定社会,立国安民,有利于正常封建秩序的重建。所以,在南北朝时期,以玄学为契机,我国中古时期社会思想文化中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儒、释、道开始逐渐融合在一起,促进了中国社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此背景之下,宋齐之际的夷夏争论中,不仅参加辩论的双方也大都受过儒学和玄学的熏陶,本身就是受到三教融合趋势影响的表现。而且通过这次夷夏之辩,也深化了人们对三教同异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三者之间的融合,对我国中古时期思想文化中儒、释、道三教并重局面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之,通过这次争论,人们不仅对释、道二者间的差异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同一性,不仅为佛、道二教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客观上适应了我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势,推动了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文化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1]李养正.顾欢《夷夏论》与“夷夏”之辩述论[J].宗教学研究,1998,(3):5-10.
[2]刘立夫.弘道与明教——《弘明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4][5][6][8][9][11](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7][10](日)大正藏:第52册[M].石家庄:河北佛教协会印,2005.
[12]鲁迅.鲁迅全集:第11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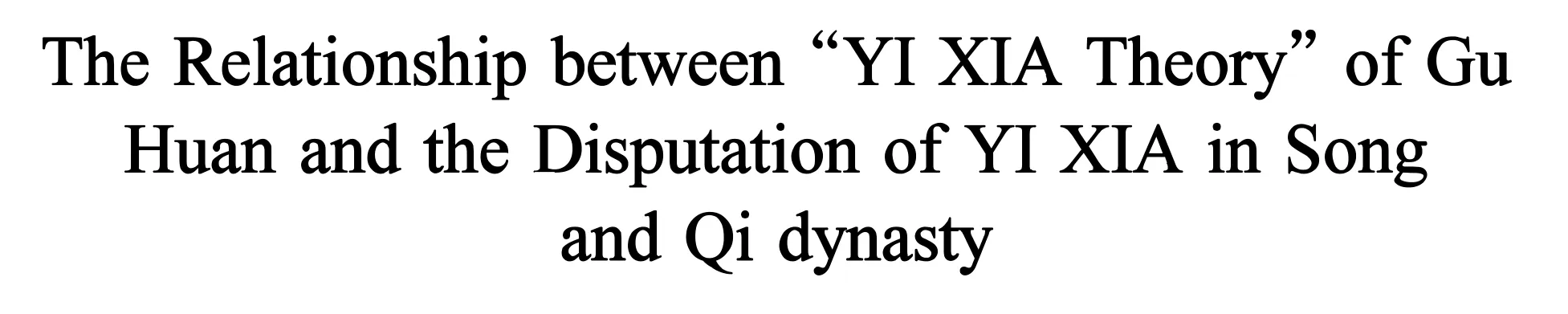
(责任编辑王建华)
Xu Dong1,Xu Min2
(1.College of Art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aiyuan Shanxi 030600;2.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GanSu 730000)
K204
A
1673-2014(2016)03-0031-04
2014年度山西省留学回国人员科研资助项目(2014—068)。
2016—03—17
许栋(1982—),男,山西大同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佛教史研究;许敏(1984—),女,山西大同人,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考古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