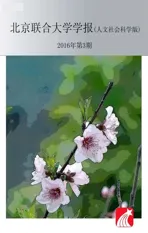文化认同与京派文化的审美张力
2016-05-30李春雨
李春雨
[摘要]京派经典性的代表作家,几乎都是外乡人。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废名笔下的“竹林”,都距北京很远,最多像周作人那样,作为一个外乡人写几篇小文,谈谈“北京的茶食”之类。这些人之所以走到一起,之所以叫“京派”,并不是他们对北京地域性的认同,而是一种更为宽泛、更为开阔的超越北京地域特性的文化认同。对京派文学来说,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历史文脉的认同;二是精神谱系的认同;三是审美追求的认同。对京派文化认同的理解,是认识京派本质内涵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文化认同;京派文学;审美张力
[中图分类号]I209.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6)03-0081-07
近年来对京派文学的研究,依然较多地集中在京派作家的文学风格与文学情趣方面,尤其是集中在对废名与沈从文等人的研究上,而对于京派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特别是在文化的大背景下,京派作家究竟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还缺乏更加充分的研究。关于京派的形成,文学史家们从1920年代早期的新月派作家到1930年代北平的大学教授作家群,再从北平与天津等地的文学编辑与文化人等,有过比较细致清晰的梳理。但是如上所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不同时期的这群作家,能形成一个文学流派?而且这些来自于完全不同地域的作家们何以被称之为“京派”作家?本文认为,文化认同是京派作家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所谓文化认同,对于京派文学来说,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是在京派文学的形成过程中,它起到一种凝聚力的作用;二是它对京派文学的审美特性构成一种特殊的张力,使这个流派既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又有很大的弹性和容量。可以说,文化认同是京派文学得以形成、发展并产生长远影响的重要因素。而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目前还很欠缺。加强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探究京派文学的特质,尤其是探讨京派文学的地域性和超地域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化是复杂的存在,文化认同也是复杂的形态。文化认同不是单向度的你认同我或我认同你,而是双向度乃至多向度的。正是在多种文化的互融互动过程中,达到某种和谐,形成某种共同的趋向。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文学,当以1930年代京、津等地的作家和文化人为主体,他们的文学思想、文学创作乃至审美追求,最大的特点就是与“京”的关系不同寻常。沈从文、林徽因、朱光潜、废名这几位京派的经典性代表作家,尤其是所谓京派的领袖人物周作人,没有一个是北京人,也没有一个人的主要代表作是写北京的。对于北京来说,他们全部都是外乡人。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废名笔下的“竹林”,都距北京很远,最多像周作人那样,作为一个外乡人写几篇小文,谈谈“北京的茶食”之类。既然如此,他们何以叫“京派”呢?也就是说这些人走到一起,并不是对北京地域性的认同,而是一种更为宽泛、更为开阔的超越北京地域特性的文化认同。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认同呢?使京派作家得以成为一个流派的所谓文化认同又特指什么呢?对京派文学来说,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历史文脉的认同;二是精神谱系的认同;三是审美追求的认同。
一、历史文脉的认同与京派文学的形成
历史文脉在相当程度上与地缘文化有关,比如当下热议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自古以来燕赵文化的刚柔并济成为了这块土地的文化特色;从历史上看,燕赵大地具有多种民族长期杂糅、共同生活的特点,这又构成了这块土地包容大度的文化气象;而近现代以来,京津冀又长期处于同一个行政区划,三地的社会发展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有着深厚悠久的文化基因,历史文脉是京津冀一体化的先天优势。对于京派文学来说,历史文脉的认同就比较复杂。京派作家分别来自于不同的地域,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基因与背景,而且浙江(周作人)、安徽(朱光潜)、湖南湘西(沈从文)、湖北(废名)、福建(林徽因)、山西(李健吾)等地的文化特色是非常鲜明独特的。但是,当这些人都聚集到京津大地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京津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虽然笔者强调,京派文学与是不是北京作家,是不是写北京的人和事,作品是不是具有北京风味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这并不是说京派作家就完全不受京津文化的影响。过于注重京派作家与京津的关系是偏颇的,尤其是以“京津”划线是不符合京派文学的性质的,而完全不考虑京派作家与京津的文化关系也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京津文化对京派作家的创作,对京派文学的形成,都是有着重要的不可忽略的作用和影响的。沈从文的《边城》写的是湘西边地的人情人性,但这与京城古老文化的对比映照是分不开的,京津(也包括南京、上海,还有青岛)等现代大都市的文化显然深深地刺激了沈从文对文明与文化的反思,长期郁积在沈从文心中的湘西生活,在京津等地得到了发酵与激活,这才有了他对湘西的赞美(有时显然是理想化的),同样也有了他对湘西的批判。可以说,“京城”是“边城”的文化参照,没有“京城”就没有“边城”。废名也是如此,他那些写湖北老家的“竹林”里的“三姑娘”的故事,“菱荡”里的故事,“桃园”里的故事,是那么清纯,那么感人,又那么令人神伤,宛如一幅幅质朴古老的传统山水画。而这些画里所承载的厚重,所透露出的叹息,远远不只是作家故乡的那些人和事了。它们有一种绵长的穿越时空的历史感,他们使人在作家故乡的故事里品出了整个古老民族的种种韵味,这里毫无疑问地浸润着废名在北京所接受的文化体验。周作人是喜欢写家乡的作家,只是他的故乡不止一个,浙东、南京、北京、东京都是故乡。惟其如此,他叙写故乡的文字渗透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信息。他写北京,人们常常被牵引到他的故乡;他写故乡,又往往从北京起笔。在周作人的笔下,已经分不出哪里是故乡,哪里是京城,哪里是本土,哪里是异国,这就是文化的融合与交汇。从周作人本身来讲,虽然学问很大,文气很足,但从浙东文化的底蕴来说,终究感到其格局有限,而北京带给周作人的是万千气象,在京城,周作人终于成为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杂家大师。在北京再久,也改不了周作人那令人难以听懂的浙东口音,而北京给予周作人的胸怀和眼光,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都读懂了。
在此,不能不说到京派文学的理论家朱光潜。朱光潜一生,除了在美学阐释方面的重要贡献之外,还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京派文学的理论家,他在京派的发展过程中提出了“静穆”的文学理念,而这一理念的重要性,至今也还远未被学界高度重视。从五四新文学以来,批判社会、关注人生的现实意义大潮风起云涌,高扬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思潮也曾一石激起千层浪,现代主义无论是理论还是手法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许多作家的青睐,受到读者的追捧,而“静穆”一直静静地躺在历史的深处。其实,“静穆”既是一种文学的涵养,又是一种文学的姿态,它完全可以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并存。事实上,中国现代作家及文人有相当一部分(或在他们人生与创作的某一阶段),是认同“静穆”理念的,是表现出“静穆”的涵养和姿态的。更重要的事实是,“静穆”的理念不可能在五四新文学兴起之时的北京产生,也没有在1930年代前后左翼文学与海派文学兴盛的上海产生,而是也只能是在1930年已经开始沉寂和安静下来,并已回归于历史文化古都的北平出现,在北平为中心的京派文学中出现,这本身就印证着京城古都文化的特有内涵和影响力。“静穆”从理念到涵养,再到姿态,都深深浸润着古都北平特有的历史文脉。
二、精神谱系的认同与京派文学的审美基础
精神谱系的认同是一个流派思想体系的基础和文化结构的支撑。京派文学正式形成于1930年代的北平,此时的北平已不再是新文化新文学的中心,已经从五四时期的高昂激越归于平和淡定,此时北平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传统文化与大学教育。可以说,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心的转移,在客观上既淡化了北平曾经一时的辉煌,又给了北平这座古老文化名城一个沉静下来的反思的机会。对于传统文化的崇尚就是对前一时期五四反传统的反省,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京派的作家和文人们与五四的激情拉开的理智的距离,对新文学与新文化的发展和建设也有了新的思考和表达。依然是注重写实的,但多了些诗意和婉转;依旧是批判社会的,但多了些冷静和哀婉。而大学教育与大学文化,原本就是京城特有的底蕴,1930年代的北平突然“空”了下来,“静”了下来,大学的价值和意义,一下子凸显出来,而这一点无疑更加重了京派文学的理性色彩,使京派文学这群新文学作家得天独厚地拥有了与传统文化精神对接的可能和机会。
先从传统文化的层面来讲,京派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仁爱之心,或者讲人道主义有一种普遍的认同和深刻的理解,并且通过仁爱之心和人道主义,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对接起来。沈从文以《边城》为代表的小说创作当然是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但近年来,许多人注意到沈从文创作中的“反现代性”,人们在沈从文的作品里充分感受到一种古典美,感受到那种多少年来贯穿在中国文脉中的仁爱之心和人道主义情怀。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的人情美、人性美,并不只是属于当时的1930年代,它更属于历史与传统,因而也更属于未来。不要把沈从文的《边城》等作品中没有写阶级对立和没有突出阶级关系简单地解释为他对阶级斗争反感或故意淡化,《边城》更重要的意义其实是在于,他通过对湘西世界人情人性的书写,强烈地执着地表达一种自古有之的深深根植于民族传统中的淳朴美好的人情人性、仁爱之心和人道之情,而它们已在中国的大地上滋生了几千年。五四文学革命也好,左翼文学革命也好,京派也好,海派也好,这个论争那个论争也好,都不会使中国传统的仁爱之心和人道之情失去力量。仁爱与人道从历史到当下,从传统到现代,其价值不减,其魅力不衰。翠翠、老船夫、大佬二佬,甚至船总,都不失仁爱之心与人道之情。还有《丈夫》里的妻子与丈夫,还有《萧萧》里的萧萧和她的家人,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性情,但仁爱之心和人道之情都是一样的。甚至在沈从文笔下,连复仇都被消解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有仇不报非君子,这是中国多少年来的老话,但沈从文让复仇变成了没有意义的事情,沈从文的这种情怀不仅体现在他自己的创作中,还影响到他的学生辈的汪曾祺等人的作品中,在汪曾祺1940年代以后的创作中,连复仇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事情。同样,汪曾祺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仁爱之心能够建立善,也能消除恶,这或许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了不起的地方。沈从文的湘西抒写,没有突出阶级矛盾,没有直接表现阶级关系,在一些人看来,是远离了当时的时代本质,是用理想遮掩了社会的真实。但从更开阔的视野去看,沈从文描写和呼唤着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价值,这不是更大的、更重要的本质与真实吗?从这一点来看,沈从文的“反现代性”才是最大的现代性。
废名也是如此,在传统与现代的对接方面,他甚至比沈从文走得更远。废名作品的诗化程度普遍超过沈从文,是诗中的诗,是唐人绝句。废名作品中远离社会现实的气象,显然是作家的一种自觉的追求,在《竹林的故事》《桃园》《菱荡》《浣衣母》等经典作品中,不仅情节内容与1930年代文学主潮所表现的气象相去甚远,甚至连写作手法都直接呈现出中国传统的表现形式:意境大于情节,景物重于人物,犹如一幅幅山水泼墨画,平淡清雅,含蓄凝重。尽管如此,废名的作品真正动人心弦的并不是这些传统的手法,而是处处跳动一颗质朴纯真的心,处处表现着一种超越蝇头利害的大爱。在《竹林的故事》里,人们都喜欢三姑娘什么?三姑娘又给了人们些什么?三姑娘无非在卖菜时常常不经意间多抓几颗菜给顾客而已,人们喜欢的就是三姑娘身上的这点清纯,最重要的是这种清纯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这些大都市里,都已经很难见到了,所以废名把三姑娘的故事安排在竹林里,所以是废名故意让读者把三姑娘的品行与竹子的品行联系在一起。三姑娘的清纯与爱心本没有多少故事可写,但仅仅这一点就已经够了,三姑娘与竹林的故事,与其说是一篇现代文学的小说,不如说是一篇传统文化的寓言!《菱荡》也是一篇时常引发争议的作品,人们争议的焦点不仅在于这篇小说已经简单到没有情节,没有冲突,甚至连人物也没有了,人们曾经认真指责过这篇小说把所有的人物关系都淡化了,那个在小说里多写了几笔的陈聋子与他的雇主之间不是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吗?怎么一点儿矛盾都没有?反而写得那么随意自如,甚至是那么和谐!我认为,与沈从文相似,废名不会用这篇小说来对抗阶级斗争的现实图景,也不至于用这篇小说来表达他对轰轰烈烈的左翼文学的不满。那么它为什么这样写呢?问题的根本在于废名有自己的文化认同,在废名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道之情、仁爱之心、和谐之美,在任何历史时代都是值得赞颂的,这是一个民族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正确态度,也是一个作家写作的应有之义。不能说在同一个历史阶段,所有的作家作品都必须发出同样的一种声音,如果那样就没有风格流派,也就没有文学创作了。废名的小说《桃园》里那个可怜的病孩子阿毛,她临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吃一个桃子,而当时不是出产桃子的季节,即使是种桃子的父亲也无可奈何,只能买了一只玻璃桃子,回来的路上还打碎了,当然,父亲的心也跟着碎了!这个凄惨的故事写在1930年代有什么意义呢?是表现底层劳动者命运的悲苦?是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与腐朽?都可以说是吧!但似乎又总觉得不那么贴切,总觉得扯得远了点儿。其实《桃园》故事的核心应该是爱吧,是无可奈何的父爱!爱有欢乐的时候,也有悲伤的时候,欢乐时的爱,人们更多地看到了欢乐,而悲伤时候的爱,人们也更多地看到了悲伤。尽管是悲伤,但那也是爱,而且是更真挚、更深沉,也是更伟大的爱!爱在什么时候讲合适?什么时候讲不合适?是用欢乐来讲好,还是用悲伤来讲更好呢?正如沈从文1930年代在他的湘西世界里讲了一连串的爱和美的故事一样,废名也在1930年代写下了一系列经典的爱和美的故事,不仅这点相同,更重要的是他们同为京派作家,他们的作品同为京派文学的经典之作,在他们的作品里共同表现出了对传统文化仁爱之心、人性之美的追求,并以此表达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阐释,这不仅是他们自己的独特之处,也是整个京派文学的独特之处。
再从大学文化的层面来看,京派作家与高等学府的密切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这个作家群体的文学立场和文学姿态。一方面,体现在京派作家重理性而相对轻情感的文学理念上。所谓的重理性并非没有或不要情感,而更多是一种表达方式的问题。比如周作人的文字很少直抒胸臆,很少浓墨重彩地表现情感方面的东西,他的《爱罗先珂君》,整篇都是平静的叙述,平静得像诉说一个跟自己没有多大关系的人的事情。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爱罗先珂的牵挂和思念,否则就不需要写这篇文章了。但从字里行间真的很少看到周作人的心绪的起伏。这种情况在周作人的笔下是常有的、普遍的,他的《故乡的野菜》《苦雨》《死法》《乌篷船》等等,莫不如此。所以有的文学史家用“淡笔写淡情”来概括周作人的文风,其实不然,周作人的文风是“淡笔写浓情”。笔是淡的,情是浓的,但在写的时候,把浓情冲淡了。周作人的这种理性的姿态对京派其他作家的影响很深很大,朱光潜就是其一。1930年代的中期,文坛上出现了一场巴金与朱光潜两人的笔战。事情主要由朱光潜对1936年曹禺发表的《日出》提出的批评引发的。朱光潜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舍不得分手》,批评《日出》第三幕写得不紧凑,与全剧关系不紧,似可不要。其实这是许多一般读者的共同感觉,甚至有的导演在排演《日出》时从舞台实际效果出发,就真的去掉了第三幕。然而曹禺对此很不买账,他已经遭遇过《雷雨》在演出时被去掉“序幕”和“尾声”的情形,曹禺认为那是砍头去尾,使《雷雨》只剩下了一个直挺挺的躯干,而这次又有人出来指责《日出》的第三幕,并被导演又砍掉了这一幕,曹禺痛彻地认为这次简直是把《日出》的心脏都挖掉了!说实话,曹禺的不满确有自己的理由。他的匠心,对《雷雨》来说是在“序幕”和“尾声”,而对《日出》来说恰恰在第三幕。关于这一点,在此不必赘述。而巴金不同,巴金是曹禺的好友,出于感情更出于自己的文学理念,巴金在《大公报》(1937年1月1日)上撰文热情赞美曹禺的剧作。他说:“我喜欢《雷雨》,《雷雨》使我流过四次泪,从没有一本戏会这样地把我感动过。”平心而论,巴金的这种评价太过于个人的主观情感,而明显缺乏应有的理性分析。对此,朱光潜无法沉默,他写下《眼泪文学》一文,针锋相对、毫不客气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文学的最高恩惠是否就是眼泪?叫人流泪的多寡是否是衡量文学价值的靠得住的标准?对于这些问题,我却很怀疑。”[1]朱光潜的话竟然引起了巴金对朱光潜一通劈头盖脸的谩骂,甚至是人身攻击。当然,朱光潜也是一通回敬。随即多位作家(主要是左翼作家如张天翼、巴人、唐弢等)对朱光潜又是一通轮番批判。而朱光潜则回归“静穆”,没有再做回应。这件事情从表面到内里其实不用多加分析,比如不用多说巴金虽然成名较早,但他的文学成就一直受到多方面的批评,批评巴金的人包括老舍,还有后来又支持巴金的巴人等;也不用说巴金受到过鲁迅的称赞,又因此多了不少底气,等等。事情本身的评判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朱光潜对巴金的质疑是正确的!岂止是朱光潜,任何明眼人都看得明明白白的,就是曾经称赞过巴金的鲁迅先生,在他自己早先写过的一篇文章《反对“含泪”的批评家》[2](1922年)中曾清楚地写道:“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如果鲁迅的话是对的,那么朱光潜的话错在哪里呢?我在这里强调的是朱光潜这种理性的而非感性的文学批评的态度,是京派作家的一种基本倾向,朱光潜与巴金此前此后都没有个人恩怨,他是从自己以及自己这个流派的文学立场出发来“多管闲事”的。
在这场笔战中倒是有一个细节是值得留意一下的,这就是在巴金最初在《大公报》上赞美曹禺剧作的时候,写文章的不止巴金一人,还有茅盾和沈从文等人。茅盾姑且不说,而沈从文是京派作家,与朱光潜是一派的。这里就引发出两个问题:一是朱光潜对谁赞美曹禺并没有意见(包括沈从文在内),但对巴金以“四次流泪”来表达对曹禺的赞美不能苟同;二是与此相关,这恰恰说明京派是松散的,并没有动辄“统一行动”的“组织纪律性”,是和而不同的。
而另一方面,京派作家的文学姿态还体现在重学理、重知识的学者式的写作方式上。周作人作为京派的首要代表作家,在相当程度上显示出京派文学的这一特点。周作人是学界公认的“文抄公”,他的绝大多数散文,无论是充满雅趣的小品文或是“凌厉”的杂文,以及那些学术性更强一些的文字,都是由“知识”与“情趣”这两个要素构成,而“知识性”往往排在前面,因为周氏的文章中首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东西就是“知识”,那些人文科技,社会历史,花鸟鱼虫,饮食茶饭,上下五千年,中外千万里,那些你闻所未闻,你知其一二不知其三四的东西,占据了周氏散文的主要内容。因此,用“开卷有益”赞誉周氏的散文,既是一种贴切的形容,也是一种极高的评价。这种知识性本是学者式散文写作的应有之义,但“知识性”不是文学的普遍的和必备的要素,文学不是教科书,“知识性”是少数作家的个性特点,而达到周作人这样的近乎“知识癖”的作家少而又少。当然,不是谁都具有这些动辄让人开卷有益的知识的。更重要的是,周作人能让这些知识入情入趣,在情与理之间达到一种和谐和默契。他的《死法》《苦雨》《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与《乌篷船》,无一不是让人开卷有益的,无论是讽刺批判,还是脉脉含情,都离不开学者式散文的那股“理趣”和“雅致”。这是周作人文字的特点,也是京派作家文字的特点,同时也是京派“不合大众”的地方。
这种学者式的理性,不能不结合到周作人的杂学来谈。周作人堪称现代文化名人中的“杂家”,“杂人”极多,而成为“杂家”的人极少。周作人的读书是少有人能与之相比的,中国古今新旧之书不说,有材料记载,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两个中国人,分别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用外文阅读原文书1000多本,平均一天一本多,其中一个就是周作人(另一人为郁达夫)。这种饱览天下之书的容量,沉醉无尽学海的气度,构成了周作人文风之“驳杂”。而这一点又往往使人联想起学界对鲁迅杂文的评价,鲁迅的小说以及《野草》《朝花夕拾》没有问题,但鲁迅杂文究竟有多大的“文学性”,却始终是学界探讨的一个问题。其实,鲁迅杂文与周作人小品文在写作方式上是有相通之处的:都是天上地下,杂七杂八,信手拈来,这就呈现出一种所谓“非纯文学”的表达方式,而这种“非纯文学”的表达方式,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学最普遍、最重要、最独特的一种基本方式。所谓“纯文学”的表达方式,从来不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形态。从这个角度来看,周作人及京派诸作家的写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谱系有一种深层次的认同与契合的。
三、文化品格的认同与京派文学的审美张力
由于历史文化的认同与精神谱系的认同,奠定了京派作家的文化品格,并进而形成了京派文学特有的审美张力。那么,京派作家在文化品格上的认同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是从容大度、淡定平和的气质。京派作家与其早先的流脉之一的新月社不同,与语丝作家群不同,也与海派作家不同,它不专注于某种文体和某种理论上的追求,它没有统一的腔调,是很松散的,组织形式松散,创作内容也很松散,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论及翻译等等,什么都有。而且各位作家的文学主张,审美情趣,以及文章风格,都不尽相同。那么,是什么东西把这样的一盘散沙汇集凝聚在一起,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风格流派的呢?应该说,这主要是一种内在的气质,但这种气质并不是作家每个人的独异个姓,而相反,是一种与北京大文化特征相通的共同的气质,它集中体现在雍容大度、古朴典雅、平和淡定等方面。还是先说周作人,他的文字,无论是优雅有趣的小品,还是枯燥刻板的读书抄,无论是五四时期“浮躁凌厉”的文章,还是“闭户读书”的文字,尽管内容不同,形式不一,但都透出一股从容大气,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很个人的、很私密的文字,也是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大的情怀和大的格局。周作人以下,无论从沈从文到废名,从李健吾到朱光潜,还是从林徽因到萧乾等等,很少在他们的文字里看到仅仅只属于自我的小天地,沈从文为什么能“从边城走向世界”呢?为什么大家闺秀的林徽因去写《九十九度中》呢?至于萧乾后来走向世界大战的战场,在世界战争的背景下写出《血肉筑成的滇缅路》,同样是毫不奇怪的,多元大气的文化格调,淡定从容的文化姿态,构成了京派作家共同的底蕴。无论写什么,无论在哪里写,都可以看到京派作家的相通的文化气象。
二是淡淡的乡愁以及蕴含其中的怀古情调。不管来自东西南北,也不管来自城镇还是乡村,京派作家有一个共同的趋向,就是都表现出一种怀古的情调,而这一情调又与他们笔下的乡愁密切相连,尤其突出的现象是,这种情调和乡愁又都与他们的“京城情结”有关。周作人在京城写下的许多文学,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家乡的怀念。最经典的依然是《故乡的野菜》和《乌篷船》等。沈从文在京城写下的《边城》就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写故乡往往是在与故乡拉开了时空距离之后,这本是人之常情,周作人、沈从文的作品也印证了这一点。但作为一个流派来说,他们的“乡”不仅仅是自己的故乡,他们的“愁”也不仅仅是对家乡或乡土的思念,在他们的“乡愁”书写中,更为重要的是流露出一种与所谓的文明都市,即与“京城”相对的广泛的“乡愁”,并进而延伸为一种幽幽的怀古情调。周作人在北京写下的那些怀念故乡的文字,不仅让人感受到作者对家乡风物民情和童年生活的深刻记忆,更让人体悟到作者所要表达的那种超越个人怀乡的人类共同的情思,而这是一种悠远的、永恒的,乃至人类固有的人情人性。周作人的许多文章都有一种幽深的怀古情调,这里的“古”,不只是古代、古典,而更是一种远古、悠久,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性情,这特别契合京城文化的大气与幽深。沈从文在京城发出他对故土边城的美好赞叹,其实《边城》的深刻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他在京城文化的发展中,深切感受到家乡边城那些古朴美好的,带有一去不返的原始人性的难得与可贵。还有他的《长河》,更是对远古纯美人性的无可挽回的逝去,表达了自己的怅然所失之痛。废名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让人很难分清他写的是现实还是梦境,是现代还是古典。他的作品从内容到笔法,可以说是京派作家古典美的突出代表。废名所写的故事也都是自己家乡的人情世故,但细细读来,好像故事里的家乡被作者抽掉了,留下的是广阔的时空,是能让所有读者触景生情的地方,是让所有人都能被感动的人和事。这些就是京派作家的独有魅力,写自我的而又超越自我,写家乡而又超越家乡,写具体的人和事而又超越这些人和事。
三是抒情与批判的平衡。京派作家是抒情的,也是赞美的。尽管他们抒情的笔触很轻,笔法很淡,但那些古朴清香的自然风光,那些纯净美好的人间情趣,甚至那些充满理想色彩和想象意味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在他们的作品中是比较集中而鲜明地呈现出来的。在周作人的笔下,人们从哪个角度都能读到一丝同情,一份理解;在沈从文笔下,人们怎么也摆脱不了那种缠绕着你的人情的暖意和人性的光彩;在废名笔下,人们甚至能够感受到那种超越时空的对美好情景的向往,感受到他是在作品中的人与读者的心中建构一座心灵相通的桥;林徽因和凌叔华笔下,分别呈现出一种古典中的现代美和现代中的古典美……
然而京派作家又是批判的,他们批判社会,批判人类自身,包括深刻反省作家自己。周作人的文字,从内容到语言风格,都透出一股冷峻,即使他写故乡、写北京日常生活的那些被称之为“美文”的作品,也都充满了反思的意味,至少是甜美与苦涩参半。沈从文在对湘西世界美好不再的惋惜中,十分鲜明地表达了对所谓都市文明的批判,他的《丈夫》《萧萧》等作品,不可能是单纯地写妓女及其丈夫是多么具有人性的美,也不可能单纯地是告诉读者童养媳也有蛮不错的命运,尽管这些都发生在湘西这个特殊地域,人们还是强烈地感受到,沈从文实际上是在这些描写背后,赋予了一种独特的针对性,他是把自己家乡的那些美好当做了对当时“都市文明”的抵抗和反思,相对以金钱势力为中心的都市社会,相对都市社会里的那种虚伪乃至虚假的人际关系,还是家乡那些古朴甚至比较荒蛮的人情人性要好得多。至于废名的作品,更使人有一种不合时宜的、远离当时社会的感觉,但这种“远离”,不正是一种以回避的方式来批判现实的吗?我们说京派作家有一种古典的美,有一种抒情的笔触,有一种“远离”现实社会的情调,但这一切并不是去逃离,并不是去刻意返古,而恰恰是在抒情与批判的平衡中,寻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创作基调——和谐。与京派作家关系密切的,有着传承之谊的汪曾祺说过:“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3]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京派作家和谐风格的很好说明。
四是沉郁静穆的整体气象。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充分展示了多姿多彩的文学态度,有金刚怒目的,有激情澎湃的,有清雅文静的等等,也还有一种姿态,那就是集中体现在京派作家身上的沉郁静穆的风格。
所谓沉郁静穆,对京派作家来说,不是指一两个人的创作风格,而是一种总体气象,是一种由内而外全方位呈现出来的整体气质:它既安静沉稳,底蕴深厚,而又敏锐多思;看是轻松闲适,却又严肃持重。从周作人、俞平伯、废名、钟敬文、沈从文、李健吾、林徽因、朱光潜,直到后来的汪曾祺等人,无不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沉郁静穆这样一种气象和特质。他们不同文体的写作,从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到文论,也都从各个侧面共同显示出老成持重、与众不同的文风。京派作家明显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群体,所谓学者型的作家,或作家型的学者,这一群体特定的身份是他们共同文风与特质的基础。京派作家论“个”来说,人人都有鲜明强烈的个性,但“融入”京派这个整体,他们各自身上的个性都自觉不自觉地显现为对京派共性特征的趋同。仅以废名为例,从单个作家来看,废名是极有个性,也极为特殊的。他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有的真正痴迷于宗教文化的作家,他对禅宗的体悟之深,使他的作品与众不同。他是最早写作所谓现代主义诗歌的诗人,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写下的那些诗作,远比后来30年代的那些现代派诗人写的现代主义诗歌还要现代,还要象征,还要抽象,还要朦胧。他的那些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也充满了奇异的景象,似“唐人绝句”,又似现代极品。但从整个京派作家的角度来考察,废名的所有独异的个性,又都与京派作家的共同审美趋向融合得非常好。他的诗化小说很能代表京派作家的田园牧歌式的情调,他的充满禅宗意味的诗作,也很能体现京派作家沉思冥想的特点,尤其是无论他的诗还是小说,都是京派作家沉郁静穆风格的经典体现,他的笔触随意而又凝重,他写的那些故事,清新淡雅,没有热闹,没有喧嚣,整个《竹林的故事》安静得似乎一根针落在地上都能听到,但你读完以后,心里却不能安静,更不能轻松,你必须为主人公的命运担忧,你不得不在主人公甜美质朴的性格里,感受到更多的哪怕是淡淡的哀伤。那些平静的描述,恬淡的言语,优美的情景和形象,在给读者极大的审美愉悦的同时,也把读者拉向沉思的境地,这是静穆的魅力,这是废名独特的魅力,也是整个京派作家共同的魅力。
[参考文献]
[1]朱光潜:《眼泪文学》,《大众知识》1937年第1卷第7期。
[2]鲁迅:《反对“含泪”的批评家》,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4页。
[3]汪曾祺:《汪曾祺作品自选集·自序》,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责任编辑 刘永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