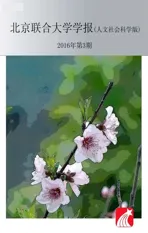论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的法律规制
2016-05-30王美舒
王美舒
[摘要]在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环境标准的制定主要是政策选择而非科学活动。我国由于忽视环境标准制定背后的利益博弈,忽略对博弈过程进行规制,造成环境标准制定中的乱象。根据风险社会理论,考虑我国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中的现状,我国在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进路上应选择优先适用“基于风险”进路、“成本—收益分析”进路,最后适用“基于技术”进路的倒三角模式。在风险沟通模式上,应综合运用听证会模式和共识会议模式。在立法形式选择上,我国应在《重金属污染防治条例》中设专章对重金属污染防治标准制定的进路、风险沟通进行规定。
[关键词]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风险社会
[中图分类号]D922.68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6)03-0064-09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我国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据环保部统计,自2005年起,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共发生特大重金属污染、中毒事件50多起,引发各类群体性事件近100余起,致使9054人血铅超标,1835人镉超标。其中,广西等三省的镉米事件,湖南、陕西等六省儿童血铅含量超标事件均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诸多重金属污染事件中,引起笔者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不少涉污企业虽达标排放,却依然引起所在地污染物总量超标,或周边居民体内重金属超过健康标准。此类现象中的典型,是发生在陕西省凤翔县的铅污染事件。2009年8月,陕西省凤翔县发生铅污染事件,当地政府公布的检测结果显示,在731名受检儿童中,有615名血铅超标。但环保部门随之提供的监测数据却显示,涉污企业东岭冶炼的废水、废气、固废水淬渣的排放均符合国家标准,该公司所在地的地下水、周边土壤和地表水铅浓度等,也均符合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为何在有环境标准且排污企业达标排放的情况下,仍会出现周围生态环境污染物浓度超标或者使当地人健康受严重威胁的情况?笔者将目光投向了重金属污染防治中的环境标准制定环节。
环境标准是 “国家为了防治环境污染、保证环境质量、维护生态平衡、保护人群健康,在综合考虑国内自然环境特征、社会经济条件和现有科学技术的基础上,规定环境中污染物的允许含量和污染源排放物的数量、浓度、时间和速率及其他有关的技术规范”。[1]与环境基准不同,环境标准并非是纯粹科学研究结果的等值,而是有权制定机关权衡多方利益,在客观的科学研究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后得出的结果。[2]在制定环境标准过程中,有权机关除了需考虑专家通过科学研究确定的环境基准,还需考虑环境标准可能带来的治理成本、产业影响。同时,公众以及相关产业从业者的意见也会影响到环境标准的制定。
但在我国,立法机关忽视了环境标准制定背后的利益博弈,并因此忽略对这一利益博弈过程进行必要的规制,造成环境标准制定中的乱象,致使标准制定过程中理念不清,思路混乱,风险沟通不足,各标准设定目的之间相互矛盾,环境保护与人体健康保护的双重目标无法兼顾。加之重金属污染具有累积性、富集性、难降解性等特点,相关环境标准的制定不是仅仅提出“以人类健康为中心”等理念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对其制定思路、制定过程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规制。为此,笔者选择风险社会理论这一视角,对重金属污染中环境标准制定问题进行探讨。
二、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环境标准及其制定
在风险社会理论中,环境标准有三个层次的意义。在最为抽象的层面,环境标准是人们在治理环境风险过程中,对环境风险现实性和建构性进行协调的产物。环境标准一方面体现了环境风险对现实环境可能造成的危害,即科学研究对环境风险的客观描述(风险的现实性);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人们对环境风险的认知和接受程度(风险的建构性)。贝克曾这样描述环境标准:“这一界线如同门槛,是必须被人们所忍耐和接受的;而界线以外则是危险状态,一定会对人类造成巨大伤害,是不应被人类所忍耐和接受的,因此也必须采取措施来防止这些物质所带来的危害越过这一界线,从而进入危险状态。”[3]从这一描述可以看到,环境标准的制定一方面遵从了风险的现实性——即所有风险都是现实存在的,但在界线之内,风险是人们必须接受的,甚至是可以被忽视的;另一方面环境标准还体现了风险的建构性——即在这一界线之外的风险,它的客观存在已经被人们所普遍认识到,也无法被人们继续忍受。在中观层面,环境标准是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介入的时点,也是政府进行环境风险规制的界限。面对环境风险时,政府一方面要认识到风险的现实性,进行风险评估,凭借科学技术判断风险存在与否及其大小。另一方面,政府还要认识到风险的建构性,及时进行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了解公众对风险的感知程度。政府既不能忽视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和感受,增加环境风险演变成社会风险的可能性;也不能因公众的主观臆想而随意对环境风险进行规制,影响科学技术发展和市场经济自由。此时,环境标准就“形同界定出国家管制介入之时点”。[4]在微观层面,环境标准体现了风险治理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博弈结果。风险现实性与建构性的二重特性,决定了政府、公众、市场、专家等多方博弈会贯穿环境标准制定的始终。因此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而非科学,决定了如何制定环境标准。”[5]而美国最高法院也曾在Indus. Union Dept v. Am. Petroleum Inst.案中指出,环境标准的制定主要是政策选择而非科学活动。[6]
在风险社会的视域中,环境标准的制定大致是这样一种情形,制定机关首先对环境问题进行分析,针对这些问题,归纳治理措施。在对治理措施进行评估后,基于科学证据和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来对制定中的环境标准进行衡量,做出适宜的选择,颁布环境标准。随后,环境标准付诸实施,而实施的过程受到来自于制定机关内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并在此基础上围绕环境标准进行沟通。最终,制定机关根据环境标准的实施情况和社会公众意见,在一定期限内对环境标准进行修订和完善。
三、 风险社会视域下环境标准制定之规制
从美国、德国等国家的立法和实践看,各国对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的规制有三种进路,即“基于风险”进路,“基于技术”进路和“成本—收益分析”进路。
(一) “基于风险”进路
“基于风险”进路是以“零风险”或者最大限度降低健康风险为目标,不考虑执行环境标准所需的成本的一种制定进路。从美国重金属污染防治的经验看,在“基于风险”进路下制定出的环境标准可以促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应享有什么样的环境质量,并积极通过标准的制定来争取更优的环境。因此,“基于风险”进路下的环境标准具有较强的纲领性和倡议性。“基于风险”进路还可以使环境利益和公众健康利益成为压倒成本估算的“王牌”,从而帮助公众在面对其他利益集团时能够“权力扭转”(power-shifting),最大可能地维护自身的环境和健康权益。
美国在其《清洁空气法》中,循着“基于风险”进路,对环境标准制定过程进行了规定。按照美国《清洁空气法》第108节和第109节的规定,想要针对某一污染物制定环境标准,环保署应首先将其列入标准制定的计划中,这一计划中的污染物需“在人们的预期中能够威胁公众健康和福利”。将污染物列入计划中之后,环保署应在12个月之内发布最新的“基准文件”(criteria document),这一文件的作用并非提供指南或任何标准,而是将有关污染物的科学研究进行总结,“准确地反映有关此类污染物在空气中各含量水平可能带来的健康和福利威胁的最新科学研究成果”See 42 USC § 7408(a)(2), The Administrator shall issue air quality criteria for an air pollutant within 12 months after he has included such pollutant in a list under paragraph (1). Air quality criteria for an air pollutant shall accurately reflect the latest scientific knowledge useful in indicating the kind and extent of all identifiable effects on public health or welfare which may be expected from the presence of such pollutant in the ambient air, in varying quantities.,为新标准的制定提供科学基础。随后,这一“基准文件”连同“参考意见”(staff paper)进入科学评估阶段,由“清洁空气科学顾问委员会”(CASAC)进行审查。顾问委员会在审查期间,还会召开公开听证会(public hearing),以听取来自各个利益集团、科学团体、环保组织和公众的意见。在听取各方意见后,环保署对“基准文件”进行修改,并再次提交顾问委员会审议。顾问委员会综合“基准文件”做出最终评估,并将这一最终评估结果送回到环保署进行审批。在“基准文件”和“参考意见”经过政策审阅和实施评估后,环保署对最终标准进行签署,并提交给国会。
美国空气中铅含量标准的制定过程即遵循了“基于风险”进路。1978年10月5日,经过三次单独审议、三次草拟,美国环保署公布了空气中铅含量标准;[7]随后,在多年准备的基础上,经过两次审议、两次草拟,美国环保署又于2008年11月12日公布了新的空气中铅含量标准。在整个标准制定过程中,美国环保署考虑的只有“保护公众健康”这一目标。即使在工业界强烈反对这样的标准的时候,美国环保署也未妥协,而是在确保“保护公众健康”这一初衷的基础上,改变标准确定思路,给出一个安全缓冲区间,使标准更易得到工业界的支持。在2008年新标准制定过程中,即使面对儿童智力与铅污染是否线性相关的质疑,美国环保署也没有因此放弃对“保护公众健康”目标的追求,抵住工业界的压力,阻止技术可行性、经济可行性以及实施标准所带来的成本纳入标准制定的考虑范围。美国环保署的做法也得到美国上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1978年的标准出台前后,环保署遭遇了多起诉讼,被起诉原因主要是工业界认为环保署超越了《清洁空气法》对其的授权,在铅污染与人类健康受损之间关系没有得到科学确证时,制定了过于严苛的环境标准,影响了工业的发展。在2008年的标准中,问题也同样出现。面对这些质疑,美国上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例,支持了环保署风险预防的做法,并指出“环保署的任务是制定出保护公众健康的环境标准,这一标准既不能过于严苛,也不能太过宽松,应该恰好能在保护公众健康的同时,提供适当的安全缓冲区间”,[7]“《清洁空气法》作为一个整体,明确无误地禁止环
保署在制定环境标准的过程中考虑成本问题”。[8]由此明确了环境标准制定中“基于风险”的进路。
虽然“基于风险”进路很好地规制了环境标准制定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博弈,促进了铅污染的防治,但其缺陷也不容忽视。其中一个缺陷,就是国会在“基于风险”进路中用来指引标准制定的语言不切实际,使得标准制定耗时耗力,甚至出现因成本过高,而致使标准制定最终夭折的现象。[9]同时,何为“安全”,何为“公众健康可接受的风险”也无法真正得到确定。特别是当标准制定的对象是“无阈值污染物”(non-threshold pollutant)时,“安全”和“公众健康可接受的风险”更无从确定,因为无阈值污染物,不管其以何种数量级存在,都会带来健康风险,这类污染物只要存在,就没有“安全”可言。[10]在面对“基于风险”进路这一缺陷时,美国环保署表面上虽然依然坚持“基于风险”进路,实际上已经开始对经济和技术可行性进行考虑,并开展了成本—收益分析。[7]
(二)“基于技术”进路
在遵循“基于技术”进路中,标准制定机关和公众需放弃理想但无法达到的环境改进目标,考虑技术最佳可得,以避免环境标准的实行给经济带来大范围的负面影响。这一进路在实际中易于操作,依此进路制定出的标准也较为容易地获得公众信任,对经济发展损害较少,因此受到各国标准制定机关的欢迎。
在美国,“基于技术”进路首先规定在美国《清洁水法案》中,并被运用于美国国家污染物减排标准(National Pollutant Discharge Elimination Standards, NPDES)中。甚至可以说,由于《清洁水法案》中最良善技术标准的成功,促进了这一进路在美国其他环境法案中的运用。[11]在制定环境标准过程中,环保署必须考虑成本,在成本合理的基础上,寻找到经济上可得的技术。通常而言,这种技术既可以是某一行业的最佳实践技术,也可以是当下无法获得,但有合理理由相信在标准实施时可得的技术。遵循“基于技术”进路制定的环境标准,在重金属水污染防治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正是这些良好的效果,促使国会在《清洁空气法》1990年修正案中抛弃了在空气污染物排放制定过程中适用“基于风险”进路的思路,转而适用“基于技术”进路,并在修正案中规定了5种污染物排放标准。它们是“合理可得控制技术(Reasonably Available Control Technology, RACT)”标准、“最佳证明可得技术(Best Demonstrated Available Technology, BDAT)”标准、“最佳可得控制技术(Best Available Control Technology, BACT)”标准、“最大可得控制技术(Maximum Achievable Control Technology, MACT)”标准、“最低可得减排(Lowest Achievable Emissions Reduction, LAER)标准。[12]
虽然“基于技术”进路得到了广泛运用,但依然受到较多批评。有学者指出,“环境标准是为获得环境效益而设定的目标或路径,但基于技术的进路仅仅考虑了技术成本和产业的经济能力,并没有考虑环境效益”,[13]这是对环境保护目标的背离。此外,在标准制定机关运用这一进路时,也面临信息不对称问题。环境标准所规制的产业从业者对于自身技术水平拥有更全面、更真实的信息,标准制定机关则不得不从产业从业者那里获取信息和数据。在这一过程中,从业者为了降低污染控制的成本,就有充足的动机来夸大实行某一良善技术所需的成本,进而影响标准制定机关的评估,并促使标准制定机关采取较为宽松的环境标准。即使要求相关产业向监测机关定期报告其排放情况,也会因行政部门缺乏快捷的信息收集途径,而影响到标准的制定。此外,基于产业保护或商业秘密保护的要求,标准制定机关无法公开全部与标准制定有关的信息,这使得环境标准制定的正当性受到质疑。为此,有的国家在采用“基于技术”进路时,还注意利用“基于风险”进路予以平衡。如美国《清洁空气法》1990年修正案第112条规定,环保署在采取基于技术的进路制定出环境标准后,对仍存在的健康风险进行报告,并针对该风险向国会提供建议。若国会未予采纳,那么在制定出此标准后的8年内,环保署必须颁布补充性的环境标准,而这一补充性标准必须是基于风险的制定进路下的,“以提供适当的安全余地来保护公众健康,或者在考虑成本、能源、安全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情况下,预防负面环境影响”。
(三)“成本—收益分析”进路
“成本—收益分析”进路是指通过估算执行环境标准所花费的成本和所得利益,进而选择最佳标准的进路。在各国环境立法中,明确要求在环境标准制定过程中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并不多见。以美国为例,大部分的立法都以“保护公众健康”和“可行性”为标准制定的核心词汇,如《清洁空气法》。但这类法案并不绝对排斥“成本—收益分析”进路的运用,在《清洁空气法》中,虽然环保署被明确要求“确保包括易感人群在内的所有人群不受空气污染的侵害”,也同时被允许在选择减污技术时广泛考虑到可能带来的利与弊。而明确规定环保署在制定环境标准的过程中要考虑成本—收益平衡的则出现在《有毒物质控制法》(TSCA)和《联邦杀虫剂、除菌剂即灭鼠剂法》(FIFRA)中。《联邦杀虫剂、除菌剂即灭鼠剂法》(FIFRA)规定,标准制定机关应关注杀虫剂是否会“对环境产生太大的副作用”的问题,并考虑“使用任何杀虫剂所涉及的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成本和收益。”
“成本—收益分析”进路本质上是一个特定的标准制定程序,一般可分为两部分工作。第一部分工作,即为标准制定机关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规制可能带来的效应进行分析。在这一部分工作中,标准制定机关除了对标准实施后可能产生的成本和收益有清晰认识外,还应当尽可能多地量化与其有关联的效应,努力将规范性价值(包括生命、健康和审美)换算成可计算的金钱或者其等价物。第二部分工作,即为标准制定机关在决策所产生的效应无法弥补成本时,向公众进行解释。“成本—收益分析”进路有很多优势。一方面,这一进路可以通过全面展示科学对某一问题的认识,促使人们克服“目光狭隘(narrow perspective)”所引起的认知扭曲,平息人们对某些风险的不理性恐惧。另一方面,这一进路通过对环境风险信息的披露与衡量,促进了民主的进步。在这一进路没有得以实行时,利益集团可以轻易通过对数字的操纵来塑造人们的偏见,扩大某一风险,缩小另一风险,从而控制民意。“成本—收益分析”正是通过对数字的披露与比较,防止民意被误导和利用。[14]
但“成本—收益分析”进路也有其缺陷。在对收益的估算过程中,标准制定机关时常无法对所有结果进行全面、准确的分析。即使标准制定机关穷尽所有结果,它在信息获得方面仍具有天然局限。在美国饮用水中砷含量标准制定过程中,美国环保署缺乏关于疾病风险的优质数据,仅能以其他粗糙数据来代替。如此一来,这一数据就受到了不同利益集团的攻击:环境律师认为环保署通过“呼吸道疾病研究”得到的风险发生率太低;而工业律师则对这一数据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认为提供数据的调查受众面太窄,不足以代表真正的砷污染风险。虽然美国环境署的数据获取过程都是经过精心计划的,但也无法避免信息广度和准确度方面的缺陷。在收益的货币化方面,反对将生命、健康换算成金钱的声音一直存在,有学者直接指出,“生命、健康与财富、金钱分属于不同的领域”,[15]无法进行比较,更不能给出货币化的结论。在美国饮用水中砷含量标准制定过程中,由于环保署使用的是“生命数”而非“生命年数”,这使得儿童生命价值的货币化结果被低估,而老年人生命价值的货币化结果被高估,每个生命610万美元的货币化结果也饱受质疑。[16]学者莉莎·海泽琳(Lisa Heinzerling)就对“成本—收益分析”进路批评道:“最好不要把问题搞得太明白,在直觉和证据之间也不要试图去寻找任何联系,即使找到了,这样的联系也是自相矛盾的。有些人相信将风险、成本与收益通过精确的数据表达出来,可以对现实进行不偏倚的反映,从而有利于政府作出正确的决策这种观点只能使人们对隐藏在数字后面的价值越来越无知。”[17]
四、 我国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的法律规制
(一)我国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之现状
1. 思路混乱
从现有立法看,我国环境标准的制定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思路。我国《环境保护法》虽然有对环境标准的制定进行规定,但主要都是授权性规定,并没有对环境标准的制定进行原则上的规定。在《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虽然都有与环境标准相关的规定,但都集中在授权性和环境标准实施的范畴内,对理解环境标准制定原则并无裨益。在《标准化法》中,第8、9、11条规定了标准制定的原则,但这一原则是针对包括产业标准、卫生标准在内的所有标准制定工作而言的,对环境标准制定的指导意义并不大。因此在与环境标准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就只剩下《环境标准管理办法》对我们理解我国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中的原则有帮助。
《环境标准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为防治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保护人体健康,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对环境保护工作中需要统一的各项技术规范和技术要求,制定环境标准。”第10条规定:“制定环境标准应遵循下列原则:(一)以国家环境保护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及有关规章为依据,以保护人体健康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促进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二)环境标准应与国家的技术水平、社会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三)各类环境标准之间应协调配套;(四)标准应便于实施与监督。”将这两条规定总结起来,可以看到“以保护人体健康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本质是对“基于风险”进路的规定;“环境标准应与国家的技术水平、社会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实质上是关于“基于技术”进路的规定。
“基于技术”进路一直是我国制定环境标准的常用方法,“综合考虑到我国目前环境质量状况和经济技术水平”“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环境管理需求”“结合我国经济技术承受能力”等字眼频繁出现在相关的编制说明和政府文件中。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开始重视“基于风险”进路的运用。李克强总理在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把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切实解决影响科学发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基本的环境质量、不损害群众健康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一条底线,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二五”发展规划》中,也有类似表述:“以保护人体健康为目标,以健康风险评估为手段,制定相关标准。”除了“基于风险”进路,“成本—收益分析”进路也曾受到过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关注,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曾提出:“应积极探索对政府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政府立法不仅要考虑立法成本,还要研究其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标准制定的进路都处在混用不清的状态。本应适用“基于风险”进路的环境标准却依照“基于技术”进路来制定,如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铅含量标准的制定,就将人体中血铅含量的阈值忽略掉,仅从我国空气治理技术所能达到的水平出发,制定标准;而另一些本应遵循“基于技术”进路来制定的环境标准最后却按照“基于风险”进路来制定,导致标准过高,不能实行,例如土壤中镉含量标准的制定。另一些标准制定虽明确提出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最终却陷入了“基于技术”的进路中。制定标准过程对健康价值的漠视,对环境标准的随意放宽等现象比比皆是,使“成本—收益分析”成为了口号。
2. 公众缺位
在我国,除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在修订过程中公布了编制说明外,其他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都未公布编制说明或有关标准制定的其他文件。从环保部的网站上看,各环境标准草案的意见征集也都向几个固定研究机构发出,却不向公众公布全部内容。即使公布,环保部也没有对标准中的一系列科学术语向公众进行简单、明了的解释和教育,使得公众没有更多的机会来理解和评价环境标准的制定。
而这仅仅是我国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中公众缺位的一个侧面,虽然《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2006年)》第33条第2款中规定,“对涉及社会公众利益、影响重大的标准,通过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政府网站、报刊等公共传播媒介公布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征求意见”;《关于收集和处理社会公众对国家环保标准草案意见事宜的通知》也指出“环境标准在制定过程中,要采用公开的方式广泛征求各有关方面和社会公众的意见。……环境标准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均同时通过国家环保总局网站公布征求意见稿,社会公众可利用留言方式对标准制修订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实际情况是,公众并不经常登陆环保部网站,无从知晓正在修订中的环境标准,更无法提出有效、合理的意见。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我国环境标准制定流程中,收集、处理和回应公众意见的环节是被排除在外的,所有的意见征集和讨论都限于专家、科研机构和标准制定机关之间,即使有公众将意见提交给标准制定机关,这些意见也没有畅通的反馈渠道,无法影响标准的制定。
(二)我国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的立法内容选择
1. 制定进路之立法选择
综合各国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在制定进路上,我国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过程中的法律规制,应采用“基于风险”进路、“基于技术”进路和“成本—收益分析”进路混合的思路,但应侧重“基于风险”进路和“成本—收益分析”进路的运用,而将“基于技术”进路放在次要位置上,从而形成倒三角的进路模型。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有以下几个理由:
其一,在与我国环境标准制定程序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基于风险”进路虽然常以“保护人体健康”等词语出现,但在实际的标准制定工作中,这样的词语常被当作口号而忽略,被“基于技术”进路所替代。在重金属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面对“基于技术”进路在污染防治上的失败,“基于风险”进路应该被着重强调,以扭转“基于技术”进路主导的局面。而在“基于风险”进路为中心的基础上,则应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来弥补“基于风险”进路偏理想化所带来的弊端,使环境标准能够在实现保护公众健康目标的同时,不会受到产业界的强烈反对或消极抵抗。
其二,从美国环境标准制定过程中看,“保护人体健康”的目标主要通过“基于风险”进路加以贯彻时,也并没有排斥“成本—收益分析”,甚至需要“成本—收益分析”进路在微观层面上进一步实现。即面对成本过于巨大但收益甚微的风险规制,政府可不马上采取风险规制措施,以保护公众的人体健康;在风险规制措施选择上,当两个措施同时满足“基于风险”进路的要求时,需要依赖“成本—收益分析”进路来做出最终抉择。因此,在强调“基于风险”进路时,将“成本—收益分析”进路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也是重金属污染防治中运用的应有之义。
如此一来,这三个进路在我国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中就形成了一个倒三角模式,即在环境标准制定过程中优先适用“基于风险”进路和“成本—收益分析”进路,其次才适用“基于技术”进路。
2. 风险沟通之立法选择
针对我国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中公众缺失现象,我国可借鉴美国、德国、丹麦等国在环境标准制定中的风险沟通经验,在美国的听证会模式基础上,结合丹麦的共识会议模式,形成符合中国本土情况的风险沟通模式。
从美国的听证会模式、德国的环境标准化协会,以及丹麦的共识会议的优劣看,美国的听证会模式能使最大范围的公众了解环境标准的制定,但这一模式不利于公众、专家、产业者和标准制定者面对面地沟通,降低了风险沟通的教育和减缓恐惧的功效。德国的环境标准化组织模式虽然可以最大限度地将各个利益集团吸收到环境标准制定的程序中,为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提供良好的平台。但德国模式的对象主要集中于科技界和产业界,真正的公众很难进入;即使进入,在专业人士面前,公众也很难准确表达出自己的意愿和想法。而丹麦模式虽然弥补了美国和德国模式的缺陷,但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一模式仅能在人口规模小、公民素质高的国家得以顺利实现,而在人口规模大的国家,这一模式很难凸显其优势。因此我国无法单独借鉴任意一种模式。同时,我国人口众多,从中随机抽选公民参与到共识会议中显然无法解决我国环境标准制定过程中沟通不足的问题,反而会让舆论质疑公众人选的公正性。共识会议的模式也会使得公众受到科学知识教育的机会减少,不能单独选择。而德国模式在我国实行起来也比较困难,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缺乏像德国一样的NGO基础,无法通过NGO模式来解决环境标准制定过程中的风险沟通问题。因此,在我国现行条件下,就只能选择美国的听证会模式。这种模式比较适合像我国这样地域广阔、各地重金属污染情况不同的国家。同时这一模式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制度基础。听证会已经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得到了多年实践,只需借鉴共识会模式中对科学知识的教育和沟通环节的经验,就可完成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过程中风险沟通的目的。
在立法中,除了依照行政程序法中听证会程序规定来制定相关环境,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需要着重强调:其一,听证会的启动不能再依相关人员申请,而应由标准制定机关主动召开;其二,听证会的组成人员应由公众、科研工作人员和相关产业代表组成;其三,在听证会的准备工作中,应增设科学知识培训的互动型会议,帮助公众理解相关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的科学知识,并可以随时在此会议上向有关专家提出疑问;其四,在听证会结束后,标准制定机关应全面公布整个听证会的记录,并对听证会上各利益群体的建议和疑问做出系统的、书面的回应。
(三)我国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的立法模式选择
根据我国立法现状,在立法模式上,我国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程序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各单行法、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对相关制定程序分散规定,二是在正在起草过程中的重金属污染防治条例中设专章进行规定。
在我国环境法体系中,重金属污染防治和环境标准制定都是以分散立法的形式存在的。其中,《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对重金属污染防治进行了零星规定。 《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则对环境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进行了规定。这样的立法方式具有一定合理性,重金属污染问题在各环境介质中都有不同的表现,根据每种介质中的问题进行分散立法,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环境标准的制定也有同样的情形,因此进行分散立法无可厚非。实际上,在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重金属污染防治中,也都采分散立法模式。但问题在于,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重金属污染防治立法虽然是分散式的,但可以做到“形散而神不散”。在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立法机关都以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为中心,以水环境、大气环境和固体废弃物的重金属污染防治为辅助进行立法。在每个法律中,环境标准的制定原则、制定进路和风险沟通都被详细规定。因此,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虽然在形式上是分散的,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在体系内有针对性地解决各自的重金属污染问题。而我国现行的重金属污染防治立法在“形”和“神”上都是分散的,造成了重金属污染防治法律依据零散、不成体系的现象。若我国对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的制定也采取分散式立法,笔者认为,应以正在起草过程中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为中心,在其中对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的制定进路进行规定,并将“基于风险”进路作为标准制定的首选进路;同时,《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中都应与《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规定相连接,结合自身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对各自有关环境标准的规定进行调整,并增加对标准制定进路的规定。而对标准制定过程中风险沟通的规定,笔者认为,不应在各环境单行法中进行,而应由《标准化法》和《环境标准管理办法》来解决。
随着重金属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已经有学者开始呼吁制定《重金属污染防治条例》,从现有资料看,国家环保部法规司正在加紧这方面的工作, 以此来应对频发的重金属污染事件。如果《重金属污染防治条例》能够顺利进入新一届人大的立法规划中,则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的制定就有必要设专章进行规定。在《重金属污染防治条例》中,环境标准制定一章应放在总则之后,其他章节之前。一方面这可以体现环境标准作为其他环境制度的基础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在重金属污染防治中,环境标准制定对其他防治措施的决定性影响。具体到环境标准制定一章中,“基于风险”进路应首先被规定,并对“基于风险”进路中应考虑的各因素进行详细解释。在“基于风险”进路之后,应对“成本—收益分析”进路进行规定,并对成本与收益的估算方法、货币化方法进行解释。最后,对“基于技术”进路及其运用限度进行规定。在对标准制定进路进行规定后,还应规定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过程中的风险沟通。笔者认为,这一部分规定的详略程度,应根据《环境标准管理办法》的修订情况来定。如果《环境标准管理办法》对标准制定过程中的风险沟通进行了详细规定,《重金属污染防治条例》中就只需进行概括性的规定,并对《环境标准管理办法》进行指引;如果《环境标准管理办法》没有进行修订,则《重金属污染防治条例》中就应根据重金属污染问题的社会特性,对风险沟通方式进行较为详细的规定。
以上两种立法模式各有优劣。分散立法模式中各单行的法律层级较高,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的相关规定虽简略,但可通过后续制定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来充实和完善;同时,分散立法模式可以针对不同环境介质各自的问题,在标准制定进路上有所侧重。但分散立法模式极有可能陷入“形散且神散”的境地,最终使得对环境标准制定程序的规定沦为口号;对各单行法的修改耗时耗力,使得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的立法体系在很长的时间内无法建立起来。在《重金属污染防治条例》中设专章进行规定,其主要缺陷是条例的层级太低,在诸多程序性规定上受限较多;但在条例中设专章进行规定,可以很好实现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的法律规制,并不会受到其他法律法规修订的牵涉。
根据我国现实情况,笔者认为,对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的立法应选择在《重金属污染防治条例》中设专章的模式。一方面,从现有研究和趋势看,《土壤污染防治法》无法在近期出台,如果选择分散立法的模式,作为中心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不存在,仅对其他各单行法进行简单修补也无法改变重金属污染防治不力的现状;而《重金属污染防治条例》由于层级较低,受到阻力较小,反而会更快出台,从而使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过程得到更早的规范。另一方面,从我国的立法教训来看,对某一问题的法律规定的“形散”,极有可能造成“神散”的结果,这甚至引发了 “出现一个问题,立一个法”的恶性循环。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考虑,笔者认为,在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的立法形式选择上,我国应选择《重金属污染防治条例》中设专章的模式。
[参考文献]
[1]周珂:《环境法(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版,第53页。
[2]Daniel A. Farber, Jody Freeman, Ann E. Carlson.: Cases and Materials on Environmental Law(8th Edition), West Publication, 2001, pp.704-707.
[3]Register, Federal.:“National Primary Drinking Water Regulations: Arsenic and Clarifications to Compliance and New Source Contaminants Monitoring”, Vol. 66, No. 78, 20580, April 23, 2001, pp.203-214.
[4]Olson, Erik.:“Arsenic Everywhere, and Bush Is Not Helping”, Baltimore Sun, May14, 2001, 9A. Fialka, John. “Arsenic and Wild Space: Green Activists from Across Spectrum Unit against Bush”,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1, 2001, A20. Musil, Robert K.: “Arsenic on Tap”, New York Times, April 24, 2001, A18. Bruce Handy, Glynis Sweeny. “Safety Is for Sissies”, Times, April 16, 2001, A88. Mark Barabak, “Bush Criticized As Fear of Environment Grows”, LA Times, April 20, 2001.
[5]Pierce, Richard J.: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ss, The Foundation Press, 1985, pp.175-179.
[6]Indus. Union Dept v. Am. Petroleum Inst., 448 U.S. 607, 706.
[7]Lead Industries Association Inc. v.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647 F.2d 1130.
[8]Whitman v. American Trucking Associations, 531 U.S. 457.
[9]Federal Register, Vol. 73, No. 219, Rules and Regulations, November 12, 2008.
[10]Agency for Toxic Substances & Disease Registry (ATSDR), Public Health Statement: Lead, 2007, pp.11
[11]Farber, Daniel A. Freeman, Jody. Carlson, Ann E.:Cases and Materials on Environmental Law(8th Edition), West Publication, 2001, pp.704-707
[12]Sunstein, Cass R. Laws of Fear: Beyond the Precautiona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Ackeran, Bruce. Stewart, Richard.: “Reforming Environmental Law: The Democratic Case for Market Incentives”, Columbia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1988, Vol.13, p.171.
[14]张默:《合同第三人的利益和保护》,《人大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
[15]David M. Driesen, Rovert W. Adler:Environmental Law: A Conceptual and Pragmatic Approach, Aspen Publishers, 2007, pp.239-240.
[16][美]凯斯·R·孙斯坦:《风险与理性——安全、法律及环境》,师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158页。
[17]Heinzerling, Lisa.: “Regulatory Costs of Mythic Proportions”, Yale Law Journal, 1981, Vol.3, p.107.
(责任编辑 刘永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