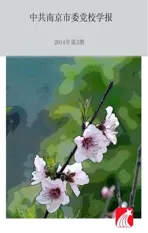行政公布食品安全消费警示制度的检视与反思*
2014-07-31何骏
何 骏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 上海 200042)
一、引言
中国的食品安全消费警示公布路径有二:一是通过民间自治团体即消费者协会;二是通过具有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前者是消费警示公布制度的创立者,通过启动“消费警示工程”、制订《消费警示发布制度实施规范》等,对食品安全领域的消费警示进行事前规制,即使对该消费警示有争议,也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加以事后解决,实践中以消费者协会为诉讼主体的案件也不乏其例。反观后者,由于行政机关法律地位的特殊性,更应该对其介入市场的行政行为保持适度警惕,作为一类新型的政府规制手段,①尤其应该注意其发布食品安全消费警示的条件、方式、程序和时限等,确保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目的性,否则容易陷入管制的法治危机和信任危机,加之行政事后救济的局限性,此种控制消费警示发布过程的法律治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典型事件”引发对法律规范的拷问
(一)警示失误与警示怠惰
事件一:(砒霜门事件)2009年11月,海南省海口市工商局在对该市部分市场销售的各类饮料食品进行抽样初检后,发现农夫山泉部分饮料产品砷成分超标。于是工商部门就此发布消费警示,并强调上述结果经过海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和海口市卫生防疫站复检核实。消息一出,很快被各大门户网站转载。但是该事件最终调查结果显示,确认检测机构初检结果有误,海口市工商局在工作过程中存在程序不当。[1]
事件二:(金浩茶油事件)2010年8月中旬,境外微博披露金浩茶油苯(a)芘超标。事实上,2月份湖南省质监局派出执法人员到金浩工厂抽样,检测结果发现26个样本中,9个存在苯(a)芘超标,最严重的超过国家标准3倍,但是质监局却借口“没有统一公开发布的权限”在长达半年之内未公之于众。[2]
上述两则事例中所称的“消费警示”相当于德国法上的“公共警告”,德国学者哈特穆特·毛雷尔认为:“公共警告是事实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政府机构对居民公开发布的声明,提示居民注意特定的工商业或者农业产品,或者其他现象。”[3]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行政机关运用消费警示的形式发布食品安全信息,提示公众注意购物、饮食,但却容易引发行政作为(包括不作为)违法或不当的问题,是规范缺失的问题,还是有法不依的问题?不管是“程序不当”还是“无职权依据”都应当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中重新审视。
(二)食品安全消费警示在法规范中的定位
“行政机关公布危险信息或者违法事实,这是风险沟通的重要方式,有助于消费者自我防御风险。但行政机关公布危险信息或者违法事实可能具有两种效果,其一是给消费者以提醒,其二是可能会给生产经营者造成严重的损失,即具有惩罚的效果。”[4]因此,必须厘清食品安全消费警示存在的正当性基础,这是行政机关发布食品安全消费警示的前提和依据。近年来,德国围绕行政机关发布“警告”的权限问题积累了比较多经验和判例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学说:一种观点认为,联邦政府发出警告的权限是根据《基本法》本身推导得出的,具有宪法上的支撑力,无须其他法律进行授权;另一种观点认为,某一组织规范也附随地包含有完成该事项时排除危险的权限。但是,该附随权限也只不过是一种组织规范,因此,在伴有命令、强制的时候,还是需要有根据规范。[5]事实上,两种观点的立意是不同的,前者强调国家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共同体提供保护,却忽略了缺乏法规范规制的权力容易失控;后者则是基于对权力的不信任,而通过法律授权的形式严密规范权力的运行。“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关乎公众的生命和健康,笔者认为,行政机关公布食品安全消费警示应当具备组织法上的依据和行为法上的依据是比较理想的选择,而且应该对行为根据予以重点关怀。
实际上,食品安全消费警示在中国的立法中表述得颇为模糊,以致于不同学者间理论纷争不断。有些立法直接以“消费警示”的字眼出现,②如《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其第52条第1款第3项规定:“发布消费警示,告知消费者停止购买或者食用不安全食品。”其他规范性文件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乳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0〕42号)第4条第2项要求“工商机关对不在名录内的婴幼儿配方乳粉要立即检查、发出消费警示”。这些立法不仅效力层级比较低,而且更具部门和地方特色,基本上只是一些宣示性和口号性的文字,对消费警示的规制作用有限,实难成为发布消费警示的规范依据。那么,是否可以从法律或是行政法规中找到规范依据呢?首先,《食品安全法》第82条中规定,县级以上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公布食品安全日常监督管理信息。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公布信息,应当做到准确、及时、客观。消费警示作为日常监督管理信息的一种,应该遵循该条的规定。其次,食品安全消费警示作为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资讯的一种活动,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一部分,从行政法规层面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0条也将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列为应当重点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并以专章的形式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和程序进行了规定。然而,纵观目前食品安全消费警示立法现状,笔者认为有必要做适度检讨。一方面,《食品安全法》第12条、17条、53条、69条、72条、82条、83条虽然对食品安全信息公布做了相关规定,但是对消费警示的规定似乎都是“擦边球”,甚至已经成为行政机关规避执法风险的借口;另一方面,除《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外,是否存在其他特殊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则可以供行政机关公布消费警示作为参考。
三、透视食品安全消费警示的理论与实践
(一)对其法律关系的类型化思考
传统行政法学理论认为,行政法律关系主要存在于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最终表现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认真分析食品安全消费警示的法律关系的主体结构,其实能够发现其与普通的行政活动存在一些差别。根据消费警示的公布基础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是行政机关基于多年同类事件的执法结果、公众投诉等经验性结论作出判断,认为需要发布消费警示,而警示内容并没有指出特定的可能侵权主体或者物品;二是,行政机关基于个案执法结果,认为可能会对公众造成巨大损害而发布的消费警示。此种消费警示也是向公众提示风险,只是该警示明确列明造成危险的具体物或者人,因而涉及到了具体第三方。[6]以上论述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法律关系的构造取决于食品安全消费警示公布的内容而定,既可能涉及双方关系,也可能涉及三方关系。
1.行政机关和社会公众——双方法律关系
这类法律关系运作机理是,行政机关基于生存、照顾的理念,针对市场中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提示消费者注意某方面的危险事项。一般来说,这类消费警示常见于重大节假日期间,如“黄石市食品安全监管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节日食品安全消费警示”、“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六一’儿童节食品安全消费警示”等。在该法律关系中,行为双方受到法律的拘束力可能很弱,行政机关发布消费警示完全是“好意施惠”行为,无意于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社会公众的“接受”也完全是一项自觉自愿的行为,缺乏强制力和执行力,有别于传统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高权行政,或可归入行政指导的范畴,类似于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为实现一定行政之目的,以辅导、协助、劝告、建议或其他不具有法律上强制力之方法,促使特定人为一定之作为或不作为的认知行为。[7]实践中,因这类法律关系产生的争议并不多见。
2.行政机关、社会公众和食品企业——三方法律关系
具体而言,根据消费警示内容提及的食品企业是否具体、特定,又可以将该法律关系细化为以下两类,如图所示:

所谓的“唯一、明确”是指行政机关在消费警示中点名道姓地指出某公司或企业的食品存在某方面的安全问题,实质上等同于曝光其违法行为。如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湘飘四海”牛肉菌落超标76倍的消费警示、北京市食品办发布湖南“涵哥”食品甜蜜素超标的消费警示以及常德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公布广州市果王食品有限公司、长沙老火夫食品贸易有限公司不合格的消费警示等。所谓的“概括、但能确定范围”是指从行政机关公布的消费警示中仅能发现特定区域的某类食品可能存在危险,但事实上也圈定了生产这类食品的企业。这种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表述暧昧,如贵阳市云岩区质监局公布其辖区内糕点抽检不合格的消费警示,公告中虽然提到其对贵州饭店有限责任公司、贵阳云岩皇家食品厂等6家糕点生产单位进行食品安全情况抽样检查,并检测出有质量不合格的食品,但并没有明确是那几家单位的食品存在质量不合格。
笔者认为,行政机关应当尽可能地明晰消费警示所涉的法律关系,避免发布这种隐性包含某类食品生产企业的消费警示。一来容易伤及无辜,可能侵害合法经营企业的经济自由;二来容易导致社会公众的无所适从,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史蒂芬·布雷耶大法官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公众能够理解被披露的信息,或可以以信息为依据自由地选择,或者相信信息与选择之间具有实质的关联时,披露才有可能起作用。”[9]总而言之,涉及三方法律关系的消费警示运作逻辑是,行政主体发布警示信息,社会公众在获取信息的同时对相关食品企业施加舆论谴责和购买选择的压力,进而对被公布者的名誉、财产利益等方面产生实质性影响。有趣的是,行政机关似乎用了一种“柔性执法”的手段而对违反企业产生了间接的强制力。
(二)公布食品安全消费警示存在的问题
第一,公布主体五花八门、权限依据不明确。从主体的职权性看,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只能是行政主体依职权发布的行政行为,发布主体必须具有组织法上依据,否则构成越权。[10]《食品安全法》规定,县级以上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公布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信息。这或许成为当前行政机关发布消费警示的唯一职权依据。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正是用《食品安全法》的这条规定为自己辩解没有越权。此外,某个质监局的办公室、某食品安全委员会对外发布消费警示也为数不少,这些“办公室”、“食品安全委员会”并没有行政主体资格,其发布消费警示的行为涉嫌违法。从源头上看,主要是因为消费警示在我国立法中既不明确而且比较分散,没有形成统一的制度,更重要的是由于在食品安全领域试行“多头管理、分段监管”,使得相关职能部门具备发布消费警示的理由。
第二,程序运作失范、违反正当程序现象屡见。“行政决定中或多或少地具有裁量的余地,为了公正地行使裁量权,使程序公正、透明,也是重要的”。[11]立法中不曾明确消费警示发布的目的、方法、手段和时限等,这留给行政机关发布消费警示很大的裁量自由。即使《食品安全法》提到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公布信息应当做到准确、及时、客观,但是如此不确定的概念势必加大行政机关主观参与行政的程度,给行政权力的滥用留下灰色空间。其实,作为一项政府信息公开形式,大多数行政机关并没有遵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程序,没有在消费警示公布前对内容的真实性进行审慎审查。在“砒霜门事件”中,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并没有给农夫山泉公司陈述、申辩或说明理由的机会,笔者认为即便是没有法律规范进行规制,至少也违背了正当程序原则。
四、对公布食品安全消费警示的行政法控制
(一)放眼德日:重视行政的过程性
行政管理的最终目的应当是维护作为社会中的“人”的尊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自由。[12]行政机关发布食品安全消费警示在考虑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不可忽视对营业主体基本权利的保障。德国在2005年颁布的《食品、日用品和饲料法典》第40条第1款第3项指出,具体情况下有充分根据说明,某种产品会危害或已经危害到安全和健康,并且由于科学认识方面的不足,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在一定时间内还无法消除这一不安全性。本款内容实际上肯定了行政机关具有发布消费警示的职权。当然该职权的行使受到一定的限制:只有当存在有公共利益,并且与当事人的利益相比,该利益更为重要时,才允许向公众发布信息,这是比例原则在食品安全消费警示中的体现;本条第2款规定了行政机关先行提示义务即行政公布消费警示的前提是行政机关提醒食品企业主向公众发布信息而其没有采取发布措施;第3款规定在消费警示发布前应当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第4款则明确了错误发布消费警示的补救机制:应以向公众发布信息的同样方式发布公告。申言之,德国模式的优势在于通过落实一系列的程序法律机制,从而达到维护公益和私益的均衡。但是,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是,对于“双方型”消费警示,是否也需要通过如此繁琐的程序加以控制,是否会降低行政主体发布市场危险信息的能动性,从而产生警示不足的倾向。
日本《食品卫生法》第63条规定:“为了防止发生食品卫生上的危害,厚生劳动大臣和都道府县知事可公布违反本法或违反依本法所作处理者的名称等,应当努力明了食品卫生上的危害状况。”本条中“努力明了危害状况”含义比较模糊,行政主体难以把握,但是日本审判实践中发展了许多公布消费警示的原则和规则来约束行政机关的公布行为,这些规则界定出了“努力明了危害状况”的具体操作情形。较为典型的是对“大阪0-157食物中毒事件”的判决,该份判决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其一,发布消费警示行为属于法律保留还是行政自主因消费警示的法律属性而异;其二,公布消费消费警示不是任意行为,行政机关发布消费警示应当注意证据的确凿和充分,并对发布行为负有适当的注意义务;其三,从行政手段和目的的对称性角度考虑,公布消费警示应当符合比例原则。
(二)行政便宜与裁量收缩的运用
有学者认为:“如果某种公共警告作出将造成特定人权利与法益的损害,那么这种巨大的侵害性权力应该为立法机关所保留,并通过限定行使条件、程序、方式的授权条款赋予行政机关,而不能由行政机关任意创制并行使。”[13]诚然,该学者已经注意到区分不同类型消费警示发布程序的必要性,笔者认为,发布“双方型”消费警示应以行政便宜为原则,而发布“三方型”消费警示应遵循裁量收缩的规则。
行政便宜是指行政机关可以根据自己的裁量进行行政活动,受到法律的拘束较小,更多考虑的是行政效率和行政成本。“双方型”消费警示采用行政便宜主义的理论基础在于其不涉及第三方主体,仅仅是行政机关和社会公众。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社会公众难以获得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食品信息,而行政机关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社会公众提供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信息,如危险来源、表现形式、危害范围、发生概率等是福利行政表现之一。至于发布消费警示的时机、方式、条件和程序完全由行政机关自我安排,发布该消费警示具有灵活性和应变性,与行政便宜主义是契合的。考量这类消费警示发布合法与否的主要依据是公布机关是否具有组织法上的权限。相反,发布“三方型”消费警示的规则则要复杂得多,多数情况下公布机关的裁量权力可能会压缩至零,换句话说就是行政主体必须做出裁量决定,甚至是某一种决定。裁量收缩是《食品安全法》第82条规定的“客观、准确”标准的实现途径之一,因此,更应该关注的是裁量收缩在“三方型”食品安全消费警示上的运用,并对行政机关的发布行为作合法性和合理性评价。对于可能侵害食品生产者经济利益的消费警示发布是否需要法律授权在理论上不无争议,王贵松教授认为,要求只有存在法律的授权才允许发布风险公告,这是不现实、不妥当的。[14]这种观点在不对警示公告作具体区分的情况下是成立的,因为行政面对纷繁复杂的食品安全问题需要便宜,但作类型化思考后,适用法律保留变得必要。“如果事实行为构成对权利的干涉(效果上与命性干涉一样),或者可能限制基本权利时,必须具备相应的法律授权才能实施。”[15]一旦法律对发布消费警示的条件、方式、程序等作出规定,规范食品监管部门发布消费警示的要件裁量的运作也是大有裨益的,德国的法律规定可能是一个借鉴,诸如“金浩茶油事件”这类裁量怠惰、“砒霜门事件”这类裁量肆意的消费警示便会销声匿迹。
(三)正当程序视角下的“三方型”消费警示
“双方型”消费警示一般来说只要不越权发布,如何发布消费警示,食品监管部门拥有判断余地,法律不应该对其有过多的限制。而“三方型”消费警示公布则应该从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出发,进行制度构造和完善。
首先,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公开食品安全监管信息是政府的一项职责,但是否有必要警示所有检查中发现的危险信息,不无疑问。如果只是一般轻微违法就公开相应企业的名称、所涉产品等信息,虽然有益于保障社会公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但是对于食品厂商而言是具有“毁灭性”的,这种情况下的法益比较:经营权大于健康权。相比之下,采取财产担保、责令召回、强制下架等措施更为妥帖。
其次,说明理由是公布食品消费警示不可逾越的步骤。行政行为说明理由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对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裁量是所考虑的政策、公益等因素。[16]所以,在食品安全消费警示公布之前,行政机关应当将消费警示及发布消费警示的依据一并告知涉及的食品企业,并且应该听取其陈述和申辩,必要时还应当适用听证程序,然后依据听证决定是否发布消费警示。当然,如果消费警示中提及的某种危险属于迫在眉睫,不及时公开将会对公众的生命、健康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则应该排除听证程序的适用。
最后,关于食品安全消费警示发布的时限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8条规定,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应当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目前食品安全领域的立法并没有对消费警示公布的时限做出过具体规定,所以,遵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8条的规定是对“及时”标准最好的法律回应。概言之,设计出的食品消费警示公布程序是符合比例原则的,应把公众的健康与安全、行政成本与效率、司法审查的成本与效率、(特定)相对人的程序参与权与财产权等实体权利等都纳入最大化计算的等式之中。[17]
注释:
①一般而言,行政执法机关基于公益目的发布公共警示信息是针对不特定主体的单方行为,不具有强制力,也没有设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因此,其实质是一种公告,应属事实行为。(陈新:《行政执法中的公共警示法律问题探析》,载《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4 期。)2008,37.
②笔者以“食品安全”和“消费警示”为关键字通过对“北大法宝”的检索,得到的结果是:部门规章12篇,地方性法规1篇,地方规范性文件101篇。
[1]万静.“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提示消费警示应规范发布[N].法制日报,2011-10-17(006).
[2]陈黎明、谭剑.金浩茶油事件:“秘而不宣”谁之责.
[3][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93.
[4]王贵松.日本食品安全法研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167.
[5][日]大桥洋一.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革[M],吕艳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7.
[6]林沈节.“消费警示”及其制度化——从“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谈起[J].东方法学,2011,(2).
[7]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86.
[9][美]史蒂芬·布雷耶.规制及其改革[M],李红雷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41.
[10]于杨曜.论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规制[J].学海,2012,(1).
[11]盐野宏.行政法总论[M],杨建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77.
[12]湛中乐.现代行政过程论——法治理念、原则与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3.
[13]朱春华、罗鹏.公共警告的现代兴起及其法治化研究[J].政治与法律,2008,(4).
[14]王贵松.食品安全风险公告的界限与责任[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5).
[15][德]汉斯·J.沃尔夫等.行政法(第二卷)[M].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2.193.
[16]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12.
[17]朱春华.公共警告与“信息惩罚”之间的正义——“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折射的法律命题[J].行政法学研究,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