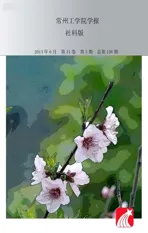狂欢化诗学视域下的《西游记》
2013-04-02王正刚
王正刚
(广东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广东 揭阳 522000)
中国佛教源自印度,在唐代臻于鼎盛,唐朝帝王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韩愈因为直谏迎佛骨而得罪唐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据说唐太宗在起兵抗隋、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他即位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派高僧玄奘西行印度取经——这是《西游记》的由来:纯官方话语权叙述。但大众在欣赏这个以保证官方话语权为目的的取经故事时,老少皆宜,笑声不断:或笑孙悟空的顽皮,或笑猪八戒的粗笨,还有笑唐僧的古板、神仙的世俗等。其实这一系列的阴差阳错、滑稽可笑、幽默可爱的人物或事件背后,暗合着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西行取经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一路狂欢。巴赫金认为:“狂欢节,是人民大众以诙谐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这是人民大众的节庆生活。”①在此类充满欢笑的全民狂欢《西游记》的“第二种生活”中,全民参与,充满欢笑,高尚的主题、宗教的清律、严肃的制度都不复存在,而等级、宗教、崇高一次次被摒弃,神圣、权威一次次被“脱冕”,当以狂欢化的视角来看待作品中的世界、神灵与世人时,严肃正统的权威官方世界只剩下戏拟、调侃、反讽、嘲笑的碎片。
一、二元对立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代表了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与思想在特殊的年代寻找突围的缝隙和表达的空间。狂欢诗学就是在这种特殊士壤与现实基础上得以生成的,表现出两种生活、两种语言、两种文化这三个二元对立因素。巴赫金是在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二元对立中展开思考的。官方话语无趣,充满了空洞的说教、陈腐的观念与僵硬的道德指令,它严肃、呆板、假正经与故作威严,经过了权力的渗透与整合,不可避免地制造出某种全社会的紧张气氛和民众的恐惧心理。
为天下芸芸众生,历尽千辛万苦、远涉千山万水的取经更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故事。对于取经,用官方语言、权威的表达方式是:“如来讲罢,对众言回‘我现四大部洲,众生善恶,各方不一:……我西牛贺洲者,不贪不杀,养气潜灵,虽无上真,人人固寿;但那南赠部洲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我今有三藏真经,可以劝人为善’。 诸菩萨闻言,合掌皈依,向佛前问曰:‘如来有哪三藏真经?’如来曰:‘我有法一藏,谈天;论一藏,说地;经一藏,度鬼。三藏共计三十五部,该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乃是修真之径,正善之门。我待要送上东土,叵耐那方众生愚蠢,毁谤真言,不识我法门之要旨,怠慢了瑜迦之正宗。……’”②如来身为西方佛老,代表的是官方权威。他金口玉言,说南赠部洲是口舌凶场,是非恶海,而自己有三藏真经,可以劝人为善,想永传东土,劝他众生!这是何等崇高的主题,何等神圣的使命!只有广结善缘,普度众生的菩萨才能做到。但只要用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为武器,剥离那宗教的外衣和清律的遮蔽,在狂欢化诗学的视域中,就会发现等级、宗教、崇高将不复存在,神圣、权威将被“脱冕”。这段话中,如来夹杂私心,满口胡言,普度众生,竟然只是为了一己之私。
因为四大部洲的情况根本就不是如来讲的这个样子。西牛贺洲,如来自己扬言是“不贪不杀,养气潜灵”,其实是妖魔乱世,强盗横行。唐僧四人西行路上,到万寿山五庄观就是西牛贺洲了,这一路上不知有多少妖魔鬼怪,就算是靠近灵山都是如此,比如:玉华县的狮子精、金平府的犀牛怪、百脚山下的蜈蚣精、铜台府抢劫寇员外家的强盗……,太多太多了。至于如来想送经过去普度众生的南瞻部洲,如来描述是“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可唐僧四人一路西来,所有的国家无不称赞南瞻部洲的大唐是“天朝上国”“中华大国”,十分景仰,历史上也是著名的“贞观之治”。如来之所以说谎,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私利:他想把自己的佛教思想远播“东土”,因为东土大唐“天高地厚,地广人稠,……,(但是)不遵佛教,不向善缘,不敬三光,不重五谷”③。人多物多钱多,但又不敬佛祖,如来不甘心失去这么大的潜在市场才想传经过去的!但如来又怕把“经”送去后被人轻视了,才千方百计让东土大唐派人历尽艰辛来“取真经”,这叫“欲擒故纵”。这所有的一切,悟空也看出了端倪。过狮驼国时,悟空使出浑身解数,也没能斗赢大鹏精,不禁心灰意冷:“悟空凄凄惨惨的,自思自忖,以心问心道:‘这都是我佛如来坐在那极乐之境,没得事干,弄了那三藏之经!若果有心劝善,理当送上东土,却不是个万古流传?只是舍不得送去,却教我等来取……’”④
更有意思的是:如来明明答应传给东土大唐“三藏”真经,但等到唐僧师徒来取经时,却只给了一藏之数,“如来吩咐阿傩、伽叶:‘将我那三藏中,三十五部之内,各检几卷与他,教他传流东土,永注洪恩。”阿傩、伽叶心领神会,“在藏真经,共三十五部,各部中检出五千零四十八卷(合一藏之数),与东土圣僧传留在唐。’”⑤更有甚者,一些重要的经文,如总数一百卷的《金刚经》《法华经》分别才传了一卷、十卷给东土,东土之人如何拿这百里挑一、十里挑一的经文来普度众生,如来是不管了。堂堂佛祖,说话也不算数,说好的“三藏”成了“一藏”,重要的经文百里挑一,这和世俗无赖有何区别?难怪巴赫金说:“国王和小丑生来都是同一命。”⑥在《西游记》中,如来的满口善言、普度众生就好似给国王加冕,而暗中的包藏私利、最终的言而无信好比是脱冕。“这种狂欢式的加冕和脱冕,意指着任何制度、任何神圣、任何权威都有令人发笑的相对性,使一切被神圣化、崇高化的东西脱离等级森严、消除了神圣权威,瓦解官方的、庸俗的主流意识,实现了身份与对话的平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由的、平等的、民主的精神。”也难怪悟空大闹天宫时喊出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口号。
二、话语的狂欢
《西游记》大胆地用喜剧的语言把严肃的宗教题材作品从虔诚、严肃、高雅、禁忌中解放出来,打破语言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用民俗化的广场语言、戏谑的时尚语言来象征、模拟、讽刺、幽默现实。“这样的言语摆脱了规则与等级的束缚以及一般语言的种种清规戒律,而变成一种仿佛是特殊的语言,一种针对官方语言的黑话。”⑦
唐僧师徒十三年跋山涉水,来到灵山求经,本来是一件隆重、神圣、严肃、高洁之事,可这真经的主人——如来却纵容手下——阿傩、伽叶索要贿赂。没有钱财,阿傩、伽叶就用白纸来糊弄唐僧师徒,直到唐僧送出从长安带来的紫金钵,阿傩、伽叶才拿出真正的经书。对此,直性子的悟空在如来的大雄宝殿叫嚷对质时,如来不仅毫无愧疚之意,一方面护短手下,玩弄文字游戏说什么:白本者,乃无字真经也,倒也是好的。真是话语权在手,就可以混淆黑白。一方面他大言不惭亲口承认:“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平安,亡者超度,只讨了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⑧诵一次收费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如来还觉得不合算,一副生意人的斤斤计较,利益至上,哪有半分慈悲为怀!这些言语,在《西游记》中就成了“特殊的语言,一种针对官方语言的黑话”,来象征、模拟、讽刺、幽默现实生活,真是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故事发展到这里,无不让人笑破了肚皮,笑岔了气。这种带有狂欢色彩的笑能让观众暂时脱离现实生活的束缚和困扰,从而获利一种心里的解脱,一种压迫被移除的快感。“狂欢式的笑的特性在于‘与自由不可分离的和本质的联系’。它显示了人们从道德律令和本能欲望的紧张对峙中所获得的自由。”⑨
不但如来,文本中其他神仙大多如此,其神圣的面具下都有着令人发笑的灵魂,所以说:菩萨妖精,妖精菩萨,本为一体,以出场较多的观音为例。文本第十二章,玄奘主持“水陆大会”,替唐太宗超度那些地狱里不能超生的亡魂,观音化身为疥癞游僧来观看,而法师(玄奘)在台上,念一会儿《受生度亡经》,谈一会儿《安邦天宝篆》,又宣一会儿《修功卷》。观音就近前来,拍着宝台,厉声高叫道:那和尚,你只会谈小乘教法,可会谈大乘乎?一个“拍”字,一个“厉声高叫”,可见当时观音毫无救苦救难之菩萨风范,全然气急败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玄奘念的经是小乘佛法,而观音要传的是大乘佛法,这不是一家人啊。观音只好当众表态,拍着台子说玄奘讲的经“度不得亡者超生,只可浑俗和光而已”,这不是说玄奘在欺骗世人,在欺君吗?这也把世俗高僧玄奘和佛门菩萨观音置入悖论之中——二人必有一人说谎——到底谁在骗人?
第十三回《陷虎穴金星解厄 双叉岭伯钦留僧》,玄奘路过双叉岭,被猛虎袭扰,刘伯钦出手相救,因此留宿刘伯钦家。第二天是刘伯钦父亲周忌,刘家就请玄奘做点佛事。第二天,玄奘“先念了净口业的真言,又念了净身心的神咒,然后开《度亡经》一卷。诵毕,伯钦又请写荐亡疏一道,再开念《金刚经》、《观音经》……”玄奘超度死者,用的必然是自己认为最有效、最熟悉的经文。他第一念的经是《度亡经》,这就是前一回在“水陆大会”上首先念的《受生度亡经》,而且这本经书在第三十五回又出现了一次,这一次的名字成了《受生经》。好好一本《受生度亡经》,却被作者拆成《度亡经》和《受生经》,其实是同一本经文,他特意用了个拆字障眼法,而且是有意的欲盖弥彰!这一伏笔旁击,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笔法实在是太妙。玄奘念的小乘佛法的经是能够消解罪业,超度亡魂的!而且作者还特意安排伯钦父亲托梦给三个亲人,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既然小乘佛法也能超度亡魂,那在“水陆大会”台前,说谎的就是观音菩萨。观音也是为了如来,不得不说谎,他不把玄奘的小乘佛法说得一钱不值,别人怎么会穿过千山万水去取如来的大乘佛法。
“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⑩《西游记》正是这样一部游走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神圣和世俗、高尚和下流之间的大众狂欢,只不过大多情况下是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伏笔旁击的话语逸出罢了。
三、思维方式的颠覆
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颠覆,他从不主张以一种力量、一种声音压倒其对立面,成为新的权威,新的中心,他承认处于边缘的力量、声音有其独特的价值。只有在狂欢节这一特定的氛围中,现有的秩序才得以消失,人的自由精神和放纵的欲望才得以体现。因此狂欢节的秩序是一种对现有秩序的颠覆和否定。放在《西游记》中,其最高尚、最神圣的取经事件其实可以用最世俗、最放纵的观点来解构、颠覆和否定。从取经的第一男主角玄奘出发,换个角度来解构这事,会有颠覆的效果:并不是权威的官方语言说法,玄奘是舍己为人、为君分忧、为民解愁,他是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去取经。
在“水陆大会”的台前,玄奘和观音就能不能超度亡魂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佛法辩论赛。观音见理论上无法说服大唐人,只好现出菩萨真身来!而且还特地在空中停留多时,时间长到吴道子可以依样作画。要知道,观音来长安寻找取经人时可是悄悄进村的。当时观音和木叉化身两个疥癞游僧,暂住长安的一座土地神祠,吩咐长安的土地和城隍等小神:汝等切不可走漏一毫消息。我奉佛旨,特来此处寻访取经人。借你庙宇,暂住几日,待访着真僧即回。要知道,去西天取经是惊天地、动鬼神、夺造化的一件大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观音本想干得神不知鬼不觉。
菩萨真身一现,玄奘无话可说,他不可能说菩萨在骗人啊!有谁会相信啊!所以等唐太宗问:谁肯领旨上西天拜佛求经时,玄奘立马站了出来。因为一来他被太宗封了高官——都僧纲;二来他收了太宗价值七千两银子的袈裟和锡杖;三来观音菩萨现身,说玄奘在“水陆大会”上讲的小乘佛法不能度鬼,那玄奘就有欺君之罪!玄奘不站出来去取西经,可能是死路一条!
玄奘接下取经的差事,回到洪福寺,在和几个徒弟的谈话中也流露了真意:大抵是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耳。这说的是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而关键是观音说谎骗大家,玄奘吃了哑巴亏却没法子讲清楚。所以徒弟问玄奘何时取经回来时,玄奘只能是模棱两可:或三二年,或五七年。这说明玄奘自己既没把握也没决心,只是先应付了眼前再说!而更有意思的是,到第二天唐太宗为他送行,临出去时问他“几时可回”时,玄奘一点也不模糊,用非常肯定、非常干脆的八个字回答:只在三年,径回上国。同一个玄奘,面对徒弟们时:或三二年,或五七年,没个定准。面对太宗:只在三年!玄奘还是高僧呢!这脸也变得太快!这话说得太滑稽可笑、太狂欢化了!当然,他昧心说三年,是为了安太宗之心,应付眼前!如果临行前玄奘照实说不知多少年才能回来,说不定太宗龙颜大怒,立即换人了。
在中世纪的欧洲,各种宗教仪式是虔诚、隆重、神圣的,而世俗化的民间节日圣诞节、复活节等则带有强烈的狂欢节色彩,此时,所有民众都摆脱了日常生活中的戒律清规,连基督教僧侣们也停止了日常的课业,彻底解脱,狂吃狂饮,一道狂欢,《西游记》就是中国神仙们的狂欢故事。在这大众狂欢中,原有的天、地、人、神、鬼秩序才得以消失,自由精神和放纵的欲望才得以体现。传经的人为的是自己地盘的扩大,取经的人是给别人逼得没办法!而对原本严肃性宗教题材的解构,让“狂欢化”成为《西游记》的内在特性之一:神仙也会说谎,唐僧并非完人。这种狂欢节的秩序是一种对现有秩序的颠覆和否定,是以一种独特的感觉视角体验时代,从中可以感受到纷繁万状的生活原生乐趣,将人类的生命力推向了极致,或许这也是《西游记》这部古怪离奇的小说可以和《红楼梦》并列为四大名著的原因之一吧。
注释:
①⑥⑦(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3页,第227页,第214页。
②③④⑤⑧吴承恩:《西游记》,岳麓书社,1987年,第51页,第78页,第595页,第751页,第750页。
⑨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8页。
⑩(美)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