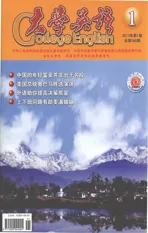一代君王,两行泪——以悲剧净化论解读莎士比亚《裘里斯·凯撒》
2013-03-26麦丽斯
麦丽斯 郑 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91)
一代君王,两行泪
——以悲剧净化论解读莎士比亚《裘里斯·凯撒》
麦丽斯 郑 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91)
《裘里斯·凯撒》是一部莎士比亚独具匠心的历史剧。这部名剧借用真实历史事件,看似描写古罗马时期,君王因暴虐统治不顾人民疾苦而没落,实则是借古讽今,针砭时弊地反应出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时期专制集权、贵族压迫和群众不满情绪三者之间纷乱复杂的关系。本文采用悲剧净化理论,从人民对凯撒的态度、人民对凯撒遇害心生的怜悯和恐惧,以及观众心灵获得净化的角度,分析指出莎士比亚其实是把人民当做这部戏的主角,唤醒人们正确的道德价值判断;同时对统治者发出警告:要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不然群众不满的情绪终会化作熊熊大火吞噬一切。
莎士比亚,凯撒,亚里士多德,悲剧净化
作者信息:麦丽斯(1990-),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引言
《裘里斯·凯撒》是一部莎士比亚独具匠心的历史剧。这部名剧借用真实历史事件,看似描写古罗马时期,君王因暴虐统治不顾人民疾苦而没落,实则是借古讽今,针砭时弊地指出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专制集权、贵族民主和群众情绪三者之间纷乱复杂的关系。剧中主要人物的性格都十分深刻而又多样。这部剧并非是简单反映历史的复仇剧,而是具有政治智慧的悲剧。诚如美国学者布鲁姆所说,“莎士比亚有意识地在他的戏剧中传达他的政治智慧,他有政治意图,他对美与感人事物的理解也首先建立在对公民社会的关切之上”(布鲁姆2003:111)。
一、亚里士多德悲剧“净化说”
深究剧本,莎士比亚的政治意图赫然纸上:这位戏剧巨匠正是希望对统治者起到警示作用。让人民感同身受的体验到当前的政治形式,从而使得他们的心灵透过剧中人物多舛的命运获得净化。这恰如其分地反应了亚里士多德《诗学》里提到的“卡塔西斯”,即悲剧的净化作用。
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前384-322)的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学》和《修辞学》里。他扬弃了柏拉图的观点,开创性地提出“戏剧摹仿说”,介绍艺术行为实则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摹仿。亚里士多德不仅在在艺术本体论方面,从生物学引进了有机整体论思想,而且还在艺术的社会公用方面,以观众接受心理学为核心,深入研究悲剧的心理根源和净化作用。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集大成思想主要包含在《诗学》里,以“摹仿说”、“有机整体论”、“净化说”、“艺术种类”为四大支柱。同时他给悲剧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
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亚里士多 1996: 20)。
然而亚里士多德并未对疏泄这种情绪的卡塔西斯效应做明确解释。这便为后世对这一说法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国外有古典主义时期的高乃依重新解释“净化说”。他认为“悲剧净化的实质就是引起怜悯和恐惧的情绪,并教导人们克制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从而避免精神上的冲突和损伤”(程孟辉1996:159)。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莱辛则认为这种净化反而加强了我们感受怜悯的能力。德国古典悲剧学说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则把净化与冲突结合在一起,认为冲突的结局是悲剧的结果,而在这过程中是对自我伦理的重新审视,不断分裂和解,最终达到统一。国内学者对这一理论的发展和阐释有两个主导看法,一是美学家朱光潜提出“净化说”,二是罗念生为代表的“陶冶说”。从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阐释莎翁经典《裘里斯·凯撒》,重新审视内嵌在文本中的含义,体会莎士比亚的政治哲学。
二、人民对凯撒的恐惧和怜悯
《裘里斯·凯撒》的主要内容围绕着古罗马奠基人凯撒(前100-44年)的被害展开,公元前44年,一手掌控大权局势的凯撒,在一次庆功宴上,三次拒绝献给他加冕的王冠。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执政官凯歇斯无法遏制嫉妒的火焰,他对权力的欲望无限膨胀,阴谋要将凯撒置于死地。他假借消灭“独裁者”为名,劝说素来以正直著称的首席执行官勃鲁托斯与他结盟,联合其他贵族,保家卫国,除掉凯撒。勃鲁托斯心系国家的安危,虽然身为凯撒好友,也不惜冒着“弑兄”的罪名,担任叛党领袖参加了谋反。执政官凯歇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清楚要想发动政变,必须依赖勃鲁托斯的声望,因此他言听计从,甚至最后连勃鲁托斯错误的判断也屈服了。勃鲁托斯被称为“最高贵的罗马人”,可是在政治领域却表现得十分天真,在凯撒被乱剑砍死之后,他非但没有同意处死凯撒的亲信安东尼大将,反而允许他收敛凯撒的尸体,并向公众做哀悼演说。安东尼借此机会煽动民众,让群众对对凯撒被刺的事件情绪不满,反对勃鲁托斯的呼声高涨。勃鲁托斯等人被迫逃亡,公元前42年腓利比一役,勃鲁托斯又犯了战略错误,全军覆灭,最终他不堪失败的屈辱自刎而亡。
这部高潮迭起的历史剧,让观众的心在观看时也随之不断起伏。凯撒和勃鲁托斯曾经都是时代的英雄,最后却落到满盘皆输的下场,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他们最后壮烈的死亡,在观众心里引起了恐惧感。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好的悲剧,首先不应该表现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因为这既不能引发恐惧,亦不能引发怜悯”,其次不应该表现“坏人由败逆之境转入顺达之境,因为这与悲剧精神背道而驰”既不能引起同情,也不能引发怜悯和恐惧。架构精良的悲剧应该介于两者之间,应该表现人物从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最重要的是“人物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后果严重的错误”(陈中梅1996:98)。凯撒本来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功臣,但是他输给了权力和欲望,把自己的缺点全数暴露在敌人面前,屈从于专制的魔咒。他本来有睿智的头脑和眼光,一开始便判断出凯歇斯是一个小人:“那个凯歇斯有一张消瘦憔悴的脸;他用心思太多;这种人是危险的”(莎士比亚1978:1.2.)。随后,从凯歇斯的口中,我们知道凯撒甚至三次拒绝加冕,给人一种正直不看重功名利禄的印象,但是之后剧情的发展中,他一步步在权力的诱惑下走下了神坛,他性格中的缺陷令他变得与一般民众无异。凯歇斯嘲笑凯撒也会生病,也会觉得害怕痛苦,“这位天神也会颤抖;他的懦怯的嘴唇失去了血色,那使全世界惊悚的眼睛也没有了光彩”。这样刻意的描述,拉近了观众与凯撒的距离,神化的王的性格是多样的,并非是单一的,不是由单一事件堆砌成的。莎士比亚笔下的凯撒,更多的表现出他的迷信和自傲,面对妻子凯尔弗妮娅的劝谏,他固执己见,坚持出门,还说:“凯撒一定要出去。恐吓我的东西只敢在我背后装腔作势;它们一看见凯撒的脸,就会销声匿迹”,凯尔弗妮娅不断苦苦哀求,请求他一定要留下来,凯撒再次说:“天意注定的事,难道是人力所能逃避的吗?凯撒一定要出去;因为这些预兆不是给凯撒一个人看,而是给所有的世人看的”(莎士比1978:2.2),可以看出凯撒对于自己的决定非常武断,他口中所言天意,正是他逐渐失去睿智头脑的表现,而这里他在说自己的时候,没有用第一人称“我”,全部都是第三人称的口吻,仿佛他已经不是自己,消失了个体存在的界限,而作者也好像是在借助凯撒的口吻,对所有居高自傲的统治者发出警告,如果任由这种负面情绪发展下去,那么将会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特别是作为统治者的观众会在心中扪心自问,担心自己也会落入类似下场。
亚里士多德给恐惧和怜悯的产生下了定义,“怜悯的对象是遭受了不该遭受不幸的人,而恐惧的产生是因为遭受不幸者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诗学》1996:97)。尽管凯撒这样一位高傲的君主有其缺陷,人们最终却对他的死充满怜悯。临死前他仍然如同钢铁一般坚韧,自比为辰星,坚持自己的主张,显示出一派王者的气度。面对威严的法律,他只说:“可是你不要痴心,以为凯撒也有那样卑劣的血液,会因为这种可以使傻瓜们感动的甘言美语、弯腰屈膝和无耻的摇尾乞怜而融化了他的坚强的意志。按照判决,你的兄弟必须放逐出境”,他的这一番话,使他与容易被人煽动的勃鲁托斯形成鲜明对比,只有君王有这样的魄力和行动力。之后,凯歇斯率领众人挥刀向凯撒砍下,这位君主却在看清勃鲁托斯也参与在谋害他的计划之中时,悲愤交加地说出:“勃鲁托斯,你也在内吗?那么倒下吧,凯撒!”(莎士比亚 3.1)。最后这一声充满悲凉的喊叫,他仿佛是让不甘心的自己瞑目,曾经是彼此信任的兄弟,一心提携扶持的大将,其实一直在背后参与谋害自己,这样的剧情,不得不使人产生畏惧和怜悯之情。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怜悯的情绪正是产生在“惨痛事件发生在近亲之间,比如发生了兄弟杀死或企图杀死兄弟,儿子杀死或企图杀死父亲,母亲杀死或企图杀死儿子、儿子杀死或企图杀死母亲或诸如此类的可怕事例”(陈中梅1996:105)。人们不免要对面对被亲信背叛的凯撒产生同情,这位战功赫赫的将军本应战死沙场,完成他的使命,最后却完全陷落在权力的角逐之中,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者。而做出这一切的,是被所有人尊敬,又一位神化的大将军——勃鲁托斯。所以不难看出莎翁嘲讽的态度,把他们都描绘成沦落为专制独裁的奴隶,而且发出警告,要对身边暗藏的杀机提高警惕。
三、从民众的态度中反思,得到净化
莎士比亚“在描写人物和生活时并没有表明自己对问题的观点,而是把问题留给人物,让他们用自己最合适的方法去解决”(Bahktin 1984:6)。这场政治明争暗斗,不仅让上层的精英人物元气大伤,其实真正受苦的还是无辜的民众。通过阅读文中民众的态度,身为普通群众的观众心中的情绪也能得到梳理和净化。
《裘》剧正是用于教育和净化的作用。一开始,莎士比亚不是选择奢华的宫殿或者凯撒凯旋的场景,而是把视角放在罗马的街道上,护民官弗莱维斯对应该受他保护的民众第一句话就是:“去!回家去,你们这些懒得做事的东西,回家去。”不仅毫无同情,反而充满骄傲蛮横,对民众的境遇毫不关心。之后,弗莱维斯质问这些市民:
冷酷无情的罗马人啊,你们忘记了庞贝吗?……现在你们却穿起了新衣服,放假庆祝,把鲜花散布在踏着庞贝的血迹凯旋回来的那人的路上吗?快去!奔回你们的屋子里,跪在地上,祈祷神明饶恕你们的忘恩负义吧,否则上天的灾祸一定要降在你们头上了。
民众似乎对于谁当政态度摇摆,只要有新的执政官就很快忘记之前的一任,可是而实际上民众并非是“冥顽不灵”的东西,他们其实关心的只是谁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谁更在乎他们的利益,市民乙面对护民官的拷问,只说:“不瞒您说,先生,我要叫他们多走破几双鞋子,让我好多做几注生意。可是实实在在,先生,我们今天因为要迎接凯撒,庆祝他的凯旋,所以才放了一天假。”可见庞贝当政的时候,罗马人过的并不幸福,他们本来期待的生活没有如约而至,所以当有一位新的当政的人出现的时候,未来的生活使人民重新燃起希望,走到街上去庆祝,迎接新的生活。
但是这样平静的生活并没持续多久,很快,又一场暴风骤雨袭来,凯撒死于陷害,勃鲁托斯和凯歇斯等人当政。民众不明事理,只能被动接受结果,当他们想要听到背后的原因时,就出现了《裘里斯·凯撒》这部剧中最出名的勃鲁托斯和安东尼的广场演讲。勃鲁托斯曾经在谋划杀掉凯撒时,口口声声地强调:“只有叫他(凯撒)死这一个办法;我自己对他并没有私怨,只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莎士比亚 1978:2.1),但是他其实并没有把民众的利益纳入考虑范围之内,从他对民众说话的内容这一点便昭然若揭:“各位罗马人,各位亲爱的同胞们!请你们静静地听我解释。为了我的名誉,请你们相信我;尊重我的名誉,这样你们就会相信我的话。”他所言之事的全部都是为了他的荣誉和利益,他的名誉甚至高于事情的真相。“为了罗马的好处,我杀死了我的最好的朋友”,当人民听到这样的言辞时,他们不得不选择相信,因为他们渴望和谐宁静的心已经等了太久太久,但是民众并不是愚昧无知,之前他们一听到有新的接班人便举国同庆,然而现在他们变得明智,听到勃鲁托斯的保证之后,他们的反应十分具有讽刺意味:“市民丙:让他做凯撒。”“市民丁:让凯撒的一切光荣都归于勃鲁托斯。”他们知道即使换了一位君主,似乎也不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不过是在君主这个位置上换了一个人,带来的结果却不尽相同。当听到安东的对于凯撒的死因之后,他们的表现则更加耐人寻味:“市民乙:仔细想起来,凯撒是有点儿死得冤枉。”“市民丙:列位,他死得冤枉吗?我怕换了一个人来,比他还不如哩。”剧中的凯撒之死,引起了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同情,如果说这个时候剧里的民众唤起的是一丝同情,他们之后的变化就是激起人们的恐惧心理。听过安东尼宣读凯撒的遗嘱,民众认为所有的一起都是由于勃鲁托斯引起,他们扬言要烧掉勃鲁托斯的房子,
市民甲:再也不会有了,再也不会有了!来,我们去,我们去!我们要在神圣的地方把他的尸体火化,就用那些火把去焚烧叛徒们的屋子。抬起这尸体来。
市民乙:去点起火来。市民丙:把凳子拉下来烧。
市民丁:把椅子、窗门——什么东西一起拉下来烧。
民众开始逐步失去理智的价值判断,甚至丧失最起码的判断标准,变成疯狂杀戮的刽子手,
市民乙:撕碎他的身体;他是一个奸贼。
诗人西那:我是诗人西那,我是诗人西那。
市民丁:撕碎他,因为他做了坏诗;撕碎他,因为他做了坏诗。
看到这一幕,不仅是普通的人,连统治者恐怕更要为之震动,如果不正确对待民众不满的情绪,最后仇恨的火焰会撕裂一切,即使是真理也都将不复存在。
莎士比亚创作《裘里斯·凯撒》正处于1599-1601年之间,这个期间的英国正处于从农本主义向重商主义的转型期,当时英国的政权主要掌握在贵族手里,政治模式非常落后,而且道德价值标准也没有得到统一。田俊武教授指出莎翁的这部剧表现的是:“莎士比亚是借这部历史剧揭示在一个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年代,人们失去了统一的价值标准,没有了绝对的对与错,而这种价值观的缺位是会给社会造成动荡不安的”(田俊武,安琦2011:94)。但是莎士比亚的目的不止于此,他希望观看戏剧的人民,能够在心底产生共鸣,引发他们的怜悯和恐惧,从而对这些情感进行反思和梳理,从而能够达到净化的目的,使得他们为自己能获得秩序正常的生活而努力。亚里士多德所言,“悲剧之所以引发怜悯和恐惧,其目的不是为了赞美和崇扬这些情感,而是为了把它们疏导粗去,从而使人们得以较长时间地保持健康的心态”(《诗学》1996:228)。对于凯撒遇刺的怜悯和恐惧,以及民众反应的感同身受,能把长期积攒起来的负面情绪都在观看的过程都排泄出去,剧中的情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就如同服下一剂良药。
四、结语
苏格拉底曾说,美德是对恐惧的净化,净化的对象包括肉体和灵魂,净化的目的是消除积弊,保留精华。莎士比亚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场视听盛宴,同时也为他们的心灵提供了饕餮大餐。凯撒作 为一代君主,输给自己的缺陷和错误,武断地判断局势,导致他失去了自己的优势,最后只能沦为政治棋盘上被丢弃的棋子。人们为他最后的境遇抛下同情的泪水,统治者也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严防沦落同样的命运。而剧中民众的表现,更是对当时英国社会的醍醐灌顶,从让人同情的受压迫者,到令人发指的疯狂杀戮者,民众的过失在于一次道德判断的失误。透过分析这部历史剧,观看的统治者和民众的心灵获得了一次彻底的洗涤。莎士比亚不愧为一代大师,他的主张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Bakhtin,Mikhail (1984).Problems of Dostoevsky’ s Poetics.Ed.&Trans.by Caryl Emers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布鲁姆(美)(2003).政治哲学与诗[C].张辉.巨人与侏儒.北京:华夏出版社。
程孟辉(1996).西方悲剧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莎士比亚(英)(1978).裘里斯·凯撒[M].莎士比亚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田俊武,安琦(2011).《裘里斯·凯撒》与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
亚里士多德,陈中梅译注(1996).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