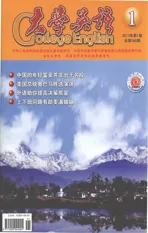从生态伦理学角度分析《纳尼亚传奇》里非人类形象的塑造及意义
2013-03-26李立人
李立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91)
《纳尼亚传奇》的作者C.S.路易斯(CliveStaplesLewis,1898-1963)既是英国著名的文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学者、文学批评家,也是20世纪公认的重要基督教作者。他毕生从事文学、哲学、神学的研究工作,对中古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造诣尤深,其作品深受基督教思想以及中古文化的影响。因而国内外学者对其著名奇幻作品《纳尼亚传奇》的评论和研究意见分歧,主要呈现两种倾向:其一,《纳尼亚传奇》是一部类似《天路历程》的基督教寓言,该作品载有说教寓意和劝教功能;其二,《纳尼亚传奇》是一部神话故事,从希腊神话、北欧神话、中世纪传奇和圣经故事汲取了丰富的文学养分,是一部极富文学想象的魅力之作。而本文以生态伦理学中非人类中心主义学派的相关理论为框架,从生态伦理角度分析《纳尼亚传奇》里非人类形象的塑造及其意义,不但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解读视角,同时在生态问题日趋严重,人与自然日益疏离的今天,路易斯借助能言动物的形象,批判了过度膨胀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关系,对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具有一定的启示。
一、生态伦理批评
自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以来,在提倡理性、张扬人性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人的主体性得到重视,人类对自然的驾驭作用被广泛宣扬,“天赋人权”的思想盛极一时。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是万物的主宰者,是高等的、有智慧的生命,而其他生物则是低等的、没有智慧的生命,因而必然受到人类的统治和支配。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使人成为了唯一的言说主体,剥夺了自然的话语权,疏离了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加剧了两者的分崩离析甚至使两者转向极端对立的两端。人类的欲望是个无底洞,结果是其它存在物必须不断地耗尽自身来满足人类的贪欲,因而人类在不断向自然索取的同时,对自然的破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日渐疏离。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表达了对自然和人类关系的重新确认,生态中心主义应运而生。生态中心主义强调将文学研究扩展到整个生物圈,从全新的视角,重构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关系,将道德关怀的范围从人类社会扩展到了自然界以及自然界的所有自然存在物,迫使人类从主体地位退位成为万物的一支,成为万物平等的一员。人与世界以及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不再定性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
二、《纳尼亚传奇》中能言动物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嘲讽
《圣经﹒旧约》里关于“创世纪”的传说中上帝授权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1:26),从而确立了人类对自然的管辖权;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主人公之口喊出:人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将自己视为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认为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甚至就连地球本身——都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Carson1962)。然而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定位。而生态中心主义否认人类的优越性,认为“人类是地球共同体的普通成员,自然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每一个有机体都是生命的中心,生物共同体中的各个物种之间平等,因而要求人类尊重自然,维护生物共同体成员的利益。而人类天生优越论只不过是人类对自然根深蒂固的偏见而已”(P.Taylor1986:168)。在《纳尼亚传奇》中,C.S.路易斯借助能言动物的形象,批驳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对人类自认为至高无上的权力进行了讽刺。
作为当代奇幻儿童文学的经典作品,《纳尼亚传奇》塑造了众多非人类形象,如狮王阿斯兰、白女巫、纳尼亚的居民——各种能言动物,如羊人、海狸夫妇、老鼠将军等。各种非人类形象都被赋予了灵性与心智,甚至被表现为英雄和神灵。在这些能言动物身上,读者看到的是与人类同样的理性、智慧和对理想的追求。动物们在国家的事务安排和社会地位上与人类是完全平等的,甚至老鼠也可以出任将军,他们与人类一样拥有公民的权利。极具讽刺意义的是,人类却成了纳尼亚建立之初的“第二个笑柄”——在动物们眼里,人类成了“大莴苣”(路易斯2001:105)。 安德鲁舅舅作为第一个进入纳尼亚的成人,竭力让自己不去相信眼前这和谐的一切。深受人类中心主义影响的他不愿放弃现实社会里人们对动物的态度,因而无法理解动物们的话语,以至于被孤立于这奇幻世界里。所以,人类将自己与自然割裂开来,结果只能是自然对人类的惩罚。
C.S.路易斯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的质疑与批判,还集中体现在阿斯兰这一形象的塑造上。纳尼亚奇幻世界里的主宰者不是人类,而是一头狮子阿斯兰,这本身便是对“人类主宰论”的挑战。而阿斯兰无疑是路易斯在《纳尼亚传奇》里设置的伟大形象。它与上帝具有同样的神力,“以最美妙的声音创造了星星、太阳、大地、植物和动物,并挑选了每种动物中的一对,让其成为能言的智慧动物,与树神、农神、河神和人类一起成为纳尼亚的居民”(路易斯2005:105)。阿斯兰身上集中了上帝的博爱、荣耀乃至睿智,人们没有见过它,但在纳尼亚的存亡关头,它会回来。反而是身为人类的艾蒙德,屈服于内心的私欲,企图成为纳尼亚的创造者和独裁者,在女巫的引诱下出卖了阿斯兰和自己的兄妹。在艾蒙德身上体现的是人类的欲望与罪恶:人类在文明进程中迅速异化,急欲超出自己的限度去获取一种权利,去表达驾驭他人、驾驭自然的欲望。狮王阿斯兰为了救赎艾蒙德,与邪恶的白女巫达成协议,代他受死,并宽恕了艾蒙德的背叛,且告诉艾蒙德的兄弟姐妹“过去的事就不必跟他提了”(路易斯2005:135)。在狮王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圣爱的闪光。而路易斯将纳尼亚王国公正而博爱的创建者和管理者的形象赋予一头雄狮,这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动物,与自然界万物的关系。
在《狮子、女巫和魔衣橱》中,路易斯还安排了一个巧妙的对比:在狮王阿斯兰的正义之师中,有一个人头牛的形象(abullwiththeheadofman),而在邪恶白女巫的乌合之众里,却是牛头怪的形象(bull-headedmen)。前者是具有人类头脑的动物,而后者是长着人身却没有思想能力的怪物,这其中所蕴含的意义是深刻而发人深思的。前者是动物,却被赋予了人类的灵性与心智,拥有理性、智慧和对理想的追求,这让人联想到纳尼亚朴实善良的动物居民,为读者带来愉悦和希望;而后者虽拥有人类的身体,却缺失善恶是非准则,只有无尽的杀戮欲和掠夺欲,这些“那些看上去像人又不是人的东西”(路易斯2005:64),为纳尼亚带来的是邪恶和寒冷。究竟是人头使它/他成为人还是人身决定他/它成为人,路易斯虽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是其对无休止贪婪地掠取资源,压制残害其它物种的所谓的万物主宰者的嘲讽溢于言表。
三、《纳尼亚传奇》里能言动物对生态文明的诉求
生态伦理学家施韦泽曾经说过:“把爱的原则扩展到动物,这对伦理学是一场革命。”他还强调:“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才是伦理的”(施韦泽2003:9)。人和自然中的其他生物之间不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C.S.路易斯在《纳尼亚传奇》中塑造了一系列充满奇幻色彩的非人类形象,对这些非人类形象,路易斯充满着敬畏与尊重,并感悟着这些生命的存在价值。他不把他们看作是比人类低等的动物,在他看来,动物之间的感情,人与动物之间的感情可能还会比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更加深厚、真挚。小说中那些普通的老鼠,在帮助阿斯兰咬断捆绑它的绳索时立下大功,于是就被奖励成为能言老鼠;在统领的“雷佩契普”身上,读者看到的是骑士风度和勇敢精神;羊人“图姆纳斯”与人类露西建立起纯真的友情,并为这份情谊舍生取义……在路易斯创造的这些非人类他者的形象中,读者看到的是多元的、多层次的人文精神。
纳尼亚故事的时代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化武器,却用来吞噬人类的生命,摧毁其生存环境。为了远离战火而被送往乡下的孩子们,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到纳尼亚的传奇世界,一幅神奇瑰丽的画卷由此展开:这里的太阳年轻又温暖、树木能走动、野兽会说话、神圣的水显灵了……这是一个众生平等、万类竞自由的世界。纳尼亚王国创立之初,阿斯兰便嘱咐能言动物对那些哑兽“要善待它们,珍惜它们”(路易斯2001:96)。在《魔法师的外甥》中小主人公堤格雷对安德鲁舅舅拿豚鼠做魔法戒指实验的行为深恶痛绝,这也体现了作者对人类不公正对待动物行为的批判。那些被阿斯兰唤醒的森林之神、河神、树神、仙女与所有的动物、鸟类及人类构成了一个生态和谐的理想王国。在这个理想王国里,大自然拥有高乎一切的神奇力量,精神和灵魂的存在,就把时间万事万物全部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可以说,《纳尼亚传奇》借着奇幻的翅膀,传递着万物有灵、生命平等、敬畏生命的生态观。
反观现实社会,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开采,使自然灾害频发,由生态危机而引发的生存危机使人越来越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因而现代生态审美着眼于人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审美关系,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旨趣,将世间万物视为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生态共同体。俄罗斯思想家奥斯宾曾提出:“我们认识到了地球——它的土壤、山脉、河流、森林、气候、植物和动物——的不可分割性,并且把他作为一个整体来尊重,不是作为有用的仆人,而是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物”(何怀宏 2002)。从生态伦理角度切入《纳尼亚传奇》,读者不难发现,这个灵性飞舞的奇幻世界所昭示的作者的平等意识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审美观。
四、结语
《纳尼亚传奇》中塑造的非人类形象体现了现代社会追求平等、自由的理念,成为人类理想社会的代言人,摒弃了人性中的贪婪与异化,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存。作为现代奇幻文学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纳尼亚传奇》呼吁人们敬畏生命,回归自然,重构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关系,建设绿色生态文明,这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与自然日益疏远的现代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Holy Bible (2009).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Taylor, Paul W. (1986). Respect for Nature: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S.路易斯(2001).魔法师的外甥[M].米友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C.S.路易斯(2005).狮子、女巫和魔衣橱[M].陈良廷,刘文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阿尔贝特﹒施韦泽(2003).敬畏生命[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何怀宏(2002).生态伦理——精神资源和哲学基础[C].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