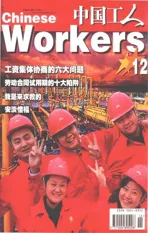工资条例:让每一个劳动者都有“话语权”
2010-11-18任小平
任小平
工资条例:让每一个劳动者都有“话语权”
任小平
最近,各类媒体都在关注《工资条例》,焦点聚在可能会将“工资协商”和“同工同酬”这两个东西写进去。
不可否认,这两个东西都是目前在分配领域中最关键、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众所周知的事情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GDP蛋糕越来越大,2009年达到33万亿元,“蛋糕”的“膨胀速度”(增速)平均达到9.8%。这成为同期世界经济的奇迹。但与奇迹相伴的问题就是,广大民众,特别是劳动者并未高兴起来,反而出现了“生活越好、牢骚越多”的怪现象。
由此,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是人不知足,还是制度出了问题呢?如果是人不知足,另当别论,但如果是后者,那我们是否需要做点什么?尤其是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是不是到了该有所作为的时候了?
面对日益增多的“牢骚”,人不知足无可厚非。因为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不知足”才有发展的动力,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不断的“不知足”中得到了发展。就这一点来看,我们不应该去说教让劳动者要“知足”。
当然,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让劳动者“知足”的理由不是没有。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和改革开放之前比较,大家的工资都翻了“几倍”。以笔者为例,1996年参加工作,工资不到500元,现而今已经是5 000元了,工作14年,涨了有10倍,按说很快了吧,也挺知足的。但事实就是笔者知足不起来,为什么呢?原来发现自己身边的人,不管是学业、岗位还是技能有没有差距,他们的工资都比笔者高,特别是一些在金融、央企乃至政府部门的“哥们儿”,每每见面,实觉钱包“汗颜”。
笔者终于明白,原来“生活越好,牢骚越多”,不是自己不满意自己,而是和别人比了之后,失落感很强烈。理论上的话叫“相对公平感”缺失。为什么“失落”呢?技不如人,想想不应该,怎么也算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吧;是单位不好,好像也不是,学校可是“黄金机构”,“旱涝保收”。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经过思索,问题不在于技不如人、单位不好,而是分配制度出了问题。
在经济学的理论中,好的分配制度应该效率优先;在社会学的理论中,公平才是分配制度好坏的标准。如果用马克思讲的一句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分析的话,那就是好的分配制度应该把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融合起来,那就是中央提出的“效率和公平”。所以,只有效率,没有公平,效率最终会被公平毁掉;相反,只有公平,没有效率,公平本身也没有基础,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锅饭”就是这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的分配制度呢?从1978年开始考察,有学者将它分为四个阶段:一是1978年至1984年,解放思想,恢复按劳分配原则;二是1985年至1991年,打破两个“大锅饭”(企业对国家,职工对企业),调整分配关系;三是1992年至1999年,确立改革目标,培育新的分配机制,后来叫作“市场机制决定、企业自主分配、职工民主参与,政府监控指导”;四是2000年至今,工资分配制度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核心就是强调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要求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从四个阶段的提法来看,应该是符合“效率”和“公平”两个标准的,说明制度的价值偏好是没有问题的。既然制度本身没有错,问题只能出在是制度在执行中“走偏了”。
从现实的情况看,制度“走偏”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是以分配为例,“蛋糕”现在做出来了,并且很大,说明我们的分配制度还是有效率的;但是“蛋糕”谁来“切”?怎么“切”?“切”多少就很有讲究了。
理论上,政府、资本和劳动者共同在“切”蛋糕,都在“蛋糕”做大的过程中分到了一份看起来还不错的“好处”。在“切”的比例方面,尽管各方的数据不一致,但公认的感觉是,劳动者的比例拿得最少,不仅表现在绝对数的比例方面,还表现在比例的增长幅度方面,劳动者都是拿得最少的。这就是问题的根本,“公平感”的缺失。
“公平感”缺失的后果是什么呢?从大的方面看是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这方面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事例了;而从小的方面看,就是我们的“效率”可能会被“公平”毁掉。
在这次的金融危机中,我们的感受更为深刻。原来依赖的出口大幅减少,原来要卖给境外的东西卖不动,以外向型为主的企业,特别是中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当一部分不能经营或者不能有效经营,置身其中的工人,主要是农民工不得不卷起铺盖回家,就业形式一下就严峻起来。
面对“外需”严重不足的现实,我们开始老调重弹,又把内需搬出来,并且以从未有过的急迫心情来需要内需。观念转过来了,但市场不认账,发现很多东西买不起或者不愿买,原因不是不需要,而是“没钱”,这就是“内需不足”。“内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办?政府搞了以4万亿为内容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经过1年,成效确实很明显,中国经济走出了漂亮的“V型反转”,全年增长率达到了8.7%,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奇迹。
但奇迹的背后是什么呢?是真实性内需贡献的还是政府在“买单”呢?后者的比重可能大一些。为了让内需“旺”起来,成为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引擎”,政府想了很多的办法,最核心的就是要让老百姓有一个明确的预期,一个敢于花钱的预期。于是,在政府的主导下,2009年我们基本上建立了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再加上政府前几年做的一些工作,现在基本上实现了“种地不交税、上学不付费、看病不太贵、老了无所畏”,特别是“老了无所‘畏’”,更关键。为什么无所“畏”呢?因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一个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老有所养了。再加上温总理讲,本届政府要做到人均120元,敢花钱的预期就更明确了。
预期明确以后,但内需仍然没有“旺”起来。原来是没钱花。为什么没钱,因为收入低。这么大的“蛋糕”收入都去哪里了呢?原来人们发现,政府和资本拿得很多,劳动者拿得不多。怎么解决?就是要把这个比例给调过来,政府让一点,资本少拿一点,劳动者增加一点,这就是中央提出要加大初次分配比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今年政府工作的一个重头戏就是“分配”,用温总理的话讲就是,“做大蛋糕是政府的责任,分好蛋糕是政府的良知”。而媒体热炒的《工资条例》,应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寄予厚望的,是政府责任之后的“良知”行动。
但我们需要更深入思考的是,是不是有了《工资条例》,分配失衡的问题就能解决呢?比较正确的观点是,《工资条例》解决不了所有的分配问题,但没有这个东西所有问题都解决不了。从这个角度看,《工资条例》被赋予了“破题”的功能,如何解题,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摸索。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重大疑难问题的解决显然不能仅仅靠一个制度,这是不现实的。既然如此,《工资条例》的目的是什么呢?调节失衡的分配制度或许太过于功利,并且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如果说《工资条例》能够出来的话,笔者认为,其最大的意义应该在于:让每一个劳动者都有说话的权利,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感觉到劳动体面,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感受到做人的尊严。但对每一个劳动者而言,怎么说话呢?
首先,要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说话。
“资本+劳动=利润”。公式很简单,也很“骨感”,但利润中有多少是资本贡献的,有多少是劳动贡献的却“纠缠不清”。资本家说,没有我的资本,你就没有工作,还奢谈什么工资;劳动者说,没有我的劳动,你的资本也赚不了钱。看来各有各的道理,如果双方要“较真”,可能都没有好处。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经济学家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谁“稀缺”,谁的贡献就大,也就可以多拿一点,这就是资本雇佣劳动的由来。
看来,资本之所以能够雇佣劳动,根源在于它很稀缺。既然稀缺,大家都想要,谁给的条件优惠就给谁,资本的“买方”地位由此形成。
面对资本的强势,原本在计划经济时代很有“话语权”的劳动者不得不“妥协”。“妥协”的后果就是在滋长“资本持续傲慢”的同时,不得不承受低于预期的工资价格。一旦劳动者对工资表现出些许的不满,严重的后果就是“走人”。资本之所以敢这么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劳动者后面有N个替补在等着上岗,这就是为什么“富士康”尽管在员工“九连跳”后,每天的厂门外还有千八百的人等着进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也是资本的底气所在。
所以,要让劳动者能够说话还真不容易。谁让你“过剩”呢?从效率的角度讲,面对过剩的劳动力,劳动者“噤声”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如果把这个问题跳出效率的范畴考察,问题就很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公平”的缺失,直接的后果就是破坏效率可持续增加的社会环境。请不要忘记,富人之所以是富人,归根到底是他的财富能够在社会环境中得到保持。如果这个环境被破坏了,富人也可能会“一无所有”。因此,我们讲“企业家要有道德血液”。正如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所言,如果社会财富只集聚在少数人手里,是不公道的,注定是不得人心的,必将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理论上,富人的道德血液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发性的培养道德意识,并将意识融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但和资本要素的所有者是人一样,劳动力要素的所有者也是人。既然大家都是人,“生而平等”应该是一个基本的人权理念。因此,企业家不能把劳动力要素和其他要素一样等同管理,要结合劳动力要素的“人”化特质,寄予更多的人本关怀,要让每一个劳动者有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二是遵循法规,在程序合法的情况下获取收益。过去的经验表明,在资本“贪婪”的驱使下,自发性的道德意识几乎没有,而约束的法律机制又没有到位。因此,《工资条例》的首要目的就是要给劳动者一个能够说话的权利,让资本家明白,给劳动者说话的权利,不是施舍,而是制度的要求。如果一个连制度都无所畏的资本,估计也长不了。
其次,要让每一个劳动者都“敢”说话
《工资条例》给予了劳动者能够说话的权利,但劳动者是否将能够转变为行动,这涉及到一个说话“胆量”的问题。换句话说,面对资本的强势,劳动者有没有说话的“底气”?
理论上,“底气”是否足够的条件有两个:(1)家底是否殷实。家底越殷实,说话的底气越足,这就是大家都在说“富二代”有点找不着北的一个重要原因,“钱多胆壮”;(2)制度鼓励。好的制度应该是让好人变得更好,让不好的人无处遁形。这样,制度的价值功能才能彰显,制度的权威才能得到认可,制度的执行才能不被“规避”。
《工资条例》出台,无疑给了劳动者一个能够说话的机会。面对过剩、并且在将来一段时间还有可能继续过剩的劳动力市场,劳动者能不能把制度赋予的权利变为行动,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因素需要分析,还有许多的技术需要予以支撑。因此,劳动者要把权利变为行动,关键是要有权利的意识,并不断培养对权利意识的维护能力。
受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劳动者普遍存在一种对资本、对制度、对权力的敬畏。正是这种敬畏,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敬畏变成一种服从乃至“奴从”,后果就堪忧了。
那么,劳动者的权利意识如何培育呢?社会的说教和制度的引导固然是重要的,但关键还是要自己把自己当回事。权利是天生的,但天生的权利更需要后天的保护。因此,劳动者就要做到有所需、有所不需。在生存面前,“面包固然重要”,但比面包更重要的还有尊严和价值。古人言,“怜者不受嗟来之食,志者不饮盗泉之水”;我国著名散文家朱自清教授也有一句话:“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
现实当中,劳动者为了一份“面包”,不惜牺牲尊严乃至生命的现象也是有的。这既是劳动者的不幸,也是制度的不雅,更是社会文明的“污点”。如何改变,首要的就是要劳动者去树立自己的权利意识。自己的权利只有自己争取,权利才能受到尊重,侵害权利的人才能有所畏惧。
与此同时,劳动者还应将个体的权利融入集体的权利中予以表达,并以集体的意志发声。中国工会作为劳动者的“代言人”,既是劳动者权利意识培育的重要主体,更是劳动者权利维护的重要保障。因此,要把最广大的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胡锦涛总书记也明确指出:工会要把表达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作为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既是广大职工的迫切需求,也是执政党的殷切期望,更是中国工会需要承担的神圣使命。
面对日益趋紧的劳资关系,执政党对工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也承诺将更多的资源和手段赋予工会组织,要把党政所需、职工所急、工会所能的事情交给工会组织去办,要不断扩大工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工资条例》将工资协商引入的制度预期就是,要让广大职工不仅“能”说话,还应该“敢”说话。这就要求广大劳动者,在自觉培养和维护自身权利意识的同时,更加自觉地将个人的权利意识融入到工会组织中,并通过工会组织更加强有力地维护自身的权益。只有这样,劳动者的个人权利才有保障,劳动者的尊严才能得到有效的彰显,劳动关系可持续性和谐才有基础。
最后,要让每一个劳动者都“会”说话
《工资条例》赋予了职工“能”说话、“敢”说话的权利,但更重要一点是,劳动者要“会”说话。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实现劳动者自身权益,实现劳资双赢和劳资和谐的关键手段。
就总体上的趋势而言,劳资共赢是双方诉求的根本目标。但在具体的时点上,劳资利益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面对具体利益的纠葛,理论上的解决办法只有两个:一是“鱼死网破”;二是学会“妥协”。比较而言,“鱼死网破”不应提倡,除非触及最基本的底线,否则不应出现。因此,作为理性的利益主体和社会成员的劳资双方,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要学会“妥协”,在“妥协”中共生、共享、共成长。这就是《工资条例》中所衍生出的另一个制度偏好,以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利益问题、权利问题。
所以,劳动者要“会”说话,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学会“协商”。冲突总是源于“误解”和“不信任”。消除“误解”和“不信任”,也就减少了很多冲突。要做到这一点,劳动者就应该自觉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培养协商的意识。意识决定行动,好的意识才有好的行动,也才有好的结果。尤其是在尊严面前,单纯的以生命做赌注的利益诉求方式绝对不值得鼓励。因此,敬畏生命才能推崇协商。公民社会的一个最大进步就在于社会性的协商机制。协商的目的不一定就是要达到某一特定的目的,更优的制度内涵在于双方的沟通,并通过沟通来弥合分歧,消除误解,累积信任。这在我国当前的劳资关系状态下尤为紧迫,也是制度层面应予以高度重视的内容。
二是要培养规则意识。协商的目的是凝聚共识,无论是否能够达成共识,在协商的过程中都要有规则意识,对协商的结果应自觉遵守。只有这样,协商文化才能培育,协商意识才能完善,协商成效才能显著。不可否认,在当前的劳资协商中,也确实存在一种“单方文化”,要么接受、要么破裂,这实际上就是没有很好的规则意识。
三是要善于应用制度所允许的压力机制,确保协商目标的实现。现实当中确实存在一种现象,就是有一方不愿意协商;即使协商,也不愿意妥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资方的因素更多一些。资方之所以这样,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是确实还比较“稀缺”,还有一个就是既往路径下劳动者习惯性的被“噤声”所导致的资本傲慢。
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有适度的压力机制,并且是制度所允许的压力机制。从目前的情况看,可选的压力机制包括申请制度救济,比如劳动仲裁、法律诉讼等;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更加重视和发挥工会的作用。
笔者一直强调,国情不同,劳动关系调整的范式不一样,工会的功能也存在差异。在压力机制方面,中国工会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劳动关系理论,但可以基于国情创新压力机制实现的方式和路径。而“源头参与、科学维权”无疑是建构有中国特色劳资协商压力机制的有效选择。通过源头参与,将与协商有关的压力机制诉诸于制度设立的完善性方面,为实际的应用提供制度基础,以保证压力机制的程序合法;在具体的维权行动方面,要讲究科学,这就要求工会要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始终将劳动者的权益作为自己最核心的使命予以实施。也只有这样,中国国情下的工会多维目标才能实现,工会的社会功能也才能充分发挥。
综上所述,面对《工资条例》出台的潜在期望,固然可以从技术层面对目前失衡的分配秩序和劳资关系有所改善,但作为事关劳动者最核心经济权益的工资,《工资条例》最大的制度价值应该是要给劳动者一个“能”说话的机会,“敢”说话的“底气”和“会”说话的能力。还是那句话,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就是,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东西归市场,凡是市场搞不好的东西归政府,但政府并不是简单地应用行政权力予以干预,而是要弄出一个好的制度,并在制度的执行中扮演好“裁判者”的角色。只有这样,社会的权利意识、规则意识才能有据可依,劳资关系也不例外。
栏目主持:纪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