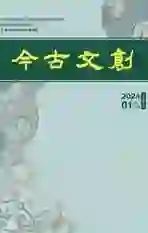海南非遗“黎族民间故事” 外译策略研究
2024-02-02王军
【摘要】海南非遗黎族民间故事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体裁多样、题材多元,具有独特的黎族魅力和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价值。黎族民间故事外译应克服读者小众、人才稀缺、传播乏力、投入不足等挑战,充分利用国内各级分散型贊助,施行政府主导的中外民族学专家合作外译模式,采用民族志翻译方法,保持黎族原汁原味的民族特色,保障译文质量和文化价值,加强外译载体、传播体系和黎族文化品牌建设,突破黎族典籍外译困局,讲好黎族故事,向世界传播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之声。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民间故事;典籍外译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1-0102-11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1.033
基金项目:三亚学院人才引进项目“赫·乔·威尔斯《〈墙中门〉及其它故事》短篇小说集翻译研究”(项目编号:USYRC23-07)。
文化象征着国家形象、民族精神和软实力。国际竞争不仅体现在军事经济硬实力,还表现在文化软实力上,是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我国外宣翻译的重要使命。中国有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一起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只有少数民族文化切实走出去,才能推动中华文化全面走向世界,在世界文化拼图中拥有与我国悠久历史、伟大文明和经济实力相当的国际地位。
海南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区和唯一热带岛屿。随着海南省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和国际旅游岛建设,传承非遗黎族民间文学,传播黎族民俗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一环。黎族是中国海南岛上生活最久的居民,分为赛黎、润黎、美孚黎、杞黎和哈黎五大族群,现有人口160余万。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至公元3世纪左右,骆越人广泛居住在我国的东南和南部。大约3000年前,骆越人的一支定居海南岛,后称为黎族。黎族在周秦时期称作“儋耳”“离耳”“穿胸”“雕题”等。汉代后称为“骆越”“蛮”或“蛮夷”“俚”“僚”“俚僚”等。唐代开始正式采用“黎”为专用族名,宋代普遍称其为“黎”族,沿用至今。黎族先人进入海南岛之时,居住在海南岛沿海地带,后迁至海南岛中部五指山腹地,形成“小分散、大集中”状态。主要聚居地在琼中、白沙、五指山、保亭等市县,杂居地有万宁、陵水、三亚、乐东、东方、儋州、昌江等市县,散居在琼山、琼海、澄迈、定安、屯昌等市县。黎族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缓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黎族五指山聚居区仍处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生活习俗古老,氏族公社经济制度落后,但是沉积了丰厚的黎族特色文化,形态原始,自然淳朴[1]。
黎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黎语支。黎族并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大多会使用汉文。1957年党和政府帮助黎民制定了拉丁字母形式的黎文,但很少有人使用。黎族人民信奉“万物有灵,灵魂不灭”,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日月山川,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都有灵魂,可承载鬼魂显灵。鬼魂主宰天地万物、兴衰祸福。根据不同崇拜对象,形成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体系。黎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民间故事折射出洪荒年代人类的原始记忆,是海南省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文化部门对黎族民间故事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普查,一是少数民族普查(1955-1962),二是海南民间文学3套集成编纂普查(1979-2000);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2005-2009)[2]。多次普查采集整理了黎族民间故事5000余篇,是黎族人民口耳相传、世代积淀的民族文学瑰宝。“黎族民间故事”于2009年10月12日列入《海南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十余年来,海南省推出了一系列保护非遗传承、展现海南文化特色的宣传活动,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儋州调声、椰雕、琼剧、崖州民歌等渐为世人所知,但在非遗宣传中较少提到黎族民间故事。黎族民间故事外文版图书目前出版较少,且基本在国内发行,但也为其有朝一日走出国门积蓄了力量,为向世界传播黎族声音积累了火种。
一、黎族民间故事研究概述
国外学者对海南岛黎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兴趣一直很浓厚。早在1925年,法国传教士萨维纳(Francois Marie Savina)在海南各地实地考察,记录方言和习俗,编纂了《海南话-法语》《临高语-法语》《黎语-法语》等三部词典。1929年发表了长篇论文《海南岛志》,记录了黎族民居建筑、动植物分布、黎女绣面,和一则关于黎族狗始祖的黎族传说,这是黎族社会历史调查中首次记载的黎族民间故事。根据故事情节推测黎族的来源可能是因为遭难或者流放。此外还记录了黎族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风俗习惯,如在灶房产子;丧葬宰牛狂欢,不上坟;生病不请医生,请巫婆;婚后七天,新娘回返娘家,怀孕后才入夫居,即黎族“不落夫家”的奇特婚俗等。此外,德国人类学者史图博(H· Stubel)采用民族学研究方法,观察记录了黎族结构体制、族源构成、文化风俗等,于1937年出版专著《海南岛民族志》,是黎学的诞生标志。之后,日本和中国台湾等研究人员对海南岛进行了全面考察,留存不菲的调研资料,其中最著名的是1979年日本研究学者小叶田淳著述出版的《海南岛史》,记载了海南岛从秦汉朝代到晚清时期的发展通史,引用参考了大量国内外关于海南历史的文献资料,及其亲身在海南岛实地考察,从古迹碑刻上获得的许多珍贵一手史料。为此,日本小叶田淳著《海南岛史》与法国萨维纳著《海南岛志》并称为“海南历史双璧”。这些国外学者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视角对海南以及黎族深入调查、细致研究,形成的宝贵田野考察资料,对今天黎族民间故事外译,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和研究意义。
国内学者近百年来利用人类学和民族学理论方法对黎族民间故事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新中国成立前有刘咸的《海南黎人纹身之研究》《海南黎人面具考》,以及民族民俗学家岑家梧经过民族专题研究和田野调查,发表的《海南島黎人来源考略》《黎族母系氏族制的遗迹》等等。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开展黎族文化传统和民间故事的调研整理、学术研究。早期黎族民间故事文学著作有1958年吴彦启等人编辑的《勇敢的打拖》,1960年杜桐著叙事诗集《甘工鸟》和1962年华南师范学院出版的《黎族民间故事选》。
20世纪80年代后,更多学者走进黎族聚居村寨,描述、归纳、分类、整理黎族民间文化、社会风俗、氏族构成等,拓展了黎族研究广度和深度。1993年王养民、马姿燕著《黎族文化初探》和1997年邢植朝著《黎族文化溯源》研究评述了黎族的哲学、伦理、思维、宗教、审美、文化起源、禁忌、黎锦、服饰、历法、节日等。在整理编辑黎族民间故事基础上,出版了多部选集和专著。如1982年符震、苏海鸥编著的《黎族民间故事集》是第一部全面搜集、系统整理黎族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且正式出版的黎族民间文学集成。1984年韩伯泉、郭小东著《黎族民间文学概说》论述了黎族叙事长诗、神话传说、歌谣、谜语、谚语的文学源流,及其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
进入21世纪,随着国力增强,民族政策开放和海南国际旅游岛、自贸港建设,海南黎族历史、文学、文化、医疗、宗教等多元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队伍日益壮大。2001年王学萍主编《黎族传统文化》及其2004年著《中国黎族》被誉为黎学界在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研究方面的标志性著作,涵盖黎族社会历史、旅游地理、服饰民居、文身风习、宗教哲学、文学艺术、语言文化等,并配有500多张图片,形象生动、全面深入地介绍了独特灿烂的黎族社会发展与民俗文化。2006年潘先锷著《黎族辟邪文化》、2007年高泽强著《祭祀与辟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2008年詹贤武著《海南历史文化大系(社会卷)之海南民间禁忌文化》等,向人们展现了禁忌的奇异黎族民间信仰世界。这一时期对黎族民间故事调研搜集、编辑整理、学术研究的成果十分显著。如2002年龙敏等编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海南卷》和2010年符桂花主编的《海南民间故事大集》将黎族民间故事分成神话、传说和故事三大类,传说继续分为人物、地方、动植物和风俗类传说等小类。故事细分为动物、幻想、鬼怪、生活、机智人物、时政、笑话、寓言故事等小类。2004年黎族作家王海与汉族文化学者江冰合著《从远古走向现代:黎族文化与黎族文学》超越传统文学研究视角,从文化角度阐释文学,以文学传承文化。2009年王海在《黎族神话类型略论》中,将黎族神话分为世界开辟、人类起源、洪水、自然和英雄神话五类。2018年智宇晖在《“早发的神箭”与黎族历史文化关系考论》中,将黎族民间故事中蕴含追求理想、反抗压迫母题的故事统一归为“早发的神箭”类型,即造反英雄失败的故事,在壮族、侗族、布依族、仡佬族中都有类似情节故事流传。“早发的神箭”故事与黎族的图腾崇拜、民族英雄和贬低文化融合变异,具有黎族独特的地域特色。2018年王海、高泽强主编《探寻远去的记忆——生态文化视角下的黎族民俗与民间文学》,利用生态民俗学理论方法分析黎族民间文学艺术生存状况与发展趋势[3]。2022年黎族学者黄呈主编《记忆与传承:黎族记忆里的保亭民间故事》收录了以往未被搜集整理,流传于保亭县黎族群众中的精品,尤其是一些笑话故事,短小精悍,幽默滑稽,体现了黎族人民勇敢、智慧和独特的文化韵味。2023年吴娟在《海南非遗黎族民间故事译介研究》中应用生态翻译学理论分析了黎族民间故事外译的目的、主体、对象和方法,探讨了外译传播新路径。近年来,海南省各类基金课题资助项目和海南省高校翻译人才培养更加重视黎族民间故事外译研究。如2022年海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外宣视角下非遗黎族民间故事的保护、传承和发展研究”“海南省民间故事中英双语平行语料库建设研究”等。海南师范大学指导MTI翻硕学生以符震、苏海鸥编著的《黎族民间故事集》为源语文本,开展翻译实践,结合翻译理论,总结黎族民间故事英译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撰写翻译实践报告形式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为黎族民间故事翻译人才的培养添砖加瓦。这些成果都为今天的黎族民间故事外译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文本素材、考证资料和研究基础。
但黎族民间故事研究仍存在缺乏系统性、创新性和“新时代”特征等不足之处。虽然黎学研究搜集黎族历史和民族志材料,整理黎族民间文学素材,参考借鉴国内外黎族研究成果,并通过田野调查获得一手黎族社会文化资料,编辑出版了大量科学、客观、严谨的黎族研究学术论文和专著,为今日黎族文学文化“走出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黎族民间故事外译和国际传播提供了丰富的语料,但是,目前对黎族民间文学研究偏重于搜集整理口头文学材料和对黎族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的宏观研究,只是对田野调查获得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横向描述介绍和对直观经验信息的浅层建构。黎族文学体裁和类型划分单一,未形成多维细分体系,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和专题研究。因此,黎族民间故事研究亟待改进研究范式,突出创新点,建设多学科专家交叉合作研究团队,对黎族民间文学的历史脉络、现实状况和未来趋势进行纵向梳理和系统研究。以往研究偏重于黎族的起源经历、历史传统,忽视了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和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黎族社会现实状况的关注,未能与时俱进地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在黎族文化建设中的体现,黎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化建构模式,文旅开发对黎族社会的影响,以及在“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和数字化时代中,黎族意识、性格、生态、结构、关系等黎族社会文化变迁的新时代特征等等。因此,面临新时代的新议题和新挑战,稳步推进黎族社会文化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吸引国内外民族文化研究专家和人才汇聚琼台,应用先进的研究理论、方法和现代设备,从历时和共时多视角深入分析黎族社会文化特色,建立多学科、多层次、国际化黎族民间文学与文化多元一体研究体系,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3]。
二、黎族民间故事的内涵特征
黎族民间故事具有体裁多样,题材多元,文化内涵丰富,黎族特色浓厚等特征。广义的黎族民间故事包括人民群众口头散文叙事文学的各种体裁和形式,其中有神话、传说,还有其他各种样式的故事,如动物故事、幻想故事、生活故事、童话、寓言、叙事长诗、民间歌谣、笑话、谚语、谜语等,是黎族人民对人类起源、社会观念、道德伦理、自然现象等的理解、想象和梦想。黎族民间故事与其历史进程紧密相关,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神话产生自远古时代。鲁迅先生说:“昔时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之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今谓之神话。”黎族神话内容主要是对宇宙万物起源的想象,如《大力神》《伟代造动物》《三个民族同一源》等都是黎族初民创作流传的神话。黎族神话分为开辟类、人类起源类、自然类、洪水类、英雄类神话五种。开辟类神话中有与其他民族相似的射日神话《大力神》,讲述远古混沌世界,天有七个日月,大力神射落六个日月,担土垒山,落发为林,流汗成河,筋疲力尽,为防天塌,只手撑天,形成如今巍峨雄伟的五指山。又有神话《山区和平原的由来》讲述天上有五个日月,神人万家射日落月后,为整饬洪水后高低不平的地面,造大牛巨耙,耙平琼海、文昌为平原,因几根耙齿脱落,漏出石头,使琼中、白沙、保亭、东方等地成为山区。这两篇神话包含了黎族初民根据特定的生存环境,展开想象,对开天辟地、日月自然等世界生成、宇宙生灭形成人类早期的原始朴素认知,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体现了黎族先人崇拜自然伟力,主动适应自然世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淳朴认知,以及黎人开天辟地、劳动缔造世界、努力征服自然的豪迈气魄和思想光芒。大力神临终前担心天倾,只手撑天,化成五指山,体现了黎族先民“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的原始信念,大力神并未消亡,其不灭灵魂以其他方式永恒存续。
但最具黎族特色的开辟神话当属《苍蝇吃日月》。远古时期,一片水世界,无人无陆地,只有鱼在水中游。天神番焦塔用七个金箩筐与七个银箩筐,担土填水,垒地造山,呼气成风,吐沫成云。完工之时,番焦塔用力将最后一箩筐土向天上抛去,沙土飞扬,变成满天星斗,扁担化成彩虹,金箩筐变成七个太阳,银箩筐变成七个月亮。陆地出现,水域变小,鱼类生活拥挤不堪,鱼王命令部分鱼类搬迁到陆地上生活,后来这些鱼类就变成了人类。那时,天地间距较近,七个太阳月亮使大地酷热难当,人类只能在洞穴生活。番焦塔体谅人们生活辛苦,双手撑高青天,又派苍蝇趁日月睡觉时,孵卵其上,无数苍蝇蛆蛹一夜之间吃掉了六个日月,一时天平地安,日暖月恬,雨顺风调,人们在地面上开垦种植,生育繁衍,生活和美幸福[4]。《苍蝇吃日月》与《大力神》和《山川和平原的由来》相比,具有独特的黎族特色和文化研究价值。它是黎族神话中,关于人类起源方面,唯一讲述天神同时创造出人与万物的作品,其他神话情节多是洪水过后,人类避难重生的故事。前两篇神话中的射日情节在其他民族故事中常能见到,但黎族神话情节更曲折,过程更艰难,而驱使苍蝇吃掉日月,很有生活,接地气,富有想象力和黎族特色,为多视角研究和外译黎族民间故事,传播黎族文化精神提供了新的素材。
黎族传说的内容贯穿古今,丰富多彩。海南岛自古孤悬海外,与世隔绝。黎族先民生活在深山老林,闭塞交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许多黎民仍保留着原始社会的生活状态,因此流传下来的民间传说也充满了古老时代的意味。黎族的原始社会生活创造了“合亩制”、原始崇拜、刀耕火种等传说内容。汉族从汉代开始进入海南岛,带来了中原文化。彼时封建社会状态和中原文化色彩逐渐融入黎族民间故事之中。如《纺织女神黄道婆》的传说、反抗封建婚姻的《甘工鸟》传说等。进入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历史时期,黎族的民间故事增添了反映社会时代精神的新内容。有讽刺财主、贪官、长工斗财主、革命起义等内容。黎族民间传说可分为人物、地方、风俗和动植物传说等。人物传说又可分为外来历史人物、本地英杰人物和虚幻人物传说三类。海南是封建王朝历代流放贬臣的地方。在汉武帝海南设县置郡后,多由朝廷谪贬降职、流放边陲的官员到海南府州县任职。这些文官武将多数能与当地黎民打成一片、同甘共苦、開疆扩土,为改善黎民生活,建设海南做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黎民的敬重和崇拜。黎民结合历史传奇和丰富想象,从多重视角,以口头传颂形式,叙述宣扬了他们的丰功伟绩和传说事迹。入琼历史人物传说有讲述伏波将军马援和路博德戡乱救民、开拓疆土等英勇事迹的《将军试剑峰》《白马井》《洗兵桥》等;歌颂女中豪杰冼夫人爱民如子、促进民族团结的《营根比武》《冼夫人解救俚女》等;赞颂唐朝名相李德裕与黎民同甘共苦的《李德裕的传说》《李德裕在黎寨》等;颂扬拥有汉族黎族双重身份、传播纺织技术的著名纺织家黄道婆的《从黄四妹到黄道婆》《纺织女神黄道婆》等。这些黎族历史上真实的著名人物,其英勇事迹与传奇故事深入黎民内心,一代代口口相传,流传不绝,是闪耀黎民情感和智慧的精神灯塔,体现了黎族人民对历史名人和英雄人物的民族印记和思念情怀,以及黎汉两族自古交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黎族风俗传说是黎族特有地理气候、生产生活、社会历史的反映,包括节日、习俗、器物和禁忌传说。《纹面的传说》《刺脸》等讲述了黎族女子绣脸或绣面的传说,即在脸上刺青、身上纹身,黎语叫“打登”“模欧”,是黎族传统习俗。黎族女子12岁绣面,又称“开面”,相当于黎族“少女成人礼”。绣面纹身始于唐末宋初,海南战乱时期,烧杀抢掠,冲突不断。为保护女孩不被外族部落抢走,形成了纹面纹身的习俗。随着社会发展,现代黎族年轻人已没有绣脸习俗了。在五指山和保亭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能看到绣脸的黎族老人。绣脸手艺现在面临失传,以后只能在图片和录像上看到这种神秘的黎族文化。《山兰稻种》中提到了“砍山兰”的黎族原始火耕农业生产方式。黎族先民砍伐树木,平整成园,种植作物,待土地肥力失去时,弃之不用,再择新地;生产技术提高后,焚烧草木,将草木灰混入土中,延长土地肥力。砍山焚烧,播种收获,黎族“砍山兰”有着浓厚的民族地域特色和原始色彩。
黎族故事通常以日常事物、广泛背景和趣味情节来反映黎民的生活现实和精神追求,包括动物、幻想、鬼怪、生活、机智、寓言、笑话等多种故事内容和形式。《狗与黄猄》《黑猿与猴子》《雷公蛇与乌龟》等动物故事中将动物拟人化,具有了人的思维性格和行为习惯,或精明、狡诈,或愚笨、憨厚,或忘恩负义,或争权夺利,象征着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表现了黎族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百态。幻想故事《诺实和玉丹》《阿机和阿尼》中小伙子为守护爱情,与专横权势、财主恶霸奋力斗争并取得胜利。《尔蔚》与龙子相爱,嫂子却逼其嫁给财主,并乔装成尔蔚杀死龙子,尔蔚银针刺喉以死殉情,与龙子共葬深潭。黎族幻想故事以奇幻情节和浪漫色彩而感动人心,表达了黎族人民对美好爱情和幸福婚姻的渴望,对辛苦劳作者和英雄领袖的崇拜赞美,对为富不仁和为官不廉的痛恨反抗,对贫穷悲苦生活的不满抗争。在幻想故事中实现了黎族人民现实中的生活理想和精神愿望。
黎族民间故事是口头文学,经过民间采风、口口相传收集而来,具有特殊的名词与术语体系,叙事特点表现为口语化、方言化、情节简单化。描写和叙述多以流水句形式呈现。方言土语、专有名词、文化负载词较多,如黎族歌曲乐器名称:儋州调声、临高渔歌、崖州民歌,独木鼓、叮咚、口弓等;黎族运动游戏:射箭、转石、荡秋千、拉乌龟等;黎族舞蹈:舂米舞、打柴舞、钱铃双刀舞等;黎族节日:元宵、军坡、三月三等;黎族餐饮:山兰米酒、老爸茶、竹筒香饭等;黎族生活用语如:巴曼(男人)、拜考(妻子)、索巴曼(青年小伙子)、尔蔚(少女)、包麦(玉米)、番豆(花生)、苦万(野果名)、胶蜜树(菠萝蜜树)等;黎族神话人物如:伟代(创造万物的全能者)、帕隆扣(男大力士)、土地神、雷公、黎母、螃蟹精等。黎族俗语谚语是海南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语言艺术反映,多含类比、夸张、重复等修辞手法,用黎语读起来,和谐押韵,朗朗上口,译成汉语,缺失了黎族韵味,丧失了音美。如:“椰子水是甜是酸,先喝一口就知道。”“甘蔗是甜的,榨出来的糖也是甜的; 说话是真的,听的人也觉得甜蜜。”“汉区闪,抓牛唇; 黎区闪,带鱼串; 侾区闪,用刀劈。”“星多月不明,鱼多水不清; 饭碗相撞多了要破,夫妻不和要分离。”“有坡地就有红薯,有力气就有金钱”等等,具有丰富的黎族文学色彩和文化魅力。
最独特和有翻译难度的体裁是黎族长诗与歌谣。长诗是黎族人民创作传承的长篇韵文口头作品,如反映社会斗争题材的《姐弟俩》《阿丢和阿藤的故事》《龙蓬》等;反映爱情婚姻题材的《甘工鸟》《猎哥与仙妹》等。黎族民间歌谣,从其内容上可分为古歌、劳动歌、仪式歌、生活歌、情歌等五大类。从唱法、音调韵律上可分为两类:传统黎歌和汉化黎歌。传统黎歌是用黎语咏唱的黎族歌谣,歌调古朴粗犷,保留了质朴的原生态,如歌谣《魔鬼呀,你看我!》:“魔鬼呀!你看打扮得像蟒蛇,又像眼镜蛇,皮肤滑如坛,华丽像野猪、山鸡,丰满像山猪,我瘦就变肥呵,魔鬼呀!”[5]黎族长诗与歌谣译为汉语时丢失了原文的部分韵律、内涵和魅力,在黎語直译外语或汉语转译时能否实现原文和译文的音美、意美和形美对等,能否被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是对译者策略选择的重大挑战。
黎族民间故事各类型间内容存在交叉,体现其多层次和多维度特征。其文化内涵折射出远古黎族初民从崇拜依赖自然、原始探索自然,到认识自然、与自然作斗争的精神演化,以及黎族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到男权为主的父系氏族社会、阶级社会的社会形态演变。
三、黎族民间故事的传播效果
世界语言文化交流存在不平等现象,英语语言文化处于强势霸权地位,汉语等第三世界国家的语言外译处于弱势,信息化和全球化导致语言文化多样性受到挑战。早在1991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指出,世界上每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消亡,同时消失的是语言承载的历史文化、思想传统、发明创造。任由全球化带来的世界英语化,任由一种又一种语言消亡,那么最终世界上可能只会存在一种语言,即英语语言的世界霸权。根据2023年5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书籍翻译数据库(UNESCO Index Translationum)的检索结果,至2019年,以英语为译出语的书籍数量是1266110部,以英语为译入语的书籍数量为164509部,英语译出译入比为7.696:1。以汉语为译出语的书籍数量是14071部,以汉语为译入语的书籍数量为63123部,汉语译出译入比为1:4.486。以英语为译出语的书籍数量是以汉语为译出语的书籍数量的89.98倍。汉语处于世界语言文化交流的弱势。那么作为口头传承的黎语更是处于世界文化交流的外围边缘,随时有传承断绝的可能,并非危言耸听。根据2020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超千万人口的少数民族有壮族、维吾尔族、回族、苗族和满族5个,不到1万人口的民族有6个:鄂伦春族、独龙族、赫哲族、珞巴族、塔塔尔族、高山族。黎族人口1602104,排名少数民族人口第16位。黎族位于中国南海西北部的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隔琼州海峡与广东相望,地处热带,气候炎热,历史上社会发展相对落后。黎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使用汉字,汉族语言文化的同化影响较大。从人口社会、地理气候、教育程度、传播效果来看,黎族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存在不利条件,处于弱势地位,保护和传承黎族语言文化刻不容缓。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媒介的语言”。因此传播黎族民间故事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避免黎族语言文化消亡,维护世界语言多元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使命。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在非遗保护和文明互鉴国家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少数民族文学外译主要由外国个体译者进行,新中国成立后转变为以国家机构为译介主导,以国内译者或国内外译者合作为译介主体。换句话说,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的少数民族文学外译途径是国家集中型赞助外译模式,由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央编译局、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以及众多出版社、发行公司等贯彻实施。出版的《中国文学》(英文版)是中国向其他国家推广传播中国文学的重要途径,按体裁分为小说、散文、诗歌、论文、文艺述评、民间故事等类别。就民间故事来说,《中国文学》(英文版)50年间登载过英文版藏族民间故事28篇,维吾尔族民间故事26篇,回族民间故事18篇,蒙古族民间故事13篇,白族寓言12篇,傣族民间故事3篇,彝族民间叙事诗《阿诗玛》1篇,塔塔尔族民间故事1篇,哈萨克族民间故事1篇。可惜的是黎族民间故事未能入选出版。50年间除汉族文学外,《中国文学》(英文版)外译各类少数民族文学作品500余篇,涵盖藏族、蒙古族、满族、回族等20多个民族,包括黎族作品2篇:1976年的黎族诗歌Li Brocade for Chairman Mao和1982年黄政生著、胡世光译的文艺述评《黎族妇女服饰》,相比其他少数民族,黎族文学外译比例较低[7]。1995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编译的百部《大中华文库》(英汉对照)未见少数民族作品。1981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开始发行世界150多个国家的“熊猫丛书”和2011年以来广受国外读者喜爱的《人民文学》外文版在世界各国人民和当代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间建立了连接桥梁,可惜的是,黎族民间故事未能参与其中。但可喜的是,近年来地方出版社零星发行了收录黎族民间故事的外文版或中外对照图书,为当前黎族民间故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界传播开了个好头。2010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发行了边赞襄编著、曹华民译《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故事选》(汉英对照版),收录了黎族民间故事3篇《两只熊的故事》(The Story of Two Bears)《孟征捉猴子》(Mengzheng Caught Monkeys)和《老树和乌鸦》(The Old Tree and the Crow)[7],以及壮族、苗族、藏族、瑶族、土家族、布依族、侗族、傣族、高山族、彝族、仡佬族、纳西族、哈尼族、毛南族、水族、门巴族、佤族、傈僳族、怒族等20个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58篇。2013年天津新蕾出版社发行了李学勤、潘守永编著的《中国56个民族神话故事典藏·名家绘本:黎族、傣族卷(英文版)》(Classic Myths of China’s 56 Ethnic Groups with Illustrations by Famous Artists: The Volume of Li and Dai Ethnic Groups),图文并茂地用英语为外国儿童读者讲述了有趣的黎族神话故事4篇: Zodiac for Brothers (兄弟星座)、A Tale of Mt. Five Fingers (五指山传说)、Fairy Lake(仙人湖)和A Deer Glancing Back(鹿回头)[8],以及傣族神话3篇。这些黎族民间故事译本尽管数量稀少,但为外国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黎族思想情感、历史文化的大门,也为黎族民间故事对外传播打开通道。随着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和立体式大外宣格局建设,少数民族文学外译赞助呈现多层次、多元化,由国家集中型赞助转变为更加立体高效的分散型赞助模式,这是展现丰富多彩中华民族形象,推进黎族民间故事外译的挑战和机遇。
外在表现不尽如人意,内在宣传重视不足,群众基础薄弱,品牌经营意识淡薄,外宣效果差。目前黎族民间故事,甚至整个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仅仅局限于海南黎族聚居地和黎族民俗文化景区。只有聚居地附近的一些小学会邀请黎族民间故事传承人到学校为学生讲故事,这种形式非常符合黎族民间故事口头文学的传承特点。学生很喜欢黎族神话传说故事,听得入了迷。但是除了黎族聚居区外,其他地方就没有这样民间故事传承活动了。黎族民俗文化景区中的静态民间故事展示区陈列了一些带有中英文说明的图片和展览作品,但文字既不醒目,图片又缺乏吸引力,英文译文错漏较多。导游对民间故事的讲解仅限于照本宣科,对黎族文化背景及其宗教信仰知之甚少。外语导游稀缺,仅为念诵译文水平,与外国游客的交流能力欠缺。因此黎族非遗民间故事在省内和国内的宣传十分有限,没有使中外游客达到了解黎族创世神话和民间传说,感受黎族先民征服自然、刀耕火种的勇敢智慧,感动为爱情和自由不惜牺牲和不懈拼搏,欣赏独特的黎族传统文化风俗等。总之,黎族民间故事的内宣与外译传播效果尚有很大提升空间[9]。
四、黎族民间故事的外译策略
(一)黎语直接外译
黎族民间故事翻译类型从译者角度可分为国内译者翻译、国外译者翻译和中外合作翻译三种形式;从源语文本语言角度可分为以汉语为中介语的转译或重译和从黎族口头文学直接翻译。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和全球化发展,中外专家学者可以线上线下同步合作,更加深入具体、便捷高效地开展研究与翻译黎族非遗文学。尽管转译在翻译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早期佛经是由西域胡语译为汉语,但其转译存在很多意义流失与误解错译,致使佛教派别林立、争论不休,所以才有玄奘贞观三年,出长安、经敦煌、过新疆,辗转抵达印度佛教那烂陀寺,求取梵文真经[10]。因此说,以真人实景作画,能更准确生动传达人与景的风姿气质、诗情画意,而对画临摹,则会失真失色。现在非遗黎族民间故事传承和保护开展向好,随着国家和海南高等教育的发展,黎族年青一代文化教育水平有很大提高,且黎族大多会使用汉字,易于交流沟通,这些都为黎族民间故事的源语直接翻译提供了坚实基础。目前国家赞助的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大多是从汉语譯为外语,缺少以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文化仪式等民族志内容呈现的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外国读者感觉隔了一层纱,不能直接清晰了解黎族的传统历史和风俗习惯,不能满足读者期待,不利于黎族民间文学走出去。黎语直接外译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民族传承,保留民族特色和文化特质,最大程度实现黎族民间故事的文学和文化价值。
(二)汉语中介转译
在缺乏既精通黎语、汉语、译语,又熟悉黎族文化,又懂得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人才之时,转译就是必然的选择,且有其相对的优势。首先,黎族民间故事存在多种汉语版本,质量不一。转译时,应选择优秀汉语中介文本,以保留保护、准确传达、丰富展现黎族语言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其外语译文效果要优于懂得黎语和译语,但对黎族民俗文化历史渊源不甚了解的译者。其二,从诗学角度看,用汉语翻译黎语,也就是用更丰富的诗学语言来表达质朴的黎族民间故事,增添其文学色彩和意境,有助于更好地外译传播。其三,汉语在黎族民间故事外译中,不仅有中介属性,还有监督职能。也就是说,汉译本是对黎族民间故事内容进行了一次有效筛选,筛除了不符合“好故事”要求的部分,保证了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的意识形态要求和文化质量。
(三)民族志研究译介
鉴于西方读者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习惯和地方风俗比较感兴趣,在翻译黎族民间故事类少数民族口头文学时,可采用民族志翻译方法,将黎族民间故事研究与黎族社会习俗、历史文化联系起来,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澳大利亚人类学者贺大卫(David Holm)就是采用民族志方法翻译的《罕王与祖王》,把古壮字研究与考察壮族社会风俗、文化习惯紧密结合起来,打破了语言学和语文学的学科研究壁垒,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赞扬。民族志翻译法要求民族学、民俗学专家和翻译人员密切合作,开展田野调查,或者民族学专家也是译者,这样译文中的民族志知识传达更加准确,文化价值更高。
以文化研究为目的外译黎族民间故事时,可通过客观描写和主观阐释,详细记录黎族民族志和解释黎族文化。仔细观察黎族文化行为,通过田野调查获得黎族民间故事、历史传说和宗教仪轨一手材料,查找相关文学资料、政治文献、隐喻意象等,综合一体,记录在案。以这种方式外译黎族民间故事时,需要添加大量注释说明,可采用加注法和释译法,尽管这样的译文会显得冗长繁杂,可读性底,但因为资料翔实、民族志细致可考,使国外文化研究学者能够更加全面具体深入地了解黎族文化,具有更高的文化研究价值。
以文学艺术研究为目的外译黎族民间故事时,特别是黎族歌谣时,由于是口传文学,因此在以往的书面记载中,往往遗漏了其声音传递的力量、韵味和魅力。因此在对黎族诗歌进行民族志研究时,可采用或开发一套记录符号系统,详细记录诗歌表演者的声音长短停顿、音量大小、采用注释说明其手势动作、面部表情等。民族志诗学研究方法不仅能记录黎族诗歌的文字,而且记载了其音量、音调、音效等副语言特质,体态、道具、表情等非语言特点,所形成的译文能还原黎族歌谣表演时的原始语境,为黎族民间故事的国外文学艺术研究提供了直观形象的研究素材,具有较大的文艺研究价值。
(四)黎族作家外语创译
在“‘离开黎族,我就不是一个作家’——黎族当代作家访谈”中,《黎乡月》《黎山魂》作者龙敏谈到自己创作语言的三重转换过程:第一遍打腹稿,用黎语,展现黎族文化特征;第二遍修改时,用海南话,便于海南本地交流沟通;第三遍定稿,用汉语普通话,以便国内广泛传播。龙敏的母亲擅长唱黎族民歌,多年来他整理汉译了很多黎族民歌。扎根乡村的黎族作家高照清指出黎族作家用黎语思维,汉语表达,因为黎语和汉语语序完全相反,造成很多黎族作家表达不够顺畅。只有掌握汉字,熟悉汉语及其文化的黎族作家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黎族作家亚根的每部长篇小说中都有黎族民歌,蕴含着黎族民间故事。在他看来,黎族民间文学是培育其创作的母乳,很多优秀的黎族民间故事都可以改编成长篇小说或史诗[11]。而这里讲的黎族作家外语创译,指的就是黎族作家用外语呈现以黎族民间故事为基调的文学作品,既可以用外语创译方法将黎族民间故事改编为长篇小说或史诗,也可以黎族民间故事为素材,结合黎族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以外语进行再创作。换句话说,在龙敏的三重语言转换创作过程上,再加一重,这第四重是汉语普通话转换为外语。也可简化为二重转换,即直接从黎语转换为外语文学作品。黎族作家直接用外语基于黎族民间故事进行再创作能促进黎族文学“走出去”,扩大其国际传播范围,增强其在西方文学文化场域的影响力。
有先例可循,后殖民时代非洲民族文学的外译传播,就是通过一些非洲作家直接用法语、英语等欧洲语言写作,以外语为载体,传达非洲民间传说、谚语等非洲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内容,将非洲文学文化中的言语和非言语元素译为欧洲语言,将非洲文学概念和文化价值观念以外语书面语形式传播向世界,提高了非洲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这种翻译形式不同于传统的一种语言文本到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转换,它是以弱势民族文学为创作核心和灵感源泉,源语作家直接以译语创作的翻译形式,是丹麦亨利克·戈特利布(Henrik Gottlieb)称之为的灵感型翻译,他将文本概念从传统的实体文本扩大到非语言交际文本,即一套感官符号具有交际意图时就形成了文本。将翻译概念扩展为新组感官符号及其衍生品能够传递原组感官符号的交际意图和思想感情即为翻译。而灵感型翻译就是相对于源文本的更具创造性和更加自由的衍生翻译。加拿大保罗·班迪亚(Paul Bandia)等学者认为非洲作家用法语等欧洲语言直接写作的做法属于翻译行为。虽然非洲作家的外语作品找不到与其一一对应的原文,但是其作品内容、形式、风格与欧洲文学特点截然不同,传承的是非洲口传民族文学的文学题材、文化传统和表达技巧。且口传文学版本众多,非洲作家博采众家之长,化为向世界传播非洲文学文化的创作灵感和源泉[12]。
黎族民间故事外译与非洲口传文学对外传播都是由弱势民族文学向强势文学系统的输入,面临的问题存在着共同之处,其以民族文学为魂,以外语为体的创译写作方式,推动非洲文学快速走向世界,值得借鉴。作为历史上欧洲的殖民地,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比利时语、葡萄牙语等欧洲语言是非洲国家的官方语言,非洲人从小就会说两种以上语言,后殖民时代的非洲作家具有外语写作基础。与其相似,我国经过多年外语教育事业发展,复合型语言人才培养,改革开放,网络化、国际化融合,举办36年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等,我国包括黎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外语水平得到了长足进步,为直接外语创译民族文学提供了语言保障。只有黎族自己的民族学家、文学家、翻译家才能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和适切传达黎族民间故事中饱含的民族文化仪式、民俗历史内涵,其直接用外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才会有最与众不同的动人黎族风采和迷人黎族风范,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独一无二的黎族文化魅力。
(五)中外专家合作外译
目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外译成功范例是中外专家译者合作研究翻译模式,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双赢模式。翻译不仅是双语的转换,还是跨文化交际社会行为。研究表明,由目的语国家译者翻译的,或者由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的我国文学作品更容易被目的语读者接受,在目的语文化领域中更易取得成功。如闵福德(John Minford)译《中国民间故事》,戴乃迭(Gladys Yang)译沈从文《湘西散记》《边城及其他》,科恩(Don J. Cohn)译《老舍小说选》,刘宇昆(Ken Liu)譯刘慈欣《三体》,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译莫言《红高粱》《生死疲劳》等。对国内外译者的选择会影响了译文的文学质量、文化价值、传播广度和接受程度。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认为国内译者翻译的壮族《布洛陀史诗》不是标准的英文,指出其原因是没有与具有英语母语水平的校对者合作翻译所致[13]。相比国内译者,外国译者不仅母语水平高,翻译质量好,能更好适应目的语国家接受语境和读者期待。因此,聘请外国译者、专家、学者参与黎族民间故事翻译是必由之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黎族民间故事的中外专家合作外译模式可以参考借鉴壮族《布洛陀经诗》的成功外译案例。1993年来自澳大利亚的人类学学者贺大卫(Divid Holm)在南宁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签署合作研究和翻译《布洛陀经诗》的正式协议。贺大卫通过田野考察,与壮族学者探讨交流史诗的背景知识与文化内涵,录制方言吟诵,转录国际音标,经文注释等,创作出4部/篇《布洛陀经诗》译本:2001年《东兰古歌》(The Ancient Song of Doengving),2003年《杀牛祭祖宗》(Killing a Buffalo for the Ancestors),2004年《招魂》(Recalling Lost Souls)和2015年《罕王与祖王》(Hanvueng:The Goose King and the Ancestral King),均在国外出版,其中三部由美国知名出版社发行出版,借助英美主流图书销售体系进入了英美各大书店和图书馆。《东兰古歌》英译本被35个国家566家图书馆收藏,《杀牛祭祖宗》英译本被8个国家39家图书馆收藏,《招魂》英译本被9个国家20家图书馆收藏,《罕王与祖王》英译本被26个国家479家图书馆收藏。收获了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的热心评论,在《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专业学术期刊上有多篇评论文章。相比之下,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壮族典籍英译研究——以布洛陀史诗为例》,其研究成果,韩家权等译《布洛陀史诗》(壮汉英对照)2012年经广西人民出版社发行出版,获得了项目评委肯定和国内学者赞誉,但在国外仅有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1家收藏,没有获得海外读者评论以及发表于国外学术刊物的评论文章。比较而言,以国内译者为翻译主体的韩译本,尽管在国内看来成果丰富,但是其译文完全无法走出国门,未融入世界文化传播系统,未被西方读者了解关注,国际传播效果甚微。而以中外专家合作为翻译主体的贺译本,尤其是贺大卫和我国壮族学者蒙元耀合著的《罕王与祖王》已融入英语国家文学文化传播系统和图书渠道,得到读者广泛关注和反馈评价,以及专业学者的研究兴趣,真正让世界开始聆听悠久神奇的中国壮族文化故事。借鉴壮族典籍外译的成功经验,黎族民间故事外译应加强中外专家合作研究,利用国外专家的先进方法、译语优势和传播渠道,促进黎族声音向世界有效传播。
海南自贸港建设使其成为中国民族文学文化输出的桥头堡,应充分利用国家分散型赞助,实施政府主导的多元立体、国际合作外译模式,实现黎族民间故事源语文本选择、翻译校对、编辑整理、出版发行一条龙,保持黎族原汁原味的民族特色,保障译文质量和文化价值。组织成立“海南民族语言文化与译介研究基地”,建设翻译制度、制定翻译规划、培养翻译人才,提升翻译能力,设置翻译标准,建立海南非遗黎族民间故事翻译工作平台,以国内外著名黎族研究专家和翻译家为译介主体,实行黎族民间故事外译国际招标,提高黎族文学价值国际认可度,突破黎族典籍外译困局,促进我国黎族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
(六)平衡归化异化
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之间是金字塔形式的关系。在塔尖是翻译策略,根据以作者还是读者为中心在文化層面分为异化和归化策略;在塔身是翻译方法,实现异化策略的翻译方法包括意译(含释义法和套译法)、仿译、改译、创译等,实现归化策略的翻译方法包括零翻译、音译、逐词翻译、直译等;在塔底是采用翻译方法时具体使用的五类翻译技巧:增译、减译、分译、合译和转换[14]。 从文化、政治和诗学层面分析黎族民间故事外译策略,学者们分为两派:一是受韦努蒂理论中贬低归化、提倡异化思想影响的异化派,二是认为只有通过归化性的语言才能更好传达原文中异质内容和思想情调,才能更好地为译入语读者接受的归化派。实际上,归化和异化并非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绝对对立选择,而是在归化和异化策略两极间的渐变体。一般来说,当以汉语为本族语的译者将英语文本译为汉语时,倾向于使用归化的方法处理文本,相反,将汉语译成英语时,译文中异化的成分相对要高一些。因此黎族民讲故事译者应在尊重原文文学和文化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根据赞助人需要、出版商要求、译入语国家和读者接受程度等灵活平衡归化和异化,以实现黎族民间故事和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互鉴交流的外译目的。历史上一些中国文学典籍的外译策略和传播结果值得学习和借鉴。如赛珍珠在翻译《水浒传》时,灵活采用异化和归化策略,采用异化策略以保留原文章回体小说的文学范式和四字成语结构,尽管国内学者认为其译文死译、误译,但却给外国读者带来了异种文化的新鲜情调。同时在处理一些名称采用了归化策略,使译语读者能准确理解和感同身受。赛珍珠译本在美国登上了“每月图书俱乐部”,深受美国读者喜爱,十分畅销,就是其能根据不同对象采用适合的翻译策略,在作者和译者间实现了双赢。适度异化使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进入到美国文化系统,促进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接受,巩固了中国文化在美国文学文化场域中的地位,有益于两国民族文化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而极端异化,由于其含有的异质元素过多,造成译语读者的阅读理解障碍,无法接受,造成外译传播失效。如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译本中尽量保留了中国源语文化的异质元素,但却令外国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也就丧失了阅读兴趣。杨戴译本尽管在国内广受好评,但在英语国家却受到冷落。所以黎族民间故事的翻译策略应围绕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外译目的,制定切实可行、行之有效、适时转化、灵活平衡的异化归化策略。黎族民间故事外译的异化派不必排斥归化策略,畏之如虎,斥其忘本不忠,倾向欧洲中心论,没有保护好黎族文化特色等,其实这只是民族自卑心理在作怪。在目前西方文化强势输入的形势下,适当归化外译,异化归化有机结合,使西方读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接受黎族文化,慢慢地将我国民族文化异质因素渗透进去,能够更好地融入英语等西方语言文化系统,这是审时度势的应对策略,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持久战略。
黎族民间故事生动形象地表现了黎族特色的文化风俗。在翻译黎族民间故事,尤其是处理黎族文化负载词时,译者应尽量保留其原汁原味的黎族文化内涵。因此,译者只有熟悉黎族和目的语文化背景,才能熟练应用归化和异化策略,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既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又能保持原文含义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1.对于源语译语语序结构相同的词汇或者句子,可以采用异化策略和直译的方法,在结构与语义上忠实于原文,且尽可能保留原文中黎族文化特色与行文风格。如:
原文:古时候,在海南岛中部有一座山,叫“五指山”。
译文:In ancient times, in the middle of Hainan Island was a mountain called Five-Finger Mountain.
2.黎族民间故事中一些词汇和句子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可采用异化策略和直译+句外注释的方法,准确传达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和颇具特色的黎族文化。如:
原文:黄道婆,你要在三天之内给我织出当代最美的崖州被,我要作为贡品献给皇帝。
译文:Huang Daopo, you must knit me within three days the most beautiful Yazhou Quilt in modern times, and I will present it as a tribute to the emperor. (Note: As the essence of Li brocade, Yazhou Quilt is a large quilt embroidered with the prominent dragon pattern, originally from ancient Yazhou city. )
3.当原文在目的语中没有意义对应的词汇表达时,可采用音译+句内注释的方法,这种异化策略可以较好地在译语环境中传播黎族特色文化。如:
原文:黎族“三月三节”,是海南黎族人民悼念勤劳勇敢的祖先、表达对爱情幸福向往之情的传统节日。
译文:“San Yue San Festival” , or the Lunar March 3rd Festival, of Li Ethnic Group is a traditional one for Li people in Hainan to mourn their hardworking and brave ancestors and express their yearning for love and happiness.
4.采用归化策略和意译的方法,包括释义、套译和创译法,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同时尽量保留原文信息,在原文充分性和译文可接受性之间达成平衡,避免文化误读和文化冲突的情况。
原文:姑娘们躲在绿树丛中,手持带香味的树叶遮着面,悄悄窥视意中人。
译文:Girls hiding in the green trees, holding fragrant leaves to cover their faces, shyly gaze at their Mr. Rights.
(七)培养黎族外译人才
黎族民间故事外译需要高水平的专业翻译人才和数字新媒体人才,以保障通过传播介质和国外读者顺利沟通。优秀的黎族译者能够在把黎族民间故事翻译成外国人理解的语言时,保留黎族独特的文学和文化韵味。目前海南中小学阶段的外语教育和高等學校的黎族翻译人才培养方面存在诸多不足:缺乏培养黎族翻译人才的合格师资队伍;翻译专业课程设置尚需完善;黎族民间故事和黎族文化的翻译实践较少等。2022年张晓辉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文呼吁建立海南高校外语翻译人才库,服务海南省的自贸港和国家旅游岛建设,促进海南省重点产业的发展格局,通过翻译把海南当地的特色产品和民族文化推广宣传到世界各地,带动海南经济、贸易和文化产业的现代化发展[15]。因此,应优化学校翻译专业课程设置,开设黎族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和文化课程,培养学生对黎语、汉语和英法德日等外国语言的感知和理解能力,增加对黎族民间故事、传统文化风俗和当代黎族作家文学作品的学习和翻译实践,建设产学研互动合作平台,培养适合中国式现代化、数字化,顺应文化输出战略,具有黎族文化功底和国际传播能力的新时代复合型翻译人才。此外,黎族民间故事对外传播离不开信息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新媒体人才。海南高校应与数字媒体企业合作,共建高素质师资队伍,开拓协同育人渠道,改进数字新媒体人才培养方案,优化数字新媒体专业课程,培养数字新媒体高素质人才,为黎族民间故事的数字文化传播提供人才保障。
黎族民间故事外译至少涉及三语语言文化和民族知识:首先,应了解黎语,熟悉黎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社会历史、宗教文化、传说典故等,才能准确理解民间故事中的方言俚语、社会习俗和价值取向,从口头黎族源语直接翻译成目的语,避免误解错译,学术价值高,是国内外民俗学者比较认可的译介方式。其次,精通汉语,因黎族民间故事口口相传,不著文字,因此目前均以汉语形式结集成册,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海南卷》《黎族民间故事大集》等。国内外译者可以汉语译本为中介,结合当地文化习俗,走访黎族村民,开展田野考察,转译为目的语。最后,须通晓目的语,有深厚文学功底、广博的民族学、民俗学知识,才能恰当译介黎族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缩小中外文化差异,传达原文语言文化内涵和情感价值,提高译文在目的语民众中的接受程度,使我国少数民族的非遗“好故事”走出去,向世界展现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
(八)塑造黎族文化传播品牌,加强外译载体和传播体系建设
增强黎族民间故事外译的“内推力”和“外拓力”,塑造黎族民间故事文化传播品牌。
尊重接受方意识形态、诗学观念和读者期待,提高黎族民间故事译本在目标读者中的接受度。首先,加强黎族民间故事外译的“内推力”,积极参加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大学高校赞助少数民族文学外译的工程项目,如国家省市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少数民族作家海外推广计划、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翻译工程、中外作家交流营等。
其次,增强黎族民间故事译介的“外拓力”,紧密合作国外主流图书出版与销售公司、知名报纸期刊、连锁书店、世界各大国立、公共和大学图书馆、教育系统、研究学者、华侨海南会馆等,努力融入国外主流传播和接受系统,避免少数民族文学传播边缘化[16]。
再次,充分利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多媒体传播渠道,提升黎族民间故事的世界知名度、影响力和国际传播能力。开拓海南国际传播网(HICN)、海南广电国际融媒体中心、三沙卫视等海南自主国际传播平台建设。培育拓展海南国际传播网在海外主流社交媒体Facebook、Twitter、YouTube、Instagram的官方账号HiHainan、The Voice of Hainan等。拓宽传播渠道,充分利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国际科研论坛、国际文化体育赛事等国际盛会,与中央和海外媒体合作宣传报道海南风土人情、民俗文化等。
黎族民间故事传播应树立文化品牌意识,合纵连横,创新经营,引燃黎族文化品牌效应。
黎族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塑造黎族文化品牌,首先要加强黎族文化自觉意识。国家和海南省对非遗黎族民间故事的对外传播给予了鼓励政策和大力支持,但是具体的实施和推动,还需要依靠黎族民众自身的行动力和创造力。最了解黎族社会文化和传统风俗的群体只有黎族本身,因此黎族人在挖掘黎族民间故事历史传承、文化内涵和研究价值方面先天具有无人能比的优势。提升黎族文化自觉性是塑造黎族文化品牌和开发黎族文化产业的先决条件。政府部门可以将蕴含黎族文化风俗的民间故事拍成文化宣传片,举办黎族文化传统知识的宣讲活动,或者拍摄成电影、电视剧、动画片,在影视网站和App上播放,将创世神话和斩妖除魔的英雄故事编成网络游戏,以迎合现代年轻人的文化兴趣和信息媒介获取习惯。将有民族特色的故事人物形象化,拍摄成精良打造IP、视觉效果震撼、名人双语配音的短视频,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短视频网站传播。在景区文化演出中,通过5D沉浸式观看感受,观众会对故事人物情节有更深刻的印象。润物细无声,在潜意识中传播黎族民间故事和文化,从而增强黎族人民,特别年轻一代黎民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认同,提升黎族人民的文化自豪感和民族自信,从内心里产生强烈的内在驱动,愿意去主动积极地传播黎族民间故事等传统文化。其次要加强保护黎族文学和文化底蕴的独特性。随着社会网络化和全球化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和途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难保持黎族自身的独特性,不受现代时尚因素的影响。为此,一方面,要避免为了经济利益,将黎族文化过度商业化,逐渐丧失黎族特色,只剩下外在的形式空壳,丢失了灵魂,沦为同质化严重的摆设。另一方面,不能过度保守,在教育黎族儿童了解和传承黎族文化的同时,应积极吸收有助于巩固和培养黎族民族特色的外来文化因子,丰富黎族文化内涵,深厚文化底蕴,扩大黎族文化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树立黎族文化典型品牌。最后要依靠自身的外向型黎族文化企业,塑造黎族文化品牌。顺应我国“文化走出去”和“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战略指引,开办外向型黎族文化企业能更有效地促进黎族民间故事和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吸引世界对黎族非遗文化价值的关注目光,在世界文化拼图中努力占据自己应得的位置。数字时代的黎族民间故事外译应夯实内在文化宣传基础,对外以多媒体为载体,网络为路径,外语为媒介,数字技术为保障,打造黎族民间故事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
虽然黎族民间故事属于口头文学,译介难度大,读者小众化,传播边缘化,但在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时代浪潮中,利用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外译的多维赞助资源,采取中外知名民俗家和翻译家合作翻译方式,采用民族志翻译方法和适度异化翻译策略,必将取得黎族民间故事外译的双赢结果:国外专家学者在国际上取得丰硕黎族文化研究成果的同时,黎族民间故事在国外文学场域中的传播和接受度也会大幅提高,促进世界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传承保护和研究交流,实现中国文化外宣翻译的最终目标: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参考文献:
[1]符桂花.黎族民间故事大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9:4.
[2]吴娟.海南非遗黎族民间故事译介研究[J].文学教育(上),2022,(11):172-174.
[3]黄晓坚.海南黎族传说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9.
[4]王海.黎族神话类型略论[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9,30(05):11-15+136.
[5]唐宁.海南历代移民与黎族歌谣变迁初探[J].艺术教育,2015,(07):150-151.
[6]夏维红.国家赞助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研究(1951-2019)[D].广西民族大学,2020.
[7]边赞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故事选(汉英对照版)[M].曹华民译.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10:60-70.
[8]李学勤,潘守永.中国56个民族神话故事典藏·名家绘本:黎族、傣族卷(英文版)[M].天津:新蕾出版社, 2013:2.
[9]陈珞瑜.后殖民视域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外译现状、策略、途径及出路[J].外国语文研究,2017,3(05):76-84.
[10]刘雪芹.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外译的类型、目的与策略[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6(04):13-17.
[11]杨春,阿荣,胡艳红,姜可欣,孔林林.“离开黎族,我就不是一个作家”—黎族当代作家访谈[EB/OL].中国作家网,2016-7-4.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3/2013-04-03/158735.html.
[12]Bandia,P.African European-language literature and writing as translation:some ethnical issues[A].in HermansTheo(ed.)Translating Others(Vol. 2)[C]. 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 Ltd.2006.
[13]Bender,M.Co-creations,master texts,and monuments:
long narrative poems of ethnic minority groups in China[J].CHINOPERL:Journal of 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2019,38:65-90.
[14]熊兵.翻譯研究中的概念混淆——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为例[J].中国翻译,2014,35(03):82-88.
[15]张晓辉.构建海南语言服务型翻译人才库[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6-07(007).
[16]张敏,李野.基于网络爬虫的少数民族文学对外传播成效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45(02):173-177.
作者简介:
王军,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三亚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