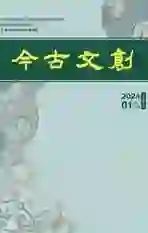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下《伊芙琳》与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对比研究
2024-02-02李舒雅
李舒雅
【摘要】詹姆斯·乔伊斯和威廉·福克纳都是重要的现代主义文学家。《伊芙琳》和《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讲述了两位女主人公在男权思想以及传统伦理道德统治下的悲惨人生。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对比分析伊芙琳和艾米丽的伦理环境、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试图探讨二者悲剧背后的原因,以及小说所传达的伦理价值。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选择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1-004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1.014
一、引言
詹姆斯·乔伊斯是爱尔兰最重要的现代主义文学家之一。他的小说、戏剧和诗歌作品对20世纪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代表作《尤利西斯》是20世纪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伊芙琳》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的一篇,讲述了一个名叫伊芙琳的女孩在家庭、爱情和生活的压力下所做出的抉择。《伊芙琳》以乔伊斯特有的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了爱尔兰社会中女性受到的压迫和限制,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伦理观念的思考。
同为现代主义文学家,威廉·福克纳出生于美国南方贵族世家,对“南方文艺复兴”起到了推动作用。辛克莱·刘易斯称福克纳“把南方从多愁善感的女人的眼泪中解放了出来”。《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是福克纳发表于1930年的短篇小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小说讲述了出生于南方贵族世家的艾米丽爱上北方人荷马·巴伦后遭弃将其毒死,从此与尸骨为伴直至死去的故事。在作品里可以看到作者笔下美国南方贵族阶级日趋没落的衰亡历史。
文学伦理学批评最早由聂珍钊教授于2004年提出。他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的立场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研究作家以及与文学有关问题的研究方法”[3]。不同于社会的伦理学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以通过想象而虚构的艺术世界为对象,研究文学及文学描写的道德现象,以及作者与文学、与社会等的道德关系问题,而前者是以现实社会、社会生活和社会中的人为对象,研究社会和社会中所有的道德现象[1]。因此,在研究对象上,二者有本质的区别。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对比分析主人公伊芙琳和艾米丽伦理环境、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的异同点,探讨小说传达的伦理价值。
二、伊芙琳和艾米丽伦理环境对比分析
“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3]。
《都柏林人》中的十五个故事置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按照童年、青年、成年以及公共生活四个部分排序。《伊芙琳》是其中的第四篇,属于“青年”期。之所以选择都柏林,是因为乔伊斯认为这个城市处于麻木状态的核心。爱尔兰有近八个世纪被英国统治的外在殖民史,而在宗教上则有更长的内在殖民历史。在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下,整个爱尔兰处于麻木不仁、死气沉沉的“瘫痪”状态。爱尔兰的天主教不仅把持着人民的精神和道德生活,还插手政治,政治与宗教冲突不断,动荡不安。19世纪的大饥荒使得爱尔兰人口锐减,大量人口流向美洲,移民潮经久不息,经济处于停滞的状态,普通老百姓艰难地过着日子。正如文中开篇,伊芙琳回忆起以往和弟弟妹妹玩耍的场景,而现在,“瓦特一家已迁往英格兰。一切都变了。现在她也要走了,像其他人一样,离开她的家”。20世纪初的爱尔兰社会男权思想仍旧根深蒂固,女性的社会角色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并未受到重视。伊芙琳的母亲生前就受到虐待,悲惨死去。而在伊芙琳成长的过程中,父亲也从未像喜欢她的两个兄弟那样喜欢过她,仅仅因为她是个女孩。
伊芙琳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母亲早早病逝,兄弟哈利常年在外奔波,家中只有父亲和她,以及两个年幼的孩子。本该是父女俩相依为命的场景,然而,父亲却并不喜欢伊芙琳,有时甚至还用暴力威胁她。母亲走后,生活的重担便落到了她的头上。除了承担繁重的家务,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她还在百货商店打工补贴家用。即使每星期把全部工资——仅仅七个先令如数交出,也免不了父亲的指责。“他说她常常乱花钱,说她没有头脑,还说他不会把他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给她抛到街上”[7]。无论家庭还是社会都不是伊芙琳的避风港。
1620年,随着102名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到达美国,清教被带到了美国。福克纳笔下的美国南方是清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清教的宗教要义认为妇女要保持贞操,也就是说要用理智的意识来压制人的自由本能和原始欲望[8]。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艾米丽所处的小镇则是内战后美国南方社会的缩影。在内战后的南方社会,传统的伦理制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父权制统治着人们的思想[1]。艾米丽出生在社会等级森严的美国南部,从小接受传统和道德教育。然而,在战争时期由于北方工业化的入侵,南方的传统价值观逐渐走向衰落,正如小说开头第一句“艾米丽·格里尔森小姐过世之际,镇上所有人都去吊丧:男人们是出于某种敬慕之情,对他们来说,一座丰碑倒下了”[6]。艾米丽的去世也意味着南方一直保持的英国封建贵族的传统也在慢慢衰落。
和伊芙琳不同的是,艾米丽是美国南方贵族家庭的独生女,她居住在鎮上最为繁华的地段,在这一地段逐渐被汽修厂和轧棉机侵占的情况下,“只有艾米丽小姐的房子挺立依旧,在棉花车和汽油泵的簇拥下,日趋朽败,却仍桀骜不驯、卖弄风情,着实碍眼至极”[6]。艾米丽的父亲是封建专制的守卫者,他将艾米丽培养成南方淑女,拒绝了所追求她的年轻男士。
艾米丽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都要高于伊芙琳,她不必像伊芙琳那样为了生计每日辛苦劳作,甚至在小镇上被人们视为“丰碑”。然而,她们有一个共同点——都生活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之中,她们必须顺从父亲的意志,维护父亲的权威,压抑自己的自由意志。
三、伊芙琳和艾米丽伦理身份对比分析
聂珍钊教授认为,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有多种分类,如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社会身份的主体是人,而身份是人特有的特征,因此“人的身份就是伦理身份”[4]。
在小说《伊芙琳》中,首先伊芙琳的身份是女儿。在伊芙琳的家庭中,母亲早早病逝,两个兄弟一个死了,另一个在外奔波,家中只剩下她和粗暴无比的父亲。伊芙琳早早就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每日除了繁重的家务之外,还要外出打工补贴家用。而父亲的残暴对她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甚至恐吓她,“说要不是看在她死去的母亲的份上,就会对她如何如何”[7]。在父亲发现她和弗兰克的关系之后,甚至还明令禁止她和弗兰克有任何的来往,还与弗兰克吵了一架。此后,伊芙琳只能偷偷与弗兰克见面。伊芙琳还是百货店的一名员工,但是不仅工资低,还常常受到上司的排挤,“她总是显摆她比她强,尤其是每当有人听着的时候”[7]。对大家来说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中,她都几乎没有得到过关爱。
而另一边,同样作为女儿,艾米丽不必为了生计而辛劳,但是女儿的身份给了艾米丽一个伦理要求,那就是要孝顺父亲。作为一个生活在贵族家庭的女儿,任何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都将使艾米丽收到社会的鄙夷,甚至影响到整个家族的地位和尊严。父亲在世的时候,对艾米丽的婚姻非常重视,对女婿的选择有着严格而挑剔的要求。而艾米丽对自己的婚姻唯一的选择就是保持沉默和顺从,任由他赶走所有追求她的年轻男士。然而,正是他的谨慎选择和一次次的拒绝,葬送了艾米丽光辉灿烂的青春期,葬送了她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也葬送了她获得幸福的机会。而正是因为对父亲过于依赖,父亲的死使艾米丽受了重伤,久病不起。虽然父亲的去世宣告了她作为女儿的伦理身份和义务的终结,但她作为南方淑女的社会身份无法脱下,她仍然是贵族群体一个有影响力的代表。她受过良好的教育,一直被镇上的人看作是上流社会的楷模和贵族权威的代表,对她的婚姻也抱有很高的期待,“艾米丽小姐坐在里头,灯立在她身后,那笔挺的身躯纹丝不动,宛似圣像一具”,“她的头发已经剪短,看上去像位少女,肖似教堂彩窗上的天使”[6],从镇上居民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她怀着敬畏之情。
作为女儿的伦理身份要求伊芙琳和艾米丽要顺从父亲的意愿,遵守家庭伦理道德,这是二人家庭身份的一个相似之处。但是,二者在社会身份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伊芙琳在社会上不受重视,在打工的店内常常受到排挤,社会地位低下;而艾米丽则是贵族阶级,即便家族逐渐没落,在艾米丽生活的小镇上,她仍然有较高的影响力。这也就意味着,伊芙琳面临的伦理困境更多地来自家庭伦理道德的约束,而艾米丽面对的伦理困境更多地来自南方淑女的社会身份所带来的约束。
四、伊芙琳和艾米丽伦理选择对比分析
“在文学作品中,伦理选择往往同解决伦理困境联系在一起,因此伦理选择需要解决伦理两难的问题”[4]。
伊芙琳在家庭中不受重视,在工作中又受到排挤,而弗兰克的出现给伊芙琳的生活带来了希望。他每晚都会去商店接她下班,帶她去看戏剧,为她唱歌。她憧憬着和弗兰克的新生活,“在她的新家,在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情况不会像那个样子。那时,她就结了婚”,“那时,人们会尊重她。她不会受到她妈妈生前所受的那种对待”[7]。再回想起母亲生前可怜的景象—— “平平凡凡耗尽了生命,临终都操碎了心”,令她浑身颤抖。她不想重蹈母亲的覆辙,只想尽快逃离一眼望到头的生活。但是,另一边,她又想起自己在母亲去世前的许诺—— “她曾许诺一定要尽力维持这个家”[7]。真的要走的时候,对这个家还是有点舍不得的。甚至她还回想起了父亲慈祥的样子,不久前在她生病的时候还给她读故事,烤面包片。
摆在她面前的有两条路,如果留下来,她就要继续走母亲的老路,放弃自己的爱情;如果选择跟弗兰克远走他乡,她就要抛弃这里的一切,违背自己的诺言。从伊芙琳的身上我们能够联想到乔伊斯的经历,大学毕业后,乔伊斯离开爱尔兰来到巴黎,随后母亲病危又回到爱尔兰,母亲病逝后在朋友的资助下又私奔到欧洲。乔伊斯的离开让其陷入了伦理困境,母亲病逝令他耿耿于怀,因此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围绕都柏林的生活展开的,以此来弥补内心的愧疚。
在诺斯华尔码头即将上船时,伊芙琳却退缩了。尽管伊芙琳没有逃离,她的思想却发生了变化,她短暂地有了想要开始新生活的想法,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5]。但是最终还是缺乏勇气,放弃了自己的幸福,选择了责任,继续当一个照顾父亲的女儿和一名小店员。
随着艾米丽父亲的去世,艾米丽作为女儿的伦理义务也完成了,她也不需要再压抑自己的自由意志,尽管父亲留给她的唯一财产只有一栋房子。就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年夏天,镇上铺设步道,艾米丽认识了一个名叫荷马·巴伦的北方佬。很快,艾米丽便爱上了荷马,每逢礼拜天下午两人便一起驾车出游。然而,镇上的人们却并不看好他们,认为她“令全镇蒙羞,于后辈而言亦是坏榜样”[6]。一时之间,艾米丽和荷马成为了小镇人议论的话柄。由于艾米丽的出身,人们期望艾米丽严格遵守传统和道德规范,保持淑女的优雅和风度。而艾米丽的所作所为,是对贵族身份的玷污,对南方传统的挑战,对伦理秩序的扰乱。他们一开始希望寻求艾米丽在亚拉巴马的亲戚的帮助,但是多年前她父亲和她们因为遗产的问题断绝了来往。她们转而迫使浸礼会牧师去劝说,然而,交谈过后,牧师拒绝再跑第二趟,而艾米丽在下一周的周日照例和荷马策马上街。最后,牧师夫人不得已给艾米丽在亚拉巴马的亲戚写信,结果也是于事无补。荷马本来可以成为艾米丽摆脱家庭、社会伦理道德约束,实现自由意志的契机,然而,他却无意与艾米丽组建家庭,最终导致了艾米丽的悲剧命运。艾米丽不彻底的反抗终究敌不过父亲三十多年的影响,在付出得不到回应,惨遭抛弃之后,艾米丽最终走向了极端,选择了毒死荷马,让他的尸体陪伴自己度过了余生[8]。
伊芙琳和艾米丽在面对伦理困境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伊芙琳虽然有了短暂的觉醒,但都柏林的道德瘫痪剥夺了她追求新生活的勇气,在最后关头没有力量冲破现实的禁锢,还是选择留在都柏林。而艾米丽生长在男权意识和传统姻亲观念根深蒂固的南方小镇,她知道如果继续和荷马在一起会影响自己的声誉和家庭的社会地位,违背父亲对自己的厚望。面对伦理困境,她还是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追求爱情。然而,她爱上的是一个和自己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她们的爱情也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五、结语
伊芙琳和艾米丽虽然来自不同国家,但是她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都是生活在男权社会下的女性,二者具有诸多可比性。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对两位主人公的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选择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发现,伊芙琳和艾米丽在伦理环境和伦理身份上有许多的相似之处。20世纪的爱尔兰政治动荡,经济停滞,整个社会在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下处于“瘫痪”状态,而艾米丽所处的美国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受到北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逐渐走向衰落。男权思想根深蒂固的伦理环境以及作为女儿的伦理身份,要求她们必须顺从父亲的意志,压抑自己的自由意志。但是,另一方面,二者又有不同之处。在伦理身份上,伊芙琳是一个贫穷家庭的女儿,母亲去世后,她需要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而艾米丽是旧南方贵族阶层的女儿,她面临的伦理困境是她的行为需要符合一个南方淑女的特征。在伦理选择上,伊芙琳仅仅有了短暂的觉醒,伦理环境和伦理身份还是限制了她追求自由意志;而艾米麗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不顾父亲和小镇人民的反对,对伦理困境做出了反抗,但是最终扭曲的价值观还是导致她做出了有悖伦理道德的杀人行为。
参考文献:
[1]陈阳.《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文学伦理学批评[J].中国校外教育,2013,(12):37-38.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J].外国文学研究,2004,(05):16-24+169.
[3]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32(01):12-22.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王素娟.乔伊斯小说中伊芙琳选择之伦理探究[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6):85-86.
[6]威廉·福克纳.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M].叶紫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
[7]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M].王逢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8]张婧婧.《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文学伦理学解读[J].名作欣赏,2015,(03):8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