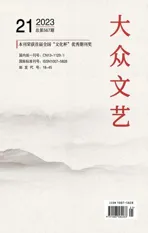明代“诗与故事”类型民间故事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
2023-12-19陶馨雅
陶馨雅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江苏南京 210044)
明代“诗与故事”类型的民间故事是以诗歌、对联作为其主要构成要素,因而这一类故事又可分为吟诗故事和对联故事两种。吟诗故事以诗歌作为故事类型核。按照故事的内容类型又可细分为十七字诗型故事、三笑事型故事、三婿赞马型故事、讽观竞渡型故事、春雨似油型故事和真老乌龟型故事。对联故事以对联为故事类型核,按照故事的内容类型又可分为长江作浴盆型故事和八王四鬼型故事。[1]
一、“诗与故事”类型民间故事的叙事结构
(一)三叠式结构形态
“诗与故事”类型的民间故事很多以数字三为结构铺展,或是三个事件的并列叙述,或是三个主要人物递进纠葛。关于三个事件的并列叙述,最典型的是明代郎瑛《七类修稿》里“三笑事”型故事。这一类故事主要讲述的是发生在明嘉靖年间的三件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包括“为人接生的稳婆生子于产家”“医生急病死于病家”“捕头反被强盗打劫称强盗爷爷”。三个内容上毫无关联的故事以一种荒诞的审美为连接点,依次叙述,并列展开,呈现出“叙事线索横向连接投射到一根垂直的暗轴上”的结构特征。三个主要人物的递进纠葛以明代冯梦龙《笑府》中的“三婿赞马”型故事为代表。故事讲述杭州有个人有三个女婿,一天他买了一匹新马要求三个女婿称赞马之快疾,雅俗皆可。大女婿说:“水面搁金针,丈人骑马到山阴,骑去又骑来,金针还未沉。”二女婿也很快作出了应答:“火上放鹅毛,丈人骑马到余姚,骑去又骑来,鹅毛尚未焦。”三女婿不会有些呆楞,想了许久也没答案,这是丈母娘撒一响屁,他突然来了灵感,说道:“丈母撒个屁,丈人骑马到会稽,骑去又骑来,孔门犹未闭。”这一类型故事中大女婿和二女婿通常以科举士子和富商的身份出现,而三女婿通常是勤劳朴实的农民形象,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构成了三人之间矛盾核心,通过你一言我一语的“赛诗”层层递进鲜明反应人物形象和性格,从而在雅与俗的碰撞中对功利至上的社会价值观进行幽默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
(二)二元对立的矛盾结构
二元对立的结构观念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从法国著名学者列维•斯特劳斯开始:“列维•斯特劳斯批判普罗普把形式独立于内容之外,而抹杀了词汇的存在,他开始重新审视民间叙事的内容含义……用二元对立的观念分解原有的叙事形式,将其重新组合成深层结构。”[2]民间“诗与故事”类型的故事中,“二元对立”建立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上,呈现出审美上的美与丑、伦理上的善与恶、思想观念新与旧的对立。这一结构在对联故事里有普遍的应用。首先是长江作浴盆型故事,初见于明代江盈科撰写的《谈丛》,故事讲的是明代大学士《永乐大典》编撰者解缙小时候的佚闻。解缙九岁时随父亲到江中洗浴,将衣服一同挂在树上。他的父亲即兴说道:“千年老树为衣架”,解缙答道:“万里长江作浴盆”。这一则对联除了体现最基本的格式对仗外,还展现了父子两代人思维方式上的不同:谢父“树作衣架”取材于较为常见的生活用法,而解缙的“长江作浴盆”虽然同样取材于周围的环境,但较其父之言多了一层想象和夸张的色彩,具有年轻人的特色。其次是八王四鬼型故事,初见于明代张谊撰写的《宦游记闻》,写的是安南国来使来朝觐见,作出“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脑”求对,馆伴之子程篁墩思维敏捷随即对出:“魑魅魍魉四小鬼各样肚肠。”来使震惊。自此每年朝贡从无断绝。这里将居心叵测的南安国来使的“丑”和官员之子的机智的“美”二元对立,用百姓听得懂的简单冲突的对撞展现现实外交中的复杂状况。
(三)全知视角下的循环结构
循环结构是指故事叙事时按照时间发展顺序、首尾呼应的回环结构,这种结构在明代“诗与故事”类型的民间故事中就体现在故事原型在发展过程中对诗句意思的补充说明上,这里以春雨似油型故事和真老龟型故事为例。春雨似油型故事初见于明代冯梦龙编撰的《古今谭概》,说的是明代大学士《永乐大典》编撰者解缙小时候的佚闻。相传解缙四岁时外出游玩遇到雨天,因路滑摔倒而被周围人讥笑。他站起来后作诗一首给予反击:“细雨落绸缪,砖街滑似油。凤凰跌在地,笑杀一群牛。”后来在不同的版本中诗句略有调整,但故事框架基本没有改变,到近人吴个厂撰写的《笑话大观》,故事情节中增加了一句解缙的辩解之词:“我所言者,乃笑坏众公侯,非笑煞一群牛也。”增加的“辩解之词”实则就是作者对这则故事的理解和情感抒发,通过点明文意使故事整体前后照应。真老乌龟型故事初见于明代阑庄撰写的《驹阴冗记》。故事说的是明代福州人郑唐,有飘逸之才,喜好作讥讽之诗。他为权贵作祝寿诗:“精神炯炯,老貌堂堂,乌巾白发,龟鹤呈祥。”。后来有人读到此作,说“此四语横读,则‘精老乌龟’也”。那个权贵方才明白,于是毁去。这里的“后人读此”同样也是作者的批解之语,首尾呼应,旨趣了然。全知视角叙述是民间故事“说故事”的过程中最典型的叙述方式,循环结构的故事结尾作者借人物之口道出诗的旨趣,让故事的内涵更加清晰明了。
二、“诗”的位置与叙事作用
(一)以诗为核心:作语言的游戏
在明代诗与故事类型的民间故事中,“诗”多出自主人公之口,出现在故事的情节跌宕处,或抒情状物,或回击讽刺。用诗的方式既完成了人物性格的刻画,也推动了故事情节叙述的发展,诗在这类故事中最突出的作用也在幽默的氛围中体现出来:通过语言的自我突出来促人发笑。巴赫金认为民间诙谐文化通过取消等级、颠倒秩序和戏仿嘲弄来令人发笑——这种笑是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它既是欢乐的、兴奋地,同时也是讥笑的、冷嘲热讽的,它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再生。”[3]以诗为核心的民间故事属于这种诙谐文化。故事的旁白叙述提供了一般意义上的文本语境“丈人和女婿”“官员和平民”“官员和外宾”,诗的插入使矛盾集中于一处爆发,从而令人发笑营造出一种狂欢的氛围——这是一种对对立的价值和森严的等级的模糊化的处理,反映出多元的道德评判标准下民间社会特有的语言智慧和文化逻辑。
(二)故事的结尾:叙事的总结
在明代的诗与故事民间故事类型中,诗作为叙事的总结插入到故事的尾端属于较少数情况,这种情况下的“诗”往往不太注重自身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蕴,只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总结故事的内容,起到概括和纲领的作用,比较容易让读者记住,也方便故事的流传,如“三笑事”型故事本身以三个并不关联的故事并列展开,线索并不明晰,但在文末加上了“常有人赋嘲讽诗一首:稳婆生子收生处,医士医人死病家。更有一般堪笑者,捕官被盗叫爷爷。”加以总结,整个故事方才从零散趋于统一,这更体现了抒情诗歌和叙事文本相结合的技巧法则与口传文学无意识的选择和书面作品有意识的加工自然交织的统一。
三、雅俗共赏的语言特色
(一)生活化的通俗语言
诗与故事类型属于民间现实故事,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对社会生活有生动地体现和深刻的反思,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在语言艺术形式上,诗与故事类型的民间故事利用“诗歌”这一叙事核心,文艺的展现多面而真实的现实生活。明代袁宏道在《答李子髯》诗中说:“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偕君听竹枝。”[4]“闾巷有真诗”说的就是李梦阳“真诗在民间”的观点,表达对民间作品中诗歌的认同,以及对世俗价值的张扬。明代的现实生活既有解缙父子“千年老树为衣架,万里长江作浴盆”随性风雅,也有郑唐“精老乌龟”首字讽刺诗的犀利揭露,更有三笑事类型对生活现实细节的捕捉和啼笑皆非的巧妙处理等,三言两句诗性的反应明代社会生活群像,体现出作者精妙的语言处理功力。
简明扼要的旁白和人物诗化的语言共同构成了“诗与故事”类型的人物刻画系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民间故事的演绎脱离不开生动鲜活的人物,诗与故事类型的民间故事亦然。这一类型的故事情节通过安排人物间诗化的语言和精神的交流,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使人物形象更加的生动立体,也更为听众所喜爱。有的时候,人物形象的丰满是通过情节和对话的增加和修改来实现的,而这一方法早在先秦就已经实践。宋代朱熹在《楚辞辩证•天问》中说道:“而次问特战国时俚俗相传之语,如今世俗增伽降无之祈,许逊斩蛟蜃精之类。本无依据,而好事者遂假托撰造以实之。”[5]前文所述春雨似油型故事在自明代以来的演变中主人公——幼年解缙的对话数量有了增加,这些诗性的回答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幼年解缙的形象,由坚韧聪慧、才思敏捷到明辨是非、幽默诙谐、坚韧聪慧、才思敏捷,也让玩笑背后理性现实更自然直接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二)文人诗学语言的借鉴
“诗与故事”类型的民间故事记载始见于明代,明代商品经济发达,文化下移,世俗文学繁荣,明代诗学受到俗文学和俗文化的影响产生了新的求“真”观念:世俗俗情得到士大夫的认可,进入诗学表现领域;士大夫对个性的追求和张扬;强调诗歌创作过程的自然性和诗歌本身的真实性。“诗”的领域里的求真观念同时也影响了民间文学领域的创作。明代的日常用语与秦汉时期已有较大差距,可以说在明代已有了古与今的区别。诗与故事类型的民间故事虽在故事的讲述中大量运用了诗歌、对联的元素,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民间故事文学性较强,但与明代相对的古代的同类文献对比,则更加的通俗易懂。明代袁宗道在《论文》中对此现象进行了相关论述:“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转隔碍,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论文曰,辞达而已。达不达,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无不达者。今人读古书不即通晓,辄谓古文奇奥,今人下笔不宜平易。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6]通俗易懂的故事语言不仅是时代文化背景下的必然,更是创作者在写作之初考虑的故事能不能为社会各阶层接受的问题和这样的故事能不能满足民间故事口口相传的要求的问题。明代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有言:“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7]明代的诗与故事类型的民间故事中所出现的诗歌有非常明显的口语化、俚语化的倾向,有时甚至俗气扑面。如三婿赞马型的故事里大女婿和二女婿分别用“水面搁金针,金针犹未沉”“火上放鹅毛,鹅毛尚未焦”来形容老丈人的良驹速度之快,而三女婿给出的答案却是“丈母撒个屁,空门犹未闭”。从作者设置的三个答案看出,语言风格上都是简明易懂,生动形象的,然而有时为了故事效果,俗气也在所难免。
四、思想文化内涵
诗与故事类型的民间故事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展现特定时代下的生活模式,创作者将生活与想象、叙事与诗情、体验与感悟融合在一篇之中,呈现出一种具有生活意蕴的、富含诗学审美特征的风格。
诗与故事类型的民间故事中频繁出现的“作诗联对”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往往巧妙融合诗意与哲理,成为现实生活中百姓美好愿望的象征性表达。“作诗联对”一方面既丰富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增强故事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又在另一方面利用诗歌和对联本身的文体优势提升了故事的艺术感染力,因此这种象征性对诗与故事类型的民间故事的讲述和传播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明代诗与故事类型的民间写实故事的诞生和发展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各阶层的人民对诗学生活的崇尚。这种崇拜是受到明代独特的市民大众文化和传统文化滋养的产物,反映出明代市民阶层深厚的文化情结:这种情结在普通市民的家中是亲人聚会的调剂品——如三婿赞马型故事中三个女婿按照老丈人的要求为新马题赞,在文人家是日常生活里即兴的玩笑——如长江作浴盆型故事里解缙和他的父亲在江中洗浴时即兴而起“千年老树为衣架,万里长江作浴盆”的诙谐对子。这些诗歌、对联生活化的展现体现了明代市诗学生活的普遍性,也隐含了明代这一类型民间故事的创作者们对于深厚诗学传统的自信和自豪,他们的笔下承载着“民间”与“文学”——文采飞扬间传播诙谐幽默的促狭和浸润传统诗学精神的文化。可以说正因为根植于明代文化的诗学传统,诗歌和对联才得以在民间故事中绽放独特的魅力,从而形成“诗与故事”这一特殊的民间故事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