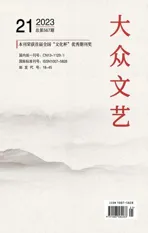重构疯癫
——符号学视域下《太阳照常升起》中疯妈的主体身份建构
2023-12-19张潇
张 潇
(仰恩大学,福建泉州 362014)
1964年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丁•麦茨发表的《电影:语言系统还是语言》一文将电影视为一种符号系统,这就为电影批评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径。就国内的电影创作情况而言,姜文导演的充满隐喻味的《太阳照常升起》无疑是一部典型的具有符号学批判价值的电影作品。
《太阳照常升起》被姜文称作是“上苍赐给他的礼物”[1]。该作之所以受到姜文如此的偏爱,是因为这是一个植根于他生命体验的时代幻梦。而编织梦的关键即在于姜文充分发掘了影像的符号①潜能,他跳跃了语言的逻辑藩篱,利用暗含隐喻的视觉符号在瞬间引发读者的下意识反应,这与俄罗斯符号学家洛特曼所认为的“电影是由不同符号建构而成的复杂系统,电影文本是在不断克服其语言手段,践行符号潜能”[2]的观念不谋而合。正是基于对符号的精准把握,姜文造就了一个张扬男性伟力的时代幻梦。梦里萦绕着旧时代的视觉符号,由“红太阳”所统筹,建构成一个承载男性权力春梦的符号系统。男人基于符号话语来践行权力,并因此实现对于女性的意向性塑造,将她们异化为权力的能指。然而,这样的叙事策略却被一个叫作疯妈的女性所颠覆。那么,疯妈是怎样在男性的视野中实现自我的言说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影片的符号表达中捕捉到人物的生命欲求。
一、男性叙事中的疯妈:作为权力的能指
观众对于疯妈的形象感知首先体现在姜文的叙事安排中。作为一个有着旺盛表达欲求的非主流导演,姜文不屑于将电影作为故事的附庸以满足观众的格式化视野[1]。于是他用碎片化的形式疏离情节,试图在魔幻的图景中显现出荒诞的真实。也因此导致了疯妈的形象被切割在叙事的碎片中。在不同的碎片中疯妈面临着李不空和儿子的注视,作为他们权力的能指和故事的注脚,沦为了空洞的符号。
(一)树上的女疯子
影片的第一组叙事段落标记为“1976,春,南部”,由一双长着黄须子的鱼鞋开启。疯妈买鞋,儿子撞翻了鞋,疯妈追逐儿子。伴随着摇摇晃晃的镜头语言,久石让的配乐响起——《太阳照常升起》。而后,魔幻的情节发生了:一只锦鸡叼走了疯妈挂在枝头的鱼鞋,还一直叫嚣着“我知道,我知道。”于是,疯妈狂热地追逐着小鸟。这一幕恰好被儿子看到,摄影机由此开始追随着儿子,从儿子的视角来呈现疯妈的疯狂。儿子看见疯妈在树上大声地重复着呼唤:“阿廖莎,别害怕,火车在上面停下啦!天一亮他就笑啦!”儿子看见母亲的状态,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接疯妈下树。因为在他看来母亲的所作所为是丢人的举动。在第二次接疯妈下树时,疯妈给他讲了个寓言,儿子给这个寓言取了个名字,“树上的疯子”,批判性地暗指着疯子对于现实的脱离,以此映射自己的母亲。
村庄并不是疯妈的家乡,而是疯妈丈夫李不空的故乡,疯妈在此如同一个异乡客,接受着人们的注视与毁谤。在儿子去村口迎接了一个男人后,疯妈消失了,演变成河流上漂淌着的旧式军装。至此,儿子没有发现疯妈的秘密,观众也没有看懂疯妈的形象,二者的对于疯妈的感知,都共同地停留在树上的女疯子以及一个遥远的阿廖莎。
(二)失语的姑娘
后来疯妈的衣服在河上漂流,梁师傅弹唱的《美丽的梭罗河》响起,疯妈的结局成了歌曲的情景,河流不断虚化,吉他逐渐明朗。尽管衔接两个段落之间的转场动作顺畅自然,但依然无法弥合情节线索的断裂,观众只能暂时将疯妈的印象搁浅,从而关注于当下的片段。
影片的第二个段落围绕着一把脱离枪带的猎枪和一个湿漉漉的林医生展开,突出表现了梁师傅唐师傅两个男人的纷纷情欲。在当时,隐喻是表达情欲最安全的方式,两个男人中唐师傅因为擅长隐喻而在当时压抑环境中犹如蝴蝶穿花,得到了林医生和食堂一众女职工的倾慕。而梁师傅则因为直白的表达屡屡受挫,被误认为是偷摸林医生屁股的流氓,最终自杀收场。梁师傅死后,疯妈重新回到了荧幕,然而却不再是观众所熟悉的疯癫状态,而是很多年前一个沉默不言的寻夫姑娘。她所寻找的李不空虽然从未出现,但观众却早已将对唐师傅梁师傅的印象残留,填充进这个空洞的形象中。因为从疯妈的沉默中,观众可以觉察到李不空同样也是一个擅长欺骗女性的男性叙事者。年轻的疯妈在戈壁上遇见了从南洋回来寻找爱人的姑娘,两个姑娘骑着骆驼并肩而行,一个喋喋不休,一个沉默不语,尽管她们都是在践行着寻夫的主题。疯妈的沉默隐喻着存在感的缺失。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中写道:“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所以我们能够随时随刻从这所家宅以这种方式以达乎存在者。”[3]当镜头切换到疯妈寻夫的线索时,再次重申了疯妈的失语,基于她所找寻的李不空的缺位,疯妈所有的表达都是无效的。疯妈的言语难以在社会空间落地,从而发挥意义。与此同时,南洋姑娘则沉浸在高举着猎枪的唐师傅的怀抱里,就像很多年前被李不空的枪所吸引的疯妈一般。
疯妈因为李不空而失语,又在很多年以后,被李不空的儿子叙述成为树上的女疯子。可以发现,在男性叙事中,男性基于符号话语垄断了对于现象的定义权,而作为被定义的疯妈缺少自我言说的机会,只是作为男性权力意志的能指。
二、疯妈的选择:在疯癫中存在
在对影片完成文本阅读后,终于可以就疯妈形象提炼出来“树上的女疯子”和“失语的姑娘”这两个核心的符号。基于时间线索把二者串联起来后,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年轻的疯妈因为“失语”的痛苦,最终疯癫。但是,这样的串联无法延续姜文电影的审美趣味,更无法解释疯妈旺盛的生命力。所以有必要从符号层面深入发掘疯妈与疯癫之间的对话,在重读中发现疯妈生命的温度。
(一)疯癫的前奏——疯妈的叛逆
在疯妈正式被赋予疯癫的名义前,她曾经发生过对于男性叙事的叛逆。这一幕出现在在仓库里接受李不空的遗物的时候。当时,李不空想要通过桌子上破了洞的军装、三只辫子进行隐喻,妄图再次实现对于疯妈的意向性塑造,就像很多年前用枪和军装成为疯妈心中的英雄那样,只不过这次他是想彻底抛弃疯妈。
这种展示暗含着李不空对于疯妈的支配逻辑:通过桌上的物件对自身形象进行陌生化处理,于是疯妈为了实现认知只能屈从于当下的语境中,去顺从符号所蕴含的隐喻,去接受李不空已经死去的谎言。对此,疯妈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从此,你就叫阿廖莎吧。”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回答,因为这句话其实意味着疯妈不再忠诚地接受着李不空的诠释,而是主动地定义李不空。从此,疯妈终于有勇气去表达自己的欲求。
离开仓库以后,疯妈在火车上生下孩子,而火车经过的午夜戈壁上正在进行着一场盛大的狂欢,这是唐师傅的婚礼。此时疯妈的故事和梁师傅唐师傅的故事形成了一个巧妙的互文关系,狂欢场景中梁师傅肆意地拍着女人们的屁股,女人在此作为男性欲望施展的客体,然而火车里的疯妈则已经试图走出这样的客体位置。疯妈产子后抱着孩子站在高塔上对着照常升起的太阳高声呐喊,她不仅消解了李不空的符号话语,甚至还将这种用符号施展欲望的方法为己所用,恣意汪洋地发泄着心中早已压抑许久的情感,这无疑导致了男性叙事的危机,从此,她成为别人口中的疯子。
(二)疯癫的初衷——规训疯妈的权柄
麦茨认为,不同于寓意明确的形象符号,相对抽象的设定性符号拥有着更多被诠释的可能[4]。作为典型的设定性符号,疯癫本是临床医学对于精神病患者的症候表述,却如福柯所言,在社会层面异化成为实现权力意志的权柄,表达着理性秩序对于非理性人群的排斥和否定[5]。在两性关系中,这个权柄往往被男性拿来实施对于女性的支配,巴特勒将这种支配行为言说为“性别操演”②,由此诞生了“阁楼上的疯女人”③。女性因为疯癫,所以需要接受理性秩序的安排,比如《雷雨》里周朴园借口繁漪有病,所以得好好听话。而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李不空通过信件向疯妈讲述了“树上的疯子”这个典故,隐晦地表达对于疯子的偏见;而疯妈的儿子则愤怒于他母亲疯子的身份,执着于让疯妈下树,去做回一个正常人。父与子都试图以疯癫为名强调对于疯妈的塑造权。
(三)疯癫的演化——疯妈存在的栖居
然而,“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命运并没有在疯妈身上应验。其本质原因在于疯妈并不排斥疯癫的身份,无须为了摆脱疯癫的身份而接受规训。恰恰相反,她充分享受着疯癫。疯妈基于疯癫斩断了与社会的交流机制,形成了自我意识的闭环,那么男性利用疯癫所言说的权力意志自然就土崩瓦解。此外,疯妈显然注意到了疯癫者在人世间自说自话的特权,她开始利用疯癫的身份去建立自己的符号系统,并以此对抗过往所接受到的规训。于是,疯妈将疯癫从男性的权柄演化成为自身存在的栖居之地。
她首先对李不空的形象进行了消解,将李不空从居高临下的“英雄”演变成了一个任由自己言说的“阿廖莎”。而消解李不空的关键则在于对于枪的消解。在李不空标榜自我的符号体系中,枪是最核心的要素,被他设置为男性力量的隐喻,并以此吸引女性。而在疯妈的表述中,枪可长可短,枪演绎成了一种虚伪的面纱,骗人的道具。枪不再能够吸引疯妈,枪直指罪恶。疯妈的认知在那把标志性的猎枪上得到了验证。这把猎枪本是一位母亲给自己儿子的礼物,作为儿子的梁师傅却把枪赠与唐师傅,自己则用枪带自缢。于是这把猎枪脱离了枪带,好似一个男人脱离了他与母亲关联的脐带。没有了枪带的猎枪彻底沦为欲望的能指,新主人唐师傅曾在猩红色的“天尽头”用猎枪狂放地张扬着自己的力量,一手怀抱着美女,一手高举着猎枪,射向天空。很多年后他又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用这把枪杀死了疯妈的儿子。由此得知,脱离了母性关联的枪最终引发了危险的漩涡,吞噬着女性,也吞噬着掌握着枪的男性自身。好在另一个母亲疯妈用疯言疯语对枪进行了祛魅,祛除掉了枪暗指男性荣耀的神圣光环,并将其复归回暴力的本质,于是,李不空唐师傅等人利用枪所建构的话语权荡然无存。疯妈对着鸟儿所说的“你也不是什么都知道”,正是对于李不空的胜利的宣告。
脱离了枪的指涉的疯妈,在疯癫的行为中再造了一套自圆其说的符号系统,以此来满足自己的存在体验。她用鹅卵石筑成的房子模拟子宫,不仅通过伪装来避免男性的染指,还在其中摆放红色娘子军的照片作为自己的旗帜;用爬树和挖树的行为复刻当年生育的场景;在追逐鞋子的过程中复刻当年寻找孩子的情形。可以发现,疯妈先是用疯癫话语摧毁了男性叙事的施展路径,又在男性缺位的情况下自给自足地演绎了恋爱到生育的完整过程,并从中获取到存在的主体性感知。
在自身独立以后,疯妈甚至能够对儿子的认知进行重塑,成功地在实践层面瓦解了男性叙事的延续。儿子虽从未与父亲李不空谋面,却依然通过父亲残留的线索沉浸在对于父亲的骄傲中,试图延续父亲的意志,对自己的母亲进行塑造,让她做回一个正常人。为此,他不惜去偷窥疯妈的隐秘生活。疯妈清醒地发现了儿子的行为意图,她反倒利用李不空的书信潜移默化地对儿子的认知实现重塑。李不空的书信本是父子意志传承的载体,疯妈却将信件的解释权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于是父子之间的交流路径被斩断了,儿子所接受到的父亲的信息其实是他母亲的意志。疯妈的一句“只能说你没懂,不能说你没看见”让儿子返璞归真,脱离了来自父系传承的权力欲望,回归到纯然无知的天然状态。引发他对于真实的尊重,对于世界的好奇。讽刺的是,后来也是因为求知直接导致了儿子的死亡。在实现这三个目的后,疯妈撑着河边的一块草皮消失不见,她不再存在于他者的注视中,她想去哪就去哪。
三、结语
基于符号的视域欣赏《太阳照常升起》,可以发现,在太阳的照耀下,男性深陷进对于权力的无意识崇拜中。他们将权力意志隐含在符号话语中,以此实现对于女性的意向性投射,妄图把她们异化成为权力的能指。而这种权力施展路径在疯妈这里却遭遇了危机,于是他们赋予疯妈了疯癫的名义,意图以疯癫为名对疯妈进行深入的规训。然而,疯妈却在犹如革命般的激情中对疯癫进行了重构,使其成为自身存在的栖居,因此掌握了通过符号话语言说自我的能力,在疯癫中生长出旺盛的生命力。于是她能够走出男性的叙事安排并打破权力对于真实的遮蔽,最终实现了主体身份的建构,成为故事里最接近太阳的人。
注释:
①符号是群体信息交流过程中物体、现象、概念的具体指代形式。电影作为一种交际系统,影像符号是其表达意义的重要路径。
②此概念出自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她认为在两性关系中,男性作为主体对作为客体的女性进行意向塑造,女性需要进行操演行为以满足男性的期待视野。
③此概念出自S.M.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是指被男权以疯癫之名进行支配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