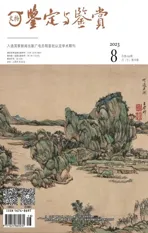浅析《金庞整孝行碑》
2023-11-13邵丹
邵丹
(芮城县博物馆,山西 芮城 044600)
0 引言
《金庞整孝行碑》,青石质,圆首,方座。高1.6米,宽0.6米,厚0.18米,额题“大金庞整孝行之记”,大定二十二年(1182)十月八日立。碑文楷书,26行,满行40字。原碑卧原村乡任家庄村北农田中,1982年运回芮城县博物馆。碑文有数处漫漶不清,碑文识读以《三晋石刻大全》及《山右石刻丛编》为准。
1 碑文所载人名、地名释义
庞整,“世居河东县风陵乡小李村”,妻范氏。河东县,指今永济市。永济,古称蒲坂,秦属河东郡。西汉高祖二年(前205)建蒲反县,东汉改为蒲坂县,并沿用至北周。隋开皇十六年(596)置河东县,大业二年(606),蒲坂县并入河东县,并沿用至明。此碑所立之时正值金世宗时期,此时河东县隶属河东南路河中府。清雍正六年(1728),置永济县。风陵乡,指今风陵渡镇。风陵渡,又称风陵津,原为战国时期魏国故地封陵,秦承其名,有“封陵津印”流传后世,后封陵演变为风陵。《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唐代河东道河中府下辖十三县,其中“河东,次赤。南有风陵关,圣历元年(698)置”。自永济置县以来直到清代、民国,风陵渡归其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风陵渡归芮城县管辖,此碑也由芮城县博物馆收藏。
庞整与其妻共育子四人,由碑文“善信之祖考已逝……父庞整挺石勒字”“长男庞源□□□省”及文末“源深温善信等同立石”可知四人从长及幼分别为:庞源、庞深、庞温、庞善信。因善信本为道士对俗家信徒的称呼,此作其道名。较此碑稍后的《金明昌六年冲和大德雷公寿堂记碑》的碑文末也有记载:“门人苏善信、郑善基、李善治,法孙种惟静、韦惟仁、李局静等立石。”由此可见,庞善信为其道名,本名不得而知,仅知其“隶业于本村常志清观”。
碑文撰写者其名因碑文漫漶无法得知,仅知其为张姓,籍贯不详。据文中撰者自述其“不幸流离顿挫,株守途穷”,可以推断撰者或许不是本地人,只是寄居在小李村。碑文书丹者为张拱,“蔚□逸人张拱书丹”。逸人,也称逸民,一般指节行超逸、避世隐居的人。其籍贯仅余首字“蔚”,查《金史·地理志》有西京路蔚州,“下,县五:灵仙、广灵、灵丘、定安、飞狐”。至于蔚县,则是晚在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才改蔚州卫,置蔚县。所以此处“蔚□”应指蔚州。
范蔚宗,即范晔,字蔚宗,南朝宋史学家,撰有《后汉书》。陈蕃,字仲举,举孝廉入仕,东汉桓帝、灵帝时名臣,士林领袖,学中流言“不畏强御陈仲举”。赵宣,《后汉书·陈蕃传》所记人物,因孝行作伪被陈蕃论罪处罚。撰者以其孝行之伪来反衬庞整孝行之真。
姚栖云,唐孝子。撰者自述“予又尝览旧县之图□,见唐孝子姚□云行状,□以葺庐墓□三世同居,后□为□□旌大门闾,于今辉映乡社”。据《宋史·孝友列传》记载:“姚宗明,河中永乐人也。其十世祖栖云。(栖云)招魂葬其父,庐于墓次,终身哀慕不衰。河中尹浑瑊上其事,诏加优赐,表其门,名其乡曰孝悌,社曰节义,里曰敬爱。”撰者以庞公孝行可媲美姚栖云,且都以孝行获得皇帝诏奖,均属光耀门楣、名泽乡里之事。
2 庞整孝行事迹及立碑始末
据碑文记载,庞整之父早逝,其母王氏逝世后,庞整“挺石勒字誓字:必为寝处冢藏,定省如在”。在大定二十年(1180)三月二日迁葬时,庞整“屏去妻孥□隧而入,敬爱存诚,不啻生事”。越初八日,庞整长子庞源前去探视,发现其父仆倒在地,“救两时须方苏”。在庞整为父母守孝期间,曾有警异数事,撰者直述如下:其一,“□十八日,于圹中觉有秽恶□□”,庞整执意不回,到了第二天“反为异香芬郁”。其二,“六月十二日,公以饮膳□□河鱼作梗,不胜孱弱。是夕,有二人送药来,服之立愈”。这些事迹及异象经上报朝廷,得到金世宗的认可,下诏予以褒奖。庞整为父母守孝时所显示的种种异象,是自东汉以来旌表制度宣教的谶纬化在金朝的反映。这些所谓异象,本身充斥着各种鬼神附会及天人感应,在东汉及其后的历代史书中不绝,常见的诸如:有白鹊、白乌、白狼、白兔等白色动物在庐墓旁出现;有甘露降下、甘泉涌出等异象;或者飞鸟群集,禾生九穗,光怪陆离,无奇不有。《金史·孝友列传》中也记有此类异事。如王震,“母没,哀泣过礼,目生翳。服除,目不疗而愈,皆以为孝感所致”。又如刘政,“(其母)葬之日,飞鸟哀鸣,翔集丘木间”。这些记载于史书中的孝亲异事,客观上强化了孝子孝行的表现效果,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人们思想认知层次相适应,但在今天,我们应予以客观看待。
关于立碑经过,撰者在碑文里有详述。撰者在其家“掩门块坐”时,有人叩门,“起视之,即小李村黄冠庞师也”。黄冠,即为道士代称。由其称“善信之祖考已逝……父庞整挺石勒字……”可知来人就是庞整的小儿子,在本村常志清观中为道士。善信,本是对佛道信徒的称呼,即善男信女之意,此处用作其道名,撰者则尊称其黄冠庞师。撰者听其讲述其父庞整于大定二十年(1180)三月二日入隧孝亲,定省如在的事迹,除此外还有期间发生的“警异数事”。撰者自述“祝予为父庶扬其美,恳求再四,义不得辞,因直述其事云”。可见,此孝行事迹是由庞整之子告诉撰者,并请求他为庞整孝行进行书写褒扬。后“公之孝行远达宸听,诏下褒美”,庞整孝行事迹经官府上报朝廷,得到了金世宗的褒奖,并最终于大定二十二年(1182)十月八日立石以记。中国古代丧服制度规定,子女为父母守丧,衣斩衰,服丧三年,汉代戴德、郑玄将三年丧期改为二十七月。自唐代到清代,基本实行这一丧期制度。按照这一制度,综合碑文中服丧期开始之日与立碑之日可得出结论,庞整所服丧期符合“二十七月之丧”的规定。
3 碑文所反映金世宗时期的宗教政策及教化措施
传主庞整,碑文记载其“为人敦厚,颇乐天竺法”,可见其对佛法颇感兴趣。庞整“内一子为道士,隶业于本村常志清观”,撰者称其黄冠庞师,即庞善信。而撰者本人,则为饱学宿儒。其在碑文中自述“自龆龀间侍□先子”,之后“求访硕德耆儒”“自尔后,潜心黄卷者三十年”,后流离顿挫,“止与周孔方策相对而已”。儒释道三教在庞整孝行这一事件上达成了一致:身为道士的庞善信为信奉佛教的父亲庞整的孝行事迹,向本村儒生求文,并得到了最高官方金世宗的降诏褒奖。这个事件恰如其分地诠释了当时儒释道三教在河东地区相得益彰的情况,这既与金世宗时期的宗教政策与教化政策密切相关,也是儒释道三教融合大背景下的产物。
3.1 金世宗时的宗教政策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之后便深入内地各处传播。“至少在公元3至4世纪,佛教已传入山西”,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唐时达至兴盛。到了金朝统治时期,山西佛教经过金初的恢复后有所发展,在世宗、章宗时期达到了发展高峰。金世宗对佛教的态度有过几次反复。早年间,金世宗受其母贞懿皇后信佛的影响,颇信佛法,并为其母增大东京清安寺旧佛塔,以志纪念。大定八年(1168),金世宗对臣下秘书监移剌子敬等说:“至于佛法,尤所未信。”并以“梁武帝为同泰寺奴、辽道宗以民户赐寺僧,复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为戒。大定十四年(1174),诏谕宰臣:“闻愚民祈福,多建佛寺,虽已条禁,尚多犯者,宜申约束,无令徒费财用。”大定十八年,(1178)下禁令“禁民间无得创兴寺观”。直到大定二十六年(1186),“香山寺成,赐名大永安,给田二千亩,栗七千株,钱二万贯”,并频繁临幸寺庙:“八月辛丑,幸仙洞寺。壬寅,幸香林、净名二寺。九月甲辰朔,幸盘山上方寺。因篇历中盘、天香、感化诸寺”。此时金世宗对佛教态度大变,或与其太子于大定二十五年(1185)早逝且新储君未确立有关。虽如此,金世宗时期仅山西地区新修、重建的寺院就多达76所,在整个金代占比最重,可见其时佛教香火之盛。同时期的河东地区,也有乡民为父母祈福,捐资修建经幢的事例。如现藏于芮城县博物馆的《大金陀罗尼经幢》,为许安世、许安民为其祖父祈福而建,于大定二十六年(1186)立石。
道教是中国传统宗教,早期以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为两大派别。到了金朝,道教主要有三大派别,分别为太一教、大道教、全真教。三大派别在传教过程中都借助了金朝帝王的支持,以金世宗为例,他曾多次召见三派掌教人物,如曾诏大道教掌教刘德仁,诏太一教二祖肖道熙往长天观,诏全真教王处一、丘处机到京师问询。其中全真教创教时间最晚,但最为流行,影响最大,在山西地区先由晋南传入,后传遍三晋,道观数量以“临汾、运城两地区的分布最为广泛”。如碑文中的常志清观就位于小李村,应当是本地信众集资修建。
儒教,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包含许多宗教元素,视其为宗教。金朝虽是少数民族所建政权,但对于儒教也是颇为重视。以金世宗为例,他虽有女真本位思想,但还是继承了熙宗、海陵王的汉化政策,金朝在其治下,典章制度建设又更进了一步,其汉化措施已有诸多论述,现仅论述其对孔子的尊奉措施。金世宗即位不久,于大定三年(1163),继承历朝尊孔政策,封孔子后人为衍圣公,“以孔总为袭封衍圣公”。大定二十年(1180),又特授其兖州曲阜令,“特授袭封衍圣公孔总兖州曲阜令,封爵如故”。同时,祭祀孔子的礼仪也得以完善并施行。大定十四年(1174),国子监进言,以“国家承平日久,典章文物粲然备具”,请求拟定祭祀孔子的器物、行礼次序等内容。于是礼官参照唐《开元礼》,制定了详细的祭祀孔子的礼乐仪式,并于大定二十三年(1183)得以实施,“以尚书右丞张汝弼摄太尉,致祭于至圣文宣王庙”。
3.2 金世宗的教化政策
自汉代以来,中央朝廷便将“以孝治天下”的儒家理念制度化,此举为后世历代王朝所继承,影响中国两千余年。金朝虽是少数民族政权,但也继承了这一政策。以金世宗为例,其本人就是孝子。他对其母十分孝顺,“深念遗命”,为母亲建神御殿,“招有司增大旧塔,起奉兹殿于塔前”。此外,大定八年(1168),又制定了“子为改嫁母服丧三年”的制度。对皇子、亲王,金世宗教育他们“人之行,莫大于孝弟。汝等宜尽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儒家经典《孝经》更是被金世宗用作亲军的教育教材,大定二十三年(1183)“以女直字《孝经》千部付点检司分赐护卫亲军”。除了借用中原汉文化孝义经典外,金世宗还注重从其本民族的淳朴古风中汲取孝义教化,称“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并以此告诫其皇太子:“汝惟无忘祖宗淳厚之风,以勤修道德为孝。”
对于孝义之人,金世宗也予以褒奖,主张“凡士民之孝弟渊睦者举而用之”。如移剌余里也,其妾之四子为嫡母守孝三年。金世宗“因猎,过而闻之,赐钱五百贯,仍令县官积钱于市,以示县民,然后给之,以为孝子之劝”。又如孝子刘政,“世宗时尝官之”,这是世宗朝赐孝子官职的唯一例子。除此,还有一事可见金世宗对孝子的褒奖。大定二十七年(1187)四月庚午,金世宗因为所进御膳味不调适询问尚食局直长,得知其因为“老母病剧,私心愦乱”,所以才“有失尝视”,金世宗宽恕了其过失,“上嘉其孝,即令还家侍疾,俟平愈乃来”。
《金庞整孝行碑》碑文以撰者口吻道出“今明天子在上,制礼乐,举孝廉,行见公之孝行达于宸听,诏下褒美”。如前文所述,世宗对移剌余里也之子的孝行赐钱奖励。章宗时,对孝子的嘉奖也有物质奖励,明昌三年,棣州孝子刘瑜“诏赐粟帛”,赐锦州孝子刘庆祐绢、粟,云内孝子孟兴“诏赐帛十匹、粟二十石”。照此制度,对庞整孝行,金世宗也应该给予过物质方面的奖励,碑文中略去不谈,只侧重精神嘉奖。碑文以撰者之口将金世宗降诏褒奖的目的道出,“不惟□渥光大于一门,亦将移风易俗”,使“小儿皆慕曾闵之行,贻来世之懿范”。曾闵,即曾子与闵子骞,皆孔子弟子,且皆以孝行著称。金世宗对于庞整及其他孝子的褒奖,目的在于维护和延续自汉以来的“以孝治天下”的政策,进而巩固统治。综观《金史·孝友列传》,终金一世,仅记载孝友六人,此碑内容可补史之阙。
3.3 三教融合的大背景
儒家,或称儒教,自孔子创立以来,历经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及秦朝的焚书坑儒,至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儒家超然于百家之上,获得了独尊地位。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与先秦道家有密切关系,在汉代黄老思想的基础上,吸收古代神仙方术和民间巫术,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得以形成。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儒释道三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相互争斗、相互学习、相互融合,在隋唐时期便有三教合一的趋势,唐高祖李渊称“三教虽异,善归一揆”。经隋唐时期的三教讲论与融合,三教合流在北宋时期已大致成型。到了金世宗时期,处于儒释道融合的大背景下,再加上金朝为女真民族创立,金朝统治者在国家政策层面,对于儒释道三教并用、三教并崇,皆为统治之用。以孝道思想为例,佛教与道教在与儒教的交流融合中发展、修正自身学说,淡化其宗教内涵,并逐步与世俗伦理相结合,在宋金时期在其教派主张中得以显现。如北宋著名禅师契嵩,著有《孝论》,指出孝道既是成佛的基础,又是成佛的目的,儒佛在孝道上并无二致。道教重要派别之一的全真教在创教之时,其教祖王重阳也将儒家《孝经》作为全真教经典之一。庞整本人,碑文中虽未明言其为佛教徒,仅称“颇乐天竺法”,其为母守孝,“未遵佛教仪轨”。笔者认为,三教融合的历史大背景,加上金朝统治者的三教并用政策,才使得庞整虽信仰佛教,但仍遵从儒家孝道为母守孝。
4 结论
综上,对《金庞整孝行碑》记载的庞整为母亲守孝的事迹,其孝心应该予以肯定,其孝行则应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考察,至于其在守孝期间发生的种种异象,则应该予以客观对待。该碑侧面反映了在金世宗时期,统治者三教并用的宗教政策及继承中原汉王朝“以孝治天下”的教化措施,此碑也是儒释道三教融合大背景下的产物,反映了普通乡民无论其宗教信仰如何,其安身立命之本仍旧是儒家思想,足见儒家思想影响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