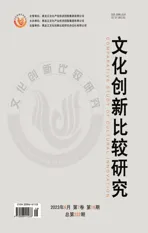王昌龄《诗格》中的主客交融理论探析
2023-09-12吴佳蔚
吴佳蔚
(海南开放大学,海南海口 570208)
诗格类著作的发展在唐五代时期日益兴盛。罗根泽提出,诗格有两个兴盛的时代,一在初盛唐,一在晚唐五代以至宋代的初年[1]。初、盛唐诗格的基本面貌,最直接、最基本的材料是日本僧人空海法师的著作《文镜秘府论》。《文镜秘府论》是一部集初、盛唐诗格之大成的著作。作为盛唐诗格类著作的重要代表,王昌龄的《诗格》被收录其中。《诗格》分为两卷,卷上包括十七势、六义、论文意等部分,卷下包括诗有三境、诗有三思、常用体十四等。王昌龄对唐代诗格发展贡献突出,是强调精神与世界统一的“诗格”的先驱思想家[2]。
1 主客交融的诗歌体势
唐五代诗格中的“势”,是我国古代诗学理论中的重要范畴之一。王昌龄对“十七势”进行了具体的论述,探讨了作诗的方法、样式、诗意的呈现等。“十七势”是王昌龄《诗格》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体现了王昌龄的文学理念,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国内外不少学者都曾提出自己对于“十七势”的理解。美国学者李珍华在《王昌龄研究》中提出,《文镜秘府论》中《地卷》十七势提出比较详尽的技术问题以指导如何处理诗头、诗肚和诗尾的结构。在王昌龄看来,“势”既有关于结构,也有关于气势。他所论的十七势,虽然每一势着重处理一首诗中的一个部分,整体来说是为了将各个部分衔接在一起,使从头到尾气势贯通无碍[3]。李振华简要地概括了“十七势”的要义,浅显易懂。
我国学者王运熙、杨明则认为,《文镜秘府论》地卷引王昌龄论“十七势”的文字,着重讲诗的章法句法。体势在文学理论批评中大抵指作品的风貌。王昌龄的“十七势”,多指一篇中部分章句的写作技巧[4]。王运熙、杨明通过《体性》《定势》和王昌龄“十七势”的对比来分析“十七势”的涵义。巩本栋则从“势”的来源、本义及其与兵家、书法理论的关系来分析“十七势”的内涵,他认为:“王昌龄《诗格》中所列‘十七势’,其取名同于书论,直接承袭兵家之书,讨论作诗的技巧和方法,其用意亦承刘勰文章体势之说和兵家、书家之说,是论诗歌的运思或意脉的流转、向背和变化。 ”[5]
根据学者的观点,总的来说,“十七势”不仅论述了诗头、诗肚和诗尾的具体作法,如“直把入作势”“一句直比势”“含思落句势”等,还论述了如何使诗歌诗意更巧妙地呈现出来、如何使诗歌更加具有韵味,如“理入景势”“景入理势”“生杀回薄势”等,对后人创作及理解诗歌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1.1 “理入景势”“景入理势”
王昌龄在“十七势”中对“理入景势”和“景入理势”这“两势”都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如,第十五,理入景势。理入景势者,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理欲入景势,皆须引理语,入一地及居处,所在便论之。其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昌龄诗云:“时与醉林壑,因之惰农桑。槐烟稍含夜,楼月深苍茫。”再如,第十六,景入理势。景入理势者,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凡景语入理语,皆须相惬,当收意紧,不可正言。景语势收之,便论理语,无相管摄。方令人皆不作意,慎之。昌龄诗云:“桑叶下墟落,鹍鸡鸣渚田。物情每衰极,吾道方渊然。”[6]
王昌龄在这“两势”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情”字,但这里的“理”即诗人主观之“理”,包括诗人意欲揭示之理、诗人的情感等。王昌龄“理入景势”中论述的是在诗歌创作中如何以“理”入“景”,使“景”与“理”相惬。他认为诗歌不能一味讲“理”,需要和景相结合。“皆须引理语,入一地及居处”即诗人主观之“理”须融入景物之中,使诗人之“理”与自然之“景”融合在一起,否则诗歌索然无味。正如王昌龄的诗歌(佚诗)先提及因陶醉于山林之中而无心农桑之事,然后描绘了山林中静谧的夜色——枝叶茂密的槐树逐渐被月色吞没,只见一轮明月挂于高楼之上。王昌龄醉情于山水之间的闲适之情和山林中的景色交融在一起,主体(诗人之情)与客体(山林之景)交融。
王昌龄在“景入理势”中论述的是在诗歌创作中如何以“景”入“理”。王昌龄认为“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诗歌中所描绘之事需要“景”与“意”,即诗人之情交融,不宜轻易采取景语和理语“无相管摄”、没有任何联系的写法。他以自己的诗歌 (佚诗)作为范例——“桑叶下墟落,鹍鸡鸣渚田”,先描写远离世俗的田园风光,然后写道:“物情每衰极,吾道方渊然”,揭示以平和的心境面对事物的兴衰之理。主体 (义理、道理)与客体(景色)交融。
唐代佛教兴盛,王昌龄因受到佛教的影响,他在诗歌作品中阐发了他对于佛道、禅理的深刻感悟,如《静法师东斋》这首诗同样体现了主客交融。
筑室在人境,遂得真隐情。春尽草木变,雨来池馆清。
琴书全雅道,视听已无生。闭户脱三界,白云自虚盈[7]。
首联描写在众人聚居的地方构筑房舍,却能得到“真隐情”。这两句诗和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其五》中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8]有异曲同工之妙。王昌龄虽然在诗歌开头就提到了真正的“隐情”,但这一理念的表达,诗人不是通过逻辑推理或者是运用明白无误的说教形式进行具体的表述,而是让“理”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他接着描写草木会因为春天逝去而发生变化,池馆的水会因为下雨而更加清澈的自然景象,通过自然景象的变化表达了一种人生感悟:人的一生和大自然的变化一样,不能强求或刻意改变,所以无论万事万物发生任何变化,都要保持一颗宁静、平和的心,这样即使“筑室在人境”,也能得到真正的隐居之情。因此,诗歌的最后一句提道“闭户不受三界所扰”,即使客观世界发生了千变万化也能全然不关心。
诗中的草木、雨、白云等自然景物与诗人意图揭示的“理”融为一体,构成了别具理味、清幽闲适的诗境之美,言有尽而意无穷。王昌龄的这首诗寓哲理于大自然景象之中,将诗趣和“理”有机地结合,借自然景象揭示了他所认可的“理”:如果真正拥有宁静、恬淡的心境,即使在闹市之中也可以得到“真隐情”。
总的来说,在这“两势”中王昌龄论述如何通过景句和理句的配合,将“景语”和诗人之“理”融为一体,这样才能更好地营造含蓄、自然、耐人寻味的诗境。“理入景势”和“景入理势”都强调“景”和“理”的配合,这两势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理句和景句的顺序。
1.2 “理入景体”“景入理体”
王昌龄所提倡的主客交融理论在“常用体十四”中“理入景体”和“景入理体”这“两体”中也有体现。
王昌龄提出理入景体九。丘迟诗:“渔潭雾未开,赤亭风已飏。”江文通诗:“一闻苦寒奏,再使艳歌伤。”颜延年诗:“凄矣自远风,伤哉千里目。”王昌龄提出景入理体十。鲍明远诗:“侵星赴早路,毕景逐前俦。”谢玄晖诗:“天际识孤舟,云中辨江树。”
在这 “两体”中王昌龄虽然没有进行具体的论述,但他列举了例诗,从这些诗句中可以了解“两体”的内涵。在“理入景体”中,王昌龄列举了丘迟的诗歌《旦发渔浦潭》、江淹的诗歌《望荆山》、颜延之的诗歌《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旦发渔浦潭》是描写诗人早晨从渔浦潭出发的所见所感之诗。渔浦潭的雾还未散开,诗人乘船在迷蒙的江面上启程远航,行至富春江边上的赤亭,已经风扬雾散,天气晴朗。渔浦潭在富春江上,从渔浦潭至赤亭的路程并不遥远,所以诗人意在通过“渔潭雾未开,赤亭风已飏”这两句诗描述行船不远,大雾便在江风中很快消散,表现出诗人对于天气迅速转晴的喜悦之情。这两句诗于景物的变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诗人的情感。《望荆山》这首诗是江淹赴荆州时所作。诗中“一闻苦寒奏,再使艳歌伤”描写了诗人在旅途之中,忽然听到有人奏起了描写行役途中艰难景况的 《苦寒行》乐曲,这曲悲歌还未结束,又听到有人唱起了悲伤的《艳歌行》。通过描写诗人在旅途中听到的感伤音乐,营造凄苦的氛围,抒发诗人在旅途之中的悲愁、感伤之情。《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这首诗是颜延之登岳阳楼所作。“凄矣自远风,伤哉千里目”,这两句诗通过描写远处之景抒发诗人因登楼触景而生发的悲慨。诗人登上岳阳楼后,远风吹来仿佛带来了凄凉之意,遥望千里,不由得悲伤万分。这两句诗通过描写远处之景抒发诗人因登楼触景而生发的悲慨。
在“景入理体”中,王昌龄则以鲍照的诗歌《上浔阳还都道中》、谢朓的《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为例。鲍照这首诗是在从浔阳到京都的路途中所作。“侵星”“毕景”意为起早歇晚,这两句诗描写了诗人一大清早起来赶早路,夜晚依然在追逐着走在前面的同路人之景。表达了诗人着急赶路,唯恐落后于前行者,还都心切之情。谢朓的《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也是在旅途中所作,这首诗是作者从建康出发到宣城任太守时所作。“天际识孤舟,云中辨江树”中的“孤舟”也写作“归舟”,水天之际能够辨认出返归之船,云雾之中能够分辨江岸的树,熟悉的景物渐行渐远。通过描写诗人乘舟远行时所看到的景物,表达出自己对建康的不舍、眷念之情,情真意切。
总之,“理入景体”“景入理体”这“两体”也强调诗中景与理的关系。五首诗都通过写景,将作者之情自然地融入其中,达到主客交融的境界。诗歌读来耐人寻味。读者可以从诗句中感受到作者的真情实感。
1.3 “生杀回薄势”
“生杀回薄势”,这一势就名字而言都颇为震慑人心。在“生杀回薄势”中,王昌龄提道:“第十四,生杀回薄势。生杀回薄势者,前说意悲凉,后以推命破之;前说世路矜骋荣宠,后以至空之理破之入道是也。”卢盛江认为,生杀回薄势是将欲抑之,先欲扬之。一扬一抑,一笔抹倒,造成意兴诗情之起伏回荡,于强烈反差和强烈反衬中造成不同寻常之艺术效果[9]。
李白的诗歌作品体现了这一势,如《行路难·其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10]。
李白通过“停杯投箸”“拔剑四顾”细节描写,以及“冰塞川”“雪满山”的景物描写体现“行路难”,抒发仕途坎坷,遭受挫折的苦闷情绪。所以李白感慨:“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这几句诗“说意悲凉”,但最后两句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破解了前面的悲凉之意,通过描写乘风破浪的场景表明李白相信有朝一日他会和南朝宋将宗悫一样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这两句诗体现了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基调,和前面的悲凉之意完全不同,鼓舞人心。因此体现了王昌龄所说的“前说意悲凉,后以推命破之”。这一势,同样也体现了王昌龄的主客交融理论。李白通过描写景物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愤懑不平,以及力图从苦闷中挣脱出来,追求理想的乐观精神。
李白的另一首诗《梦游天姥吟留别》则体现了王昌龄所说的“前说世路矜骋荣宠,后以至空之理破之入道是也”。李白首先通过“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描写了自己在梦中所见的神仙们辉煌气派的生活场景。但李白笔锋一转,“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人世间的欢乐也像梦中的仙境一样转瞬即逝,因为自古以来万事都如同东流的水一去不复返。这两句诗以自然界的规律来比喻人世间的变换,以此来破除前面所提到的“荣宠”。因此诗歌最后两句又接着写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诗歌通过对梦中场景的描写揭示出耐人深思之理,即万事万物总会有消逝之时,所以不能因为贪图一时享乐、追求荣华富贵而向权贵屈服。李白虽然在前面描写了令人向往的安逸生活,但他后面没有继续突出这种生活的可贵之处,而是以“至空之理”破除了前面的“矜骋荣宠”。王昌龄虽然在生杀回薄势中没有直接提到主客交融,但仍然围绕着如何运用作诗的技巧和方法达到主客交融这一核心展开。
王昌龄在“十七势”“常用体十四”中论述了诗歌的具体做法,从诗头、诗肚到诗尾的写作都给予后人指导。同时王昌龄也没有因为注重诗歌的样式而忽视了诗歌的意蕴,强调诗意的自然呈现、主客交融之体势的重要性。
2 主客交融的诗境
2.1 了然境象,故得形似
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一。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
“物境”主要体现的是王昌龄对创作山水诗的理解。王昌龄认为山水诗中应该物象鲜明,诗人的思想情感和山水之景自然地交融在一起。因此,“物境”指以山水等“物”为表现对象的诗歌中,主体之情志与“物”相交融形成的诗境。
盛唐诗人王维的山水诗名篇《山居秋暝》中体现了王昌龄提出的“物镜”。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11]。
这首诗是王维隐居终南山时所作,他在诗歌中生动地描写了终南山的景致。首联的“空”为整首诗歌营造了空旷幽远的氛围。空旷的终南山刚下过一场雨,傍晚时分的天气显现出秋天的凉爽。正如王维的另一首诗《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烘托了幽静之美。颔联对山中的自然景色进行了细致的描绘。明月高挂于青松之间,清泉流淌于山石之上。雨后美景如同画中描摹的一般清新自然,体现山中风景的清幽之美。颈联接着描写洗衣服的姑娘归来的场景。竹林里一阵喧闹,传来一阵阵歌声笑语,是洗衣服的姑娘结伴归来;水面上莲叶摇动,顺流而下的渔舟打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颈联将山中淳朴美好的生活之景生动地刻画出来,塑造了天真无邪的浣女形象,并且以动衬静,更加凸显山中的幽静。
王维所描写的清新、幽静的自然美景,达到与终南山景物“形似”的艺术效果。读者仿佛能够亲眼看到终南山中的景象,山中清泉、浣女的一颦一笑、渔舟的徜徉等仿佛就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诗歌的诗情与画意互相渗透,融为一体,“诗中有画”。诗人在山中幽静、远离世俗的美好景色中寄寓了他对终南山的喜爱,希望在终南山中过静谧、没有外界打扰的生活。尾联运用了《楚辞·招隐士》的典故,但反其意而用之,即尽管春日的美景已经消散,但秋景依然美丽,隐士可以留在山中。王维以“王孙”暗指自己,更进一步表达了诗人决意远离官场,隐居山中的坚定意志。正如《渭川田家》中的“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表达了王维渴望羡慕闲适的田园生活,归隐田园的愿望。整首诗通过描写清新如画的山中美景,表达了诗人寄情山水,对静谧的山中生活的向往,同时体现了诗人洁身自好,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意志。清泉、青松、翠竹、莲等都是诗人高洁情操的写照。诗人的主体情感和山中的美景在诗中自然地融为一体,形成主客交融的诗境。
2.2 目击其物,深穿其境
王昌龄在“论文意”中提出:“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如登高山之顶,下临万象,如在掌中。以此见象,心中了见,当此即用。如无有不似,仍以律调定之,然后书之于纸,会其题目,山林、日月、风景为真,以歌咏之。犹如水中见日月,文章是景,物色是本,照之须了见其象也。”“目击其物”类似于“物境”的“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王昌龄强调创作诗歌时,需要凝心在脑海中设想景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如登高山之顶,下临万象,如在掌中”则如同“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即用自己的心去观照景物,置身于客观之境中,心对客观之境做充分的把握和体会,强调对于“物”的了解、构思的重要性。《文心雕龙》也提到:“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12]作者一想到登山,脑中便充满着山的秀色;一想到观海,心里便洋溢着海的奇景。作者的构思都可以随着风云而任意驰骋。刘勰同样论述了创作过程中作者如何与外物融合。“以此见象,心中了见”,指达到“形似”的效果。通过这一系列构思之后,将心中之境呈现于诗中,即“书之于纸,会其题目,山林、日月、风景为真,以歌咏之”。“文章是景,物色是本”,强调外物是形成这一诗境的本源。王昌龄的这段“论文意”可以说是对于“物境”理论的另一种表达和补充。他认为,诗人如果有意进行诗歌创作,在创作过程中主体需要凝心与“物”融合,即诗人的主观情感须与客体(外物)融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创作出有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
“主客交融”这一核心理论在《诗格》中的“论文意”其他部分也有体现,和“两势”“两体”“诗有三境”相呼应,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王昌龄在“论文意”中提出:“夫诗,一句即须见其地居处。如‘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若空言物色,则虽好而无味,必须安立其身。”王昌龄认为诗歌须有景物,即“见其地居处”,但又不能空谈景物,诗中必须有作者主观情感的寄托,“安立其身”。正如他所列举的陶渊明诗歌《读山海经·其一》中“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诗歌开头就描写了诗人情感赖以寄托的景物:孟夏时节草木茂盛,枝叶茂密的树围绕着房屋。这两句诗描绘了静谧而万物生机勃发的乡村图景,然后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隐居之后在乡村生活中自得其乐,众鸟快乐地好像有所依托,我也喜爱我的茅庐。陶渊明的这首诗生动地体现了王昌龄所提倡的主客交融的诗境。王昌龄认为诗人的真情实感必须与景物紧密结合,与之相融,这样才能创作出具有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
王昌龄在 “论文意”中不仅列举优秀诗歌的典范,也指出了没有形成“主客交融”诗境的反面例诗:“诗有‘明月下山头,天河横戍楼。白云千万里,沧江朝夕流。浦沙望如雪,松风听似秋。不觉烟霞曙,花鸟乱芳洲’。并是物色,无安身处,不知何事如此也。”这首诗仅是罗列、堆积了一系列的景物:明月、山头、天河、戍楼、白云等,即“一向言景”,没有将诗人的主观情感融入其中,诗人之情“无安身处”,缺乏主客交融的诗境。因此诗歌显得平淡无奇,苍白无力,缺少韵味,让读者读了之后“不知何事如此也”,不理解诗歌意在说明或表达的主旨。王昌龄通过对比,再次强调了主客交融的重要意义。
3 结束语
王昌龄在《诗格》中通过对“十七势”之“理入景势”“景入理势”“生杀回薄势”等“三势”,“常用体十四”之“理入景体”“景入理体”等“两体”,以及“三境”之“物境”“论文意”的论述,反复强调了主体(创作者主观情志、感悟)与客体(景物、道理)的交融。虽然他在论述中很少直接提及 “情”,但他所强调的 “理”“意”等都包含了诗人主观情感的表达,由此可见王昌龄对主客交融的重视。总的来说,王昌龄开创性地提出了“景语”“理语”等概念,强调诗歌须“景与理相惬”“景与意相兼”“所见景物与意惬者当相兼道”等,并列举了具体的诗歌作为例子来论述诗歌的写作如何才能使情景、理景更好地交融,形成主客交融的诗境。这在诗歌创作领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后人创作诗歌提供一定的参考范式,如:皎然创作了《诗式》中的“明势”;齐己创作了《风骚旨格》中的“十势”等。王昌龄的诗论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开创意义。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的主客交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后诗论、词论的走向。在王昌龄之后,通过中唐皎然“缘境”“取境”,刘禹锡“境生于象外”,司空图“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思与境偕”,宋代严羽“妙悟”说、“兴趣”说,清代王夫之“情景相生”和王国维“意境”“境界”说等对“境”的论述与发展,逐渐形成了后世的“意境”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