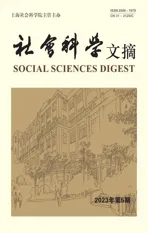理论思维:学术研究的“普照光”
2023-09-01孙正聿
文/孙正聿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是用理论把握现实、引领实践、推进文明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力量,是照亮学术研究的“普照光”。学术研究的理论思维,集中地体现为捕捉、发现和提出问题的理论洞察力,总结、提炼和升华问题的理论概括力,激活、重组和创新问题的理论想象力,分析、阐释和论证问题的理论思辨力,拓展、深化和解决问题的理论思想力。自觉地提升理论思维的洞察力、概括力、想象力、思辨力和思想力,才能坚持“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不断地在学术研究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赋予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实现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学术选题与理论思维的洞察力
学术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提出问题、确定选题。捕捉、发现和提出问题的理论思维的洞察力,直接决定学术选题的难度和深度、意义与价值。
一般而言,学术研究的“问题”,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现实问题所蕴含的理论问题;二是学术史所遗留的理论问题;三是学界正在讨论的理论问题;四是学者独立提出的理论问题。在学术研究中,这四类问题总是相互纠缠、相辅相成的。理论思维的洞察力,不仅在于从各类问题中发现和提出问题,而且在于从各类问题的复杂联系中发现和提出问题,特别是独具慧眼地从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和学术命题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中发现和提出问题。
学术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总是同学术史提供的理论成果及其遗留的理论问题密不可分。任何理论都不仅具有其特定的思想内涵,而且在其特定的思想内涵中总是蕴含着特定的时代内涵和特定的文明内涵。这意味着:任何理论都是历史性的思想;历史性的思想总是展现在思想性的历史之中;离开思想性的历史就无力考察历史性的思想。在学术史中寻找理论资源和发现理论困难,“接着讲”学术史所遗留的问题,就必须以理论思维的洞察力揭示既有理论的思想内涵中所蕴含的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从而提出和确认具有学术史意义的学术选题。
源于现实的理论问题与源于学术史的理论问题,总是聚焦于学者所关切的学术界正在讨论的问题。“跟着讲”学术界所讨论的问题,就不仅是“对着讲”不同的学术观点,而且要揭示不同学术观点所隐含的背景知识、理论资源、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特别是要深究不同学术观点所隐含的基本理念、解释原则、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在“思想的前提批判”的意义上确认学术争鸣的学术选题。离开捕捉、发现和提出问题的理论洞察力,就难以发现真正的理论困难,也就难以提出推进学术争鸣的理论问题,“跟着讲”的学术讨论就会流于“对着讲”的“自说自话”,“吸引眼球”的学术争论就会变成热闹一时的“过眼烟云”。
无论是从现实问题中提出理论问题,还是从学术史和学术争鸣中提出理论问题,其实质内容都不只是“发现”问题,而是“揭示”问题本身特定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并“赋予”问题本身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从而以新的解释原则“构成”富有新意的学术问题。因此,无论是从现实问题还是从学术史和学术争论中提出具有“真实意义”的理论问题,都需要独具慧眼地提出具有创新性的理论问题,并形成具有创新性的学术选题。提出和确定具有创新性的学术选题,有针对性的“靶子”与有创新性的“灵魂”,是相互规定、相辅相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学术研究的“破”与“立”,既是“不破不立”的,又是“不立不破”的;学术选题的“取”与“舍”,既是“不舍不取”的,又是“不取不舍”的。没有独到的“立意”和“追求”,就没有富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学术选题。理论思维的洞察力就在于,独具慧眼地从具有“隐匿性”和“强制性”的“思想的前提”中找到“破”的难点,又独具慧眼地从具有“可批判性”和“可转换性”的“思想的前提”中找到“立”的根基,从而在“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中提出具有“创新性”和“创造性”的学术选题。“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对学术研究的理论思维“洞察力”生动形象的表达,也是对学术研究的学术选题“生命力”一语中的的表达。
学术命题与理论思维的概括力
理论思维的概括力,最为重要的就是把学术思想、学术观点提炼为一系列重要的学术命题,高度概括地提炼和升华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为构建具有学理性的学术体系提供逻辑化的命题系统。
一般而言,作为学术研究成果的学术命题,可以从总体上分为四大类:一是作为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学术命题,此类命题是总体性的学术思想的理论结晶;二是作为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的学术命题,此类命题是具体性的学术观点的理论升华;三是作为逻辑环节和理论论证的学术命题,此类命题是概念发展的学术体系的理论支撑;四是作为标志概念和术语革命的学术命题,此类命题是创新性、开放性学术研究的新“阶梯”和新“支撑点”。总结、提炼和升华这四大类学术命题,集中地体现了学术研究的理论思维的“概括力”。
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术研究,总是不可回避地面对一个根基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就是对该学科的总体性理解,也就是关于该学科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问题。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术研究,总是在历史性地反思本学科的理论性质、研究对象及其学科使命的过程中,历史性地形成关于本学科的总体性学术思想理论结晶的学术命题,即作为该学科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学术命题。作为各学科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学术命题,并不是该学科的“一个重要命题”,而是照亮和引领各学科学术研究的“普照光”和“活的灵魂”。
作为特定研究论域或特定学术选题的学术研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某种总体性学术思想,即作为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学术命题的规范和引领下,形成具体性的学术观点即作为该论域或该选题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的学术命题。理论思维的概括力,生动地体现为提炼关于特定论域或特定选题的具体性的学术观点的学术命题。而把学术思想、学术观点概括为一系列学术命题,就要合乎逻辑地、层层深入地提炼出相互规定的子命题。
学术创新与理论思维的想象力
学术研究是学者以理论思维总结、积淀和升华人类文明的研究过程。这个研究过程是不断地提出和探索新问题,进而不断地形成新的学术成果的学术创新和学术创造的过程。学术创新和学术创造,不仅必须奠基于坚实的文献积累、思想积累和生活积累上,而且必须充分发挥理论思维的想象力。
一般而言,学者的学术研究,离不开两个东西:一是特殊的生存境遇及其独特的生命体验,二是特定的学术资源及其独特的理论想象。所有的学者无一例外地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时代、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特定的文明形态之中,生活于特定的国家、民族、地域、阶级、阶层、家庭之中,这构成了各个学者特殊的生存境遇。这种特殊的生存境遇,不只是为不同的学者提出某些共同问题,而且会在不同学者的独特生命体验中激发出独特的理论想象。这种独特的理论想象,又是同研究者占有的特定理论资源及由此引发的独特理论问题密不可分的。在特定的时代条件和特殊的生存境遇中,每个时代的学者都不仅面对共同的理论资源,而且会在个人已有的思想情境和生活情景中选择性地利用和活化自己占有的理论资源,从而在自己对理论资源的独到理解中激发出独特的理论想象。
理论思维的想象力,集中地体现为学术研究中的“激活背景知识的能力”。在艰苦的学术研究中,让知识“退入背景”,让知识“进入问题”,让知识“创造重组”,让知识“浴火重生”,才能以理论思维的想象力赋予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激活背景知识,首先要让知识“退入背景”,在头脑中构建知识的“分类框架”“概念框架”“检索框架”。在学术研究中,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井然有序的知识“分类框架”和“概念框架”,并在这种“分类框架”和“概念框架”中准确、迅速地调动“退入背景”的知识。让知识退入背景,而不是将知识作为外在的“文本”,这是发挥理论思维想象力的前提。
让知识“退入背景”,才能让知识“进入问题”,开展“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学术研究的“问题”,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矛盾,可以称之为理论研究的“外部问题”;一是“理论”与“理论”之间的矛盾,可以称之为理论研究的“内部问题”。理论研究的“内部问题”总是源于理论研究的“外部问题”,理论研究的“外部问题”必然引发理论研究的“内部问题”。理论思维的想象力,就在于把“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外部问题”升华为“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内部问题”,并通过创造性地解决“理论”问题而创造性地回应和回答“现实”问题。
在学术研究中,理论思维的创造力具体地表现为:一是“观察渗透理论”,以“思想”把握“表象”,把“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升华为具有概念规定的“感性具体”;二是发挥理论思维的“抽象力”,以“思想”蒸发“表象”,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以各种“片面的规定性”去把握“表象”;三是发挥理论思维的“想象力”,以“思想”重组“表象”,以“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理性具体”为思想内涵“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在以理论思维把握世界的概念运动中,“思想”表现为双重的否定和双重的超越:一方面,思想在理论思维的引领下,不断地超越概念的片面规定,使概念获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丰富的规定性,不断地形成新的“理性具体”,这就是思想的自我构建过程;另一方面,思想又在理论思维的引领下,不断地反思、批判、超越已有的“理性具体”,在更深刻的逻辑层次上重新建构“理性具体”,这就是思想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深化的过程。“思想”的双重否定和双重超越,深切地体现了人类思想运动的建构性与反思性、规定性与批判性、渐进性与飞跃性的辩证统一。理论思维的想象力,就在于不仅“合乎逻辑”地思想,而且批判地反思已有的“思想”,不断地实现“思想”在逻辑层次上的“跃迁”和“升华”,赋予“思想”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为学术研究提出具有创造性的理论问题和理论成果,从而为人类认识的拓展和深化不断地提供新的“阶梯”和“支撑点”。
学术体系与理论思维的思辨力
学术体系是由一系列的学术命题及其相互规定所构成的逻辑化的命题系统。真正的“逻辑化”的命题系统,就是实现黑格尔所指认的“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形成马克思的《资本论》所示范的“完整的艺术品”。为此,要不断提升理论思维的思辨力。
思辨力,就是“辨析思想”或“思想辨析”的能力。学术研究中的理论思维的思辨力,集中地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理论思维揭示概念、范畴、命题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的思辨力;二是以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构建概念相互规定的概念框架和思想平台的思辨力;三是以理论思维对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命题进行逻辑分析、语言分析、心理分析、社会分析的思辨力;四是以理论思维构建由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的概念深化发展的命题系统的思辨力。构建学术体系的理论思维的思辨力,就是既把“全体的自由性”诉诸“环节的必然性”,又以“环节的必然性”展示“全体的自由性”,从而用“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理性具体”构成作为“完整的艺术品”的学术体系。
作为总体性的学术思想的理论结晶,构建学术体系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是统摄和照亮整个体系的“普照光”,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全体的自由性”。这个作为“普照光”的“全体的自由性”,只有诉诸“环节的必然性”,才能成为由一系列学术命题及其相互规定所构成的逻辑化的命题系统,才能达到“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理性具体”。理论思维的“思辨力”,最主要地就体现在把“全体的自由性”诉诸“环节的必然性”。
学术经典与理论思维的思想力
学术经典是具有学术史、思想史、文明史意义的学术著作。作为学术经典的学术著作,不仅具有引领学科发展的学术史意义,而且具有跨越学科界限的思想史意义,以及超越学界范畴的文明史意义。照亮人类文明的“思想力”,是学术经典的“活的灵魂”。
任何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都具有特定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之所以成为影响深远、经久不衰、彪炳史册的“学术经典”,首先就在于其“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赋予时代性的重大理论问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不仅构建了“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而且塑造和引领了新的“时代精神”。
学术经典的“思想力”,集中地体现在它所实现的“术语的革命”。“术语的革命”,不仅依赖于理论思维的“方法的革命”,而且彰显了理论思维的“方法的革命”。“方法的革命”,不仅是学术经典“思想力”的“普照光”,而且是学术经典“思想力”的“活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