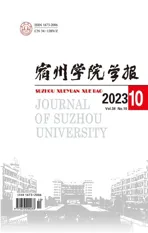东北“后工业时代”纪录片与“铁西三剑客”小说比较
2023-05-13韩波
韩 波
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合肥,230071
刚刚收官的网剧《漫长的季节》,豆瓣开分高达9.5分,创下了国产剧新高。《漫长的季节》改编自班宇的同名小说,但它并不是一部典型的悬疑剧,而是通过一起凶杀碎尸案,串联起自20年前下岗潮开始,北方小城“桦林”几个家庭发生的一系列意外,展现了家庭悲剧背后东北这片土地的肃杀与落寞。
而在这之前,大众追捧度不高,但业界评价甚高的《平原上的摩西》,同样是取材于东北的犯罪悬疑剧,同样是改编自双雪涛的同名小说,同样展示了东北老工业时代的尖利与冷峻。以2015年第2期《收获》杂志发表双雪涛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为标志,同为80后的“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在文坛崭露头角,构成“新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东北题材的影视《钢的琴》《白日焰火》《东北虎》等等随之而起,一同助推了“东北文艺复兴”潮。
其实对于东北的影视书写,远远早于“铁西三剑客”的文学书写,其标志性的人物和事件,是王兵2002年长达9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铁西区因位于沈阳长大铁路之西而得名,是新中国重型工业的摇篮,曾被称作“东方鲁尔”。铁西区跨越了日伪统治、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三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承载了沈阳大部分的工业记忆,见证了百年中国工业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铁西区迎来了数十万产业工人的“下岗潮”。在超半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铁西区是共和国长子,也是时代的弃子;曾被万众追逐,也被潮流放逐。它早年有多辉煌,日后就有多衰败,而这一切,人们不忍言说,不便言说,也不愿言说。
直到2002年,王兵的超长纪录片《铁西区》横空而出。纪录片《铁西区》无论是时长还是题材,在当时都是中国纪录片史上的史无前例,某种程度上说,它触发了“铁西三剑客”的“铁西意象”,是东北后工业时代文艺复兴潮的前奏。这一现象很值得思考。纪录片和小说,一个是纪实、一个是虚构,一个是影像、一个是文字,一个是画面、一个是语言;而同是铁西题材,同是后工业时代,同是书写小人物被大时代所裹挟的命运,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为什么会呈现出了惊人的相同性?这同样值得思考。
1 一样的场景、一样的故事
当王兵一个人单枪匹马,带着一部手持摄像机进入铁西区这一庞大的、被人所遗忘的社会群落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片破败的景象。15万人下岗,5万人失业,无数的家庭、无数人的生活被撕裂,被碾压。纪录片《铁西区》由《工厂》《艳粉街》《铁路》三部分所组成,这里有上百个面积很大的工厂,导演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在这个区域内建立一种关系。沈阳这座城市的整个工业区,是由火车铁路构建起来的,它有4条铁路线,勾连起所有的厂区。而铁路之外,是工厂,沈阳有那么多的工厂,但它其实是有主体的。沈阳冶炼厂是这座城市历史上最早的工厂,同时它又是在视觉上和占地面积上最醒目的,最有特征的一个工厂,加上之后选择的电缆厂和轧钢厂,构成工厂主体。中国的工业基础,是靠几个工业系统来建立的,比如说铁西区有生产变压器、高压开关、低压开关、电缆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在中国,铁西区是唯一拥有系统性生产能力的地方。《工厂》单元主要拍摄被时代遗弃后的工厂场景,多为车间和休息室景象的交叉剪辑。
导演在火车上拍摄的长镜头,是《铁西区》众多场面之间进行连接的重要手段,它强化了铁西区的整体感。出现在这一部分主要拍摄对象“老杜”,以前家境不错,文革时被抄家,后来在车站边上拣煤渣维持生活,同时做铁路派出所的内线。由于身份暧昧,所以能居住在车站的一间仓库里。但是后来,车站不想让他住了,就把他抓到了派出所。画面结束在晚上,一列火车在夜色里行驶,似乎暗示了老杜不可预知的生活。导演王兵一直在跟拍,一直在跟拍,一直跟拍到厂子倒闭,工人们拿到遣散工资,然后是厂子拆除,然后是剩下一片工业废墟,然后是所有的人包括老杜,都失去了生活。
这样的场景,几乎毫无二致地出现在“铁西三剑客”的笔下,厂房、车间、机器、澡堂和失落的男人,都笼罩在一片雾霾之中。由工厂、工人村、下岗、父亲等关键词支撑的东北往事,充斥了失败和失意的情绪,揭示出“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普遍的工人阶级乡愁”[1]。虽然,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是调查一桩“出租车司机劫杀案”;郑执的《生吞》是围绕“鬼楼奸杀抛尸案”展开叙述;班宇的《冬泳》叙述是和父亲离奇的死亡相关联,但他们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却都是悬念和悬疑之外的现实生活,是时代大潮中,与厂子一同衰落的人物命运。《平原上的摩西》中,突如其来的车祸,源于下岗潮所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偶然性的背后,关联着时代性。以一个高度戏剧化的叙事结构,聚焦小人物的苦难,“以魔幻的笔触切入现代人普遍经受的精神分裂,并通过每个人维系生命平衡的独特方式揭示普遍存在的灵魂撕裂与身份认同危机”[2],这是“铁西三剑客”的书写逻辑。同样是书写苦难,郑执的《仙症》显示出了更强的沉重性。《仙症》中的王战团、大姑和“我”,都是被生活卡住的小人物,都处于同一时代背景中,人物的无力,也是那段历史的无力。
“铁西三剑客”都是下岗工人的后代,以班宇为例,他出生在工人村,全家人都在沈阳变压器厂上班。爷爷是天津人,抗美援朝去了黑龙江,后来成了变压器厂的干部。爸爸长大后也进了厂,还有他奶奶、他妈妈、他姥姥和他姥爷、他大姑和他二姑,都在变压器厂上班。变压器厂、热力厂、冶炼厂……工人村的房子连成一片,大人孩子都相互认识。等到班宇长大了,厂子不存在了,但儿时的四排楼、艳粉街、工人村、劳动公园、卫工明渠,父亲的线圈车间,休息室里的铁柜子、大茶几、破沙发,还有破旧的老式浴池,甚至高温蒸腾出的弥漫水汽,都嵌在了他的生命深处。铁西区“子一代”用记忆的碎片,编织起东北往事,呈现给我们一张张如纪录片一样真实而鲜活的,普通人的面容。而这样的人物和这样的场景,早在王兵的纪录片画面里,就曾反复出现,是他整部纪录片最坚实的支撑。
“铁西三剑客”写出了一代东北产业工人的集体记忆,“在书写东北工人及工人子弟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生命方面,难能可贵地记录了一段不该被遗忘和忽略的存在,填补了当代文学的一块空白”[3],让东北之外的读者,感受到时代大潮中无数人瞬间裂开的时空。或如鲁迅先生对于东北作家萧军小说《八月的乡村》的评价:“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4]
2 一样的命运、一样的抗争
命运是一个很庞大的词语,也是一个很虚幻的词语,它在王兵的纪录片里,以一个时代下的特定整体来呈现,而班宇的小说中,则更多体现为一种个体形式。但无论怎样,有一点是共同的:“命运”以无形之手,将这些个体捧起、摔下,最后让个体消失在时代的洪流之中,“表达的其实是群体命运中个人的承受,反映的也不仅仅是个体的命运,更是时代洪流之下一群人的遭际和境遇,是群体性的命运和境况”[5]。
虽然在“时代”的庞大话语中,个体的力量十分有限,但渺小的个体仍在抗争。这同样体现在纪录片和小说中。在纪录片《铁西区》里,王兵用一些细节,凸显了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印记:当工人们知道厂子即将倒闭时,唱的是《笨小孩》:“向着天空,胸口拍一拍啊,勇敢站起来。”而下班的铃声响起,工人们走出厂子时,广播喇叭里放出的是《东方红》。这不单单是20世纪90年代与20世纪60年代的音乐冲撞,还是两种思潮在同一个时空里的交织、更迭和冲突,显示出个体对命运的不甘和抗争。在《艳粉街》里,有这样一组镜头:镜子里,映照着好友与女朋友腻歪在一起,吃着巧克力;躺在床上的刘波跟着小白在唱老情歌,而外面,时代的潮流滚滚。这给人一种强烈的命运感,是真实的时代纪录,是通过音乐找到的时代切口。个人的命运,与大时代的命运,交织地出现在王兵的镜头里,个人的命运看似随波逐流,却有一种罕见的坚韧。
同样,班宇的《漫长的季节》用一个罪案故事,把历史的撕裂与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让我们体会到了时代中的命运感,但这现实并不是一味的沉重,人物也不是一味的沉沦。班宇笔下的人物在遭遇生存危机时,往往本能地进行反抗和挣扎,虽然无济于事,但一种“悲剧美感”由此而生。班宇也没有对“下岗潮”这一特的殊历史事件做过多的铺垫和叙述,而是仅仅将它作为一种背景,关注点和关键点仍在历史时刻中的人物命运。90 年代的下岗潮对于产业工人群体而言,无疑是一次“历史的断裂”,又仿佛是一个无形的黑洞。但就在这样沉重的、无常的、难以预测的现实中,希望和幻想依然存在,如《逍遥游》里的许玲玲,戴着的那条乳白色的围脖;如《漫长的季节》里两个原本没有爱的人,生出爱的羁绊,这让沉重的现实、不堪的现实,因此而有了诗的意蕴。
20年前,王兵用纪录片的形式,直接而生猛地插入铁西,以真实的镜头展示人物的命运;20年后,班宇以“子一代”的身份回望父辈的历史,以文学的手法,虚构出一段完整的“铁西叙事”,把铁西老城“创建成一个压抑、逼仄、腐烂着的废墟意象,以一代人的独特视角追问人类精神的归处”[6]。出现在王兵镜头里的人,几乎都是“铁西三剑客”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因此无论是纪实还是虚构,都是人们对于历史的铭记,对于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捍卫,对于普通人卑微生命关注。
3 作为意象和符码的“艳粉街”
“那里发生的故事很多/我没有漂亮的儿童车/我的游戏是跳方格/大人们在忙碌地活着/我最爱五分钱的糖果。”这是著名沈阳歌手艾敬民谣风的歌曲《艳粉街里的故事》,人们对艳粉街的了解,最初也是从她开始。
艳粉街早年名叫“艳粉屯”,其历史可追溯到明朝末年,努尔哈赤分封八旗的时候。清朝初年,艳粉屯成为郑亲王的属地,屯子里的人们,专门种植一种用于制作胭脂的植物,以供王府内眷化妆使用,因此被称为胭粉屯,后来慢慢演化成为艳粉屯。
在铁西区题材的创作中,无论是纪录片还是小说,艳粉街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王兵第一次进入铁西区,最先来到的就是艳粉街,最先停留的就是街区最中心的小卖部。最终,纪录片中呈现的所有人物和事件,也都是围绕着这个小卖部展开,艳粉街作为一个意象或符码,一直贯穿纪录片拍摄的始终。在纪录片的《艳粉街》单元,镜头由铁西区政府彩券发行现场开始,主持人站在艳粉街中央,拿着麦克风推大声吆喝:“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抽烟,伤肺,喝酒,伤胃。到歌厅,高消费……买点彩券,经济又实惠。”孩子们在脏乱的街道上谈恋爱,开玩笑,神侃自己的理想和未来,周围是混乱和嘈杂的环境。后来大街上就贴出了拆迁布告,人们议论纷纷,愤愤不平,但无论怎样,最后都得搬走。有人在废墟上挖出老人的骨灰盒,想一并带走,集体生活烟消云散,和父辈不同的是,迷茫又压抑的青年人,更渴望从破旧的艳粉街搬出,而这一切,都被记录进王兵的镜头。
艳粉街里的小白,是铁西这片黑乎乎的棚户区最爱穿白衣服的男孩,也是最爱干净的一个,鞋子哪怕是沾上一点点灰,也要拿刷子刷干净。在整个艳粉街尘土飞扬时,他仍然穿着白裤子、白T恤,戴着白帽子在街上滑轮滑,与周围的焦虑格格不入。艳粉街的拆迁,是王兵在拍摄中的突发事件,但正是这样的偶然,突出了时代变迁中的不确定性。王兵向我们展示了他所观察到的的世界,让我们听到了牲畜的呜鸣声、风的咆哮声、孩子和大人的咳嗽声,以及走过泥泞的脚步声……这些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声音,组成了时代的喧响,让艳粉街的意象无比鲜明。
而在文学书写中,双雪涛中篇小说代表作《平原上的摩西》《光明堂》《飞行家》的英文小说集,就以《艳粉街》为名,因为“艳粉街龙蛇混杂,层层叠叠的棚户安置着千百社会底层生命。在居民嘈杂和喧嚣中,双雪涛感受到他们难言的隐痛,以及由此而生的隐喻”[7]。在班宇的作品中,也曾多次出现艳粉街这一地名。小说《光明堂》中的“光明堂”,是艳粉街突出的地标式建筑,而双雪涛的另一篇小说《火星》,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向艳粉街,用客观冷峻的叙述,呈现了人性在这里所经历的煎熬。艳粉街是铁西人集体生存的一个空间,他们在这里相识、相爱、甚至相杀,艳粉街在“铁西叙事”中,无疑成为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者胡箫白认为:“当一个文化实体在种种语境中不断被形塑,进而被‘固化’成为具有高度‘共享性’的‘意象’而承担特定意涵时,便说明这个文化实体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8]同样的背景,同样的场景:艳粉街的屋里没有床,只有炕,家家烧煤取暖,生炉子做饭,整条街上一大清早就弥满了烟火。这些文字的描述,与王兵的纪录片画面互为印证,构成了艳粉街的日常生活。也许《平原上的摩西》的开篇,更具有一种象征意味:1995年的平安夜,一场大雪掩藏的谜案,一次未赴之约,在艳粉街悄悄展开,而凌乱嘈杂的艳粉街,和活跃在艳粉街上的人们,也渐次展开他们艰窘的生活和内心。艳粉街对于年轻的作家来说,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它更是一种意象,一个符码,具有特殊的指向性,哪怕你是一个南方人,哪怕你身在千里之外,也能够通过艳粉街,准确触摸到铁西区生活的实质,切实感受到铁西人的物质和心灵生存困境,更能引起震撼和思考。
4 绵密堆积的细节
评论家李陀特别称道小说《逍遥游》的细节描写,认为“这些细节不但数量多,相当繁密,个个都有很高的质地和能量……而且在叙事的种种肌理当中,分工不同,各有各的功能。”[9]。大量的细节堆积,呈现出一种几近窒息的底层困境,在小说《逍遥游》中,细节从头至尾贯穿始终。而大量的细节,集体趋向小说的一大主题:贫困。小说开篇不久,就有这样一组细节:父亲骑着一辆“倒骑驴”,送身患重病的女儿许玲玲到医院去做透析,在医院附近碰到一个老同学。老同学从兜里掏出了50块钱,不好意思地说“多少是点儿心意”,这时候女儿忍不住大喊:“爸,你别要!”可是父亲不仅收下了,还“从裤兜里掏出掉漆的铁夹,按次序整理,将这张大票夹到合适的位置。”
这个段落里的第二个细节,是女儿情急之下冲口而出的一声“爸!”这是对父亲绝望的呼喊,夹杂着屈辱和自尊,还有哀求。看起来,许福明是个内心贫瘠的小人物,可是如果进入细节所提供的幽深处,他是一个复杂而立体的形象:一方面,这是一个被贫穷压垮的人;另一方面,他又无比坚韧。在呼啸而过的生活列车的碾压下,他总是能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支撑着家庭。正是依赖细节,依赖一组又一组细节,《逍遥游》撕开了生活的创伤,给读者带来不安和痛楚。小说的结尾,许玲玲“缩成一团,不断地向后移,靠在车的最里面,用破旧的棉被将自己盖住,望向对面的铁道,很期待能有一辆火车轰隆隆地驶过,但等了很久,却一直也没有,只有无尽的风声,像是谁在叹息。光隐没在轨道里,四周安静,夜海正慢慢向我走来。”李陀说,每读到《逍遥游》的结尾,他“总是感动得难以自控”[9]。
同样,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也是以繁复绵密,令人不忍直视的细节,揭示生活的真实和铁西的衰落。《铁西区》300多小时的素材,来自于王兵的手持摄像,让整部片子充满了细枝末节,超乎单一的信息堆砌,几乎成为纪录片《铁西区》的风格。在《艳粉街》单元中,有一组镜头令人印象深刻:被一片白雪覆盖的艳粉街社区空旷无人,镜头随着前行的脚步声向前推进,伴随着拍摄者不时带有寒冷质感的呼吸声。拆迁已经接近尾声,街道的轮廓还在,但很多房屋都已解体,雪下掩埋着瓦砾,远处有两个男人穿过。王兵习惯于处理现实的、历史的、政治的宏大主题,但他的宏大主题,无一不是依靠细节来呈现,来完成。在王兵的《铁西区》里,你可以看到刚刚洗完澡,光着屁股下棋的炼钢工人;上过春晚,唱过《掀起你的盖头来》的克里木,调侃来买彩票的姑娘;住在铁路旁,靠捡煤炭生存的老杜父子俩;工人们一趟趟从火车上卸货,像蚁群一般将麻袋摞高;日复一日地打开自己的饭盒,准备吃饭;一件红毛衣,和一份下岗名单……《铁西区》记录了一个庞大的社会机器,缓缓转动直到停摆的过程,让我们感受到铁西区上空笼罩的“灰色雾霾一样的贫困现实”。如果用班宇自己话说:“好像一个受伤的巨兽一点点倒下去,因其缓慢倒掉而没有什么声音。”[10]
5 结 语
王兵的纪录片和“铁西三剑客”笔下的“铁西叙事”,虽然采用的是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却在素材的选取、日常化场景的设置、细节和符号的展示上,显示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对于“铁西”来说,无论是何种书写、何种呈现、何种艺术形式,生活的逻辑和真实的力量都超越一切,它们所承载的时代中的命运感以及大量的生活细节,甚至可以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提供考据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