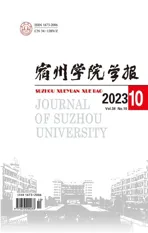嵇康对《红楼梦》的影响探微
2023-05-13刘香环
王 猛,刘香环
1.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宿州,234000;2.北部湾大学科技处,广西饮州,535000
嵇康(公元224—263),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州)人,魏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音乐家。他是竹林七贤之首,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其言行风范、精神特质和人格魅力影响深远。《红楼梦》作为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是曹雪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创新结出的硕果,它和魏晋文化、魏晋风度的关系,一直以来研究甚夥,尤以阮籍、陶渊明等人的影响研究最为突出,而关于嵇康对《红楼梦》的影响,只在相关研究中偶尔被提及,有明显被忽略的倾向,故此本文拟抛砖引玉,作进一步的探讨。
1 《红楼梦》文本多次直接、间接提及嵇康
小说第二回贾雨村向冷子兴发表“气秉说”,论及 “秉正邪两赋”者时,提到了包括魏晋名士在内的五十多个人物,其中便有嵇康:“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云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这是第一次提到嵇康,排在陶潜和阮籍之后。但可以看出,除了陶潜之外,基本是按时间顺序排列,嵇康比阮籍小了十几岁,故排在其后。有人误以为排名顺序说明曹雪芹重视阮籍的程度超过嵇康,其实不然。因为二人虽齐名,但嵇康是竹林七贤之首,且二人合称“嵇、阮”,而非相反,似乎影响力更靠前些,如《世说新语·言语》:“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1]后人两者并提时往往也是先嵇后阮,如明张元凯《晏坐二首》诗:“清啸嵇中散,沉酣阮步兵。”很少有例外。
《红楼梦》第五回中第二次涉及嵇康。写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在警幻仙子的指引下来到薄命司,翻阅“金陵十二钗正册”,看到判词之八云:“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这首诗评说王熙凤,其中“凡鸟”一典就与嵇康有关,《世说新语·简傲》说:“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字,凡鸟也。”“凤”字拆开就是“凡鸟”二字,表面是吕安讽刺嵇康弟弟嵇喜,说他是凡鸟,言下之意却主要是赞美嵇康的卓然不群,暗示他才是“凤(神鸟)”,值得“千里命驾”。而曹雪芹在小说中运用此典,意思是说王熙凤虽然称“凤”,有治家才能,但仍然不过是“凡鸟”而已。那么《红楼梦》中谁才是真正的“凤(神鸟)”呢?当然是小说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了!这里很曲折地把嵇康和宝、黛并列类比,嵇康在曹氏心中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六十六回则第三次涉及嵇康。回中写尤三姐因柳湘莲怀疑自己,愤而自杀,作者诗赞曰:“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玉山倾倒”就是关于嵇康的又一个典故,《世说新语·容止》:“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这是山涛对嵇康的评价,因为“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追求“任自然”,醉倒的样子自然与众不同,就像高大的玉山倒下去。《世说新语》很擅长写人,抓住一个醉态的细节,就描写出嵇康的气度神韵。小说用此典感慨尤三姐的自杀,可见作者对这个人物是比较赞赏的。
第七十八回晴雯死后,贾宝玉写了一篇《芙蓉女儿诔》祭奠,其中写道“雨荔秋垣,隔院希闻怨笛。”“怨笛”一词,红学家周汝昌、蔡义江都指出这里使用了有关嵇康的典故。据《晋书·向秀传》:向秀与嵇康、吕安友善交好,后嵇、吕被杀,一次向秀经过这两人的旧居,恰好听见邻人吹笛,凄切哀婉,向秀更加伤感,便写了一篇《思旧赋》,以感念故友。北周庾信诗《伤王司徒褒》曰:“唯有山阳笛,悽余《思旧篇》。”嵇康的旧居在山阳,典故又称“山阳闻笛”。贾宝玉以此典来表达对晴雯的怀念,把她比作了嵇康。晴雯虽身为下贱,但很有个性,敢于顶撞主子生气撕扇,抄捡大观园时能掀箱子抗议,都体现了可贵的反抗精神,所以宝玉在诔中直言她“高标见嫉”“直烈遭危”,显然和嵇康极为类似,而晴雯又是黛玉的影子,作者的用意可想而知。
第八十六回是第五次涉及嵇康。回中写宝玉见到黛玉看琴谱,惊讶自己从未听见黛玉会弹琴,并提起一件事说:“我们书房里挂着好几张,前年来了一个清客先生叫做什么嵇好古,老爷烦他抚了一曲。他取下琴来说都使不得,还说:‘老先生若高兴,改日携琴来请教。’想是我们老爷也不懂,他便不来了。”这个与嵇康同姓的嵇好古,善琴却又不轻易弹,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魏晋时善琴的嵇康。而且嵇康《幽愤诗》自述生平,其中恰有“抗心希古”句,“希古”道出嵇康的追求,与“好古”二字正吻合,可为一证。众所周知,嵇康以善琴知名,写过《琴赋》,反抗司马氏被杀时从容弹奏一曲《广陵散》,慷慨赴死,从此《广陵散》成为绝响,也许是嵇好古不弹的原因吧。《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虽有争议,但里面有曹雪芹的原稿不容置疑,否则的话,嵇好古的出现就太突兀了。
如上粗略统计,在《红楼梦》的小说文本中,至少先后五次直接或间接提及嵇康,其中一次是直接提其姓名,另外四次通过使用典故或影射方法提到,这在魏晋名士中鲜有人能及,可见曹雪芹心目中,嵇康是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的。
2 《红楼梦》主要人物身上有嵇康的身影
嵇康对《红楼梦》的影响,不仅通过典故,把欣赏和赞美的人物与之类比,如尤三姐、晴雯等,因为这些人身上有类似于嵇康的一面,而且还在小说最主要的人物,如贾宝玉、林黛玉、史湘云等形象的建构上,诸多方面汲取了嵇康。
受嵇康影响最突出的,无疑是男主人公贾宝玉。魏晋流行人物品鉴,以审美的眼光进行人物审美,评价和赞美人物的气质内涵、神采风韵。其中评价的名士,嵇康以自然俊美、卓然不群的风度气质最为引人注目,如《世说新语·容止》云:“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又注引《康别传》:“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 对比一下,《红楼梦》第三回对贾宝玉的描写:“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如秋月春花般的面容,顾盼生神的眼睛,岂不正是“风姿特秀(俊美)”?“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含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不用涂抹脂粉,而风姿天然,岂不就是“天质自然”吗?宝玉也正是因为 “在群形之中”,气质超凡,所以引发了贾府掌权者的错觉,以为他如嵇康一样,是“非常之器”,才寄予振兴门庭的期待,结果却大失所望。显然,在人物的外貌神情描写上,贾宝玉借鉴了嵇康的风姿神韵。
再如,贾宝玉在性情、爱好以及价值观方面,和嵇康也多有近似。如贾宝玉讨厌世俗事务,不愿和官场人物应酬,“素日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子接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就与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不堪行动受拘束’‘不堪揖拜上官’‘不堪书札酬答’‘不堪吊丧’‘不堪交际’‘不堪为官事操心’十分相类。”[2]这则是性情上的相似。
在魏晋名士中,嵇康的叛逆色彩是最强的,钟会称之“言论放荡,非毁典谟”[3]。他拒绝攀附手握生杀大权的司马氏,反对得势者钟会等人的拉拢,还写了一系列文章讥讽当权者,如《管蔡论》,借古讽今,认为周公所诛杀的管、蔡并非恶逆,甚至“未为不贤”,而对周公的圣明表示了怀疑和否定。很明显,这是借为“管蔡之乱”翻案,替造反而被司马氏镇压的毋丘俭、诸葛诞辩诬,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以周公自居的司马氏。
贾宝玉同样具有强烈的反叛色彩,不仅叛逆性格的形成原因相似,连反叛的对象也和嵇康有惊人的一致。宝玉从小就被称作“混世魔王”,“行为偏僻性乖张”,这一性格的养成,和他被视为掌上明珠,备受贾母、王夫人宠爱呵护有关。虽有贾政极力管束,但因贾母袒护,一直有心无力。而嵇康从小父亲去世,由母兄抚养长大,“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姐,不训不师。爰及冠带,冯宠自放。”可见和宝玉一样,都是因受宠放纵,缺乏约束,才形成了叛逆性格。再看二人反叛的对象:首先,宝玉 “愚顽怕读文章”,尤不喜读儒家之书,只爱看《西厢记》《牡丹亭》,以及小说野史之类杂书,他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第三回) “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第十九回)而嵇康为了反对礼法名教的虚伪,曾写《难自然好学论》一文,以反驳张辽叔的《自然好学论》。文中提出,人的本性就是“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好学不是人的自然本性,好学者往往别有所图。他还指斥六经,说“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4]其次,贾宝玉瞧不起读书考科举者,骂之为“沽名钓誉”的蠹虫。如第三十六回与袭人聊天时,批评“文死谏,武死战”,认为是“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并不知大义”。嵇康则指出那些认真读经书的人是为了“学以致荣”,追求功名利禄而已(《难自然好学论》),甚至还公开“非汤、武而薄周、孔”(《管蔡论》),结果引起司马氏的不满。复次,宝玉愤恨别人劝他走“仕途经济”,连宝钗说教也不给面子,当面斥之为“混账话”,甚至史湘云劝说时被下了逐客令:“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第三十二回)。嵇康拒绝做司马氏的官,宣称“名位为赘瘤,资财为尘垢”(《答难养生论》)因好友山涛劝自己做官,便宣布与其绝交,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可以说,在竹林七贤中,阮籍、向秀、阮咸、刘伶是不得已而仕晋,王戎、山涛则是主动求官,对待功名利禄,嵇康是唯一的例外,抵制最为坚决,与贾宝玉极为类似。
女主人公林黛玉形象,亦深受嵇康的影响,有人说她“神似嵇康的名士风流”,是“对嵇康形象的临摹”[5]。黛玉前身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草,转世后姓林,自称“草木之人”,身上有一种自然的香气“女儿香”,与宝钗身上“冷香丸”散发出的香气不同,这些都暗示她“质性自然”的特点,同时也决定了她崇尚自然、任情率性的独特性格。她敏感多疑,爱使小性,喜怒哀乐挂在脸上,同时又敢说敢做,经常得罪人也不怕得罪人,这种“非矫厉所得”[6]的个性,与宝钗经常克制自己,“会做人”的特点全然不同,体现了魏晋玄学“任自然”的影响。“任自然”作为一种自然观,主张因循各人之个性而发展,反对礼法名教异化人性。嵇康作为魏晋名士的代表人物,不满司马氏提倡名教的虚伪性,率先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主张“人之真性无为,正当自然”(《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循性而动,各附所安”(《与山巨源绝交书》)。他本人也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平日“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行为处事“贵得肆志,纵心无悔” (《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他“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 (《与山巨源绝交书》),如《世说新语·简傲》记载的一件事: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钟会是司马氏的宠臣,带着一群人来拜访嵇康,但嵇康不喜其为人,也不怕得罪对方,不仅不搭理他,甚至在其自觉无趣离开时,还不忘嘲讽一句。可见嵇康行事,完全是“纵心无悔”,纯任自然。如此任情率性,和林黛玉如出一辙。
再如,林黛玉性情的另一面是至诚至性,真情待人。小说第四十八回写香菱想学诗,一开始央求宝钗,结果被鄙视,讥笑她“得陇望蜀”;后来求到黛玉,黛玉虽然病未全好,但极为热情,立马答应说:“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作师。我虽不通,大略也还教得起你”,话音未落就开始为其讲解作诗之法来。最能体现黛玉至诚的是第四十五回,宝钗来探病,黛玉往常一直对她心存芥蒂,但当对方对自己表示一番关心后,黛玉就立刻掏心掏肺地说出心里话:“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这种内心的纯真厚朴,真诚坦荡,也正是嵇康所赞美的“显情无措” (《释私论》)。嵇康本人即是如此,如直接导致嵇康被诛的吕氏兄弟反目事件:嵇康与吕巽、吕安兄弟为友,后因吕巽奸淫弟妇事泄露,巽先发制人,反诬告吕安不孝。嵇康不忍其兄弟反目,出面调停,无果后还亲自到狱中为吕安辩诬,结果被钟会抓住把柄,向司马昭进谗,最终嵇康与吕安同日被杀。此事本与嵇康无关,但出于对朋友的真诚关切,明知可能会牵连自己,还是不惜冒险去伸张正义,从而践行了他自己所说的“君子显情无措”;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吕巽、钟会等无疑是“小人匿情为非”(《释私论》),正是嵇康所反对的。
此外,黛玉喜欢谈琴论琴,琴声悲苦,嵇康亦善琴,曾撰《琴赋》云:“赋其声音,则以悲苦为主”;黛玉感叹“孤标傲世偕谁隐”,对贾宝玉发表“知己论”,“你既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之知己矣……”(第三十二回)嵇康亦云:“鸣琴在御,谁与鼓弹?仰慕同趣,其馨若兰。”(《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识音者兮,孰能珍兮?”(《琴赋》);黛玉寄人篱下,生活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贾府,感叹“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而嵇康所处的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天下名士,少有全者” 时代,而本人又狷直狂傲,得罪司马氏集团,处境可谓真正的“风刀霜剑严相逼”;黛玉高标傲世,不屑与世俗为伍,吟唱“质本洁来还洁去”,而嵇康不畏强权,拒绝拉拢,甚至以生命完成人格升华,“质本洁来还洁去”恰是他人生的最佳注释……凡此种种,说林黛玉是对嵇康形象的临摹,并不为过。
除宝、黛之外,小说中最具魏晋风流的当数史湘云了,亦不可避免地受到嵇康的影响。小说第四十九回写她“割腥啖膻”,“大吃大嚼”鹿肉,被林黛玉嘲笑,她回击说:“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出自《菜根谭》,湘云张口即出,说明这两句或是她的价值追求。而本色即自然,说明她崇尚自然本色,视为名士风流的体现。显然,史湘云和黛玉一样,向往“任自然以托身”(嵇康《答难养生论》),都是个性率真坦荡,反对虚伪之人。但稍有不同的是,黛玉的“自然”体现为“真”(真实不掩饰),湘云更多体现为“天真”,天真烂漫,内外澄澈,光风霁月。如她说话有爱咬舌的毛病,还因此受过黛玉的嘲讽,但她毫无顾忌,照样爱说爱笑,甚至比别人话都多。《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在薛宝钗的生日宴会上,因为有个小戏子长得很像林黛玉:
凤姐笑道:“这个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你们再看不出来。”宝钗心里也知道,便只一笑不肯说。宝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说。史湘云接着笑道:“倒像林妹妹的模样儿。”宝玉听了,忙把湘云瞅了一眼,使个眼色。众人却都听了这话,留神细看,都笑起来了,说果然不错。
宝钗和众人都知道王熙凤说的是黛玉,但大家不说,是因为都知道黛玉的脾性,怕她生气。只有史湘云口无遮拦,心直口快说出来,可见其天真本色,毫无城府。也正因此,黛玉并没有生湘云的气,反而对宝玉发火,说:“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还利害呢!”认为宝玉好意提醒湘云,反而弄巧成拙,引起众人关注,便是不自然了。其实湘云的口无遮拦,无所顾忌,和嵇康完全一致,后者“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公开揭露司马氏的虚伪,表达不合作态度,二者都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是“任自然”思想的体现。不过因为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嵇康在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依然能保持本色自然,更属难能可贵罢了。
“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这是红楼十二曲中对湘云的评价,性情豪爽豁达、洒脱从容是她另一个特点。湘云身世凄苦,命运多舛,自幼父母双亡,由叔婶抚养长大,由于经济条件不好,叔婶也不待见,虽是贵族小姐,却经常要熬夜亲自做针线活。尽管如此不幸,湘云却从未和任何人谈起(只有一次拉家常无意中向薛宝钗透露过每天做活“累得慌”),也从未愁容满面,把不幸挂在脸上,反而平日是说说笑笑,乐观豁达,洒脱从容。如此格局气量,在魏晋名士中,令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嵇康。《世说新语·德行》提到王戎曾说他:“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该书注引《康别传》也说:“康性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所知王浚冲在襄城,面数百,未尝见其疾声朱颜。”身处极端恶劣恐怖环境中,一直保持冷静沉着,不喜不惧,甚至面对死亡,还从容索琴,弹奏一曲《广陵散》,成为旷世绝响。这种洒脱、从容、淡然的修养和气度,无疑影响了史湘云。
此外,史湘云的“英豪阔大”,还表现在她正直仗义,爱打抱不平。如当她得知邢岫烟被迎春房里的奶妈欺负,便生气要找对方,“骂那起老婆子丫头一顿”,黛玉打趣说她是充当荆轲、聂政(第五十七回);宝琴刚来贾府,她就提醒对方说话做事要留个心眼,提防“害咱们的”小人(第四十九回),其实她自己才最没有心眼,没有想到这样说会得罪人。湘云的这种个性,和嵇康也极为相似,明知道自身难保,还为了朋友吕安被陷害而去打抱不平,结果受牵连入狱,双双同日被杀,实属可敬可叹。
《红楼梦》中,“醉卧山石”和“大嚼鹿肉”,无疑“是湘云身上魏晋风味最浓郁显豁的两组特写镜头”[7]。第二十六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裀”:“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穰穰的围着他,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活画出湘云的憨态可掬、无所顾忌和率真任性,体现了物我合一,人与自然圆融的境界。这不由人联想起嵇康“玉山倾倒”的典故:“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同是饮酒状态下达到物我合一的审美画面,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说前者受到后者的启发影响,也不无可能。
质言之,贾宝玉、林黛玉、史湘云是《红楼梦》人物群像中最具魏晋名士风度的三位,恰是他们身上最突出地体现了嵇康多方面的影响。当然,这些形象身上可能也不乏阮籍、陶渊明等人的身影,对此前人多有论述。作者将魏晋风度融入人物形象进行创造,准确地说不是以某个魏晋名士为原型,而应是多人的杂糅,其中有嵇康的重要影响,则毋庸置疑。
3 嵇康影响《红楼梦》的原因
嵇康在《红楼梦》中留下诸多印记,并对小说重要人物形象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本原因在于曹雪芹对嵇康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范的欣赏和仰慕。曹雪芹去世后,好友敦诚为了表达悲恸之情,写了“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挽曹雪芹》)诗句,一度比之为嵇康。然而,一直以来由于人们更多关注阮籍的影响,对嵇康和《红楼梦》的关系反而造成了有意无意的忽略。
清张宜泉《春柳堂诗稿》记载曹雪芹“字梦阮”,且曹雪芹好友敦诚、敦敏《赠曹雪芹》有“步兵白眼向人斜”“一醉酕醄白眼斜” 的诗句,而阮籍“善为青白眼”,于是很多人包括一些著名红学家便认定“阮”为阮籍,以为曹雪芹倾慕的主要对象是阮籍。其实这里有很多存疑之处:古人命名取字,名、字之间必有关联,但若“梦阮”指阮籍,则很难和曹雪芹“名霑”发生联系。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人提出别号说,说“梦阮”是号不是表字,但这也只是猜测,缺乏相应的证据。
其实依笔者所见,“梦阮”的“阮”字未必指阮籍,可能另有所解。至于敦诚、敦敏的诗句也不足为据,因为阮籍“青白眼”的典故被古人大量使用,已经意象化,借以抒情写志而已,如白居易:“林间箕踞坐,白眼向人斜”(《和春深二十首》),能否将他也和阮籍绑在一起呢?不过,话说回来,因为作家深受魏晋文化的影响,又在《红楼梦》中两次提及阮籍的名字,说明曹雪芹的确受阮籍一定的影响,这一点并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重视阮籍的原因,就忽略了其他魏晋名士的影响,尤其是作为竹林七贤之首,与阮籍齐名的嵇康。如前所述,曹雪芹除了在文本中提及嵇康的姓名,还多次使用了有关嵇康的典故,甚至虚构了一个嵇好古的人物影射之,可见对嵇康的看重和仰慕。之前有人为了证明曹雪芹倾慕阮籍,发掘了不少曹、阮相似之处,其实较真起来,会发现曹雪芹和嵇康有更多的相似:
首先,二人经历、遭际相似,都经历了由盛到衰、由富到贫的过程。曹家在康熙时钟鸣鼎食,三代四人做过江宁织造,显贵一时,但雍正抄家后急剧衰落,而曹雪芹恰好经历了这一跌落过程,晚年贫困,甚至到了“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地步。嵇康出身儒学世家,自己身为魏宗室,是曹操的孙女婿,《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文章叙录》云:“康以魏长乐公主婿,迁郎中,拜中散大夫。”后来由于司马氏篡权,不屑与其合作,生活自然坠贫,《世说新语·简傲》注引《文士传》:“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家虽贫,有人就锻者,康不受值。”相似的人生体验,使曹雪芹自然地会对嵇康产生某种共鸣。
其次,二人都多才善辩。曹雪芹工诗善画,写出了古典巨制《红楼梦》,嵇康同样工书画,又善琴,诗虽不如阮籍,但文章过之,写出了《声无哀乐论》《琴赋》《养生论》等名篇。二人同是文学家、思想家和美学家,嵇康还是音乐家。曹雪芹喜欢辩论(阮籍似乎不喜辩论,因为他“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必然影响辩论效果),“大庭广众之中,高谈雄辩,旁若无人”[8],敦诚《寄怀曹雪芹》称他“高谈雄辩虱手扪”。嵇康也非常喜欢辩论,《德行》注引王隐《晋书》说嵇康“有奇才俊辩”,其现存的十三篇散文,有十二篇是论辩性质[9],《声无哀乐论》,假托东野先生与秦客七问七答,展开论辩,析理精密,其他《难自然好学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答难养生论》等,从篇名就可以看出是与人辩论之作,大都写得逻辑严密,论辩方法灵活多样。
再次,二人都具有桀骜狂放的个性和反叛意识。敦敏《题芹圃画石》称曹雪芹:“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张宜泉《题芹溪居士》:“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说曹雪芹不羡慕唐代李白和阎立本被皇帝召见或宠幸,由此可知缘何贾宝玉反对仕途经济,不喜和官宦人物来往了。这种坚韧反叛的个性,和“嵇康傲世不羁”(《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秀别传》),以功名为羁绊,坚决不做司马氏的官,甚至因好友山涛劝做官,而写了绝交书,以及蔑视得势小人钟会等等,几无二致。
多方面的高度相似性,极可能是曹雪芹倾慕嵇康,为对方的精神风范、人格魅力熏染的结果。可见嵇康在曹氏心目中的地位,丝毫不亚于阮籍。正是因为这种景仰和倾慕,深深影响了《红楼梦》的创作,才在这部鸿篇巨制中留下了许多嵇康的身影。
其外,嵇康对《红楼梦》产生极大影响,还在于他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古代的诗词歌赋普遍使用有关竹林七贤、魏晋名士的典故,其中最多的就是嵇康、阮籍和陶渊明。在通俗文学尤其是古代小说中,提及嵇康的作品更是不遑多让,除了《红楼梦》之外,嵇康的身影随处可见,如《水浒传》第七十回“梁山伯英雄惊噩梦”:“是夜卢俊义归卧帐中,便得一梦,梦见一人,其身甚长,手挽宝弓,自称‘我是嵇康,要与大宗皇帝收捕贼人,故单身到此。汝等及早各各自缚,免得费我手脚!’”这里,嵇康直接化身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此外,通俗小说《镜花缘》《林兰香》《荡寇志》《斩鬼传》《五凤吟》,以及文言小说《虞初新志》《太平广记》《异苑》《耳新》《灵鬼志》等,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提及嵇康,可见嵇康对古代小说影响之大,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红楼梦》会与一千多年前的嵇康,结下不解之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