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 望
2023-01-13温州大学吴颖慧
温州大学 吴颖慧
1
我时常分不清是我梦见了记忆深处的故乡,还是故乡把我拉进它庞杂的梦境中。
有时我奔跑在田埂上,视野里翻滚着绿麦子、黄麦子的浪潮,祖母在不远处漂浮着绿油油水草的小溪旁捣衣。“啪——”七零八碎的捣衣声穿透薄薄的夜幕,洒向溪水,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丘,沿着蜿蜒的小路潺潺流去,漫浸在沉静如水的夜色苍茫中。有时在下雨,我与祖父同坐在屋檐下,他闭着眼睛假寐,身后的竹椅在风中咿呀作响。雨沿着屋檐的凹槽处滑落,打在泛着白光的青石板上,清脆的凉意便入了耳朵。日子一如既往地久长。
上学之前,我的童年是与祖父母在乡下度过的。那是个江西西北部的边远山村,幕阜山自西南向东北绵延到这里。在江西境内,与幕阜山隔岸相望的另一条山脉,名为九岭。一道九岭,又将九江与南昌分隔开来。九江的北面,修江从山垭处跌落,蜿蜒穿过幕阜山与九岭相隔的腹地,带出了一片生机,因此得名为“修水”。沿着修江的支流远远而去,岸边零星散布着各个村庄,我的家便在其中一个小小的村庄里。一片望得见尽头的田野,三面围着连绵的幕阜与九岭山脉,有如屏障。村里疏疏落落住着几十户人家,皆是剥落了泥墙的土坯房,它们背后倚靠着连绵青山。重重青山围着房屋,斜仄的房屋和树木散落在小路旁,与小路相连的,是从各处通向田野的田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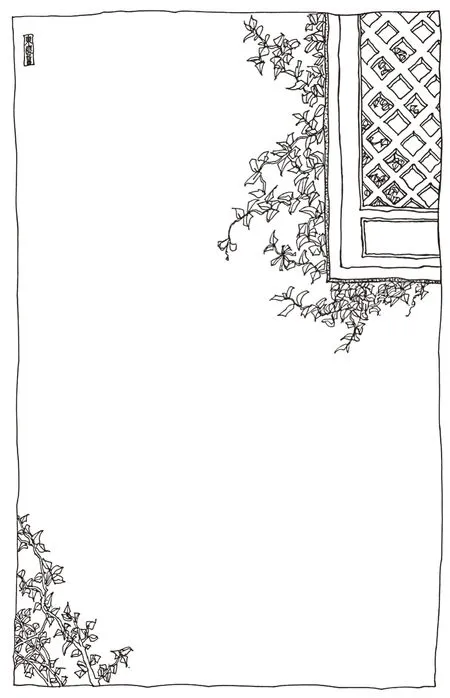
东良 《窗》
家门口不过几十步的距离,有一条浅浅的小溪,两岸的树枝垂落到溪水里,在阳光下浮漾出细细密密的波光。祖母因害怕我调皮捣乱掉进溪水里去,很少将我带到小溪边。偶有一两回,于我而言,便是宛如天赐。祖母将花花绿绿的衣裳从哐当作响的铁桶里倒出来,不顾厚重的青苔和黄泥,把浸了水的衣物重重拍在壁边,她甩甩手,袖口往腕上卷几圈,一手扯住要往水里去的衣服,一手拿起小木棒在衣服上结结实实地敲打。我坐在一旁打量溪水里的影子,一条鱼,一片树叶,几块灰白的云团,还有在涟漪里浮动的捣衣身影。亲缘血脉在这些没有生命的衣物中流动,穿在身上,又是厚重的温暖。
有风吹过来,两旁的芦苇就在风中微微摆动,不远处田野上新翻的泥土香味,随着风一阵阵飘过来。我再也坐不住了,转身朝田野跑去,与伙伴们一同疯玩,总是忘记日暮迟迟,两位老人还在等我回家。日头西斜时,祖父总从门口的树上摘下一根长满荆棘的“刺棒”,呼喊我的名字。天色渐渐黯淡下来,祖父的喊声也更加急促,他的嗓音在时间的淬炼中愈发淳厚、高昂,回荡在村庄里,远远的,像一支古老的歌谣。
时间就这样在祖父、祖母无数次的等待中偷偷流逝。上学前一天,父亲将我从乡下接到城里。他把我抱上老式自行车的后座,那是一块粗糙的小木板,我们沿着黄泥小路离开。我扭着脖子向后张望,祖父、祖母站小路中央,慢慢地、慢慢地,他们像旁边的树、屋子一般静默无声。我见过许多东西在风中伫立,都没有他们那么像岿然不动的雕像。自行车在风中缓缓地走,金属链条摩擦出细微的声响,我在自行车的后座,看着他们被黛色的山脉、昏黄的灯火晕染成相似的颜色,直到完全与故乡融为一体,隐没在茫茫夜色中。
我已经沿着小路远去。
2
彼时的我,没有想过,后来我竟再没有真正地回过故乡了。
二〇一二年夏,祖父过世了,祖母也不在老房子里住了。祖父的离去似乎带走了她对于家的归属感,一种叫空虚的东西正在酝酿,弥散在她寂寞的晚年。很多次,我看见她呆坐在城市的落地窗前,浑浊的目光投向不远处的山峦,许多尘埃在阳光下飘浮,最后跌落到她的视线之外。又或者,她的视线早已越过山丘,落到她魂牵梦萦的老屋。老屋坐落在幕阜山与田野的间隙里,是只有三间屋子的土坯房。正面三个洞里,一左一右塞着木制窗框,常年糊着泛黄的报纸,中间是简陋的木门。从门口踏上几个歪歪扭扭的台阶,便是有天井的院子,从这里可以窥见一块长方形的天空。院子后头,几块结实的长木板潦草搭成茅房,一墙之隔,圈养着大大小小的牲畜。我曾以为老屋只是破旧,但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可后来,它断裂坍塌,只剩下几块被雨打碎的残破屋瓦,几株孤零零的小草留在空荡的院子里,那里再也没有祖母弯腰择菜的身影,也没有祖父编竹篾篮子的响声。高高的山头,荒冢里,躺着我的祖父。
那是我第一次见证死亡,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竟可以有那么多的泪水。那段时间,祖母把自己关在与祖父同住了几十年的小房间里,一丝光亮也没法溜进来。墙边的窄床旁摆放着几条木板长凳,四四方方围住我的祖父。她整日痴呆地坐在灵柩旁,不进食,只盯着那个小方框里的祖父,偶尔又像看陌生人一样审视她的子孙,再扭过头看看空荡荡的门框,单薄的木门发出“吱呀”的沉闷声响。
后来的几个夜晚,我在迷蒙中看见祖母倚在门框前,粗糙的指腹在门框上反复摩挲,直到那一块消弭了声响,只有哀切哭声在夜色里游荡。那哭声推开木门,攀上家门口的板栗树,拂过树根下疏落散着的叶子和刺壳,游走在祖父天不亮就起来为那条黄泥小路铺上的大大小小的石块上。她执拗地认为,她可以守到祖父归来。而我明白,那些穿破时空的目光,最终会召回迷路的古老的灵魂。
祖父往时间的尽头走了,像所有的生命都有属于自己的年轮一样。在这之前,他生了一场大病,喊不出儿女的名字,忘记了喜欢的小猫,就连祖母,也从他的记忆中抹去了一部分。
人的记忆和忘却是从何时开始的,我无从得知。时间像雨水一样,冲走了太多流沙。有一次,我从学校去医院看他,他坐在医院的长椅上,也不再听窗外的雨声了。他守在电视机前,用手去装里面的“财神”散钱,我问他认得我吗,他只是咯咯地笑。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很无助,祖父已经喊不出我的名字了。我忽而想起那些微风拂动田野的日暮,我在田埂上奔跑,细细的汗水滴滴盘桓在空气里,夜晚有风。寻不到我的祖父在门口摘下一根“刺棒”,在黄昏中呼唤我的名字。如今,祖父无法再呼喊了,祖母的哭喊也没能让他再回来。
芒种过后,原先播下的麦子粒粒饱满浑圆,已经可以收割了。而祖父,却被种到了黑而硬的土里。
3
祖父离开以后,祖母也开始以我肉眼看不见的速度老去,以至于我很久才发觉。我以为她的手臂还能像当初挥动棒子一样有力,却发现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已。我试图用记忆去掩饰这些流逝,可真要流走的时候,我却没有办法,只能接受。很多年来,我在祖母的目光里归来或离去,跌跌撞撞,寻寻觅觅,已不再是孩童的模样。可是祖母,她总是站在那里,用力伸长脖子,手掌捂住抽痛的脸颊,仿佛如此就能燃烧她的力气,再多看一眼。终于有一天,我发现,祖母就像她身后的老屋,正在走向无可遏制的衰老,时间寂静无声地磨砺着她。时间,把她消磨成了另一副模样。
去年秋天,祖母受了严重的伤,一辆货车从她的右腿碾过,父辈们赶到时,她已因疼痛昏死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祖母被包裹在白色的病床上,断断续续发出痛苦的呻吟。她把裤腿卷起来,给我看她的伤口,那里已经是一片模糊的血肉。上半部分,是无精打采耷拉在腿骨上的皮,上面攀附着七七八八的老年斑,下半部分却肿得出奇,猩红占据了这里。我看到她时,几乎不敢呼吸。
很多时候,我觉得人是被推着走的,被时间这只看不见的手推着前行,偶尔停下来喘息,又被催促着加快了速度。可在祖母面前,时间也推不动她了。她忙忙碌碌了一辈子,十六岁的时候忙着结婚;再大一点忙着生孩子;中年的时候,她忙着养育孙子、孙女;再后来,她忙着照顾患病卧床的祖父,即便那时候祖父已经认不出她了。春天,她忙着去对面的小山上挖笋尖,给我们小孩子炒腌菜和细笋干;秋天,她忙着摘祖父种的辣椒,用竹编簸箕在太阳底下晒干,制成辣椒酱;冬天,她忙着做针线活,给一家人洗净脏衣服。到城里后,她每晚又忙着给所有她牵挂的人打电话……而现在,她显然已经力不从心。
于是,她开始盼着我长大,把书读好,找个安稳妥帖的工作;盼着我有个健康的身体,不像她落得一身顽疾。每夜,她都在祖父的遗像前点上三根香火,跳动的烛光里蕴藏着无限的愿景。她像是用生命里余下的力气虔诚祷告,为身边的人祈求一点祝福。
春天的时候,父辈们把乡下的老屋翻新,为了祖母能回到她眷恋的故土,安详地度过晚年。那个爬满了杂草的土坯房已寻不到半点影子,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咯吱作响的木门也变成了沉重的红漆铁门。我每次去看她,她不时坐在轮椅上睡觉,铁门只稍稍开了一侧,有光从外面泻进来,笼罩成一块小小的三角形,祖母坐在光圈里,头无力地垂在胸前,光与影将祖母与偌大的房间分割开来,定格成一幅寂寞的图景。她好像回到了日思夜想的那个“家”,却与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了。也许,祖母想要回到的那个地方,早已不是地理、空间上的概念,而是那段有人陪伴的时光、那些忙碌却有盼头的日子。
这次从乡下驱车离开,透过模糊的车窗,祖母拄着助步器,已经腾不开手朝我挥手,我亦不再朝着她奔跑。她的轮廓在视野里变小比以往来得更加迅疾,只有远处的幕阜山在流动中始终保持缄默。
4
在外求学多年,童年的往事在记忆里已然模糊不清,更别提阔别已久的故乡了。那里的人和事,砖和瓦,日出与日落,麦子与稻谷,都随着风烟飘散在匆匆的步履声中。但我始终忘不了祖父、祖母在家门口等着我回家的模样。他们的眼眸在黑夜里像漫天星光一样闪亮,长长的呼喊指引我去往家的方向。
在异乡,下雨的时候,我曾多次想起祖父。我曾与祖父并排坐在长长的屋檐下,听檐外的雨声稀稀落落,听他讲述过往的故事。小时候天不亮就与他的祖父上山砍柴,沉重的竹篓将他瘦小的脊背压弯,以至于现在还直不起来;他讲到他的父亲去世后,他被辗转送到不同的家庭里。十几岁那年,家里没法再养育一个孩子,他稀里糊涂跟上了行军的队伍,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见证了生与死是同等的残酷,懂得了生命是何等脆弱。后来,白云机场的某一片角落里,留下了他修长的身影,再后来,他脱下戎装,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他遇见我年轻时的祖母,他们在生产队里挣着工分,共同养育了六个儿女。他和我讲山头还有着几间土坯房,那是他一砖一瓦,一铲一锄,和着血与汗修建而成的,要分给他的几个子女。他和我讲父亲出生的时候,家里揭不开锅,亲戚朋友劝他们把他送走,可他看着小小的父亲,终究是不舍;和我说那些年他走过的路、吃过的苦;也教育我,认认真真做事,堂堂正正做人。讲得乏了,他就打个呵欠,闭上眼睛假寐了。
修水一带的梅雨,闷热又绵长。许多清晨,我看见祖父从床上爬起,戴起他自己编的竹篾帽子,拿起扁担穿过两个竹篓子,走出家门。他从山上捡下一些大小不一的石块,铺在雨中泥泞不堪的小路上。祖父母在细雨中呼喊我的名字,我踩着这些石块回家。直到我一蹦一跳到家门前,他们才长长地松口气,祖母随即拎着我洗把脸,把我塞进干燥温暖的被褥里。故乡的村庄,也在雨水中洗掉了一天的疲惫,沉入安详的睡梦中去了。
从那个离城市很远的小村庄出来后,祖父常常来梦里喊我回家,记忆便回溯到了那些与之有关的日子。院子里的大水缸,比我的个头还高,里面装的是我喝完AD 钙的空瓶子。祖母有时在昏黄的灯光下裁纸衣,有时在厨房的大灶台烧好热水,清洗她斑白的头发。我蹲在屋檐下透过天井看星星,又数着壁上趴着几条鼻涕虫……村庄的日暮,不止有通透的日头,还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红薯“哨子”。离开家乡后,我再也没有在别的地方吃到过这种味道,每逢佳节,我总期盼在陌生城市的街头寻觅到相似的气息,但更多时候,吃上一碗纯粹的家乡味道,竟成了我的奢望。
我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离开我在暮年的祖母;我经由光阴,经由山水,经由每一个陌生的城市和村庄。列车驶过各异的土地,我看见过许多殷切的目光,有些在送行,有些在等候,而那些从火车的窗口看到的陌生村庄里,会不会也有人正在恳切地呼喊另一个人的名字呢?后来,我在城市里生活了很多年,无数个夜晚,我观察对面的璀璨霓虹,楼与楼之间总是那么相似,每一幢楼都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小方框,有些发着白光,有些黑洞洞。我在这些迷离的光晕里走进走出,摸爬滚打,追寻自己的梦想,去往更好的地方。可每当夜阑人静时,生活的华美外衣被盛大的孤独与寂静剥蚀得一干二净的时候,我突然十分想念那些有人守望的黄昏。
摇摇晃晃的梦境里,远处,祖父、祖母倚在黑黢黢的门框前等我,祖父铆足了劲,大喊一声:“细姑,你怎么还不回家来?”他们的身影在我的视野里扎根,从模糊到清晰、由远到近、从小到大,我想用力看清他们,沿着源源不断的电线杆子和小平房,逆着两旁愈加驳杂向后奔走的幻影,穿过这十几年影子一般掠过的时光……
我的村庄静静地落在修江边上,黄泥的小路、土灰的墙、青黑的屋瓦与绿色的田野。遥远的幕阜山脚下,祖父、祖母站在矮矮的木门前。他们都在风中凝望。
他们总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