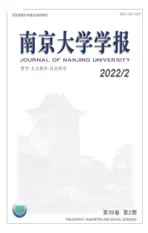历史社会学与历史叙事和机制分析的反思
2023-01-04严飞
严 飞
(清华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084)
历史社会学在国内学界是一个新鲜的事物,直到最近几年才逐步受到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双重重视,并在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中不断得到发展。 如果对历史社会学进行拆解,很自然地可以分成历史(学)与社会学两个维度,但如何处理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就不可避免地构筑出历史学者与社会学者阐释方式的分野。
历史学与社会学变成了一种不可调和的关系,被人为构建出彼此互斥的边界。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所指出的:“历史学家将社会学家看成是用粗俗难懂的行话来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毫无时空感,将活人生硬地套进他们的分类并冠以‘科学的’标签的人;而在社会学家看来,历史学家则是业余的、近视的,缺乏体系和方法的事实收集者,其‘数据库’的粗鄙不堪恰与他们的分析能力相称。”①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3 页。类似地,国内学者亦提出了相近的批评,指出社会学家进入历史领域,是带着一种足够的“自信”,期望在历史领域中采掘历史性,为原有单薄的理论叠加上一件看似厚重的历史外衣:“他们(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没有相应探矿的能力,甚至不了解什么是历史,更勿提构成历史绵延模式的意义;他们以为历史就是时间的深处,只要往深处挖就够了。 然而,他们却利用了各种理论,这种曾经驰骋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中的大型机械,结果令一片历史性的富矿区变成满目疮夷的盗采区。 历史学家们虽然有着矿脉绵延的概念,可是他们只忙于挥动铁镐,不了解史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种制造矿机的能力。”②陈新:《史学理论的性质、对象、价值与方法》,《史学月刊》2021 年第1 期。事实上,无论是历史学者还是社会学者,在研究当中都会遇到一个黑盒子难题——如何阐释历史因素与历史结果之间为何会产生关联? 例如,社会学家约翰·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就曾提出这一疑问:“从分析里,我们知道了‘输入’的部分,也知道了‘产出’的部分;但是何以致此呢? 在我们应用的统计模型这个黑盒子里,输入的部分是如何转变成产出的部分,我们其实所知甚微。”③John H. Goldthorpe, “Current Issues in Comparative Macrosociology: A Debate on Methodological Issues,”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16, 1997.换言之,无论是历史学者还是社会学者都需要去解答,在事件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了打开这一个黑盒子,历史学者选择的方式是高度重视史料,强调通过精细的历史叙事,描绘出在某一历史时刻社会秩序的模式以及该社会秩序经过长期变动后的模式,以此说明在特定研究案例里的历史因果过程。 在许多历史学者看来,历史如同岁月的年轮,单单埋首证据之中,特别是寻找到第一手的史料或从既有史料中深挖历史情境中那些不为人所注意的细微颗粒,从而开辟出崭新的历史视域,似乎已经足够。 社会学者则更加钟情于在泛起的涟漪故事中探求普遍性的法则,企图把推衍自一般社会理论的机制分析和史料等量齐观。 在社会学的分析框架里,要破解黑盒子难题,唯有通过理论说明的指引才能解决。 而理论阐述又非就事论事的泛泛而谈,必然需要找到通则性的机制,可以概推于同类别的社会现象,并在其他的文化和政治情境中得到经验验证,从而才可以产生出更进一步的经验意涵,因为理论阐述被认为可以同时赋予“更强大的解释力……以及更开阔的经验检测”①John H. Goldthorpe, “Current Issues in Comparative Macrosociology: A Debate on Methodological Issues,”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16, 1997.。 从这层意义出发,社会学追求“通则式知识”(nomothetic knowledge),旨在把握普遍规律,建立起通则性的机制定律;而历史学则关注“殊例式知识”(idiographic knowledge),旨在通过描写独特的历史现象,予以该现象特殊的位置②Edgar Kiser and Michael Hechter, “The Role of General Theory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Soci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7(1), 1991.。
与此同时,在一些学者的分析中,历史研究与社会学研究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异:二者在经验材料的获取上存在着不一样的方法论路径。 历史学者所依赖的资料,因为历史的独特性和偶发性,只能依托于前人留下的档案和史料;而社会学者却拥有一项优势,即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通过诸如抽样调查和田野访谈等研究设计去收集并搭建相关的当代资料。按照戈德索普的说法,社会学家可能创造出专为他们“量身定做”的资料和证据,而历史学家通常只能“从他们手中仅有的布料去裁制大衣”,至于包括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在内的历史社会学者,他们仅仅是“在‘历史糖果屋’(history’s sweetshop)里悠游自在地‘拼凑搭配’(pick-and-mix)”,借以构筑出他们想要的因果解释③John H. Goldthorpe, “The Use of History in Sociology: Reflections on Some Recent Tendencies,”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42(2), 1991.。
尽管一部分学者们明确提出社会学与历史学是泾渭分明的两种专业学科,无论是社会学的“历史转向”,或者是历史学的“理论转向”,都混淆了二者的专业界线。 但更多的学者指出,把“历史”与“理论”对立起来,一边是理论、科学与机制,另一边则是历史、时间性与叙事,这根本就是一个假命题,是一个虚假的二元对立④例如Jill Quadagno and Stan Knapp, “Have Historical Sociologist Forsaken Theory? Thoughts on the Theory/history Relationship,”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20(4), 1992; Craig Calhoun,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Narrative,General Theory, and Historically Specific Theor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04(3), 1998; Julia Adams, Elisabeth S.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 “Introduction: Social Theory, Modernity, and the Three Waves of Historical Sociology,”Remaking Modernity:Politics and Processe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对历史社会学而言,历史与社会都是其中不能剥离的基础要素,两者之间绝不是“A 与非A”的互斥关系。 这两个要素如同墙壁上的藤蔓一般,紧紧缠绕在一起、交织在一起。 两者的结合应该是“美美与共”式的,能够彼此借鉴利用不同学科的方法或理论,扩展历史社会学的研究疆界,在彼此的渗透与汲取中,既保存着本学科某个重要侧面,使之呈现出独特性与独立性,又试图引入其他学科作为“方法”,并时刻穿梭于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的交替之中,以提升研究的厚度与宽度。
社会学自诞生伊始,其研究目的就是致力探究历史上实存的社会如何运作与变化,关于“社会革命”“资本主义的兴起”“国家建构”“现代化进程”“暴力与自由”等经典的社会学研究都深深烙印上了历史的痕迹,而在这些研究中所使用的诸多分析概念,例如“社会因果机制的转变”“偶变性”(contingency)“序列性”(sequentiality)等,既是社会学的,也是历史学的①严飞:《历史社会学的第四波思潮:议题与趋势》,《广东社会科学》2019 年第3 期。。 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 (The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一书中便指出:“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社会学’。”在米尔斯看来,社会学的初衷,是致力于从经验、历史与观念等综合层面来透视总体生活的全貌,只有把握人类社会在历史上的多样性,才能充分阐述清楚所研究的问题。 即便是那些有限的情境、看似静态的事件,也与较大的结构性动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历史的研究是我们洞悉社会结构的必经之路。 但所谓的历史维度,并非只是提供一个时代背景,而是要提供历史关联背后的机制分析:“我们不应只是把什么东西‘说明’成‘来自过去的某种延续’,而应当追问:‘它为何会延续下来’……针对其中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尝试找出这个答案扮演了什么角色,又是如何以及为何转到了下一个阶段。”②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204、215 页。
历史学也同样高度重视理论,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③于沛:《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 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0 年第3 期。。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曾提出:“历史学,也像神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是思想的一种特殊形式。”④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8 页。既然是思想的一种特殊形式,就必然涉及反思和解释。 尽管戈德索普坚持认为,即便历史具备一定的解释能力,但由于历史本身的特殊性、偶发性特质,最多也只是一种“理论上不被解释的解释项”(theoretically unexplained explainer)⑤John H. Goldthorpe, “Current Issues in Comparative Macrosociology: A Response to the Commentaries,”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16, 1997.。 但我们同时也须注意到,理论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历史”共变的,是动态发展的,因此必然具有“历史性”。 理论起于研究假设,而假设的产生则与具体的历史条件息息相关。 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之下,即使对相同的现象也会产生出不同的理论性诠释。 某个历史事件看似偶然发生,而该事件的发生一般又存在着某些不可忽视的历史“初始条件”(initial conditions)⑥Jack A. Goldstone, “Initial Conditions, General Laws, Path Dependenc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04(3), 1998.,历史学最擅长做的,并非仅仅是去找到一种联结特定初始条件与特定结果的最佳解释原则,而是找寻到每种解释原则运用在解读各种历史事件模式时的独特优势。 我们要看到,如若缺乏了历史的纵深而单独追求理论效果,理论就只是空洞贫乏的词汇罢了,会被人为地演化为为了解释因果机制而勾连因果性。 事实上,因果关联性不但总是以“故事”的形态表现,同时,说故事的方法亦已包含镶嵌在时间过程里的各种叙事和陈述之中⑦Margaret R. Somers, “We’re No Angels: Realism, Rational Choice, and Relationality in Social Scienc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04(3), 1998.。 就连社会学学者自己都承认,社会学家都是“说故事者”(story-teller):“一个编织故事的艺匠……犹如都市中漫游的行走者,一直处于当下此刻,在一再分岔的街道上一边行走一边浏览着沿途的景观……以不断分岔的方式来编织‘社会’的图像。”⑧叶启政:《社会学家作为说故事者》,《社会》2016 年第2 期。
特别是在新史学、文化转向和叙事学转向的浪潮下,历史学需要开拓与现实意义世界的关系,社会学则需要锚定历史卷轴中的诸多动态细节,而最后的落脚点,则是行动者在历史多维图景下的选择与回应,以及如何塑造出路径不一、形态多元的历史流变路径。 特别是那些惊心动魄的重大突变事件和历史转折点,如何在时间序列的脉络上逐一呈现。 唯有如此,才能达至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在《历史的诸逻辑》(LogicsofHistory)一书中的判断,“我们才能发展出历史学和社会学科共同追求的,洞悉这个时刻变动的世界的学说”①William H. Sewell,Logics of History: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Chicago &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p.6.。
与此同时,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从来就不仅仅是历史学加上社会学,而是必然会和其他的社会学分支领域,譬如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或者是特定的研究议题,譬如革命、暴力、记忆、性别,结合在一起进行历史维度的细致解剖。 以国内近些年的研究探索为例,孟庆延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领导人王观澜的成长背景、教育经历和革命历程,勾勒出其在土地革命中“算阶级”的实践轨迹,联结了个人生命历程与中共革命中制度变迁的双重讨论②孟庆延:《“读活的书”与“算死的账”:论共产党土地革命中的“算账派”》,《社会》2016 年第4 期。。 应星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展中两个关键的“制度环境”——学校与地缘,并表明中共早期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是嵌入民国政治和教育格局中,另一方面是嵌入传统社会关系中③应星:《学校、地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网络的形成——以北伐前的江西为例》,《社会学研究》2015 年第1 期。。 郭于华在陕北骥村的女性集体化口述史研究中,关注了“婆姨们”的生活空间和历史状态。 与宏大叙事不同,她们的讲述往往是日常的、具身的,勾勒出了一幅关于“心灵的集体化”的性别记忆④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4 期。。 周晓虹则聚焦于三线建设和工业记忆,提倡一种命运共同体下的生命叙事,通过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代口述叙事,有助于通过集体记忆建构整个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意义与集体群像⑤周晓虹:《口述史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21 年第5 期。。 简而言之,历史社会学本身不足够支撑起一位学者全部的学术关怀,而是需要在跨领域的整合之下,结合具体的经验案例,再进行历史社会学的解构。
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中,历史叙事与机制分析如何有机勾连从而成为一个互有补益的整体,这其中有三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历史社会学更加倾向于把研究问题放置于比较的脉络中进行比较历史分析。 关于比较研究,涂尔干早在他1895 年出版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TheRulesofSociological Method)一书里,就强调“研究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必须从不同社会类型的各个社会中去考察这种社会现象的全部发展过程和发展状况”;他还直截了当地指出,“比较社会学不是社会学的特别分支之一,而是社会学本身”,因为“社会学不是一种纯粹地描述社会现象的方法,而是一门考察社会现象、比较社会现象、解释社会现象的科学”⑥Émile Durkheim,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2, p.157.。 尽管历史叙事的验证以及强化此段叙事与其他明确的历史叙述之间的差异实属需要,但如若放置在比较的框架中(无论是系统间比较、系统内比较,还是一个系统内子集和另一个系统的比较),就可以在对一段历史关系进行精细叙述的同时,再加入更多的可比较案例,从而将具有地方特性的历史特例抽象为具有通则性解释的历史机制,以修正或验证其他的叙述和假设。
第二,历史社会学更加关注历史行动者如何思考与回应他们所嵌入的时代环境,而不仅仅停留在去探究外在于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因果联结。 在历史分析中,宏大的现代性议题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关注国家权力和个体生命历程的互动,关切具体的人在历史情境下的生命叙事。 换言之,我们处理和面对的,是带有情感而行动的人,因此所有的社会行动,都不能抽离开行动者身处的意义世界。 在这个脉络之下,对“国家”“社会”“个体”“身份”等概念的界定,也都必须扎根于历史情境之中,而不能理所当然地视之为“先验”或“普遍”的观念。
第三,历史社会学更加强调事件序列性和历史偶变性的重要意义。 历史并非“冻结”在那里等待普遍理论去检定,相反,历史是流动的、非线性发展的。 按照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的说法,是在时间向度上由一系列“事件”串联在一起的历史过程①Andrew Abbott, “From Causes to Events: Notes on Narrative Positivism,”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20(4), 1992.,这一过程里包含了诸如诞生、死亡、融合、分裂之类的“联结的普遍类型”(generic types of links)②Andrew Abbott, “What Do Cases Do: Some Notes on Activity in Sociological Analyses,” Charles C. Ragin and Howard S. Becker,What is a Case?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77.。 在休厄尔的论述中,“事件”也是一个关键的概念,在某个时间点发生的“事件”会影响到之后某个时间点一系列的历史后果。 休厄尔认为,在历史的隧道中会发生各种事情,但这些事情大多反复出现,并伴随着某些固定的社会文化结构,而“事件”则是历史上那些“相对罕见的发生”(rare subclass of happenings),可能具有深刻撼动结构的能力,特别是那些“偶然的、未曾预料的和根本就无法预测的事件,能够破坏或改变历史的最为明显的持久趋势”③William H. Sewell, “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Terrence J. McDonald,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Ann Arbor &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休厄尔就此提出了“事件时间性”(eventful temporality)的概念,通过理解“事件”在时间轴上的起承转合来理解历史跌宕转移的过程。
历史事件的发展历程,往往可以辨识出关键的历史时刻,即“转折点”。 “转折点”是一种叙事概念,因而必须通过以时间序列为基底的叙事分析才能予以发掘和理解④Andrew Abbott, “On the Concept of Turning Point,”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16, 1997.。 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不仅关注历史事件“如何发生”,更加关注该起事件“何时发生”。 换言之,“事件”发生的“时机”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因此需要引入“事件”的过程序列分析⑤严飞:《历史图景的过程事件分析》,《社会学评论》2021 年第4 期。。 “事件”中的种种行动情节,充满着并接与偶连,而它们发生的时空,正是坐落在历史叙事的次序和位置之上。 由于这些行动元素交错在各种复杂的行动事件的网络之中,因此,带着不同问题意识的研究者,即使处理相同的历史“事件”,也必然不会涵纳相同的行动元素,做出统一性的分析⑥Larry J. Griffin,“Temporality, Event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20(4), 1992.。
下面以暴力这一个经典的研究对象作为案例,来具体看看历史社会学的实践思路。 我们在尝试将历史叙事和社会机制进行整合时,提出如下三个框架性问题。
首先,到底什么是暴力? 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Violence:AMicro-Sociology)一书中曾如此定义:“暴力分为许多种,有些短促而偶然,如一记耳光;有些大型且计划周详,如一场战争。”⑦兰德尔·柯林斯:《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1 页。换言之,暴力既有宏观层面上激进式的变革,如追求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内战、叛乱或者革命运动,也有微观层面上人们的日常冲突,如日常街坊邻居之间的口角之争或者民众之间的械斗。 尽管历史上的暴力发生多如牛毛,但不可否认的是,暴力源自于社会宏观层面的社会制度、文化环境和社会微观层面的人际互动的共同作用。 暴力还源自于地理时间的影响。 地理时间这一概念来自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对16 世纪后半期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考察,他将地理时间界定为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史,并指出长时段的地理环境结构性地制约着人类历史的深层发展①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1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8 页。。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理论作为一种历史叙事视角,对后世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譬如,薛刚的《山川分布、区域性集体暴力与军事动员》一文,从空间历史的角度描绘了暴力产生的长时段根源②薛刚:《山川分布、区域性集体暴力与军事动员——从地理时间理解近代中国的战争与历史格局》,《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 年第3 期。。 明代中期以后,因为一些从北美移植来的农作物的广泛种植,加上人口的迁移,产生了高暴力地区和低暴力地区的差异。 从地理山川的分布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远山和丘陵的高暴力地区孕育出高暴力人群,且慢慢地将暴力外溢到滨水和平原的低暴力地区,并最终形塑出近代中国地方暴力集团的差异性发展脉络,还原出特定时段的暴力实践以及对近代中国的战争所带来的深远历史影响。
如果把暴力当作一个因变量,那么如何去测量暴力,就有很多不同的分析模型,到底是死亡人数的多少(即暴力的程度)? 冲突爆发的次数(即暴力的频次)? 还是暴力所产生的破坏力度(即暴力的影响)? 过往学者在研究暴力时,因为历史数据的限制,一般会选择两个指标对暴力进行测量。 第一个指标是社会波动、政治运动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这一个数据可以从县志、府志的记载中获取,并且可以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测量其差异性。 第二个指标则是财政收入的增减,以测量暴力事件对社会发展的破坏性影响。 这一个数据也是相对来说易于从统计资料中获取的,并且也和第一个指标会有很深的关联。
其次,暴力是如何产生的? 是由结构性的社会因素外生出来的,还是在历史事件动态发展的情境中逐渐内生出来的? 从结构性的分析角度出发,解释暴力的主要自变量,是诸如阶层出身、生产形态、阶级结构、城市化进程等长时段的静态变量。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第一部著作《旺代》(TheVendée)就是一个典型的结构性分析代表③Charles Tilly,The Vendée,Cambridge &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旺代位于法国西部,当1789 年巴黎大革命的影响波及该地区时,当地发生了规模庞大的农民暴力叛乱。 蒂利认为,18 世纪后期法国城市化进程影响下的社会结构差异是导致叛乱发生的最直接原因:那些完全实现城市化的地区可以更好地适应大革命所带来的中央集权式的资产阶级政权,而那些不完全城市化的地区,由于其社会组织极不统一,因而当大革命后的权力分配流向城市资产阶级时,导致社会出现结构性的紧张,在现有权力结构中被边缘化的群体发起挑战,从而引发了规模庞大的叛乱。 但是仅有基于变量的结构性分析还不足够,会缺少历史的叙事细节,因此还需要加入“事件时间性”的框架。 从事件过程的分析角度出发,对暴力的解释会更加强调微观过程、文化意义和行动者的能动性,强调历史情境的偶变性对行动者的选择和行为的影响。 特别是在改变历史进程的那些重要时刻里,当个体为了应对情境中的冲突性紧张与恐惧时,群体和群体之间、群体内部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化和再组合,从而导致人们构建出新的对立性的身份认同,并相应采取一系列暴力性策略和行为,仿若走入一条“暴力的隧道”。 正如兰德尔·柯林斯所言:“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情境。”④兰德尔·柯林斯:《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第2 页。
再次,暴力是如何扩散的? 是从高暴力地区自上而下俯冲外溢到低暴力地区,还是如同一颗石子投到水里,慢慢地荡漾出一圈一圈的波纹? 历史社会学者常常会把暴力浪潮或者其他的过失性斗争和一些自然现象,比如野火、雪崩、瘟疫联系起来。 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描绘的正是暴力扩散的特质:在不断跌宕翻转的历史事件中,身处事件之中的每一个个体的行为都会影响到其他人的选择。 迈克尔·比格斯(Michael Biggs)曾用森林火灾来类比冲突性事件的扩散模式:在一片森林当中,每一小块区域都会有三种不同的状态——有树、没有树、有一棵正在燃烧的树。 当树木不断地被种植并绵延成片,可燃性材料就会不断堆积,而一旦有一点火星掉落到森林之中,那么与它邻近的区域中是否有树木,成了这一点火星是消失还是燃起森林大火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暴力浪潮和类似的冲突性事件中,这一点火星源自于暴力运动的参与者是否受到正向激励,推动他们更深度地参与到暴力之中,并不断感染并动员起更多的旁观者或者低密度参与者,从而导致暴力的规模和程度不断扩大和加深①Michael Biggs, “Strikes as Forest Fires: Chicago and Pari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10(6), 2005.。 正向激励又包含两大重要机制,分别是相互依赖和相互鼓舞②Michael Biggs, “Positive Feedback in Collective Mobilization: The American Strike Wave of 1886,”Theory and Society,32(2), 2003.。 这两个机制具体解释了过失性冲突从小范围现象逐渐变成大范围现象的原因。 伴随着参与到过失性斗争中的人数的增多,人们就会收到越来越多的正向反馈,他们对通过运动获得的期望收益也就越大,进而产生了更多的正向反馈,从而演化成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进程。 相对应地,随着人数的增多,参与过失性斗争的成本降低,类似于“法不责众”的心理作用使得人们更敢于参与到失范行为当中,并且不用担心因为参与而受到惩戒。 其结果是暴力从个人行为变成了大多数人的选择,而不参与则意味着离群、违背群体义务、被抵制,进而使得不参与的成本逐渐升高。
总而言之,历史叙事与机制分析并不是割裂对立的两方,彼此不可融合。 涟漪与年轮,时间是带着不同的纹理相汇,并不断回旋激荡:历史是“社会”在时间序列中的铺展,社会则是“历史”诸事件的制度性表现。 当把社会学的机制分析引入到对历史事件的解释中时,我们不是将一种或者多种社会学理论应用到历史进程的叙述中,又反过来用这一历史进程来论证这些理论的合理性,而是从历史叙事中去探求一般性的抽象机制,在漫长的历史关键节点上细数年轮、解剖纹理,并以之关照现在和未来。 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历史与社会相结合的经验研究,作为连接历史事实和社会科学阐释的桥梁,这也是历史学和社会学进行学科融合交叉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