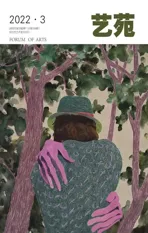从文本到舞台:《荆钗记·见娘》的戏剧性构建
2022-12-16蒋小平
徐 钊 蒋小平
柯丹邱所撰《荆钗记》位列“四大南戏”之首,其流传刊本较多、观演颇盛,在万历时期便翻用昆腔演唱成为戏班的基本家底。[1]42因观众要求演员唱念与文本一字不脱,明末越中还有“全荆钗”之名。[2]71清康熙三十三年闻正堂刻《缀白裘全集》“元集”收有《荆钗记·见母》,至乾隆二十九年《时兴雅调缀白裘新集初编》“见母”改称“见娘”并沿用至今。一段时期以来,《荆钗记》以《见娘》演唱独盛,如今成为了昆剧官生家门的“看家戏”。诚如康保成所言: “‘戏剧’是一个种概念,‘戏曲’是一个属概念,戏曲应该具备戏剧的基本属性即戏剧性。”[3]36“戏剧性”集中体现了戏剧艺术的审美特征。本文选取《见娘》这一搬演至今的折目为考察对象,主要以《六十种曲》本(以下简称《六》本)和《审音鉴古录》本 (以下简称《审》本)为例,综合文本和场上论述该出的戏剧性构建,归纳其成为经典之因,进而思考戏曲艺术戏剧性与抒情性二者的关系,以期对当代戏曲编剧创作有所启示。
一、《六》本《荆钗记·见母》
《六十种曲》是历代普及广影响大的戏曲读本之一,选录的多为当时剧坛流行的剧目。虽然《六》本《荆钗记》和贴近古本的姑苏叶氏刻本《王状元荆钗记》二者结局、关目各有不同,但以上对研究《见母》并无影响。通过比较上述两版《见母》文本,笔者发现《六》本《见母》通过拆分情节和删减丑脚初步提升了姑苏叶氏刻本《见母》的戏剧性。总体看来,《六》本《见母》的戏剧性构建主要集中在戏剧冲突的设置、戏剧技巧和表现手法的使用两方面。
(一)戏剧冲突的设置
谭霈生认为戏剧情境“是促使人物产生特有动作的客观条件,是戏剧冲突爆发和发展的契机,是戏剧情节的基础”[4]117。首先《见母》设置了能在戏中产生持续影响的事件,即玉莲投江身亡之事。《祭江》一出为王母和李成在《见母》中隐瞒真相的戏剧行动埋下伏笔,王母以【风入松】点出不忍十朋知道玉莲投江之事,李成建议隐瞒,“决不要使惊疑”也成为二人在《见母》中的首要任务。其次《见母》的内部空间环境为行馆。行馆在剧中只是承担剧情发展的客观空间环境,但从对比手法来看,十朋登科及第实现了“广寒宫必攀仙桂”的目标,当他期待家眷到来一同赴任、实现“赠母封妻”的理想之时,象征“金榜题名”“白衣到官身”的行馆空间迎来的却是玉莲投江之事,自然产生悲喜的巨大反差。时间和地点的统一也为情节叙事提供了支撑。最后,王母和李成隐瞒真相含悲上场与十朋的追问形成了一组特殊的人物关系。十朋留心推敲细细追问时,尽管王母和李成都努力克制心中苦痛,但总会在不经意间露出疑点。王母下意识流露的悲伤信号使十朋心中疑虑加重,场上气氛在三人来回对抗间变得紧张。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基于人物性格不同而产生,在三人交锋中得到展现,其间真实而深刻的人物性格也蕴涵着动人力量。
戏剧情境的设立为内外冲突开展提供了便利。一方面剧中三人皆具有强烈的内心冲突,并借由一系列的戏剧动作呈现。以十朋和李成、王母的见面为例,十朋先见到李成:“老安人小姐来了?”其不见玉莲身影,以“背问末介”暂避母亲继续追问,然而李成也只能含糊应答。尽管十朋早生疑惑,但此时母亲已在眼前,其恪守孝道以母为尊便先展开“拜母”的戏剧动作,王母也以“问儿”的行动中止了十朋的“追问”。三人各怀心事,外部动作成功地将其内心动机和情感状态揭示而出。另一方面该出设置了两组外部冲突,一是十朋和李成、王母的冲突,二是王母和十朋的冲突。前者围绕玉莲不至这一核心事件由【刮鼓令】四曲展开,人物情绪层层递进将剧情推近高潮。后者冲突产生的前提是王母认为十朋写了休书。及至二人冲突解决,十朋未写休书的真相水落石出,但王母想要隐瞒的玉莲投江之事却被揭露。这便给十朋心灵一重击,其以“跌倒介”的戏剧动作暂停了情节发展,强化人物的情感状态并在主曲【江儿水】中达到全出情感的高潮。
要之,《见母》内外冲突在具体情境中交融推进,最后以凝结在孝头髻上的悬念激化。这一过程中,十朋、王母和李成行动目的明确,又让冲突发展的具体过程直观化,表现为情节的一波三折,也呈现出动人的人物形象:王十朋对母尽孝、对妻钟情,王母严慈和李成忠厚机敏。从内外冲突的交融推进中也可见戏曲艺术叙事与抒情的融合统一。
(二)戏剧技巧和表现手法的使用
李渔曾言“戏法无真假,戏文无工拙,只是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戏法、好戏文”[5]312,可见其对悬念的肯定。悬念也是《见母》最突出的戏剧技巧,包括蕴含在孝头髻中玉莲投江的悬念和被改家书的悬念。一方面王母进状元行馆之前经李成提醒袖藏孝头髻,这时埋下了凝结在孝头髻上全出最大的悬念。看似以王母袖藏孝头髻的行动解决了危机,实则又让危机埋伏身边。悬念的发展始终建立在人物关系上,在面临被揭开和被压制的来回对抗中积蓄了力量。直至关键处剧作运用巧合,即象征死亡的孝头髻从王母袖中掉落。十朋“发现”孝头髻便猜到“儿媳妇丧幽冥”之事,王母至此才将真相和盘托出,直诉十朋之错同时包含了无奈之叹,孝头髻也成为该出关键道具。
发现和突转打破三人僵局,高潮随之而来,家书被改的悬念也随着玉莲身亡悬念的解开被消解。十朋期盼妻子到来的愿望在此刻被摧毁,戏剧情节直转而下。他先以一声“兀的不是痛杀我也”直抒伤恸,接着用“跌到介”的戏剧动作外化痛之深重。突转由此制造了一个连锁反应:玉莲身亡揭露——十朋悲痛倒地——王母伤怀哭儿。王母以【江儿水】表达害怕十朋伤心过度最终留下“年华衰暮,风烛不定,死也不着一所坟墓”的孤零一身,实现了从最初“训子”到“怜子”以及顾虑自身生存境况的真实心境转化。可见,人物情感的细腻塑造亦使人物形象趋向立体化。
另一方面对比手法在剧中使用频繁。整体来看,母子相逢本应喜乐却因丧妻变得悲痛,蕴含着极强的悲喜对比,这也奠定了该出的总基调。从细节看,曲辞创作、人物塑造等方面亦包含对比手法。如十朋和王母上场引内涵各有不同。十朋的上场唱:“一幅鸾笺飞报喜,垂白母料已知之。日渐过期,人何不至,心下转添萦系。”[6]96其中既有寄书报信之欣喜,又传递出对家眷不至的牵挂。王母上场则以“死别生离”“万种孤恓”直抒凄凉心境,饱含丧媳之痛、离家之悲,还有路途艰辛之叹。十朋和王母心境不同,用语自是不同,以上足见对比塑造人物的手法。也正因开场引子散板演唱的舒缓,才更凸显其后十朋追问玉莲之事的紧张情状。【前引】唱毕王母念出“闻说京师锦绣邦,果然风景异他乡”,李成接念“红楼翠馆笙歌沸,柳陌花街兰麝香”。一切景语皆情语,四句诗也蕴涵着京师与故乡的对比、盛景与哀情的对比。此外,谐音手法的使用亦使该出别具机趣,并主要体现在【刮鼓令】第三支。
李成面对十朋的追问虽以背躬唱出“若说起投江一事,恐唬得恩官心战惊”,但“惊”字仍被十朋听见,其紧接着问“说甚么惊字”,李成便以“曾经”的“经”机智应答,既弥补先前语言上的疏漏,又回答了十朋的追问,化险为夷。此处也存在反复铺陈的手法,以十朋四次追问和李成四次回答强化人物的情感力量。
二、《审》本《荆钗记·见娘》
刊印于道光十四年的《审音鉴古录》以丰富的舞台提示反映着乾、嘉之际昆剧折子戏演出的艺术水平。《审》本《见娘》与《六》本《见母》情节大体一致,改动之处一是关目名称的通俗化;二是《审》本在《六》本的基础上增改宾白、删去李成所唱【江儿水】第三支;三是折子戏的演出形式让艺人更关注人物的形象塑造和性格刻画,并从宾白分配的细致化和舞台表演的丰富化两方面增强了场上特质。
(一)宾白分配的细致化
宾白在戏曲中主要承担叙事功能,包括对白、独白和以“背躬”为主要形式存在的旁白。《审》本《见娘》通过增加各曲之间的宾白和曲牌内部的宾白使情节发展更加合理化。首先,各曲之间宾白的增加使戏剧情节得以照应、针线绵密。如《六》本《见母》开场十朋唱完上场引后只以独白交代其托承局带回书信又因家眷不至而挂念,《审》本《见娘》在十朋独白结束后还安排副扮院子上场,十朋吩咐院子若家眷到要来及时通报,这便和之后院子通报家眷到来的行动自然衔接,弥补了《六》本院子只在李成打听行馆时出现一次就草草下场的不足。其次,生动且符合人物身份的宾白丰富了人物形象塑造。以李成向仆从打听状元行馆的宾白为例。《六》本此处着墨不多,院子开口说了两句话把李成和王母引入便下场了。《审》本则将原有的两句宾白作了细致化处理:
(末)嗄,门上有人么?(副上)什么人?(末曲身问科)请了。(副直胸答介)唔,请。(末)借问一声。(副)问什么?(末)这里可是王状元的行寓?(副似欺式)正是。你问他怎么?(末挺身朗言恃势科)通报,家眷到了。(副惊鞠腰堆趣奉迎状)嗄,家眷到了!(末响应介)正是。(副慌恭手急退进式)请少待。老爷有请。[7]288-289
以上抓住李成询问院子的细节,增加院子和李成的互动,以及院子在知道李成家眷身份前后不同动作的对比和语气变化,让院子的形象愈加生动,李成和院子谐趣的肢体动作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剂了之前场上沉郁的气氛。
最后,《审》本下场宾白不同于《六》本中十朋因身伴无人让李成相伴赴任后再修书带回,一是十朋要接岳父母前来同享荣华,突出其孝义形象;二是补充十朋询问玉莲灵柩之事,在得知玉莲尸身无处打捞后又添伤心。《审》本下场以转折延宕十朋悲伤的情绪,也使全出基调统一起来。
除上述各曲之间的宾白增加外,《审》本曲牌内部宾白增加的现象尤为明显。如【刮鼓令】第一支,《六》本该曲内部仅有“娘”“李成舅”“我的娘”“你媳妇呵”四处带白和李成一句“小姐且是尽心侍奉”;而《审》本该曲八句曲词均被大量宾白隔开,尤其在第四句“又缘何愁闷萦”和第五句“莫不是我家荆”之间还插入一段十朋向李成询问母亲为何不乐的情节。曲牌内部宾白的增加对戏剧性构建起到了三点作用:其一宾白隔开曲文又与曲文相互参照,利于观众理解曲文含义;其二富于动作性的宾白使场上人物联系更加紧密,十朋、王母和李成的人物关系和情感色彩也随着宾白的推进不断变化、发展;其三简洁有力的宾白丰富了曲牌体戏曲的叙事性,同时以宾白引发唱段让人物抒情更为自然。再如【前腔】“心中自三省”和【前腔】“当初待起程”两曲内部相较《六》本也增加了大量宾白,后者还通过增补宾白让场上三人一共说出九次“惊”字,而且仅十朋一人就反复抛出了五次“惊”字。九次“惊”字是对《六》本中谐音手法的放大,体现着场上搬演构建戏剧性的独特方法。
(二)舞台表演的丰富化
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尤其程式化动作“不仅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也是创造舞台环境的手段”[4]7。《六》本《见母》一共只有三处“背”和“生悲介”“老旦袖出孝头髻介”“跌倒介”三个戏剧动作,而《审》本《见娘》记录有丰富的科介和表演范式。场上搬演中,科介和表演范式的添加易于放大人物内心情感并能生动地刻画人物关系。以十朋与李成的相见为例, 《审》本中十朋知道家眷到来先是“喜容式”,见到李成后则用“即立起迎科”外化心中喜悦。李成见到十朋欲叩头反被十朋“扶住”,表现出十朋对李成的关切。十朋向李成询问老安人和小姐是否都到了,李成以“呆含糊”回答。十朋“忙趋迎出”以“双跪介”的戏剧动作迎接母亲,“忙”字突出了十朋期盼已久的心情。王母让十朋起身,十朋便“立起退一步深躬”, 再“走上一迎似恭请式”接着“作惊”。以上系列动作,既表现了十朋对母亲的尊重,又描摹出十朋发现玉莲不至的惊疑。十朋再次询问李成,李成以“支吾乱指科”随意答“还在后面”,可见其内心慌乱。这时王母在内唤了一声十朋缓解了李成的危机,十朋只好“带疑进介”。相较《六》本中十朋和李成相见时仅有的两句宾白,以上通过大量科介和表演范式巧妙完成了十朋从喜乐到怀疑的情绪转变,情节发展也富有层次感。
另外,十朋从知道玉莲守节投江到“跌倒介”这部分内容在《审》本中也得到了深化处理。《六》本中王母说到岳母逼嫁玉莲不从后再难说下去,十朋“悲介”让母亲“一发说了”状态偏于冷静。直至母亲说出玉莲投江后接念:“呀!浑家为我守节而亡,兀的不是痛杀我也!”并做出“跌倒介”的动作。《审》本剧情发展至此,十朋正处于急迫想要知道真相的状态。他先“跪近问”母亲,李成阻拦王母说出真相,十朋对李成做“似打式”的动作。王母认为此时不得不说了,李成则“如无措式”。此处三人动作性格明晰,李成虽然在此宾白不多,但也以科介作为陪衬参与情节的发展。在十朋第二次追问下,王母说出玉莲改嫁不从投江之事,十朋以“极声”念出一个“嗄”字。尽管只有一字,其中也包裹着极复杂的情绪。王母紧接着“搀小生手大哭白”,强调玉莲为十朋守节而亡,十朋听罢先做“唬插网巾科” , 再“对正上”念出:“我妻子为我守节而死了,哎呀!”紧接着“顿足、痛心、哽咽、闷死直身跌下”。这里可见十朋跌倒是由内心难以承受的痛苦直接导致,经历了迅速酝酿到爆发的清晰过程,朝着正上,即观众方向:顿足——痛心——哽咽——闷死直身跌下。因其挖掘出人物的真实心境,所以具备很强的感染力。总体而言,《审》本中三人情绪存在明显递进上升的过程,人物内心活动变换急促,宾白科介交错环环相扣,烘托出紧张的舞台气氛,强化了戏剧性。此外《审》本对《六》本中“跌倒介”动作的丰富,或可视为后世戏曲“气椅”程式的雏形。
更值得一提的是,《审》本精准的舞台调度让十朋、王母和李成三人保持了三人鼎足之势,以“鼎足”的关系巧妙刻画人物关系,凝练看点。如开场十朋唱完上场引“转身正坐”居于舞台正中,突出其主体地位,王母和李成上场后十朋则将台中的位置让给母亲,李成的表演区域暂为舞台右侧,舞台之上呈现出“鼎足式”的调度。《审》本的插图也捕捉到“鼎足式”的经典布局:王母和李成相视,一坐一立,而王十朋则背对二人站立。[7]285徐凌云评价《见娘》一出:“演员必须旗鼓相当,铢两(原书作‘钅两’)悉称,才能演好。假使其中任何一角,稍为放松一点,就会影响到其他各个角色,使这出戏松懈下来。”[8]100可见对鼎之“三足”的要求之高。鼎分三足缺一不可,《审》本舞台空间的调度安排注重在场人物之间的配合,留意于细节处刻画人物关系,强化戏剧冲突并从中挖掘戏剧性。如在王母所唱【前腔】“心中自三省”中,十朋夹白问:“你媳妇为何不来呢?”其后便在“哎呀,你媳妇多灾多病”的“媳”字上插入了王母和李成的舞台调度:老旦“右手指出,左手按小生肩。末唬至右上角欲嗽,右手低摇呆式。老旦见末点头,即右手搭小生肩附耳唱”[7]292。这里以调度拆分“媳妇”二字,李成提醒王母不要说漏,突显二人的动作配合。调度结束王母才唱出“妇多灾多病”五个字,这时李成“即对右撲手,喜状点头白”说:“好,这句解说得好!”十朋随即向李成询问小姐病体如何,李成“强笑式”应答病体好了,十朋才放心也有点喜色。王母则接续唱出“况亲家两鬓星,家务事要支撑”解释玉莲不至的问题。此段虽以王母主唱、以王母和十朋的交锋为主,场上仍不忘对李成的刻画,均衡了三人关系的塑造,王母、十朋和李成正如鼎之三足共同撑起一台戏,“故《见娘》虽以官生为主角,实际上乃是一出三角并重的戏”[9]813。总之,该出舞台调度松弛得当,讲究人物表演之间的配合,也使剧情更加扣人心弦。
三、结语
以文本到舞台的视角来考察《见娘》的戏剧性构建,可以清晰地看到折子戏打磨完善的动态过程。毛晋《六十种曲》虽题为“绣刻演剧”,选录的也是当时盛行舞台的剧目,但与之后戏曲舞台首部导演学著作《审音鉴古录》相比,难免流露出“文学本”的气质。或可以说,《六》本《见母》相较贴近古本的姑苏叶氏刻本《见母》而言,已经完成了一次案头到场上的转变,凭借关键的情节安排、精彩的细节描写和动人的人物刻画,为后世能将其提炼成折子戏奠定了基础。乾嘉时期昆剧折子戏演出兴盛,观众的观戏趣味转向艺人的表演技艺,艺人对表演艺术的精益求精以及舞台实践的磨练也进一步丰富了《见娘》的排场,《审》本《见娘》也实现了以表演为中心的戏剧性提升。《审》本为后世继承昆剧表演艺术的“乾嘉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昆剧在唱腔音乐和身段表演等方面都有规范留存,加之注重表演艺术的师承延续,尽管昆剧舞台演出的《见娘》会有些微变化,但仍不出《审》本的框架。
徐凌云的《昆剧表演一得》身段谱第一集中的《见娘》详细记录了穿关砌末、面部表情、身段动作和舞台调度,还触及在表演过程中对人物塑造的体会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其中不乏有对《审》本继承和发展之处,最为可贵的是该版记录了锣鼓音乐。场上搬演中,锣鼓音乐能起到衔接宾白、唱词以及放大人物情感的作用,锣鼓的轻重缓急便于直接营造不同的场上气氛,亦与戏剧情境相呼应,利于戏剧情节的推进和戏剧冲突的展开。以当代昆剧舞台演出的《见娘》(1)为例,其中【刮鼓令】第二支演员在“媳妇”的“媳”字上稍作停顿,又加上“小锣一记”凸显停顿。又如【刮鼓令】第四支的三、四句前有句念白“啊呀亲娘嗄”,演员在念“啊”字时场上先起“小锣叫头”承接至散板“啊呀亲娘啊”一句,散板结束后立即起“小锣急尖”,王母接白:“儿啊!”十朋唱:“把就里分明说破,免孩儿疑虑生。”唱毕场上又起“小锣抽头”烘托紧张的氛围,放大人物内心的焦灼。再如当十朋发现孝头绳掉落后“场上先打四记,起唤板(勺勺勺)”,十朋念完“啊呀母亲”,念毕又打了三记锣[8]109,借此为即将迎来的戏剧高潮阶段造势。可见,锣鼓音乐在辅助达成节奏化和韵律美的戏曲表演的同时也提升了戏剧性。
综上所述,可见该出精彩并能流传后世的原因有三:一是曲牌选用与情节贴合,借助戏剧技巧和表现手法的巧妙运用,使剧情色彩丰富、别具机趣;二是塑造了特殊的人物关系,刻画了独特的人物性格,充分展现出不同行当的特长;三是在叙事与抒情的融通中传递出动人的力量,尤其剧中十朋的情感细腻多变,可分为期盼——怀疑——悲痛——怅惘四个阶段。从文本到舞台的过程中,一方面表现出了以曲牌抒情性书写为主到注重综合场上搬演的多种元素来强化戏剧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则通过添补宾白弥补叙事之不足和丰富表演技艺来凝练看点。由此可见,戏曲艺术从来不仅仅追求抒情性,经典传世之作应是戏剧性与抒情性的统一。戏剧性的提升亦有助于抒情性的表达,人物的抒情也更能产生撼动人心的效果,《见娘》一出即是如此。
注释:
(1)《昆曲艺术大典》(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音像集成·录像选汇”江苏省苏州昆剧院1987年演出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