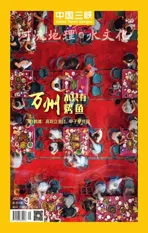诗与日常
2022-11-29栏目主持任红编辑王旭辉
栏目主持/任红 编辑/王旭辉
我们往往为生存所累,难得有时间去仔细观察我们周遭的世界,其实,诗意一直在我们眼前。比如,那些行人熙攘的街道,傍晚逐步亮起的路灯,路边一闪即逝的绿化树,乌鸫起飞时脚爪蜷缩的姿态……脚步暂停,万物是如此新鲜,而我们,只需换一种眼光去看。
威廉斯的影子

《帕特森》 2016导演:吉姆·贾木许编剧:吉姆·贾木许主演:亚当·德赖弗/格什菲·法拉哈尼 等
威廉·卡洛·威廉斯,是美国后现代诗歌鼻祖,美国主要的几个诗歌流派,如自白派、垮掉派、黑山派、纽约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威廉斯的影响。比起威廉斯在诗歌上的成就和影响力,他的生活却谈不上精彩。他的职业是儿科医生,一生以行医为生,只是在业余时间才从事诗歌创作。要给这样的诗人拍一部电影,难免沉闷枯燥。没有人愿意坐在电影院里,只为观赏诗人威廉斯给孩子看病,然后在工作间隙匆匆拿起稿纸奋笔疾书。那么,如何另辟蹊径,拍出真正的诗人电影呢?导演吉姆·贾木许取材于威廉·卡洛·威廉斯的长诗集《帕特森》的同名电影《帕特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是一部诗人电影,但却并非是一部记录诗人生平的传记片。电影描述了一个名叫帕特森的公交车司机在帕特森小镇上的生活。这位公交车司机是一位诗人,他在每天开公交车的间隙写诗,当他行走在大街小巷之时,他也用一种诗人的眼光来打量这座小城。下班后,他像其他人一样去家附近的酒吧喝一杯,然后和女友亲热。循环往复,日复一日。当然,他也是个随时会迸发灵感的诗人,每当灵感来临,他常常会摊开一张纸写下诗行。这些诗歌大多出自威廉斯的笔下,另外一些诗歌则是仿照威廉斯的风格写成。威廉斯曾有一个著名的诗歌观念:不要观念,只在事物之中。电影中的帕特森从精神到肉体都在践行着这一观念。相比他那喜欢寻找新鲜感的女友,帕特森不仅可以忍受生活的周而复始,甚至可以自得其乐,活在一种充实的人生状态里面。作为诗人,他也不想出版自己的诗歌,不想让更多人看到它们。而当他终于答应女友出版诗集后,诗集却出人意料的被他的狗撕毁了。帕特森的世俗成功之路就此夭折。不过,作为诗人的帕特森对于生活的本质依旧充满着智性的认知:“那些只是词语而已,写于水上转瞬即逝。”在诗集被撕毁的那个周日早上,帕特森独自起床,默默离开女友,在书房里的一排诗集中,他拿出的正是《威廉斯早期作品集》。
对很多人而言,诗意就如同俄罗斯导演塔可夫斯基或者希腊导演安哲罗普罗斯那样的关于民族、乡愁、记忆的宏大叙事。《帕特森》是一部诗意电影,不过,它的“诗意”与那些飘忽的长镜头、风景片以及巨大的精神性不搭边儿,其诗意诠释带有不着痕迹、漫不经心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其迷人之处在于对“诗意”电影的日常解构。在《帕特森》这部电影里,日常的很多东西都超越了本身的圈囿,依靠着诗人的眼光而呈现出了诗意的本质。
这份独特的诗意诠释方式,来源于对威廉斯的长诗集《帕特森》的取材。这部诗集共计6卷,以散文和诗体两种文体相互交错的形式,将诗人威廉斯一生生活的新泽西州帕特森市,作为一个能够承载他诗歌抱负和雄心的载体进行书写。其中的散文部分,事无巨细地描写了帕特森小城的大小事件。有学者怀疑其中的诗句“说吧!事物之外,没有思想。/帕特森先生已离开,/去休息和写作。在公共汽车,有人看到/他的思绪坐着、站着。他的/思绪飞落,散开——”带给了贾木许灵感,从而创作了这部诗意电影《帕特森》。可以说,这部电影与诗集的美学内核是相同的。
在影片的结尾,帕特森照常走出家门,他经过的仍旧是熟悉的大街小巷。当他在公园的瀑布前坐下时,一位日本诗人走来,与他一同观瀑。两人谈到了威廉斯,又谈到了纽约派的奥哈拉和金斯堡。这是一段文学上的沟通,两个人因拥有共同的阅读经历而成为了短暂的知己。临行时,这位来帕特森市朝拜威廉斯的日本诗人赠给帕特森一本空白的日记本,于是他又开始写起了诗。
是的,生活周而复始地行使着它的审判,但是诗人也能以他自身的有限方式进行着有力的反抗:写作。“你是诗人吗?”“不,我只是一名公交车司机。”电影结尾,两位诗人的这段对谈,在道出了诗歌与日常的关系的同时,也向我们贡献了一部风格独特的诗人电影。
抚摸日常

《悲伤或永生:韩东四十年诗选 》 2022韩东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雅众文化
虽然韩东身上的标签和桂冠众多,但是我个人却很不喜欢去通过某个所谓的标签来理解这样一个诗人。在我眼里,韩东的写作本身,要远比“第三代诗人”“先锋写作”“口语写作”甚至韩东自己曾经提出过的著名观念“诗到语言为止”更加重要。这本《悲伤或永生:韩东四十年诗选1982-2022》是韩东四十年创作的一个总结,我想有心的读者是可以通过这样一本书来建立起他们自己心目中韩东的形象。
记得多年前看NBA 的时候,听到解说员说,建议才开始打篮球的年轻朋友们少看詹姆斯、科比、艾弗森这样动不动就飞天遁地的运动员打球,多看看像邓肯、基德这样的球员打球,因为初学者从他们的打球方式中能学到更多的东西。我想韩东也是一名这样的诗人,以至于多年以来,我也经常向刚开始接触现代诗的朋友推荐韩东的诗。有时候觉得学习写诗其实和学习打篮球很像,像詹姆斯那样动不动就隔着两名内线暴扣的打球方式是“不可学的”,而像邓肯的内线基本功,阿兰·休斯顿的投篮手型这些则是“可学的”。当然,我不认为“可学的”和“浅显”是一回事,相反,它可能更需要一种另外的天赋,一种“显性”天赋以外的天赋。
我经常和诗人朋友们在私下里讨论韩东的诗,抛开我们各自的审美趣味不谈,我们都一致认为韩东可能是国内当代最冷静的几个诗歌写作者之一,也就是说,韩东太清楚自己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韩东曾说过,他追求一种“跌到高处”的写作,或者说是一种“在自己的水平线以下写”的写作。从韩东的写作题材,我们应该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韩东是如何将自己的写作付诸于行动的。韩东最常写的题材就是“日常”,而且还是用一种精心提炼过的“日常语言”来写“日常生活”。在韩东的笔下,“日常”是“去矫饰性”的,同时还是“可感”也是“可触”的。如果没有足够好的技艺,是很难做到像韩东这样能够如此精准的在“日常”中提取事物的核心的。当然,说到“诗艺”,其实很多人对“诗歌的技艺”都有着误会。主要的误会来自于很多人会误以为“诗艺”是一种修辞学层面上的技艺,从而忽视了心智方面的技艺。有一类写作者,手上的“活儿”似乎很漂亮,可一旦结合自己的经验和认知,就会显得很分裂;还有一类写作者,谈写作观念谈得非常透彻,但一旦落实到自己的写作上就一塌糊涂。而韩东的价值以及他的重要性,在我看来不仅是源于他是当代最早的一批完全使用提炼过的日常口语来抒写日常经验的诗人,也在于他是当代,把观念和写作结合的最好几个诗人之一。
曾经听过某个诗歌批评家批评过国内当代诗歌里“唯脑”式的写作和“唯心”式的写作。从诗歌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唯脑”还是“唯心”,一旦玩过了头,都很容易极端化,使诗歌失去应有的平衡。而在韩东的诗里,我们很难见到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失衡”的写作。以这本《悲伤或永生》为例,里面的每一首诗都感觉像是一件件的器物,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几乎挑不出什么硬伤。我想,韩东的写作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也和他对诗歌里的“手”的使用有关。韩东曾经说过,“写作过程中尽量让你的手去思考,头脑的工作尽量消极。”我们知道,“手”作为人体一个部位,手的距离,无论是离“脑”,还是离“心”,都是相近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手”是“脑”和“心”之间的一座桥梁。从表面上看,“手”看上去远没有“脑”和“心”那么复杂,那么高大上,但是“手”又是诚实的,因为“手”每天都要和现实产生无数次的抚摸和碰撞。韩东的诗,既是一门日常语言的艺术,同时还是一门“抚摸”的手艺。在这里,我指的“手艺”,是把“手”和“艺”分开的。我想,细心的读者或许能发现,在韩东的相当一部分作品里,“手”是永远“在场”的。我甚至认为,韩东的一系列写“手”的诗,像《工人的手》《一摸就亮》《抚摸》等作品比他的成名作《你见过大海》更能展现出韩东诗歌中对日常经验的抚摸之美。我们知道, 诗歌语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充满了“对抗性”的,以至于到朦胧诗时期,这种“对抗性”都丝毫没有减弱。而韩东的诗歌写作和他的前辈们相比,一个很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在具体的写作中,减缓和减弱了这种“对抗性”,尤其是在近些年,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韩东的诗歌越来越像一双抚摸日常的手,以至于我们如果只读他后来的作品,甚至会忘掉这双手曾经也有过“拳头”的一面。

流俗地里有天光

《流俗地》 2021[马来西亚] 黎紫书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锡都的无线德士电台,盲女银霞在电话里认出失踪已久的大辉的声音,故事就从这样一个宿命般的场景开始。仿佛是谜团的开端,引出种种前缘。《流俗地》是黎紫书继《告别的年代》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极具小说形式感的探索,充满叙事技巧和实验气息,四个杜丽安的故事串联起几代女性的命运。此外,历史的想象、国族的寓言,这些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脱离不开的符号仍若隐若现地附着在故事中。而在暌违十年的《流俗地》中,黎紫书采用了一种更为现实、传统的小说叙述方式去讲述一个盲女和一座城市的故事,沉重的历史与种族问题隐于故事的背后,不再成为枷锁,脱离某种技巧并没有使她的小说失去吸引力,反而显示出对故事的更多自信,也显示出“形式”之外更加强大的叙事功力。
黎紫书是马来西亚作家,不同于黄锦树、张贵兴等前辈笔下蕉风椰雨的雨林传奇,黎紫书聚焦的一直是她的家乡怡保——即《流俗地》中的锡都。这座因锡矿而闻名的城市吸引了大量华人,他们是城市的底层,为生存奔忙,卑微如尘,又都有各自的悲欢。
流俗地是市井之地,故事中的人们居住在近打组屋,黎紫书形容这里是坊间草民众生的寄居之所:“人们莫不是因为潦倒,住不起像样的房子,人生被逼到了困境,才会落难似的聚集在那楼里,忍受狭隘的过道和逼仄的居室,因而楼上楼的居民多数抱着寄居的心态,从搬进去的那一日起,便打定主意有一天一定会搬走的;走的那一日也意味着困境已度,人生路上走到了宽敞地,再不需要与同病相怜者相濡以沫。”
作为一个暂居之地,组屋注定要见证住客的分离聚散,人事浮沉。三位主角,银霞、细辉、拉祖是自小一同长大的“铁三角”,都住在这个聚集着各个民族,世俗万象的楼上楼里,听着楼上楼下的家长里短,分享彼此的成长与心事。最苦难的生活里,也有烟火热闹与短暂光亮。小说中有两次写到三人外出,都是手牵手走在路上,亲密无间。对银霞来说,细辉和拉祖或许是她与世界相接的触角,带给彼时身处黑暗世界里的她一丝光亮。银霞第一次感受到“光”便是在拉祖家的理发店里,老化电路的镇流器声音哀哀鼓噪,银霞由此便明白“听到这声音,便是有了光”。
但银霞身上也有着某种“传奇”,莲珠姑姑说她是“眼盲心不盲”,她听觉灵敏,记忆力极强,能背下一整本《大伯公千字文》,还曾背下半本棋谱,同细辉一起与拉祖对弈。后来她成为锡都无线德士电台的接线员,以记忆将锡都的街巷镌刻在脑海里,联络这座城市的南来北往。
可祖屋终究不是能困住他们的鸽子笼,他们于此共同成长,也逐渐分离。拉祖天生聪颖,去更广阔的世界里读书,细辉因为有莲珠姑姑的帮衬,到城里成家立业,银霞也曾有过寻求光明与自由的机会,去盲人学校读书,最后却还是被命运推回组屋的暗室里,独自在黑暗中摸索,迎接未知的前路与坎坷。
后来的每次相聚都以死亡和新生为契机,细辉母亲的葬礼,银霞契父的葬礼、母亲的葬礼,还有细辉的婚礼,莲珠姑姑孩子的满月酒,送走一代人,迎来一代人,悲欢离合,各有天命。作品有许多章节以人物命名,似乎每个人的命运都足以构成一段故事,仔细读来,却是每个人背后都有自己沉重的过往和隐秘的伤痕,有各自的苦难与残酷。
婵娟或许无意致学生死去,但却逃不开冤魂入梦;马票嫂一生机灵洞明,晚年却被衰老困在模糊的时间中挣扎不得。大辉对莲珠的情感隔着亲情人伦,蕙兰父亲的爱与欲则因性别而不敢见于天日,只能领受各自的苦与孤独。银霞眼中最“光明”的拉祖,似乎不负所有人的期望,一路念书,到都城当律师,为穷人出头,未曾料到壮年生命却戛然而止于自家门口。而银霞也在摸索光明路上陷入更深的黑暗中,她在盲人学校时被人性侵,但因看不见,连犯人是谁都无从得知。黎紫书用最悲悯的笔一点点揭开这些潜藏的伤痛,令人得以见人性种种,爱欲,善恶、罪与救赎的复杂与丰富。
序言中说,《流俗地》写的是“现实的有情与无情,人之为人的流俗与不俗”。
儿时拉祖与银霞最喜欢做一问答。
拉祖问:银霞,告诉我,伽尼萨断掉了哪一根象牙?
我当然记得,断了的是右牙。银霞笑。说着举起右掌,举到胸前靠近肩膀处,是为象头神的手印。
断掉的右牙象征伽尼萨为人类做出的牺牲。她说。
一次,拉祖的母亲对银霞说:“所以那些生下来便少了条腿缺了条胳膊啊,或者有什么别的残缺的,必然也曾经在前世为别人牺牲过了。”
冥冥之中仿佛一种象征,银霞的前半生总在摸索光明的路上被迫残缺,而拉祖为了捍卫光明与正义献出了自己的后半生。拉祖的母亲迪蒂普用另一种维度的逻辑解释了他们的命运。在温情与悲悯之外,小说似乎在“匹夫匹妇,似水流年”的故事中写出了一丝神性与慈悲,在俗世的最暗处透出了一抹天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