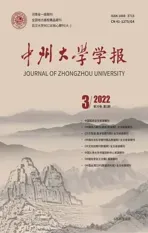兵法与小说叙事的关系(对话)
2022-11-23孙青瑜
墨 白,孙青瑜
(河南省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1)
孙青瑜:近段我重读了历代兵法典籍,发现兵法与艺术之间,尤其在应用学上,二者有不少大道相通之处。
墨白:大凡应用学,都有一个变死法为活术、奇正相生的玄机,从学到用,从用到会用,从会用到致用,不光要下功夫,也需要天赋。
孙青瑜:欧阳修说苏东坡,“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这个“善”字,是功夫,还是天赋?
墨白:前后两个善意思不一样,第一个善是爱,爱读书,属于刻苦好学的功夫;第二个善是会的意思,会用书,属于天赋,二者的关系就像一堆干柴和一根火柴,如果没火星点燃,它们就无法进入能量生成和转化。
孙青瑜:可是,天赋支持不动功夫运化的现象,比比皆是;像四声五呼十三辙的大理儿,可能很多唱家都懂,但同一首词曲,能“度”出“腔到象成,象成情生”者,却寥寥无几。
墨白:在同等努力、同等学养的条件下,什么才能拉开距离?天赋!天赋是一个人化知为用的能力,也就是一个人的创造力。天赋这东西,有时在诗人这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比如法国诗人兰波。兰波14岁那年用拉丁文写了一首60行的诗,寄给拿破仑三世的儿子。兰波18岁那年,诗人魏尔伦26岁,他读了兰波的诗,寄钱给兰波,让他去巴黎。兰波19岁时,出版了《地狱一季》,完成了著名的《彩图集》。但这里不仅是天赋,还有一个诗歌形式的问题。在写作技法与用法的关系里,就存在着“化知为用”。比如像你以前说的口法与润法:口法好学,润法难为。
孙青瑜:对,润法虽然也是法,却不同于口法,它属于用,化知为用的用,怎么化知为用,怎么用好、用妙,就属于天赋才能把握的部分。
墨白:写作也是一样。同一个故事,同一个主题,你写我也写,但写出的层次,肯定会分出高低、远近来。比如兰波的诗歌。兰波的诗歌混合了儿童的怀旧与幻觉,一些诗句还含有麻醉品的影响,他诗歌的忧郁和眩晕标明了整个20世纪的诗歌特征。与兰波同时代的另一个诗人马拉美说,兰波是“艺术史上独特的奇迹。横空出世的一颗流星,毫无目的地照亮自身的存在,转瞬即逝”。他一个19岁的青年,且不说天赋,诗歌的形式从何而来?那肯定是模仿。
孙青瑜:任何艺术都起于模仿,模仿阶段属于功夫,拉开距离的则是应用能力。
墨白:应用能力就是天赋,是感悟,是创造。就像王闿运说的:“诗亦有家数,易模拟,其难亦在于变化。” 这个规律,在艺术家这里很普遍,比如法国画家图卢兹-劳特累克。劳特累克出身贵族,他14岁那年摔断了左腿,第二年又不小心折断了右腿。由于父母近亲通婚,他患有先天性的骨骼疾病,从此他的双腿停止发育,上半身却正常生长,短小的双腿支撑着硕大的上半身,成年后身高仅150厘米,不幸变成了侏儒。劳特累克18岁去巴黎学画,在几年的学习期间,他游遍了巴黎的美术展馆和画廊,结识了凡·高、德加、雷诺阿、马奈等画家。在所有的印象派画家中,他最崇拜的是德加。他把德加作为自己精神上的老师,处处向他学习。这个过程,就是模拟的过程,但艺术的变化,是靠天赋。劳特累克在掌握了绘画的技法之后,他没有像雷诺阿那样画阳光下健康青春的人体,没有像莫奈那样表现光色颤动中的大自然,也没有像凡·高将满腔的热情熔化在色彩和笔触之中,而是专门描写巴黎的“红磨坊”,表现没有贵族只有庶民的社交娱乐场所,他从不粉饰生活,而是用嘲讽夸张的画笔,描写可笑而令人生厌的形象。这种情景,在中国的诗歌里也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
孙青瑜:是,是这样。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与长天一色”,其实借用的是庾信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但是二者表达的境界却天壤之别,原因就是布局陈象的境界不同、格局不同,构成了两重天的景象。
墨白:这就属于天赋,你可以看,古今中外的大艺术家,并没有深学过兵法,但是他们对兵法应用学却有一种天生的把握能力。
孙青瑜:对,可能这就是天赋,王勃对兵法应用和艺术应用之间,好像就有一种天生的变通能力。纵观他的翻写手法,其实都取胜在用象的格局和布局上。比如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也是借用别人的诗,也就是曹植的“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不想被他轻轻一翻,就翻成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翻成了妇孺皆知的名句;由此可见,同样的对仗手法,因为选象的格局不同,用的境界天壤之别。
墨白:这就是死法好学,活法难为。
孙青瑜:嗯,尤其唐朝格律盛兴以后, “抠死法”者更多,甚至有不少诗人词人压根不通音律,没有度曲的基础和能力,只用“格律”抠死字眼,“抠”到最后“抠”的词曲背离,自己还浑然不知。
墨白:学以致用,需要天赋,也需要知识,二者都具备了,学与用之间还有一个化知为用的过程,才能达到熟能生巧。如果压根就没有化用生巧的基础知识,肯定无从化用,更无从生巧。
孙青瑜:确实。
墨白:就像你最初写作时,学你爸(作家孙方友)的“翻三番”,你仅知道“翻三番”真经,却没有化知为用的手上功夫,也是没得番的,一翻就假了,弄巧成拙。“巧”不好营造,要巧到大巧无痕,才是真巧,巧后得妙,才是真妙。巧若过了头,妙没得到却适得其反,这需要真功夫,需要长期的写作实践与感悟。
孙青瑜:我初习作时,就是您说的这种只知其技,却没有化知道为用到的手上功夫。但是慢慢地,从体用关系上我也算是变相取到了真经,虽然这些经验功夫没能用在小说创作上,却在美学和哲学上,给了我灵感。
墨白:在小说创作上,你是受你爸的影响。其实,在哲学与美学上,你爸也影响了你,尤其是美学应用分析这一块。你爸多年的创作经验和叙事技法,对你在美学上的探索,起着引导作用。但更重要的还是你自己的艺术实践,多年来,你刻苦读书,在艺术经验、艺术认知上,都有自己独到的悟道;这一点,虽然我还没有读到你新修的中国哲学史,但在《存在与神经:点域认知论》里,都已证明了这一点。
孙青瑜:在美学上,我特别重视应用美学理论;因为我觉得理论的目的不是为了理论,而是为了致用,是为了道高一尺、技精一丈的致用。所以,我一直在努力挖掘各种艺术的手法,尤其是古老的艺术手法。
墨白:中国传统的叙事艺术,在你爸的《陈州笔记》里随处可见,尤其是这个以巧致妙。巧真不好为,更不易达到。在《陈州笔记》里,小说叙事的翻三番,日臻完美,这一独特的叙事艺术,达到了以巧致妙的境界。其实,你爸的小说叙事里的翻三番,就是运用了兵法理论中的奇正相正,这就是天赋。
孙青瑜:我发现在不同艺术门类的创作里,其实都有一个中庸理论。用我爸的话说,就是奇事、巧事要朝平上写;而平事呢,要朝上奇推,才能达到奇正相生。在艺术应用学上,这奇与正的关系就是兵法学上的用局和谋局的过程。怎么用局和布局,才能达到奇巧不离正,奇以正规之,正要以奇推之?又巧到自然而然?这里首要做的,就是盗尽天机!用局属于盗尽天机,也就是取自然为局,布局属于借自然谋局。
墨白:你爸笔记小说中的翻三番,就属于典型的叙事谋局。
孙青瑜:具体到技法上,我爸说得形象,叫“抽线头”。这个抽线头就是当小说走不动时,回头看看,反复看,看看前面哪个细节可以利用并延展出发展空间;抽线头为“盗尽天机”取自然为局。只有把自然之“局”抽尽了,用尽了,才能展开布局,并把后续的布局与故事“抽”得自然而然,把前面的细节和描述“抽”到笔无废墨。
墨白:《三国演义》里的叙事就属于“抽线头”,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物、每一个背景都“抽”得好,自然而然。
孙青瑜:对,尤其是“草船借箭”和“借东风”两计。
墨白:这两计的主角,罗贯中为什么不选孙权、周瑜,或者曹操、司马懿?
孙青瑜:因为“草船借箭”这一计里涉及天象学问题,而在三国时代的诸多军事家里,只有诸葛亮一人是奇门高人,是高深的天象学家,只有他有能力提前推算到那一天起不起雾,或者说,正是因为诸葛亮是象数大家,才演绎出这两计。
墨白:对,因为在整个三国人物里,只有诸葛亮一个人能够用活“草船借箭”,所以,把这场戏安排在“诸葛亮”身上,那是会“抽”,这根线抽出了艺术真实。你不是说,准备修编兵部吗?
孙青瑜:经您这么一说,我突然发现,《三国演义》虽是一部小说,但在兵法史上的地位,却是举足轻重,这就像医理和临床应用学,律数与古琴弹奏,美学与艺术创作、数学与自然科学……
墨白:有觉悟。法也好,道也好,理也好,你读过,我也背过,可会不会用?会不会活用?则在人,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天赋,有觉悟。如果你把三十六计背得滚瓜烂熟,不会用或者用不好,那就是纸上谈兵。“随机应变”是用好兵法的前提。机,时机,也就是《鬼谷子七十二术》里所说的“用尽天机”, 只有把时间和局势把握精准了,才能出奇归正。你刚才说的“借东风”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讲的就是时机;有了时机,还要看有没有“出奇制胜”的能力;当然,“时机”是“能力”的基础,只有对时和机都摸透了,才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像“草船借箭”一节。你说,如果这一计取在大晴天、大白天,没有雾,能行得通吗?
孙青瑜:说得对。正是诸葛亮摸透了时机,大清早,赶上雾天,朦朦胧胧的,用几船草人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盗尽天机,属于取自然为局。
墨白:除了善取自然为局,也有善于“布”局的高手。比如刚才我们说的韩信,他就善用布局,不但逼死了项羽,也暗渡了陈仓。
孙青瑜:经典。我看兵部这一节,需要搬您这个老将来替我修。现在抖音上有一个“太极人”,他就善于“布局”,剑走偏锋,一“抖”就“抖”获了百万粉丝。按说,这个人的“太极拳”并不比别人打得好,但他却敢于借“旁门”出奇,利用后期制作把他的太极都“合成”在唯美至极的仙境里,不但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也把太极打出了仙风道骨之气。
墨白:这是聪明人,也算有天赋。
孙青瑜:是。“兵法”好学,但能出奇归正、执中达变者,真是太少了。通过这个“太极人”,我发现,当实力上没有超人之处时,面对诸多同样的专业人,同样的内功,同样的档次,怎么能够在“诸多的同样”里脱颖而出?那就要剑走偏锋,谋“旁门左道”来取胜。这就像《乾坤大略》里讲的:“兵只一道耶?曰:‘不然。’所向既明,则正道在不必言矣。然不得奇道以佐之,则不能取胜。”
墨白:兵法本来就叫诡道,说得好听一点叫巧取,说得不好听,其实就是阴谋诡计。
孙青瑜:嗯,凡兵起必用诡道。诸葛亮在《奇门遁甲统宗》开篇讲:“遁甲为兵而设,为阴象,为诡道。”从《七十二术》到《孙子兵法》,从《武侯八阵》到《三十六计》,都属“阴谋诡计”。
墨白:战争就是这样,你死我活,有法能供巧取,谁愿意傻着脸被消耗实力?所以刘基在《百战奇略》里说:“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但这里还有个用好用不好的问题,像《三国演义》里的人物都学兵法,可用家的层次、结果则不同。关羽之死,以及关羽死后刘备为其复仇,皆属于“智不及而谋大者毁”。
孙青瑜:还有曹操,按说他作为第一个注解《孙子兵法》的专家,应该能斗过诸葛亮,可为什么一直斗不过诸葛亮,原因就是,诸葛亮是用“奇门”演绎《孙子兵法》。
墨白:诸葛亮是演绎,那叫天赋,是创造;曹操是注解《孙子兵法》,那叫匠人。写小说也一样。都读鲁迅,有的人读着读着就读成了作家,有的就只记住了阿Q、孔乙己,记住了茴香豆。小说家也多不相同,有的会写人物,会用情节和细节……
孙青瑜:是,比如施耐庵,就非常会写人物。你看他写的宋江,只要他一听说谁谁落难了,皆是不远万里“雪中送炭”,一次两次,就奇到了假。但受惠者不但不觉得假,还感恩涕零,称其为“及时雨”。这可能就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他利用别人落难时的焦渴和需要,一次次把大假书写成了“无巧不成书”,为宋江日后聚拢“梁山好汉”,铺垫了“合情合理”的一笔;或者说,人落难时普遍的焦渴和需要,就是“及时雨”之所以“及时”的无形布局。
墨白:所以,无巧不成书里的这个巧,也不是瞎巧,这里面有一个艺术真实的问题。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我们明明知道人不能变成甲壳虫,但我们相信这个故事情节,因为《变形记》关照的是人的精神世界,达到了艺术真实。用兵法理论来说,想出奇制胜,首先要把局谋好,才能巧到自然而然,才能巧到顺理成章,奇而归正、奇以致巧致妙,也就是金庸所说的“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否则就巧假了,就失去了艺术真实。
孙青瑜:嗯,我明白了,艺术布局和兵法布局属于同一个道理,能不能达到“奇正相生”的高度,在于用“局”,在于选局、布局,就像写小说一样,要把真实的细节、情节的元素分布好,故事才能达到艺术真实,才能让所借之物与意象浑然一休。
墨白:所以说,一个人用象的能力、选象的能力、布象的能力,决定着他能走多远。比如卡尔维诺《分成两半的子爵》,这篇小说的主题表达,属于非常平的选材,这是西方人人都知道的一个谚语,“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但卡尔维诺就是借用这个人人都知道的大道理,直接展开布局。
孙青瑜:哦,是这样。卡尔维诺用了一个大顺向的思维,开篇便把子爵分成两半,一半极好,一半极坏,达到了出奇归正的效果,获得了艺术真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小说创作上,卡夫卡和卡尔维诺,都是盗尽天机的谋局者;还有我崇拜的卡佛,他的小说也属于这个类型。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是直接利用人们对“陌生环境”的认知能力,截取一个个没头没尾的生活片段,直接布局,用不完整实现了更高意义上的完整,颠覆了“开头、发展、高潮、结尾”的布局模式,更颠覆了我们传统的审美认知的模式。也就是说,卡佛那些无头无尾的片段,其实就是直接利用人掉进陌生环境里的认知能力为局,达到了更高层面的完整。
墨白:对。“抽线头”不一定在文中抽。盗尽天机,不一定只局限在文内。
孙青瑜: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了达达主义,从我们“文以载道”的传统来看,达达派那些无道无技的书写形式,不但是一个非常奇葩的存在,甚至连“画匠派”都不能算。但是从神经心理学来看,它借用文外“陌生化”的现代派潮流,用文不载道,让我们看到了更深的文以载道。
墨白:奇巧要从正出发,还要回到正的怀抱,只有用局用得好,谋局才能奇巧而不离正。换句话说,可以不按套路出牌,但一定要从套路出发,因为规是定好的,所以你爸生前常说:“奇的选材要朝平上靠,平的选材要朝奇上推。奇的选材再推奇就假了,平的选材,再朝平上写,就戏不出彩了。”由此可见,无论是处世,还是从艺、打仗、用药、经商……“法”都不喜老实!
孙青瑜:嗯,“做人要直,从艺要刁”,我爸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当老实人,但是从艺则万万“老实”不得。可是,从艺如何才能做到“不老实”呢?
墨白:只有精诚于奇正相生之术,才能达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孙青瑜:嗯,兵法思维无处不在,不仅在艺术创作里用得着,像经商、为人处事等,也都有兵法思维的存在,甚至兵法的变通和应用能力,几乎影响着你在这些行业里的前途和命运。
(对话时间:2022年4月27日;地点:墨白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