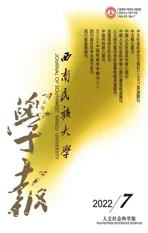送子观音:佛教中国化的生动案例
——以送子观音图像的创造史为例
2022-11-23杜阳光
杜阳光
[提要]送子观音图像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民俗观音画像,是中国人对佛教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典型代表。送子观音图像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隋唐的初创期、宋元的形成期、明清的定型期、近现代的异化期。送子观音图像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既继承了观音信仰的文化传统,又通过不断为其增添具有象征意义的民族文化元素符号,逐步摆脱了印度观音造像文化的桎梏,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送子观音图像。这启示我们,优秀的传统一定是活泼的,为其注入符合时代进步发展要求的元素,可以永葆传统文化的生机活力。
胡适先生曾说:“五、六、七三个世纪为佛教思想‘中国化’时期,‘中国化’者,去其不堪的部分,选择其最精采的部分,以适应中国人士的心理。”[1](P.542)送子观音信仰是佛教中国化最生动的案例之一。印度佛教传统中本无送子观音,只是《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中记载,观音菩萨有“应求男求女”的慈力。在中国重视生育的文化背景下,对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出现送子观音信仰。图像是宗教信仰的重要载体,送子观音图像在其信仰体系中又至为关键。图像学(lconlogy)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形成的一门方法,强调在对艺术作品描述和分类的基础上,结合图像志研究,考察图式意涵,并诠释艺术作品的世界观及时代意义。正如学者柯普-施密特所指出的那样,图像学旨在描述和重建那些因时代变迁而逐渐被遗忘的图像意义,好让人们了解艺术品的实质内容。[2](P.4-5)20世纪80年代,图像学被引入中国,对中国古代的宗教艺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图像学模型构建者欧文·潘诺夫斯基在他的《视觉艺术的意义》一书中提出了图像解读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对图像客观准确的描述,被称为图像前的描述;第二步是认真分析图像,解读图像中各元素符号的内涵意义;第三步是结合相关社会历史背景,积极揭示图像背后的社会思想观念。笔者试着依循这三个步骤,解读历代的送子观音图像,探讨中国人选择了佛教文化中哪些“最精采的部分”,又去掉了哪些“不堪的部分”,探讨其背后的社会思想原因,从而发掘其中佛教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经验。
一、隋唐时期的送子观音图像
在民族文化大融合时期,太康七年(286),高僧竺法护于长安翻译出了《正法华经》,这是《法华经》最早的译本。东晋弘始八年(406),鸠摩罗什也翻译了这部经典,命名为《妙法莲华经》,影响更大。北凉时期鸠摩罗什来华,至河西弘法,恰逢河西王沮渠蒙逊有疾患,鸠摩罗什劝其礼诵观音经,其疾遂愈。沮渠蒙逊遂命将鸠摩罗什所译《妙法华莲经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抽绎出来单独于河西地区流行,此即后世所谓的《观世音经》。[3](P.133c)据考证,在永平元年末(508)就出现了《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摩崖石刻经文及观音刻像,现存于焦作市博爱县青天河北魏摩崖石上。[4](P.39)《妙法莲华经·第二十五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主要宣传称名得度的救难思想,众生若遇各种苦厄灾难,只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菩萨就会寻声救苦,令其解脱。该品经也提到了观音菩萨可以“应求男求女”,即所谓的“应二求”思想。《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云:“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5](P.308)基于此“应二求”思想,观音信仰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送儿送女的生育功能被不断凸显强化,形成了所谓的送子观音。
从敦煌藏经洞文献看,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表现观音菩萨“应二求”的图像,主要是《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变和《观世音经》经变。唐代惠祥《弘赞法华传》记载,竺法护就曾将《正法华经·光世音菩萨普门品》抽绎出来,以《普门品经》或曰《光世音普门品经》的方式单独流传。不过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鸠摩罗什所译的《观世音经》。在敦煌出土遗书中,一卷写经之首往往题作“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廿五”,在末尾往往题写“《观世音经》一卷”。这似乎是暗示人们《观世音经》的合法性来源。从敦煌藏经洞遗书来看,单行本的《普门品经》对观音信仰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现存魏晋至隋唐的众多单行本的《普门品经》就说明了这一点。例如,西印度博物馆藏有北凉神玺三年(399)张施书写的《光世音菩萨普门品》,日本书道博物馆藏有北魏孝昌三年(527)尹波书写的《观世音经》,隋唐时期的写本《观世音经》则更多,不一一枚举。下面,我们考察一下《观世音普门品》和《观世音经》经变中的“应求男求女”图。
(一)“应求男求女”图
莫高窟第303窟,开凿不晚于隋开皇四年(584),在该窟顶部的人字形坡上,依据《观世音普门品》的记载,系统绘制了表现观音现身说法和救苦解难的经变图像。其中人字形坡的东坡上绘有“应求男求女”的经变图像:在山水树木的掩映中,两铺观音盘腿坐于阙形龛,左侧一妇女跪地,双手合十礼拜前面的观音,身后领一男孩;右侧一妇女跪地,双手合十礼拜前面观音,身后领一女孩。莫高窟第420窟约开凿于隋大业年间(605-618),该窟是表现《法华经》经变的洞窟,与第303窟一样,该窟的《观世音普门品》经变像被绘制于覆斗顶形窟顶的东坡上。图中左侧一中年妇女左手牵一童子,右手持花;右侧似一少女左手牵一女童,右手持花。值得注意的是,该窟在表现“应求男求女”经变图时,不像303窟那样表现妇女跪地双手合十向观音礼祷,描绘的似乎是求子成功后的喜悦状态,让人感觉与303窟的图像在有时间上前后衔接之感。
唐代求子的风气非常炽盛,老君、孔子、罗汉、观音等都是时人祷子的祈求对象。目前已知的莫高窟壁画与敦煌遗书中,《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经变图像约有三十余铺。表现“应求男求女”的经变壁画中,以第45窟南壁的最为著名。以往多以为第45窟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变图像为盛唐时期所作,然据近年来学者研究,认为该经变图像为中唐时期所补绘,是一种新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变图像样式。[6](P.19)图中左边站有一成年男子,头戴唐代盛行的软脚幞头,身着圆领窄袖袍服,脚登云头靴,腹下束腰,双手合十于胸前,眼睛微视前面的观音菩萨,显得谦卑虔诚。男子左后方站一垂髫童子,右边方框榜题云:“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图中右边站一个妇女,梳抛家髻,上穿赭色宽袖襦衣,下着绿色长裙,肩披紫色披巾,脚蹬云头锦履,脸颊有描红,头微低垂,似在默默祈祷。妇女后站一个头梳双环髻的女童,右边方框榜题云:“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殖(植)德本,众人爱敬。”可以判定,这幅“应求男求女”是依据《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记载所绘制。
敦煌遗书中,纸质《观世音经》经变图中也有表现“应求男求女”的内容。目前所知的纸质《观世音经》经变,共五卷,都为唐代所作。其中Ch.xxvi.a.009、Ch.xxiv.003为斯坦因所得,为白描本,现藏于大英博物馆。P.4100、P.4513、P.2010为伯希和所得,为彩绘本,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博物馆。这些纸质经变画一般装作册子或卷子,上面绘制《观世音经》所述观音救难或应求的图画,下面配以相应经文,图文并茂,类似于现在的连环画。我们以法国图书馆藏P.2010号为例,分析一下纸质《观世音经》经变图中的“应求男求女”图。图中,观音菩萨头戴化佛冠,上身袒露,斜披络腋,下穿罗裙坐于仰莲台上,披帛自双肩绕臂垂于体侧,颈饰项圈,臂戴腕钏,梳抛家髻,头及鼻嘴斜扭,似在思考;观音左侧跪一双手合十的妇女,上穿宽袖襦衣,下着长裙,梳随云髻,披帛搭双肩绕臂垂于地,表情凝重;妇女左后方分别跪着头梳丱发的童男童女,他们双手合十于胸,显得庄重肃穆。其他四件纸质《观世音经》经变图中“应求男求女”与这件基本一致,应当是按照同一粉本绘制。
(二)隋唐石雕送子观音
《王三娘造像记》记载:“天保元年正月十八日,清信女王三娘为子敬造送子观音像一区(躯),愿我子孙长□,离苦解脱。”[7](P.118)《王三娘造像记》著录于清人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中,陆氏是晚清时期著名学者,精于金石学,以博学严谨著称。如果陆增祥所录天保元年《王三娘造像记》可靠不虚,那么北齐时期就已有送子观音造像。天保元年即公元550年,恰是北齐建立之年,此时距鸠摩罗什译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已四十多年。而据王琰《冥祥记》记载,刘宋时孙道德通过礼诵《观世音经》而得子。可见在刘宋(420-479)时期观音“应求男求女”的故事在当时社会上已经有广泛影响。这可以佐证陆增祥所记天保元年(550)的《王三娘造像记》当是可信的。
目前学界公认的中国现存最早送子观音造像是隋仁寿三年的王洪渊造像。[8](P.432)这尊造像现存于山西万荣县博物馆,为砾岩石制作,通高36厘米,宽18厘米。观世音站于莲花台上,莲花台下面是一块高5厘米、宽18厘米的长方形底座,底座边上刻有王洪渊仁寿三年(603)的发愿文。如图5所示:观音右手持莲花,左手握一净瓶,瓶上站立一裸体童子,观音左右两侧各站一护法弟子,左侧弟子前站一小狮子,右侧弟子前小狮子则作俯卧状;观音身着披帛长裙,头戴花鬘宝冠,颈饰项圈,胸佩璎珞,臂有腕钏;菩萨脸形方圆,眉毛浓厚,眼睛微睁平视,鼻翼圆隆,嘴唇紧闭,下颌上刻三条淡淡胡须,呈现出祥和的神态。
玄奘《大唐两域记》载古印度人衣饰云:“男则绕腰络腋,横巾右袒;女乃檐衣下垂,通肩总覆。顶为小髻,余发垂下,或有剪髭,別为诡俗。首冠花鬟,身佩璎珞。……国王、大臣服玩良异,花鬟宝冠以为首饰,环钏璎珞而作身佩。”[9](P.84)王洪渊造像显然保留了印度王公贵族的衣饰风格,加上观音下颌上淡淡的胡须,可以肯定这是一尊男性化的观音造像,跟我们常见的隋代观音形象差别不大。观音右手持莲,有学者认为有“连(莲)生贵子”的寓意,恐是臆测。事实上,莲花在佛教中象征着清净与慈悲,是佛教各种菩萨的常持之物,只不过约从犍陀罗佛教艺术开始,右手持莲、左手握瓶就是观音造像的基本特征。这尊观音造像的特别之处是观音左手瓶上站立一裸体童子,这跟我们常见的隋代观音造像迥异,故学界将其判定为中国现存最早的送子观音造像。那么,这究竟是不是一尊送子观音(或曰观音送子)造像呢,目前公布的该造像发愿文模糊不清,依稀可确认的文字是“仁寿三年,岁次癸亥四月壬申朔八日,佛弟子王洪渊为亡男胡□,敬造[观][世][音]像一区(躯)……”[10](P.48)运城安邑县原藏有无纪年的《王黑郎妻张李等造像》,里面有提到了“王洪渊妻高敬姿”。安邑县(今安邑街道)与万荣县距离约几十公里,故王洪渊当是同一人。另,陕西洛川县博物馆藏有隋仁寿三年的王洪晖造像,洛川县距离万荣县也较近,两铺造像同为仁寿三年,加之造像主名字相近,故笔者猜测,王洪渊与王洪晖当同属一奉佛家族的昆仲。由“王洪渊为亡男胡□”敬造观世音可知,王洪渊之子已亡故,联系到造像中殊异的童子,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影响下,雕刻的一尊观音送子像。
唐代巴蜀地区佛教造像群中,也出现了观音送子摩崖石刻造像。据考察,四川省盐亭县山青庙一号龛和三号龛都有送子观音造像,且都开凿于盛唐。[11](P.50)这两龛的造型比较接近,观音跏趺坐于莲台上,身披璎珞,头束高髻,怀抱童子,左右各站一协侍(青山庙一号龛观音一侧协侍已毁)。我们可以看出,除了身边雕有童子外,隋唐时期的石雕送子观音像与当时流行的观音造形相差不大,这体现了送子观音造像初创时期的特征。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高峰,形成所谓的八大宗派,各成体系,胜义叠见,佛教艺术也开始逐步摆脱异域风格,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艺术文化。就观音图像艺术而言,隋唐时期逐步形成女相观音,为推动观音送子信仰的流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对莫高窟隋朝的第303窟、第420窟,到唐代的第45窟,“应求男求女”经变图在构图和表现技法上,都不断趋向成熟,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中国特色。王洪渊送子观音造像,在服饰装扮上虽多沿袭古印度(或者西域)的风格,但其开脸造型基本已是中原样式。特别是在观音造像中添塑童子,以此表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应求男求女”的故事,这完全是中国人的独特匠心。
二、宋代的送子观音图像考辨
20世纪,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了“唐宋变革论”,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是近世的开端。的确,相比唐代社会,宋代出现了市民文化阶层,在风俗、信仰等方面都呈现出崭新气象。就佛教信仰而言,两宋时期的佛教义理之学逐渐式微,居士佛教和民间佛教逐渐兴起。在这种背景下,观音信仰也越来越民间化,人们渴望观音帮助他们解决现实日常生活中的疑难问题,因此宋代的观音送子信仰更盛。例如《宋高僧传》卷十七载,释道丕母许氏因常持《观音普门品》,因而妊娠生道丕。洪迈《夷坚志》“翟楫得子”条和“徐熙载祷子”条,都是讲向观音祈子获验的故事。
宋代观音除了送子以外还具有护生保子的功能。《夷坚志》“安国寺观音”条记载,许洄妻孙氏妊娠将产之际,危痛万状,安国寺长老焚香为之向观音祈祷,孙氏恍惚梦见白髦妇人与之木龙,遂生子。[12](P.1300-1301)《夷坚志》“观音偈”条记载张孝纯有孙五岁不能行,在他人的劝导下,张孝纯及家人诵念称颂观音之语,不两月其孙行走如常。[13](P.5)由徐熙载、许洄妻、张孝纯孙的故事看,观音所送及所救护之子的身份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他们长大后身份不再是隋唐时期的达官显贵或者高僧大德,而更多是芸芸众生,可见宋代观音送子信仰已经深深渗透到民间社会。那么宋代的送子观音造像是什么样的,与隋唐时期的相比,又有何新的特征呢?
(一)宋代的送子观音画像
20世纪,西方学者曾在吐鲁番木头沟遗址采集到9-10世纪的一幅回鹘式坐姿观音,曾被学者认为是最早的送子观音画像。[14](P.227)主尊观音结回鹘式跏趺坐,头戴化佛冠,头光顶部绘一排坐佛,主尊观音两侧绘有若干小型的观音像;其中,主尊左侧居中的一尊小观音身著白袍,头戴白色风帽,左手托一儿童。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第29号窟左壁,也有一幅类似的画像。伯孜克里克石窟开凿于回鹘高昌王国时期,那么木头沟遗址出土的这件观音像可能也是回鹘高昌王国时期的。而我们知道回鹘的佛教主要受汉地佛教的影响,因而木头沟遗址出土的这幅回鹘式坐姿观音像可能也间接反映了汉地的观音信仰传统。如果上面的说法成立,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木头沟遗址出土的这幅观音像可能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观》经变图,主尊左侧居中的手托童子观音表现的是“应求男求女”内容。这里特别注意的是,与隋唐敦煌莫高窟表现“应求男求女”经变图有别,这里“应求男求女”图中省去了求子的妇女及女童,重点表现的是观音及男童,形成了真正意义的“送子观音像”。事实上,观音的样貌及着装打扮,跟明清时期常见的白衣送子观音已基本相差无几,这代表着送子观音形成过程中过渡期的特征,我们姑且将此称为“准送子观音像”。
上面谈到,木头沟遗址出土的高昌王国时期的送子观音像可能受到汉地传统的影响,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大约同时期的北宋汉地有送子观音画像吗?学者李翎曾云:“宋代《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法轮宝忏》云其中提及:‘世所称送子观音像,乃诃利底母形也,非观音也’,证明在宋代送子观音已出现。”[15](P.508)可惜的是《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法轮宝忏》是清僧咫观所著,并非宋人编撰,故此论难立。而笔者查到了另一条材料,可证北宋时期已有送子观音画像。清人卞永誉所著《式古堂书画汇考》一书,是根据前人著录及自己目见而辑录的一部上起魏晋、下止元明的书画品著录。《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三十二记载,宋代贺六待诏的传世画作中有送子观音像六幅[16](P.420)。据洪迈《夷坚志》卷二十四记载,贺六待诏是海州朐山(今连云港海州区)人,家世画观世音像,传至贺六待诏时画艺更工,曾感召到观世音菩萨现身。洪迈《夷坚志》成书于南宋,因而学者多将贺六待诏断定为南宋画家,其实这是不准确的。据笔者考证,其实北宋晁补之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像赞》中就讲到了贺六待诏画观音并感召观音现身的故事,只不过与《夷坚志》记载的情节略有差别。[17]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贺六待诏乃北宋画家,北宋时已经有纸本或绢本送子观音画像。值得注意的是,晁补之《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像赞》中提到贺六待诏所见的观音是身着白衣的“白衣仙”,这跟上面提到的木头沟遗址出土的高昌王国时期送子观音像是一致的。因此,可以断定北宋时期已经存在“准送子观音像”。
(二)宋代的送子观音造像
我们知道佛教信仰图像一般有画像(壁画、绢纸画)、铸像(瓷制、铁铜铸)及石雕像,上面我们已经断定在北宋时期已经有送子观音画像,那么宋代还有没有送子观音铸像和雕像呢?以往学界对此讨论较少。笔者近日在西安市博物院发现了一尊铜制鎏金观音送子造像,高12.6厘米,20世纪由西安市文物商店收购,被鉴定为宋代文物。观音半跏趺坐,身着双领下垂式通肩天衣,身披裙袍,袒胸,腹部束腰,头戴风帽,双目俯视;半裸男童坐于观音曲起的右膝上,观音左手撑住童子左脚,右手搂住其腰腹部,童子双手抬起,双脚似在顽皮地乱蹬。这尊造像整体鎏金,线条流畅,如果判断无误,那么这尊造像是目前已知现存最早的铜制鎏金观音送子造像。
宋金时期北方窑口瓷品烧造业发达,出现了如磁州窑、巩县窑、耀州窑等一批名窑,烧制了大量精品瓷器,其中就有送子观音造像。故宫博物院藏一尊宋金时期耀州窑青釉加金送子观音造像,观音通体施青釉加金彩,釉色青中泛黄,金彩大多已脱落。观音倚坐于莲台,头戴风帽,身着披肩长巾,长裙曳足,褶皱迭起,腰束有梅花状束带,颈佩项圈,上挂有心形饰品;观音发髻盘起,面目略成方圆形,双目下视,巧鼻小嘴,额有白毫;观音左手抱婴儿于胸前,右手置于膝上,童子一手放于观音手上,一手放于观音腹部,似正在嬉笑。这尊观音送子造像保存完整,细腻精美,整体上呈现出舒展流畅,简练丰满的风格,是目前已知我国现存最早的瓷制送子观音造像。这尊宋金时期耀州窑送子观音像是经故宫博物院权威专家鉴定的,且与宋金时期的耀州窑其他产品风格一致的,其是断代当是无误的。我们将西安市博物院藏宋代鎏金送子观音与这尊宋金瓷制送子观音造像对比,可以发现两尊送子观音造型非常相近,观音都身披裙袍,头戴风帽,开脸酷似,童子都或站或坐于观音腿部,因此西安博物院所藏鎏金送子观音造像也当是宋金时期的作品。除了上述的瓷制和铜质鎏金送子观音造像外,宋代巴蜀地区还出现了摩崖送子观音造像。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和《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记载,资阳市安岳县的新庙子摩崖造像、眉山市彭山县的佛儿岩沟摩崖造像、重庆市大足区的灵岩寺摩崖造像中都有宋代送子观音造像。
宋代这种新风格样式的送子观音是怎么形成的呢?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其造型及服饰风格与宋代流行的白衣观音图像非常相似,唯一的差别是送子观音身边多了一个童子,故姚崇新及于君方等学者认为这跟宋代白衣观音的流行密切相关[18](P.333-334),尽管还不清楚二者被拼接在一起的原因。经过唐代佛教的发展高峰,宋代以来佛教文化向不断民间下沉,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特点。从宋金时期的送子观音造像来看,送子观音造像已经基本脱离了《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影响,形成了独立的样式,笔者将此称之为送子观音的形成期,这也象征着宋元时期中国社会对佛教文化的消化与改造。
三、元明清时期风格多样的送子观音图像
宗教信仰需要神圣的经典作为依据和规范,随着观音信仰的民间化,人们将白衣观音和送子观音拼合在一起,称之为白衣送子观音。随着白衣送子观音的传说影响逐渐扩大,产生了《白衣观音五印心陀罗尼经》,或曰《白衣大士五印心陀罗尼经》,一般简称《白衣观音经》。从宣扬白衣观音的救护功能看,这部伪经可以追溯到11世纪流行的《白衣观音神咒》,从这部经的名称看,似乎又有密教的底色,可能是受了元代藏传佛教的影响。但这一切只是猜测。这部伪经大约产生于明代中期,北京法源寺藏有印刷于明宣宗宣德三年(1428年)年的《白衣观音五印心陀罗尼经》,这也是目前存世最早的版本。信众们向白衣送子观音求子的办法除了诵读祈祷外,就是捐资大量印发流通该经,他们认为这可以积累功德,故各地现存的《白衣观音五印心陀罗尼经》数量颇多。
到了明清时期,白衣送子观音已经成为一位有独立身份的观音,人们认为只有通过礼诵《白衣观音经》才可求子。清初梦闲子所著《今古传奇》卷七“酒中酒尼姑迷花,机中机秀才报仇”一回记载:“巫娘子道:‘我在自己绣的观音大士面前朝夕焚香,也曾暗暗祷祝,不见应验。’尼姑道:‘大娘,你不晓得求子的法,求子须求白衣送子观音,还有一卷《白衣送子经》,不是这平时的观音大士,那《白衣送子经》有许多灵验,可惜我不曾带那卷经来。’”[19]那么《白衣观音经》所记白衣送子观音像是什么样子呢?图像中各元素符号又有什么意义呢?下面试作探究。
(一)白衣送子观音像
白衣送子观音像一般被置于《白衣观音五印心陀罗尼经》扉页。画像中白衣送子观音坐在台座上,头戴花冠,身着袍服,胸佩璎珞,后有圆形背光和头光,头光背后有几株枝叶婆娑的竹子,一只鹦鹉站于竹子枝头;观音右手持杨柳枝,左手端着似盛有甘露的小碗;观音四周祥云环绕,观音右后侧一少女擎着宝幡立于云头,左前侧一童子双手合十站于旁边;观音的座台前有六个童子,三个手持莲花作敬献状,两个双手合十似正朝拜,中间一童子跪伏于地作叩首状。观音右边的少女是龙女,左前侧站立的是善财童子。善财童子与观音很早就被联系起来了。《华严经·入法界品》中讲善财童子受文殊菩萨指点,先后参访53位善知识,一路解惑释惑,最终遇到普贤菩萨而完成行愿悟道,被称为“华严五十三参”。善财童子参访的第27位善知识就是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为其解说“大悲行法门”。那么善财童子在送子观音像中又有何寓意呢?明代刊本《南海观音传》中说善财童子本是一名苦修的孤儿,观音为考验其的诚心,让众仙变化成强盗恶霸将自己逼落悬崖,善财童子毫不犹豫地随她跳崖,从而顺利通过观音的考验。
龙女在佛教也相当有名。《法华经·提婆达多品》讲龙王娑羯罗的女儿听文殊菩萨讲《法华经》后妙解信行,向佛敬献珠宝而变成男身成道。东晋编译的《摩诃僧诋律》卷四十三有“商人驱牛以赎龙女得金奉亲”故事,大意是说龙女被一离车(古印度贵族名)所捕,商人以八头牛将其赎放,龙女感其大恩,遂赠商人用不尽的龙金以供养其父母亲眷。[20](P.228)龙女报恩的故事在中国影响很大,以唐传奇《柳毅传书》为代表的笔记小说都沿袭了这个故事原型。那么观音和龙女又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南海观音传》记述龙女是龙王第三子之女,其父不幸被渔夫捉去,观音让善财童子用一吊铜钱将其赎回。老龙王为答谢观音救子,让孙女为观音送去一个颗明珠,龙女去后被观音收为弟子,并让龙女将她身边的善财童子当师兄看待。
鹦鹉也是佛教中的名鸟,尤其以《旧杂譬喻经》中鹦鹉救火的故事和《杂宝藏经》鹦鹉供养盲父母的故事最为著名。因为鹦鹉的这两个故事宣扬仁义孝敬思想,故在中国广为流行,并被改造成各种故事版本。例如《杂宝藏经》鹦鹉救火喻的故事,被刘义庆《述异记》改造为“鹦鹉救火”,并抹去了其佛教色彩。唐代宗密著《佛说盂兰盆经疏》云:“慈乌鹦鹉尚解思恩,岂况人伦而不济拔”[21](P.90),说的显然是《杂宝藏经》中鹦鹉供养盲父母的故事。1967年上海一个宣姓妇女墓中出土了一本明代说唱词话《莺哥行孝义传》,讲述了鹦鹉(莺哥)与观音的故事渊源。《莺哥行孝义传》大意是说鹦鹉为救病母来东土摘樱桃,不幸被猎户所抓,猎户又将其卖给任员外,后经鹦鹉苦劝,猎户和任员外都归佛向善;而等鹦鹉做完这些事,摘得樱桃回家时母亲已经去世,鹦鹉的善行孝心打动了观音,遂发慈力救了其母,并将鹦鹉带回紫竹林修道。这个故事显然是根据《杂宝藏经》中鹦鹉供养盲父母的故事演化而来,而清代刊刻的《鹦鹉宝卷》对《莺哥行孝义传》又作了更细致的加工创作,重点突出了鹦鹉孝亲的情节。
小说《南海观音传》约成书于16世纪,是由《香山宝卷》敷陈演义而来。据韩秉方考证,《香山宝卷》成书于崇宁二年(1103)[22](P.54),故《南海观音传》中龙女与善财童子的故事可能宋元时期就已存在。《莺哥行孝义传》原书题作《全相莺哥行孝义传》,题“永顺堂新刊”,无刊刻年代,根据与此书一起发现的其他12种书刊刻时间判断,《莺哥行孝义传》当刊刻于明成化七年至成化十四年(1471-1478)。推此推断,《莺哥行孝义传》的故事蓝本可能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也就是说,观音与善财童子、龙女及鹦鹉的故事,可能在宋代就已经基本形成。事实上,在明代成书的《西游记》第57回“真假美猴王”一节中,就已提到善财童子、龙女、白鹦哥是观音座下的弟子,而我们知道《西游记》的主要故事情节在宋元话本中已基本成型。
解析了白衣送子观音像中各组成要素的意义后,我们还不得不追问这幅图像是怎么形成的。笔者通过查考唐宋以来的观音图像,发现至迟在元代观音图像中,就出现了观音与鹦鹉、善财童子及龙女组成的图像,福建省泉州市虎屿岩元至正三年(1343年)的观音雕像就是最确切的证据。[23](P.89)元代流行的此类观音像是如何加上童子变成明代的白衣送子观音的,这种匿名拼接的过程还不得而知。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鹦鹉、善财童子及龙女被一起组合在白衣送子观音图像里,是因为他们都有孝行义举,显然这暗含了明清时期社会中的流行的忠孝观念。从明朝以后的文献图像资料来看,白衣送子观音画像在神州大地广为流传,图像基本变化不大,这标志着送子观音图像的最终定型。
(二)写经式送子观音像
除了白衣送子观音图像外,明代出现了一幅由小楷书写《观世音经》而连缀成的送子观音图,别具一格,有必要介绍。这幅画高91.8厘米,宽35.6厘米,绢本设色,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中,妇人头束高髻,饰云朵形发冠,弯眉小嘴,戴耳环,面容清秀和蔼;右腕戴玉镯,右手持杨柳枝,左手托一似钵水碗,怀抱一童子,童子怀抱一玉如意。图中人物的脸、手、脚均以细线勾勒,衣纹轮廓则以楷体小字书写的《观世音经》代替,字字相连,趣味盎然。如果仅从人物造型设计看,我们很可能将此图看作是道教的碧霞元君送子,亦或是民间信仰中的某送子娘娘。然而其衣纹轮廓用《观世音经》内容书写而成,加上图中人物所持捧的杨柳枝和似钵水碗,这又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是一幅送子观音图像,只不过观音的形象完全是世俗化了的贵妇模样。将佛经绘写成佛教图像艺术,融写经信与信仰图像为一炉,是佛教信仰中的独特艺术传统。一般只有当某部佛经在社会广为流行时,才会用这种方式呈现,例如唐代《心经》流行,敦煌莫高窟曾出土了四件唐代的塔形《心经》写本。明代出现的这幅以《观世音经》连缀而成的送子观音图,足以说明送子观音信仰在明代的盛行。
(三)铸造式送子观音像
明代瓷制品送子观音剧增,除了上述“白衣送子观音”式,铁铸或瓷制的送子观音像大多省去了龙女、善财童子及鹦鹉,这当然是出于制造方便的考虑,但也说明随着《白衣观音经》的流行,人们似乎已经相信怀抱童子的白衣观音就可以主嗣生育。这种铸造式造型的送子观音明清很多,各类材质代表性作品有:故宫博物馆藏象牙圆雕送子观音、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明代漆金木雕送子观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青铜鎏金送子观音坐像、苏黎世瑞特保格博物馆藏清代石雕送子观音、兰州市博物馆藏明代金镶玉送子观音、英国私家典藏德化窑何朝宗款送代送子观音造像。这些造像中尤其以是明代福建德化窑何朝宗款送子观音造像最为著名,被西方人誉为东方维纳斯。何朝宗款送子观音送子除少数是“白衣送子观音”式造像外,大多数是铸造式送子观音,兹介绍一尊。图中,观音赤双足呈半跏趺坐姿坐于高座,身披广袖法衣,头梳瓜瓣式高髻,脸形方圆,双目微闭,嘴唇紧拢,项挂璎珞,神态娴淑;观音左侧塑有经函卷,童子坐于观音右腿上,脸上流露着幸福的微笑。这尊塑像整体看起来明净温润,让人感觉这不像是庄严的神像,而是一对充满脉脉温情的世俗母子。何朝宗将中国古代泥塑、木雕、石刻等艺术融入瓷雕艺术中,充分运用捏、塑、雕、镂、贴、接、推、修等技法,在衣饰和手势的处理上颇具匠心,创作出来的送子观音以现实人物为蓝本,又化实为虚,使作品呈现出真善美的艺术风格,代表了中国人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追求。
受社会阶层和地域风俗影响,同一种文化往往呈现出多样性特征,送子观音图像也是如此。除了我们上述的三种类型送子观音图像外,明清时期还有文人所画的送子观音像,这些画像基本摆脱了佛教文化的桎梏。如故宫博物院藏晚明陈洪绶的一幅送子观音像,画面只绘一个中年贵妇怀抱一垂髫童子,如果没有旁边的题跋,我们很难相信这是一幅送子观音像。陈洪绶的送子观音像省略了一切带有宗教象征意义的元素符号,力求摆脱一切外在的束缚,直指本体内核,酷似晚明的禅宗文化,这代表着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四、民国以来送子观音图像的新风尚
清末以降,在革命的风浪中,社会思潮为之一新。一些职业画家也开始画送子观音,例如任伯年、王一亭著名画家等就画有送子观音像。西泠印社小龙泓洞左岩壁刻有一幅送子观音画像,乃1923年根据王一亭的画所镌刻,吴昌硕题款曰:“行善之人善结果,赠以佳儿佛日可,观世观人更观我。”[24](P.103)民国四大高僧之一的弘一法师也曾画有送子观音,《弘一法师画观音集》中观音怀抱小儿,端庄秀美,衣袂飘飘,宛如天使,别具神韵。随着近代商业的发展,在民国时期出现了印有送子观音的海报,观音的下方,画着几盒香烟,由此可以判断这幅海报可能是为推销香烟而制。画报上面的菩萨、善财童子、龙女、鹦鹉等要素与我们上面介绍的并无二致,但在绘画技法上采用炭粉擦笔法,有效解决了明暗对比等问题,酷似现代的摄影作品,让人感觉完全是现实中艳妇及俊童的形象。
近现代以来的送子观音图像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年画的盛行,送子观音开始走进千家万户。天津杨柳青年画、山东高密年画、陕西凤翔年画、山西运城年画,江苏苏州年画、四川绵竹年画等年画中,都有风格多姿的送子观音像,可谓遍布华夏大地。建国后,因为“破四旧”等移风易俗运动,送子观音年画一度销声匿迹。改革开放后,送子观音再次回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但送子观音的年画图版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如一幅1990年代的送子观音年画所示:观音端坐于在莲台上,身着白色袍衣,头梳高髻戴莲冠,观音左肩搭放拂尘,右手持净瓶,身后祥云缭绕于紫竹间;观音莲座上放着聚宝盆,里面装着元宝、珍珠等奇珍异宝;观音右侧一童女身穿刺绣肚兜,肩擎金鱼,左侧一童男双手合十举着一个福字。两侧对联曰:“求子得子子成龙,求财得财财成堆。”横批写着“观音送子”。八九十年代,国家实施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社会上开始流行“儿女双全”的观念,观音两侧的一对金童玉女则反映了人们的理想期待。如果不是专业研究人员,很难知道这幅图中的观音两侧的童女童女,是原本的龙女和善财童子,更难理解其中所象征的孝道思想内涵。至于原来画像中的鹦鹉,则早已被抹去,因为人们早已不知它所代表的文化意义,观音及童子的形象设计,明显是受到了当时热播的电视剧《西游记》的影响,通俗文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图中的鲤鱼和聚宝盆,显然是人们有意添加上去的新元素符号,因为鱼有“鲤鱼送子”和“年年有鱼”的双重内涵,而聚宝盆则象征着兴旺发达,这反映了八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中,人们追财逐富的社会思潮。这些新变化表明,民国以来随着传统文化的断裂和新社会观念的形成,送子观音图像又演化出新的风尚,笔者将此称之为送子观音图像的异化期。在此,送子观音似乎仅仅是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求子符号,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现实需求添加新的元素,然后赋予其自己所期待的意义,这也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结语
送子观音图像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尊民俗观音画像,是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典型代表。送子观音图像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隋唐的初创期、宋代的形成期,元明清的定型期、近现代的异化期。第一阶段中,就莫高窟壁画而言,由隋到唐的“应求男求女”在构图方式和表现技法上,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中国特色。就石雕造像来说,王洪渊造像中的童子完全是根据中国人的想象所添加的,是对印度观音造像模式的突破。第二阶段中,从宋金时期的两尊造像来看,送子观音造像形式已经基本脱离了《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影响,与隋朝的王洪渊造像也风格迥异,形成了独立的样式,这也象征着宋元时期中国社会对佛教文化的消化与改造。从社会思想的角度分析,宋代佛教信仰逐步心性化、民俗化,这与宋代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密切相关。第三阶段中,从最具代表性的白衣送子观音像来说,鹦鹉、善财童子及龙女被镶嵌进白衣送子观音图像,是因为它们在当时都是忠孝仁义的象征,这显然暗含了明清时期社会中对人际伦理关系的期待。从写经式送子观音像来看,陈洪绶款的送子观音画像力求摆脱一切外在的桎梏,试图省略了一切带有宗教象征意义的符号束缚,直指本体自身,代表着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似在以送子观音图像为艺术媒介,宣扬晚明的禅宗文化。从何朝宗款瓷制送子观音来看,以现实人物为蓝本,化实为虚,删繁就简,使作品具有真善美的艺术风格,代表着中国式的审美价值。第四阶段中,从流行的送子观音年画来看,龙女和善财童子被改造成俗世的童男童女,鹦鹉则被抹去,增添的元宝和金鱼则象征着对财富的渴望。
以《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应求男求女”为经典依据,在1400多年的传承创新中,送子观音图像不断丰富完善,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送子观音图像,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依旧有强大的文化生命力。送子观音图像的形成过程启发我们,优秀的传统一定是活泼的,它之所以值得被传承,是因为它具有面向未来成长的潜在“可能性”,可以为新的创造提供价值力量;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一定要为其注入符合时代进步发展要求文化元素,从而保持蓬勃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