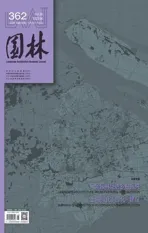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原真性保护研究
2022-06-21陈国栋
陈国栋 王 浩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南京 210037)
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与建设过程中,植物景观原真性保护是历史文化名村风貌保护长期被忽视的一环,而原真性原则是国际遗产保护领域的核心原则。从风景园林学科视角结合文化遗产领域原真性相关知识,解析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风貌原真性的内涵,从古树名木景观和一般性植物景观两个层面分析目前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原真性保护现状及问题,探究植物景观对于历史文化名村风貌原真性的重要意义,指出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原真性具有“不可替代性”“动态性”“相对性”的特征,针对性地提出了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原真性的保护策略,以期为历史文化名村风貌的整体性研究提供参考。
风景园林;乡村植物;文化心理;历史文化名村;原真性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与利用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其关注焦点不仅仅是乡村产业的发展、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生态环境的改善与自然文化特色的传承同样不容忽视[1-2]。能够较完整地反映一定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是历史文化名村评定标准之一,乡村风貌是乡村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的集合体,承载着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建筑营造等信息,是历史文化名村原真性保护的重要内容[3]。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商业经营与文化旅游逐渐成为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与利用的主要途径。过度的商业开发给历史文化名村风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特别是植物景观呈现城市化、公园化的面貌,风貌的原真性正在逐步失去。相比于普通村落,历史文化名村的植物景观多树龄长的植被,其特色根植于乡村传统文化心理,因此也是历史文化名村风貌、文化保护的重要对象。然而,除了古树名木,植物景观在物质外形上不如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建筑那样具有被保护的典型性,在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实践中易被忽视。基于以上考虑,文章尝试分析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的原真性问题,以期为历史文化名村风貌的整体性研究提供参考。
1 既有研究的概况与问题
1.1 相关研究概况
1.1.1 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原真性”(authenticity)源于希腊和拉丁语的“权威的”(authoritative)和“起源的”(original)两个单词,主要表示有原创的、非复制的、非仿造的意思。1964年《威尼斯宪章》首次将“原真性”概念引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界,并提出“将文化遗产原真性信息完整地传递下去是我们共同的责任”;1994年《奈良文件》明确了文化遗产的多样性,指出难以将原真性评价置于固定标准;200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操作指南》进一步明确提名《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必须经过设计、材料、工艺和背景环境4个方面的原真性检测。上述国际性文件奠定了“原真性”原则在国际现代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于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达成了基本共识[4-5]。中国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原真性”概念,但其思想在国内早有体现,梁思成先生提出的文物建筑“整旧如旧”的原则某种程度上与国际社会的“原真性”原则是一脉相承的[6]。1985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成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标志着中国遗产保护理论开始与国际接轨[7]。国内遗产保护原真性研究方向主要有对“原真性”概念的辨析,对国际社会有关“原真性”政策规章的解读以及遗产保护“原真性”原则在实际案例中的应用;保护对象主要是建筑遗产、遗址遗产、历史园林遗产等,鲜有针对植物景观遗产的保护[8-10]。
1.1.2 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风貌原真性
历史文化名村景观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与历史价值,兼具自然和文化属性,属于重要的文化遗产类型。根据《关于乡村景观遗产准则》(2017),乡村景观遗产可以分为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物质遗产属于乡村风貌的物理表征,包括其生产性土地、水系、植被、聚落、乡村建筑、基础设施等;非物质遗产是乡村文化表征,包括乡村相关的风俗习惯、传统文化、聚落身份及归属感的表达[11]。历史文化名村景观风貌是基于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传统所形成的可感知的景观特征和文化内涵,是历经千百年后地域自然生境条件和人文生态需求的双重选择结果。目前历史文化名村景观原真性保护主要集中在对乡村建筑、聚落空间格局、自然山水形态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较少涉及植物景观原真性保护,忽视了乡村植物的遗产价值。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实践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农村绿化,更加注重植物景观对于历史文化名村风貌整体性的价值和意义,包括视觉和文化心理两方面。因此,综合上述分析,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风貌原真性至少应涵盖以下几点内容:(1)符合乡村文化心理、营建传统;(2)包含乡村建成初期及后续各个历史时期合理地、适当地变化与叠加,能够真实、有效地反映特定历史时期及地域的植物景观风貌特征;(3)植物景观空间实体与乡村地域文化的内在统一,满足乡村行为主体对于乡村风貌的“原真性”体验,能够唤起村民及游客内心的乡愁记忆[4-5,11-12]。
1.2 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原真性保护现状及问题
乡村植物景观是指对乡村地域范围内自然生长或长期引种驯化后能适应当地环境的植物材料进行艺术的组合,为创造愉悦、美的享受所形成的景观。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区别于其他乡村植物景观的本质特征是其所承载的文化价值与情感内涵,研究将历史文化名村中的植物景观分为两类,一类是古树名木景观,树木本身就是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拥有生态、经济、文化以及科研等多重价值;另一类是一般性植物景观,植物材料本身不一定具有遗产价值,经过精心搭配所形成的植物群落景观,其配置模式和布局结构能够映射出乡村发展的文化脉络,体现乡村的生态格局,包含农业遗产景观。
1.2.1 古树名木景观
古树名木是指树龄在100年以上,或者是稀有、名贵、具有一定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的树木,被称作“活的文物”,属于不可再生的自然文化遗产[13]。古树名木的生长反映了历史文化名村的地形地貌、民俗风情、传统园林景观、原生树种甚至是气候地域环境的变迁。历史文化名村中的古树名木保护有别于城市、风景名胜区以及景观园林中的古树名木保护,隶属于历史风貌区内的树木保护,强调树木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一般散布于院落、宗祠、村口附近。每一棵古树因其自身独特形态、经历的古老岁月以及相关的历史人物事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兼具人文和景观属性,是村落风貌原真性的重要体现。目前历史文化名村古树名木保护形势严峻,截至2019年9月底,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共公布了7批487个历史文化名村,预计在未来会达到3 000多个,而各省市地区颁布古树名木相关的保护管理条例多是针对城市环境,且管理保护标准不一,实施难度大。历史文化名村古树名木保护常用模式有两种,一种是重点保护树木资源,另一种是注重树木生长的立地环境保护,两种方法都将环境与树木割裂开,忽视了村落原真性风貌的整体保护;常用的保护手段停留在设置围挡,划定保护区,限制保护区内的负面活动,难以满足古树名木的实际生长需求[14]。此外,历史文化名村古树名木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失衡,目前历史文化名村古树名木都是以保护为主,未能充分发挥古树名木资源的综合价值,乡村居民对于古树名木科研、历史、文化价值认识不足,保护的积极性不高,主要以政府主导,缺乏保护的内驱力。
1.2.2 一般性植物景观
一般性植物景观主要分布在乡村的水岸、道路、农田、庭院、宅旁以及乡村其他公共空间,其中包括因为村落特殊地形地貌、自然环境以及地域文化共同作用所形成的农业遗产景观,如云南的梯田景观和兴化的垛田景观。农业遗产景观是历史文化名村中重要的生产资源、旅游资源和生态景观资源,体现了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智慧,能够有效传递乡村风貌的原真性信息,目前主要采用有机农业、生态旅游以及生态补偿三种保护途径[15]。农业遗产景观之外的一般性植物景观是历史文化名村景观原真性保护中长期被忽视的一项,在乡村植物景观营建过程中城市化和公园化现象严重,破坏了原有的景观风貌。一般性植物景观占据了乡村植物景观的主体地位,与乡村聚落格局关系密切,一般呈现出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态势。历史文化名村传统的圈层式保护将植物景观与乡村整体风貌割裂开,往往会造成各圈层之间风貌失调,与历史文化名村传统风貌格局整体保护的思想理念相背离。乡村植物景观是乡村居民通过大规模种植活动改造土地,以生产为目的,为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自发地与自然发生长期互动关系的结果,是一种自发性的行为。而在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营建更新过程中,建设主体转变为相关职能部门及专业规划设计人员,他们过分追求植物景观视觉效果,关注植物个体特征,引入一些“新、奇、特”的品种,丧失了地域文化特色,忽视了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的文化内涵。文化内涵是历史文化名村风貌原真性的核心价值,脱离植物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去营建植物景观,植物也仅仅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景观构建。
2 植物景观原真性保护之于历史文化名村风貌的重要意义
历史文化名村风貌原真性是乡村景观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文化意义的高度统一,风貌的原真性程度是衡量历史文化名村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普通村庄的植物景观建设以绿化为基础,强调通过增加绿地面积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重点关注植物的生态功能、美学功能。而历史文化名村中的植物景观在满足绿化功能的基础上,同时兼顾社会功能,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其原真性保护对历史文化名村传统风貌的留存具有重要意义。
2.1 历史文化名村风貌环境的视觉基础
依据词语释义,乡村风貌中“风”意为物之内涵,“貌”意为物之外显,所以历史文化名村风貌涵盖了物质环境特征与社会人文特征两方面内容。历史文化名村具有丰富的景观资源,区别于城市与一般性乡村,以自然景观资源为主,少量人工景观,其中植物景观资源占据了较大比例。植物是历史文化名村环境中主要的生命形态之一,其本身既是造景主体,又是其他景观要素不可或缺的烘托或陪衬,奠定了历史文化名村风貌的基调。植物景观作为历史文化名村风貌的基础,是一定时期、地域范围内,气候、土壤、地理、民俗文化共同作用的物质外显,带给观赏者最直接的视觉感受。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兼具自然与文化属性,二者共同作用于历史文化名村景观风貌。植物景观自然属性特征包括品种、形态、数量、布局、配置模式以及生长状况等等,与内在文化属性互为支撑,相互依存,给乡民游客带来直观的物质形态层面的视觉冲击,是地域特色与乡愁意境的重要载体,撑起了乡村植物景观风貌的整体骨架。乡村植物对于乡村风貌环境而言既是不可或缺的景观元素,同时也是重要的物质生产要素,与乡村居民生产生活联系密切,是人们感受历史文化名村风貌原真性的视觉基础。
2.2 历史文化名村生产、生态与生活环境的过渡
植物景观与村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根据人与乡村植物景观环境的互动关系,可以将植物景观分为生产型植物景观、生态型植物景观、生活型植物景观三种类型[16]。植物景观作为历史文化名村生态、生产与生活环境相互渗透、融合的纽带,将三生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乡村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如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景观,是乡民为满足生产需求,通过大规模的种植活动对山体地形进行改造的结果,属于生产型植物景观。梯田最上方是茂密的寨神林,属于风水林,作为生态型植物景观的典型代表,是人们在与自然互动中以最小人为干预的形式对乡村自然生态系统进行改造的结果,能够防风固土,抵御部分自然灾害,同时还是重要的物种资源库,为鸟类及虫类提供栖息之地,树种选择以乡土树种为主。再往下是山寨,寨内植物依附于乡村街巷、池塘以及院落空间环境进行配置布局,形成生活型植物景观,其与村民生活联系最为密切,受到生态条件、个人喜好、社会经济和文化风俗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所选择的植物通常具有美好寓意,同时满足一定的生产生活需求。最下方是种植水稻的梯田,整个村庄形成了森林—山寨—梯田的生态共生模式,如图1通过植物要素有效完成了生产、生态以及生活环境三者之间的过渡。

图1 生态共生模式Fig. 1 Ecological symbiosis pattern
2.3 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文化心理的重要表现
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除了满足视觉观感和生产功能需求之外,同时还是乡村传统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映射出传统文化心理。植物景观的外在表现形式一般有两种状态:(1)客观存在的植物实体所展示出来的景观形象;(2)感知主体基于感知客体在人脑中形成的主观印象。乡村植物景观通过其独特的形态特征和组合方式唤醒游客及村民的地域乡愁记忆,引发人们一系列的情感活动,从而赋予植物景观精神文化内涵。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核心特征就是其所承载的精神文化内涵,如果丧失了文化内涵,那乡村景观风貌的原真性就无从谈起。乡村植物景观的精神文化内涵具体表现在对古树崇拜、节日祭祀、民俗民风和生产医疗等方面。如浙江小芝镇中岙村后山,生长着一棵近900年的古罗汉松(Podocarpus macrophyllus),树旁曾发现明代祖先墓,村民在树下纳凉家常,赏秋摘果,古树早已成为乡村居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华北地区乡村庭院中多植枣树(Zizyphus jujuba)、 石 榴(Punica granatum) 和槐树(Sophora japonica)等,南方院落常见枇杷(Eriobotrya japonica)和橘树(Citrus reticulata),这些植物果实丰硕,既能果腹,又象征着多子多福的愿望。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是乡村记忆与乡愁产生和延续的见证者,是乡民情感的共鸣点,承载着乡村的精神文化意义。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的文化内涵是乡村传统文化心理的体现,综合反映了植物景观的美学、历史、科学、社会以及其他方面的价值,体现着先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文化心态,以及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人居环境营造“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17]。
3 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原真性特点
3.1 不可替代性
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原真性的形成受到经济生产、居住生活、自然环境以及精神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是自然、人文双重选择的结果,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植物种类和配置模式两方面。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由乡土植物构成,乡土植物地域性特征明显,在历经人为活动干扰、地域气候变迁以及生物物种侵害等外界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仍能茁壮生长;此外历史文化名村植物选择通常带有美好寓意,蕴含村民对植物造景和民俗民风的理解,因此历史文化名村植物种类具有不可替代性。其次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配置模式具有不可替代性,历史文化名村建村受到自然环境、宗族关系以及社会经济的共同作用,在历经千百年的发展中形成独特的景观格局,对植物景观的布局模式有着深远影响。如楠溪江中游的岩头村是五代末年金姓族人逃避战乱所建,宗族文化与耕读文化盛行,背山面田近水,植物配置强调风水文化,同时突出古朴、和谐的意境,整个村庄植物景观呈现出农—林—宅的布局模式。由此可见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布局以地形地貌为依托,构成乡村风貌的基本脉络,串联乡村不同的空间环境;同时也是对乡村生产、生态和生活环境的合理优化,与周边地形地貌,山水环境相互交融,是一种乡村环境与植物之间交融共生的传统生态经验,难以被其他配置模式所替代。
3.2 动态性
历史文化名村景观属于文化景观中“有机演进的景观”,乡村景观遗产是动态的活化遗产,因此植物景观作为历史文化名村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原真性具有动态性的特点。区别于历史文化名村景观中其他硬质性历史文化遗存,植物景观具有其特殊性,就乡村植物本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环境的变化,历经盛衰荣枯的生命规律,呈现出动态变化的时序景观。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原真性的形成是社会、时间、空间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动态过程,乡村植物种植最初是出于生产目的,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来受到社会和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逐步形成满足生产、生活、生态需求的特定的空间物质形态,成为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载体,在之后乡村聚落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植物空间形态又受到社会文化的作用,此过程不断累积重复,最终形成历史文化名村所特有的植物景观原真性风貌。因此历史文化名村的植物景观经历着由自然景观向文化景观转变,再伴随着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持续演化的过程(图2)。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的原真性所具有的动态性特征的本质是人地关系不断演换的过程,叠加了植物景观演化过程中各个时代特征信息,并且只要当地社群还存在,植物景观原真性的动态性演变就会一直发生[18]。

图2 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原真性动态演变Fig. 2 The dynamic performance of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plant landscape of the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illage
3.3 相对性
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原真性”概念具有相对性的特征,难以用遗产保护领域固定的保护标准或技术指标体系去衡量。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原真性具有时间与空间上的相对性,曾经不是原真性的植物景观,随着时间推移,经过无数社会生活的叠加,可以重新被定义为原真性的植物景观。植物作为乡村植物景观原真性的实物载体,除古树名木本身固有的遗产价值,其他植物要素则是通过构建特征化的原真性景观风貌,唤起行为主体的文化认同感,从而带来原真性体验。同时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行为主体具有相对性,原真性的遗产价值并非植物景观所固有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特定的行为主体所赋予的。不同类型行为主体对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原真性的判别也有所差异,乡村游客追求的是一种建构后的原真性,区别于城市模式化的绿化美化,能够唤起心中故乡的体验;而乡村居民所追求的是植物景观所蕴含的乡村地域深层文化,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认同,区别于其他地域的植物实体或是精神意义的典型性[19]。因此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的原真性在关注植物客体本身原真性的同时需要更加重视行为主体心理感受的原真性,其核心是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的原真性不局限于追求植物原物的真实,而是作为抽象出来的符号、标志特征能够被人认识到。所以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的原真性是主观的、可建构的,并且不断发展的,在时间、空间以及行为主体上具有相对性特征。
4 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原真性保护策略
4.1 保护植物与居民的文化关系
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风貌是由实体的物质空间与无形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共同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基于文化景观视角,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风貌原真性保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从保护有形的景观空间形态转变为保护植物与居民的文化关系。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最初是当地村民自发地以植物为主要构成元素,以家庭成员为核心,以满足生存需求为目的,对乡村人居环境进行改造的结果,呈现形式是实体的植物景观物质空间。在后续乡村的发展过程中,村民在社会关系导向和价值意识导向指引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植物景观物质空间进行改造,植物景观逐渐成为物质、社会、文化空间的结合体[20]。因此乡村居民是乡村植物景观的文化主体,通过植物要素将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以及文化空间串联起来,从而创造出植物景观风貌的原真性。保护原真性本质上是在保护文化关系,延续他们的生活文化习惯,是一种创造性的传承。在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风貌原真性保护过程中,应该减少设计干预与行政干预,鼓励村民参与乡村遗产景观的保护、利用的决策过程,协调好文化主体与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
4.2 置于乡村环境的整体保护
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的原真性保护从属于乡村风貌的原真性保护,不应该将植物景观从历史文化名村整体环境中剥离出来单独考虑,植物景观风貌应该与乡村的整体风貌相统一。乡村植物景观无法脱离乡村环境而单独存在,需要依托于乡村河道、山体、道路、聚落建筑等乡村地形地物而存在,所以对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风貌原真性进行保护时,需要对乡村建筑风格、布局环境、景观及原住民生活习惯、民俗民风统筹考虑。乡村植物依托乡村环境而存在,根据乡村环境的不同空间特征进行植物配置,形成乡村植物景观原真性特征。以乡村滨水空间为例,“数家临水自成村”是中国古村落的主要特征之一,“堤湾栽柳”“桃红柳绿”是江浙一带典型的滨水空间种植模式,树种的选择、组合方式充分考虑到乡村河道水流较缓,与生态环境适宜,与村民日常生活、生态关系密切等特点,突显了乡村的乡愁意境。植物景观作为历史文化名村景观风貌的基底,其原真性保护建立在与周边环境和谐共生的基础上,使得乡村植物景观承载更多的生态文化意义。
4.3 植物景观风貌原真性的活态修复
国内目前对于历史文化名村规划的主流思想是保护先于利用,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与村民想要发展的诉求相背离。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风貌的原真性保护不同于建筑遗产、遗址遗产以及化石遗产的静态点状保护,植物景观构建出的空间是村民地域生产生活的载体,具有重要的日常栖居意义,将植物景观风貌的原真性保护与村民的生活质量以及社会经济效益结合起来才具有可持续性。所以针对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风貌原真性的不可替代性、动态性和相对性特征,采取活态修复方法。活态修复法关注的重点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允许在延续原有功能的基础上,外在形态可以发生适当的变化,必要情况下功能也可以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人地关系。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风貌原真性的形成,是出于当时生产生活的需要,凭借已有的生产资料改造自然的结果,是无数个当代植物风貌环境的叠加,其本身的形态意义有限,重点是风貌环境所传递的地域文化内涵和乡愁记忆信息[18]。对于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风貌原真性的活态修复,拓展了原真性保护的内涵,协调了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5 总结与展望
风貌原真性是历史文化名村遗产价值的重要体现,植物景观受到社会政策、自然演替和文化内驱力的共同作用,从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文化内涵两方面影响着历史文化名村风貌原真性。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原真性保护与修复过程中应该妥善保护现存古树名木及其周边环境,延续其历史意义和纪念价值,探寻乡村植物景观形成的内在规律,修复被破坏的植物景观,同时应充分挖掘植物景观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协调好人地关系,赋予植物景观新时代的文化内涵,实现历史文化名村植物景观的可持续发展。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