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剌与元成宗朝“珍宝政治”
——以浙东两通元代摩崖石刻为中心
2022-05-17求芝蓉
求芝蓉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元代入华西域人,历来备受学术界关注。哈剌鲁(Qarluq),又译葛逻禄,是东迁西域人中的重要一支。其代表人物,文学方面有著名诗人廼贤,政治方面则当数哈剌。哈剌是元世祖、成宗时期非常活跃的军事将领、政治人物,至元年间参与攻宋,大德年间又是征八百媳妇的主帅之一。因他曾作为沿海万户府达鲁花赤长期戍守浙东,哈剌鲁人便以此为契机,定居庆元路(今宁波)。以往学者对哈剌的生平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樱井智美论述哈剌鲁人的仕官与科举时,对哈剌生平扼要梳理[1]178。马晓娟对《哈剌神道碑铭》进行了注释[2]91-98。刘晓研究“沿海万户府”,因哈剌是沿海万户府首任达鲁花赤,对其生平、家世、后人进行了详细考辨[3]105-115。以往学者几乎穷尽了相关史料,但都未注意到浙东的两通摩崖石刻。笔者经实地勘察,初步判断这两通石刻皆为哈剌手书,是认识其人汉文化水平的珍贵实证。更重要的是,这两通石刻内容相互关联,能补史之缺,揭示了哈剌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另外,结合相关波斯语史料,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元成宗热衷珍宝对朝政造成的影响。
一、新昌董村摩崖石刻
1989年,董村摩崖石刻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昌县地方志办公室进行了摩拓,1998年新昌县报社的梁少膺在《文物》公布了拓片及录文[6],并做了初步研究,发表于《书法研究》[7]。梁少膺更正了俞函三录文的一些讹误,但录文仍有缺漏。他的考辨未出俞函三之范畴,于史学研究而言,无甚推进。而其所做的书法研究,非笔者所专,本文不予置评。
2005年9月,新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委托中国文物研究所(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就董村摩崖题记编制了保护设计方案,经过细致的勘察后,2008年进行了施工。2010年出版的《新昌董村水晶矿摩崖题记保护工程报告》[8]非史学研究著作,而是“工程报告”,收录了局部照片,无准确录文与考证。目前此处摩崖石刻有了保护性的护檐,还有排水沟拦截地表水,有效减缓了其自然损毁速度。保护工程还喷上了红漆以显字,通过这样的措施让观赏与阅读更为便捷,然而有些字迹已经不甚清晰,喷漆时或漏喷,或喷错,令人遗憾。
今据笔者2017年11月的实地考察,录原文如下:
(小字四行)
中書左丞自元日至人日
親率左右於石厂山獲水
晶一藏計一萬一千三伯
七十四斤皆珎異奇絕者
(大字九行)
大德二年十一月奉
旨寻採水晶自寧海至樟
林至新昌之石厂發洩地藏貢登
天朝下闡坤珎上昭
乾德實
明 有道之所為
刻石以記其事
大德三年正月 日金吾衛上將軍
这通摩崖石刻共13行,120余字。右侧四行小字记述了这次采矿的人物、时间、地点与收获:中书左丞行浙东道宣慰使(哈剌)亲率左右,于大德三年(1299年)元日至人日(正月初一至初七),在石厂山采掘了 11 374 斤水晶。左侧九行大字是哈剌亲书的题记,讲述了采水晶的缘由是大德二年(1298年)十一月奉旨;寻采水晶的路线是宁海至樟林至新昌;并称颂此次采矿所得是“下阐坤珍,上昭乾德”,因此刻石记事。最后是年月、官衔与署名。
自至元十四年(1277年)至大德五年(1301年),前后共24年,除至元十八年(1281年)一度从征日本外,哈剌一直在浙东任职,且主要为海军将领,这可能是因为能够统领水军的蒙古人太少。因此,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哈剌入朝后,《元史·哈剌传》记“令还戍海道,授浙东宣慰使”[9]卷132;危素《合鲁公家传》记“廿四年,加镇国上将军、浙东道宣慰使,仍兼长万户府”[11];《沿海上万户府达鲁花赤哈剌德政碑》则记“丁亥(1287年)五月,宣授浙东道宣慰使,仍兼长万户府”[12]卷3,6470。《元史·哈剌传》中还说:“二十五年枢密以水军乏帅,奏兼前职”,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他又拜金吾卫上将军、中书左丞,行浙东道宣慰使,领军职如故[9]卷132,3216-3217。从传世文献来看,对朝廷而言,在“水军乏帅”的情况下,哈剌沿海万户府达鲁花赤的职责就相当重要。为此至元二十四(1287年)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朝廷在授其浙东道宣慰使之职后,又遥授中书左丞,散官也从从二品的镇国上将军,提升至辅国上将军,乃至正二品的金吾卫上将军。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至书写董村摩崖石刻的大德三年(1299年),十年间哈剌官职毫无变化,与此前他的连番升迁形成鲜明对比,个中原因值得深究。但因史料有限,前人对哈剌这十年间的行踪并无考证。而董村摩崖石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根据邓文原《故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巩国武惠公神道碑铭》的记载,哈剌任浙东宣慰使后,“会盗发处、婺,连城驿骚,上堑溪啸呼曹偶,椎埋剽掠,莫敢谁何。公获其首歼之,民以安堵”[10]754。地方志也记载了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哈剌到温州的瑞安、平阳等地荡寇的情况:“处州詹老鹞犯瑞安、平阳境,宣慰使哈剌元帅征之,不血刃而寇溃。”[15]卷17,13b但是,至元二十五(1288年)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此起彼伏的浙东民变,主要的平定者却非驻守庆元路的哈剌,而是久在江南任职的史弼。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杨镇龙在宁海、玉山起兵,前来镇压的是时为淮东宣慰使的史弼①,因此,该年闰十月史弼得以“为浙东道宣慰使,位合剌带上”[9]卷15,327。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史弼又“平处州盗”[9]卷162,3801。与史弼等人南下平叛相比,哈剌的沿海万户府驻地虽然在庆元路,距台州、处州不远,但在戡乱过程中他似乎少有作为,这或许就是其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以后官职一直无变化的一个理由。
大德三年(1299年)董村摩崖石刻,为我们揭示的很可能就是哈剌人生转折的契机,即哈剌对于自己的累年不得升迁一事并不甘心,因而积极奉旨寻采水晶,以求给喜好珍宝的成宗留下好印象。大德五年(1301年),哈剌被“征入见。擢资德大夫、云南行省右丞,偕刘深征八百媳妇国”[9]卷132,或许正是因此次寻采上供水晶而得到了机会。而这次入见也成了哈剌人生的转折点。当时志得意满的他一定想不到会因“丧师”而罢官。
三、宁海樟树村摩崖石刻
(光绪)《宁海县志》载,樟树村后石屏山上有摩崖石刻,为“元浙东宣慰使哈剌罕赛诗”:
千岩石壁任苍苔,今日石盘居士来。
洗刷浮云堪宴坐,不教独秀在天台[16]卷21,530。
县志所录的这首诗,实为南宋人所写,最早收于南宋末林表民②辑录的《天台续集别编》中:
题樟林寺(有碑。高述题名在侧)
玉盘居士
千岩石壁任苍苔,今日玉盘居士来。
洗刷云根堪宴坐,不教独秀在天台[17]卷2,11b-12a。
从“有碑。高述题名在侧”这一题记可知,《天台续集别编》收录的这首诗显然与(光绪)《宁海县志》来自同一处石刻。两者所录文字稍有歧异,应该是因为700年的风吹雨打,导致石刻年久漫漶。高述,字季明,丹阳人,元祐三年(1088年)等进士第,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为临海县令,擅长模仿苏轼的书法[18]1387。“玉盘居士”是何人,虽然无从考证,但其诗既然收录在南宋人所编诗集中,就可以肯定其为宋人。所以此诗绝对不可能是“元浙东宣慰使”所写,且元代浙东宣慰使中也无人名为“哈剌罕赛”。
2019年5月,笔者前往宁海樟树村考察,在当地村民李晓达的引领下,找到了位于樟树小学(即樟林寺旧址)后山上的石刻。这块在山野地头极为突兀的大石,因常有野鸡栖息于上,被当地人称为“雉鸡岩”。石头朝南一面即为石刻,因风雨侵蚀,文字多已漫灭,但仍可辨别出一些关键词句。现存文字共约九行。右侧残存三行大字:“……居士来。……堪宴坐,不教独秀在天台”,知即《宁海县志》所录之诗。左侧小字约有五六行,大部分漫漶,但尚可辨识出“地灵”“奉”“入贡”,以及“宣慰使哈剌书”等字。“哈剌”三字较其他字小,格式与董村石刻相同,笔法亦相似,可以认为也是哈剌亲书。
这通摩崖石刻原来应该包括北宋高述题名、南宋玉盘居士题诗、元代哈剌题记,自右至左排列。后来侵蚀严重,高述题名漫灭,(光绪)《宁海县志》将“哈剌书”误读为“哈剌罕赛”,又将南宋玉盘居士题诗和元人题记混为一谈。
七月望日避地省阬存思庵留题
时章林出白石可为水晶,有旨差路县官同金玉提举差夫取凿,又宿兵守之。吏卒旁午,指予为上户,求鸡羊酒米油铁,无以应其求,且不堪其屡也,来避于此。予念自丁丑之乱,至此凡三避矣。僧旧屋更新,怅然有感,因赋之。
去家无十里,过岭即他乡。
避地身三到,伤时泪数行。
高檐齐古树,新屋背斜阳。
我欲相邻住,青山志未偿[19]卷3,4b-5a。
“章林”即董村摩崖石刻中提及的“樟林”,距舒岳祥居所阆风(今宁海县西店镇岭口村、牌门舒村一带)仅十余里地。因此地出水晶,路县官同金玉提举奉旨取凿,又“宿兵守之”,便需要周边乡民为这些人提供食物与用具。舒岳祥因被指为上户,屡次被要求提供“鸡羊酒米油铁”,不堪其扰,只能逃避。这是1277年(丁丑)兵乱之后,舒岳祥第三次躲到省阬存思庵了。
俞函三已利用了这篇诗序,但误认为这是至元十六年(1279年)之事。根据同卷的另一篇诗序,可知此事应发生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之前,但不知具体何年:
己丑正月二十四日,避地盐□,入省坑存思庵和旧韵
到此于今四,情深即故乡。
新松知改径,旧竹不依行。
平施天犹病,周回日载阳。
邻人馈鸡黍,厚意未能偿。
雪蕻羊羔白,菘芽栗肉黄。(旧京有黄芽菜。)
为谁端有此,正尔未能忘。
觉后心无愠,修来面有光。
道人参妙趣,一炷石炉香[19]卷3,4。
己丑即至元二十六年(1279年),一开年宁海就发生了杨镇龙之乱,人口大量外流③,舒岳祥也不得不再次外出避难。根据《阆风集》中几篇诗序的记载可知,该年舒岳祥辗转宁海周边各地,曾至新昌雪溪(今浙江新昌县巧英乡雪溪村)、奉化棠溪(今浙江宁波市奉化区棠岙村)避难[20]89-90。
此处和的旧韵,前一首即为前引“七月望日”所作之诗,后一首则是《阆风集》卷五所收《题存思庵壁》:
香饭炊鱼白,新醅擘蟹黄。
秋风元不恶,乡思自难忘。
田水闲无用,山云薄有光。
篆畦消息好,一路木樨香[19]卷5,18a。
“到此于今四”一句与“七月望日”所作的“避地身三到”相呼应,可知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舒岳祥第四次避难存思庵,则第三次因樟林水晶之事避难当在之前。
总之,至元年间宁海樟林确曾出水晶,但数量可能不多,所以哈剌不得不在治下其他地区寻找水晶矿。新昌与宁海相邻,董村水晶矿也较大,直至今日尚有零星水晶出土。哈剌因此自樟林西行至新昌采掘水晶。
四、元成宗的珍宝狂热
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福建漳浦,还是浙东新昌,水晶矿的开采速度惊人。高兴大德元年(1297年)闰十二月初二上书说漳浦有水晶可采,二十八日漳浦梁山水晶场立碑,应该是开采已经告一段落。哈剌也追求速度,因为在樟林浪费了一段时间,所以他于大德三年(1299年)正月初一到初七“亲率左右”采矿。七天就采了 11 374 斤水晶,平均一天采掘 1 625 斤,以至于俞函三认为这是“劳扰逼迫”,非有道所为。但从摩崖题记的行文中,我们或可推测,此次采掘并未动用新昌当地人民。因为哈剌的浙东宣慰使并非实职,可能无法真正调动宣慰司下辖官民,所以题记中也完全没有提到新昌县官吏。他所率的“左右”,很可能是他真正能够提调的沿海万户府官兵,或许正是因为调动了有组织的军队,哈剌才能以如此速度进行采掘。
开采水晶的速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成宗对珠宝的热爱。蒙古人对高级奢侈品的追求,世所皆知[21]139-165,珠宝正是其中之一。元成宗对珠宝尤为热衷,开启了元朝“中卖宝物”的热潮[22]42。泰定元年(1324年),中书平章政事张珪上书论当世得失时,就特别提及了成宗常高价购买宝物:
中卖宝物,世祖时不闻其事,自成宗以来,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数万,当时民怀愤怨,台察交言,且所酬之钞,率皆天下生民膏血,锱铢取之,从以捶挞,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经国有用之宝,而易此不济饥寒之物,又非有司聘要和买,大抵皆时贵与斡脱中宝之人,妄称呈献,冒给回赐,高其直且十倍,蚕蠹国财,暗行分用。如沙不丁之徒,顷以增价中宝事败,具存吏牍[9]卷175,4077。
张珪此处所云沙不丁之徒增价中宝之事,应该是波斯文史书《史集》所载的一桩珍宝欺诈案。当时有商人买通朝中大臣,将海外购得的珍宝,虚报价格,售于成宗。案件被一位名叫穆古必立(又译木合比勒)的平章揭发,波及朝中十余名宰相级别的高官。成宗立刻将他们全体罢免。胆巴国师以天象有变为由求情,成宗才赦免了他们的重罪。无论如何,这一案件是元成宗朝一次不小的政治风波。汉文史料对此案多有讳饰避忌。陈得芝先生根据《元史》中的天文记载,考证此案发生于大德八年(1304年)[23]243-244。后高荣盛根据几名涉案官员履历上的共同空白,结合其他资料,考定其案发生于大德二年(1298年)[22]20-68。笔者赞同高氏之说。但陈、高二位学者所用《史集》版本均自波亦勒英译本《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翻译而来,或为自己翻译,或用周良霄所译,以为沙不丁是被成宗下旨请来估价之人⑤。而在余大钧自俄译本翻译而来的汉译本中,此译文与周良霄译本迥异⑥。查《史集》伊斯坦布尔本、塔什干本波斯文原文可知,沙不丁确实不是估价之人,而是涉案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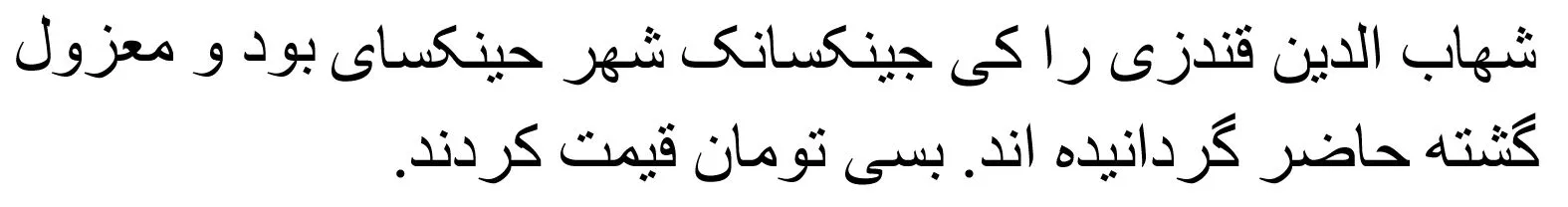

被罢职的原行在城丞相沙不丁·浑都即,被召了来。[人们]估价为三十万⑦。

由于胆巴国师的求情,涉案人员均得到了赦免。而成宗对珠宝的热爱却没有随着这次“增价中宝”案而停止,大德二年(1298年)他又设立了制用院,以“采取稀奇物货”[9]卷94,2403[24]卷19419,7218。甚至涉案人员沙不丁还继续负责这一机构,仍旧为成宗分拣稀罕物货。在感慨沙不丁是官场不倒翁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惊叹成宗对稀罕物货的热衷。
五、余论
近年来,石刻作为一种“新史料”日益受到重视。因元史史料相对匮乏,能够补史之缺的石刻文献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浙东这两通元代哈剌手书摩崖石刻,虽然字数不多,且其中一通文字多漫漶不清,但结合传世文献,仍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结合史料与其他例证,可知元成宗对珍宝的热衷,影响了当时朝廷内外政治。东南海商趁机牟利,引发了大德二年(1298年)增价中宝案,十余名中央高官一度被集体罢免。哈剌、高兴等作为地方大员,也趁机投上所好,以寻求仕途转机。开采水晶,对哈剌、高兴二人而言,都是人生的转折点。哈剌出征西南,功败垂成,只得罢官回乡闲居。而高兴得到重用,从此官运亨通。元成宗对珍宝的热衷,造成的影响当不止于此,未来或许还会有新的发现。
注 释:
① 史弼至元十九年(1282年)任浙西宣慰使,此后一直为浙西宣慰使或淮东宣慰使。这个职位,随着行省所在地的更改而改变。当江淮行省(或江浙行省)治扬州时,则设浙西宣慰司;治杭州时,则设淮东宣慰司。这是因为元朝有“其立行省者,不立宣慰司”(《元史》卷九《世祖六》,第183页)的规定,即行省治所在道不许设宣慰司(参见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第582页)。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二月十二(癸亥),“徙江淮省治杭州。改浙西道宣慰司为淮东道宣慰司,治扬州”(《元史》卷一五《世祖十二》,第320页)。所以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二月一日杨镇龙在宁海起兵时,史弼尚为浙西宣慰使,在杭州,故能迅速率军南下。
② 林表民,字逢吉,号玉溪,台州临海人,活动于宋宁宗嘉定至淳祐年间(1208—1252)。
③ 宁海周边未被杨镇龙之乱波及的地区,流入了大量人口,因此根据地方志记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籍户之时,新昌、金华等地的户数与人口数极大,空前绝后。(参见万历《新昌县志》卷六,第1页b;万历《金华府志》卷五,第10页a)
④ 王文径编《漳浦历代碑刻》,漳浦县博物馆,1994年,第66页。
⑤ “已罢黜之行在城之丞相失哈不丁当时在朝,估定其值为三十万巴里失。”参见[波斯]剌失德丁原著,波义耳英译,周良霄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11—412页。
⑥ “行在城的丞相失哈巴丁·浑都即被召了来罢了官。”参见[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87—388页。
⑦ 拉施特主编《史集》抄本,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托普帕皇宫附属图书馆藏,编号1518,第217页b,笔者汉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