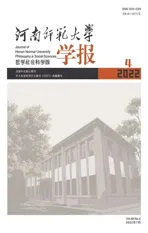元明之交宋濂的思想与行动
2022-03-18李小白
李 小 白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学界普遍接受将元至正二十年(1360)作为判断宋濂前后生活道路的时间节点。时年51岁的宋濂与刘基、叶琛、章溢等人一道,应朱元璋之聘,前往应天(今南京)赴任。从宋濂的存世文章以及后世学者的研究来看,他的心态在入仕前后确乎发生了明显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与其身份与外部处境的变化有关,更与元明之交思想文化的转型存在密切关联。学者们针对宋濂思想转变的研究已趋深入,但多是从经学、理学、文学及史学等角度入手,利用宋濂史传性质的自传书写考察其内在思想变动的文章尚不多见。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从宋濂传记式的历史书写的角度分析宋濂思想及其行动,以就教于方家。
一、宋濂传记类文章的史传性质及其早年的“古文辞”研习
宋濂一生撰写了大量传记类文章,“《四库备要》本《宋文宪公全集》收入以‘传’为题的作品60多篇,以‘记’或‘录’为题的人物传记30多篇,还写过具有传记性质的墓志铭、神道碑、行状近180篇”。可见,宋濂是一位处在唐宋传记文学与明清传记文学之间,具有承先启后意义的传记文学大家(1)陈兰村:《宋濂传记文的人格模式及艺术特色》,《宋濂暨“江南第一家”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33页。。宋濂笔下大量的传记类文章,反映了他进行史传写作的思想基础。
宋濂有意模仿诸如“太史公曰”“赞曰”“论曰”及“评曰”等史评体例,在传记文章的结尾处采用“史官曰”“赞曰”“太史公曰”“太史氏曰”“史濂曰”“金华宋濂曰”等多样化形式结尾。宋濂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的史官身份,屡屡在文末标明“前史官金华宋濂撰”“前史官宋濂撰”等官方身份(2)宋濂:《宋濂全集》卷21《采苓子传》《飞霞先生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408页。。宋濂此举,意在表明自己对传主事迹进行的是写实处理,所作评价符合传主实际。虽时有溢美或回护,但也符合传统史书笔法的处理要求,这表明宋濂对撰史有充分的自觉。他说史传的写作“要在精察之而已”,“事不可传而传之者,非也;可传而不传者,亦非也”,所叙述的史事也“必确然有征”方能入传(3)宋濂:《宋濂全集》卷18《刘真人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45页。。
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强调宋濂传记文章之中所蕴含的史传意识,认为宋濂的史评具有明显的“信实”和道德“垂训”观念(4)曾礼军:《宋濂传记文的“小说化”与“史传化”错位融合及其文体意义》,《江南文化研究》,第5辑,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160页。。宋濂在史传叙事上强调“纪事之文,当本之司马迁、班固”,重视继承史学的传统。不过,如果要从宋濂文以载道的理学家立场而言,他更重视“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叙事的价值在于明道,事实应该让位于载道垂训(5)宋濂:《宋濂全集》卷81《文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961页。。这说明宋濂的传记式书写,在坚持史事信实的基础上,同样重视载道垂训的儒家教化意图。这点我们可以从宋濂一生经历与其自我总结的三次大的思想转变加以印证。
1368年11月,时年59岁的宋濂对自己大半生进行了简要回顾:“余自十七八时,辄以古文辞为事,自以为有得也。至三十时,顿觉用心之殊微,悔之。及踰四十,辄大悔之。然如猩猩之嗜屐,虽深自惩戒,时复一践之。五十以后,非惟悔之,辄大愧之;非惟愧之,辄大恨之。”(6)宋濂:《宋濂全集》卷24《赠梁建中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492页。宋濂对“文”的认识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折。年少时,他热衷于“古文辞”;行至中年,对作文一事幡然悔悟,继而转向学问之道;及至五十岁以后,他的整体生命转向自我内在深省,对“文辞”既悔且愧,更深恨之。宋濂在与戴良的诗文往来中也有类似自述:“华龄事觚翰,志可移南山……如何中岁临,厌读仍厌观。岂为血气衰,恶此葩藻繁……方知始学谬,中夜发哀叹。”(7)宋濂:《宋濂全集》卷101《答戴学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378页。元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命宁越知府王宗显开郡学,延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沉、徐原等为训导”(8)《明太祖实录》卷7,至正十九年正月庚申,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80页。。这首诗应写于此时前后,为宋濂心路转折的又一例证。不少学者选择从宋濂所处外部环境变化的角度解释他的这一心路历程,他们将宋濂入明前后诗文创作风格迥异的原因归结为现实环境的变化,却较少留意宋濂诗文创作态度转变背后那些自传性质的书写内容。宋濂这些史传文章,反映了他一生思想流转的阶段性特征。
宋濂自幼善学,“五岁能诗,九岁善属文,当时号为神童”(9)刘基:《刘伯温集》卷2《宋景濂学士文集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3页。。宋濂的“神童”之誉带给其家人以希望。经里中长者张继之建议,“此子天分非凡,当令从名师,即有成尔”。宋濂父亲“乃携入府城,受业于闻人梦吉先生”,学习《易》《诗》《书》《春秋》等儒家经学知识(10)王祎:《宋太史传》,《全元文》,第55册,凤凰出版社,1999年,第558页。。身具这样的先天禀赋与人生机遇,宋濂曾自信地说道:“余自十七八时,辄以古文辞为事,自以为有得也。”(11)宋濂:《宋濂全集》卷24《赠梁建中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492页。年当弱冠的宋濂自言“濂在弱龄,颇有事科目之学”,即有志于科举(12)宋濂:《宋濂全集》卷56《元故翰林待制朝散大夫致仕雷府君墓志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321页。。宋濂此时已经师事吴莱。相比于科举考试,他更热衷于文辞之事,曾遵照吴莱所命,改学古诗。宋濂还向黄溍学习为文之道,“余弱龄时,即从黄文献公学为文。既得户庭而入,益求海内作者文观之,不问在朝在野,咸无弃者”(13)宋濂:《宋濂全集》卷37《题盛孔昭文稿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820页。。
年已弱冠的宋濂,文名渐为人知,“二十岁时,以文名四方。六艺经传无不精究;子史百家、山经海志及方外之书,无不穷览”(14)郑涛:《宋太史诗序》,《宋濂全集》,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319页。。方外之书如佛教经藏、道教典籍也都是他寓目的对象,但他自认为所学仍以儒家六经为主体。从宋濂自号“白牛生”的传记文章中可知他的一生学问的主体走向是“学在治心,道在五伦”。其他诸如道教服气养身之术、佛教宗门教下之学以及诸子百家等入道见志之书,宋濂自称“我虽口之,未尝心之”,辩称自己不曾偏离儒家治世之道(15)宋濂:《宋濂全集》卷16《白牛生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95页。。但是,宋濂一生出入佛老、泛滥诸子的阅读经历,即便包含他有意识地借此提升个人古文辞修养的现实意图,却也不能否认,这样做的后果让他的精神世界表现出不同思想内容纷然并陈的特点。甚至可以说,在宋濂倡言“六经皆心学”的学术口号之中(16)宋濂:《宋濂全集》卷78《六经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877页。,佛、道及诸子百家等思想所发挥的作用或许更为积极。
年轻的宋濂矢志学习古文辞,遍读群书,其才学为师友所认可。吴莱奖掖宋濂,认为“举子业不足烦景濂,曷学古文辞乎”。23岁的宋濂,“复从吴公游,益取经史及诸子百家之书而昼夜研穷之”。此后,宋濂分别师事柳贯,黄溍,深得柳、黄二人赏识,“每有咨叩,终日言之,无少倦之色”。黄溍年老,无暇顾及求文之士,多令宋濂代笔。身居高位的黄溍在元大都的官场和文坛颇有影响,宋濂为其代笔作文,故而名重一时。在京“台宪诸显人,多愿得而观之”,进一步扩大了宋濂的文名。此时的宋濂却认为忙于写作“酬应以适时用”的文章并非学问正途,意识到“文为载道之具”,为此宋濂“求古人精神心术之所寓,而大肆力于其间”,为学心路发生了转换(17)郑涛:《宋潜溪先生小传》,《宋濂全集》,第5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566页。。到了30岁,宋濂就发出了“顿觉用心之殊微,悔之”之叹(18)宋濂:《宋濂全集》卷24《赠梁建中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492页。。其间,宋濂曾参加元廷举办于钱塘的乡试,无奈落第。随后元廷诏罢科举,上进之路一时断绝。宋濂认为如果再汲汲于科举场屋之学,那就是错用此心了。左东岭也注意到科举失利之于宋濂的打击,称科举停摆是宋濂台阁之途无望转而投在吴莱门下学习诗歌古文的现实因素(19)左东岭:《〈赠梁建中序〉与宋濂元明之际文学观念的变迁》,《求是学刊》,2020年第3期。。所以,宋濂在“文辞”上有所悔,不仅有重归儒学义理生活的内在冲动,也应该有对此时的渺茫前途与不平身世的愤懑懊悔之意。
二、中年时代的学问转向
行至中年的宋濂,有意识地转换个人的学问方向。这点最早可以从他记述早年求学经历的传记材料中了解信息。宋濂践行儒家利济之道,大约始自20岁时。30岁以后,他的学问总体上朝着以“闻道”与“行道”为己任的方向转变。24岁裹粮前往诸暨白门,就学于吴莱门下。同门之中,有楼士宝、宣岊、郑深、郑涛、陈璋、胡翰、陈士贞等辈(20)徐永明:《宋濂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页。。这些同门大多家境殷实,非出身贫寒的宋濂所能比拟。宋濂求学条件相当艰苦,“短衣才能至骭,冷处前庞下,四壁萧然”,备尝凄清孤独。同门之中,仅有陈子章与宋濂亲厚,二人“灯影相望而读书之声相接”。面对这样的境遇,宋濂“心颇不能平”,以至于在言行上有所流露,为此受到陈子章的劝诫。宋濂提到“予时学未闻道”,这是理解此后宋濂学问转向的关键。宋濂此时虽“未闻道”,但已有行道之心,“吾平昔所学仲尼之德,专利济,不残生,二十而行道”(21)宋濂:《明太祖设宋濂谕钱塘龙说》,《宋濂全集》,附录2,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531页。。
造成宋濂中年时代学问转向的还有来自佛教禅宗的影响。1328至1330年间,宋濂两次前往义乌伏龙山参访千岩元长禅师。千岩元长是元代江南禅林临济大慧派中峰明本一脉的嗣法弟子,悟得禅法之后,“声光日显”。为避开声名之累,“千岩竟遁逃不见使者。久之,夜渡涛江,东走乌伤伏龙山”,有意避开元廷的招揽(22)宋濂:《宋濂全集》卷74《天龙禅师无用贵公塔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838页。。宋濂阅读大量佛教典籍,在禅学上也有心得。初次参访元长,二人辩难,多达数千言,结果宋濂在知解文字上打转,“不契而退”。两年后,宋濂再次参访元长,依然没有解开名相缠缚,尽管他声称自己阅尽五千四百卷佛教经藏。所以,元长才刻意作出“耳阅”“目观”的分别之问。宋濂不明就里,恰好落进元长的语言陷阱。元长继续发问,启发宋濂内观本性。宋濂言下顿悟,并有“扬眉向之”的心悟之举(23)宋濂:《宋濂全集》卷73《佛慧圆照无边普利大禅师塔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755页。。不过,从元长后来给宋濂的信中可知,宋濂仍旧束缚于文字相中“错认作法身”,不能彻悟禅家“不立文字”的要旨(24)释元长:《千岩和尚语录》卷1《答景濂宋公书》,CBETA(中华电子佛典协会),J32,No.B273,p0232a17。。
宋濂在元长的劝解下认识到沉溺于古文辞写作所产生的弊端,有意从心性与日常生活中进行自我纾解。来自友人的描述反映了他徜徉三教、涵泳心性的思想与行动。王祎这样描绘宋濂:“衣冠虽晋人之风,气象实宋儒之懿。”(25)王祎:《翰林学士承旨潜溪先生像赞》,《宋濂全集》,附录2,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538页。同门郑涛也有类似记载:“(宋濂)年三十,即以家业授子侄,朝夕惟从事书册,间稍有余暇,或支颐看云,或被发行松间。遇得意时,辄击缶浩歌,声振林木,翛翛然如尘外人。”(26)郑涛:《宋潜溪先生小传》,《宋濂全集》,附录2,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567页。宋濂自己也说:“濂以轻浮浅躁之资,习懒成癖,近益之以疏顽,不耐修饬。乱发被肩,累日不冠,时同二三友,徒跣梅花之下,轰笑竟日。不然则解衣偃卧,看云出岩扉中。”(27)宋濂:《宋濂全集》卷2《答郡守聘五经师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62页。入明之前,宋濂自由旷达的心性表露无遗。
在没有被朱元璋罗致帐下之前,宋濂是一位僻处乡间的儒生,经历了元朝末年的腐败与兵祸带来的种种现实苦痛,却不妨碍他有意识地关注现实政治与社会变动,致力于历代哲人所关心的哲学、伦理等问题的思索。宋濂一度认为“道不行于时”,选择退隐山林,著述自娱,自言“濂自居青萝山,山深无来者,辄日玩天人之理。久之,似觉粗有所得”(28)宋濂:《宋濂全集》卷84《青萝杂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020页。。这一时期,宋濂思想较为独立,敢言敢论,积极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尽管他的所思所著有芜杂而少系统之嫌,思之未周,但他又按捺不住行诸笔端的内在冲动,“皆一时念虑所及之言”,“所著之书,随所见笔之,而感慨系之矣”(29)宋濂:《宋濂全集》卷94《龙门子凝道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237页。。宋濂笔下的文字表明了他此时的壮怀与忧思。
宋濂这一时期的杂言、谕、寓言、说、述、文、杂史等作品,多为抨击时事的批判之作。尤以《诸子辨》《龙门子凝道记》《燕书》等作品为典型。宋濂深省元末动乱时期不可能实行儒者理想中的仁政,面对率兽食人的元朝统治者和嗜杀成性的地方割据势力,他极力呼吁统治者以民生为念,甚至有“民者,君之天也”的论断(30)宋濂:《宋濂全集》卷97《燕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289页。。这种来自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愿望,恰恰是面对社会现实却无力改变而发出的吁求和进行的苦痛挣扎。这些思考同样是宋濂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志气才学无从施展后退而著述的反映。
左东岭指出宋濂一度同意由婺州籍文人共同运作和宣传,向朝臣展示自己在大都官场的人脉和才学能力,借众人之力让自己进入大都朝臣的视野,由此获得他们的举荐而进入官场(31)左东岭:《〈赠梁建中序〉与宋濂元明之际文学观念的变迁》,《求是学刊》,2020年第3期。。宋濂这番苦心经营和婺州籍文人为推举宋濂所作的努力确实收到了理想结果。元至正九年(1349),宋濂获得朝臣危素的举荐,被朝廷由布衣擢升为将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相比于多数元代文人的出仕无门,拥有众多助力的宋濂是幸运的。宋濂经历了大多数元代中后期文人或干谒游历或参加科举的人生过程,他们的结果多是以失意归隐告终。这是元代文人最典型的人生模式,即由对外在功名的追求转而回归隐居尚志、守道自持的过程(32)左东岭:《行道与守道:元至明初文人人生模式的生成与转换》,《文史哲》,2020年第2期。。面对这样的结果,宋濂却没有接受来自大都的征聘,他选择了借故推辞,“至正中……自布衣入史馆为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选,而景濂素不嗜进,固辞避不肯就”(33)王祎:《宋太史传》,《宋濂全集》,附录2,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569页。。徐永明认为所谓“素不嗜进”都是托词,并非宋濂拒绝元朝征聘的真实原因。经他研究,先有同郡张枢辞归,后有杨维桢请托做官未遂,再有老师黄溍对元朝失去信心,最后加上自己屡屡科举失利与看到元朝行将覆灭的历史趋势,综合下来宋濂选择拒绝元廷的征聘(34)徐永明:《文臣之首——宋濂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拒绝元廷征聘后,宋濂为避开世事与人言的扰攘,决定入仙华山为道士。为此,他借戴良之笔写下一番自我剖解的话语。宋濂说:“余之所安,乃在于山林而不在于朝市,使其以此而易彼,有大不可者一,决不能者四。”自己闲散懒慢成癖,有违礼法的约束,是“大不可者”,其次还有诸如神思易于疲乏,不能承担官府冗杂的事务性工作;起居无常,不能安于官府公务的按部就班;公务宴饮,不能久坐,有碍于官府的日常接待;书法欠佳,难以承担官府堆积如山的案牍书札等。有此四点,“自度卒难于用世”,只好“顺性而动,各趋所安”,“又闻道士遗言,吐纳修养可使久寿,故即其师而问焉”,至于说士大夫的“起而嘲之”,那就赠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35)戴良:《戴良集》卷6《送宋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58页。。但从宋濂前期的做法来看,他出家归隐的理由并不充分,入山为道士不单是避世,或许更是为了掩盖藏于心底不甘的无奈之举。
戴良对宋濂“寄迹老子法”的做法感到惋惜。他说宋濂“通古晓今,有史氏长材”,出家为道士,不免与儒家济世之道相违。宋濂拒绝元廷征聘,有其不得已之处,但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转折。面对不能有所作为的元末乱局,宋濂选择道家无为之道,暂时远离尘世。即便入仙华山为道士之后,宋濂仍然徘徊于道家无为与儒家有为之间,有着思想上的波动(36)徐永明:《文臣之首——宋濂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5页。。戴良为宋濂代笔辩解,何尝不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宣传策略,目的是营造宋濂才华卓异却不为世所用的遗憾氛围,期待慧眼识才之士的出现。宋濂的根本意图也没有远离儒者经世的立场。不过也要承认,道家虚静无为的思想确实给了他此刻精神上的安慰。宋濂之所以选择披发为道而不是出家为僧,即已表明他并不能忘情于儒者济世的社会责任和人生理想。他这样做是有所保留的。
宋濂避世求取仙道的想法很短暂,他很快就从修道延生返回到儒家经世思维的旧有轨道。宋濂认为道教修炼以延生健体的做法仅仅是“一己之私”,他要代之以“君子之所志,泽及黔黎”。宋濂在仙华山并没有真正地转入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境地,而是依然汲汲于儒生修齐治平、积极有为的人生理想。宋濂外道内儒的文风背后,是他以隐待仕、相机而动的思维策略。宋濂这种待时而动的做法不过是浙东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曲折表达。他的这种想法在元末婺州并非个例,而是普遍现象,“不独宋濂,元末婺州作家群普遍具有外道内儒的文风特点。究其根本,婺学以儒为主兼容百家的学风、婺州地域文化传统中浓郁的道教氛围、元末儒释道合流为一的趋势及新道教阳道阴儒的思想,是主要成因”(37)于淑娟:《〈龙门子凝道记〉名义考论:兼论元末明初婺州作家外道内儒的文风》,《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
所以,宋濂在《太白丈人传》《龙门子凝道记》《答郡守聘五经师书》等文章中并没有峻辞拒绝来自统治者的招揽和聘用,而是要求统治者以礼相待,表达了自己要由礼而仕的执着态度。宋濂一方面“不轻于自进”,另外也流露出要求王者“致敬”并以礼待之的希冀。他认为如此才符合自比伊尹、太公望的愿望(38)宋濂:《宋濂全集》卷92《龙门子凝道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197页。。宋濂汲汲求用却要求以礼待之的矛盾心态,在他与王宗显的书信中得到集中展现。
王宗显是朱元璋的谋士,他很清楚宋濂在婺州士人心中的地位。朱元璋军队打下婺州后,改婺州为宁越府,王宗显担任知府。婺州出产谋士,时人建议朱元璋恢复金华郡学,为治理当地储备人才。王宗显向朱元璋推荐久负盛名的宋濂担任郡学五经师。朱元璋深知罗致人才对他扫平天下的意义。在宋濂之前,婺州儒士如王祎、韩留、杨遵、赵明可、萧尧、章史炳、宋冕等人已被朱元璋任命为掾史,儒士许元、叶瓒玉、胡翰、吴沉、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吴履、张起敬、孙履等人也被朱元璋招致金华,基于对元廷的失望和对朱元璋本人志向和军纪的了解,婺州精英士人纷纷投至朱元璋幕下。宋濂也认为士人兼济天下的时机已经到来。宋濂在信中虽以种种理由推脱,但整体语气之中并无深辞固拒的态度。王宗显看出宋濂的意图,于是在1360年正月,正式邀请宋濂出山,担任郡学五经师。《明太祖实录》载:“时丧乱之余,学校久废,至是始闻弦诵之声,无不忻悦。”(39)《明太祖实录》卷7,至正十九年正月庚申,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80页。宋濂之所以接受朱元璋的征召,也与他年当四五十岁却默默无闻的处境有关。他这样写道:“我生七尺躯,不乐复何因?成童即穷经,岂意坠白纷……一息能契道,何须浪云云。年当四五十,所愧在无闻。于此苟不忧,可复名为人?”(40)宋濂:《宋濂全集》卷101《答戴学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378页。这首诗也成为宋濂有意仕途的明证。
三、老境侵寻下的心态变化
王祎评价宋濂:“景濂于天下之书无不读,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说,悉得其指要。至于佛、老氏之学,尤所研究,用其义趣,制为经论,绝类其语言,寘诸其书中,无辨也。”(41)王祎:《宋太史传》,《宋濂全集》,附录2,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569页。宋濂的文风,踵武柳、黄二公而有自家面目,他本人也作为元明之交的文章家而名扬海内。陈旅曾评价柳贯、黄溍及宋濂三人的文风:“柳公之文,庞郁隆凝,如泰山之云,层铺叠涌,杳莫穷其端倪。黄公之文,清圆密切,动中法度,如孙吴用兵,神出鬼没,而部伍不乱。景濂之文,其词韵沉郁类柳公,其体裁简严类黄公。”(42)应廷育:《金华先民传》,《宋濂全集》,附录2,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582页。宋濂本人也很得意于自己的文笔,“臣少无他长,惟文墨雍容可尔”(43)吴之器:《婺书》,《宋濂全集》,附录2,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573页。。宋濂自被礼聘至朱元璋麾下,一改身为乡间儒生的创作风格。宋濂在获得不断上升的政治地位之后,他关于心灵自由和对宇宙人生社会历史的哲理思考与探索便呈现了下滑趋势(44)廖可斌:《论宋濂前后期思想的变化及其他》,《中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3期。。
已入仕途且年逾五旬的宋濂,对古文辞已经是“非惟悔之,辄大愧之;非惟愧之,辄大恨之”。我们留意到,宋濂刚被朱元璋纳入麾下,有意在事功方面崭露头角。宋濂认为,溺于文辞无法与建功立业的作为相提并论。步入仕途,强调的是建立事功,笔墨文辞并不能让宋濂获得心性工夫的提升,于是乎“自此焚毁笔砚,而游心与沂泗之滨矣”(45)宋濂:《宋濂全集》卷24《赠梁建中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492页。。尽管宋濂在这里委婉地将理学作为他远离笔砚的理由,实际却是新朝甫立,政治空气严肃,写作诗文易招祸患,以及文牍浩繁让人穷于应付等问题给他造成的现实压力,让宋濂不得不对古文辞一道做出“悔之”“愧之”乃至“恨之”的愤懑懊悔之语。
宋濂入明前后对文章写作的态度转变除了政治原因外,他的身体也不允许继续从事繁重的写作任务,“逮余五十春秋,发白心耗,腰膂如缠巨石,不能危坐,日未入即掩关鼾睡。逢掖之流有袖卷轴来者,望而畏之,若逢刀剑,力拒闭不与言”(46)宋濂:《宋濂全集》卷32《赠梵颙上人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690页。。步入老境、年高气弱的宋濂,面对接踵而至的求文者感到颇为无奈。作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充当了明初一系列文化工程的总裁官,举凡前后编修的《元史》《大明日历》《皇明宝训》等书籍,都由宋濂总裁编订。官方修史不同于私家著作,限制颇多,稍有差池,总裁官难辞其咎。受文名所累,宋濂周旋于众多求文者之间,写的多是奉命应酬的文章,所谓“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47)张廷玉:《明史》卷128《宋濂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789页。。
宋濂入明前后文风有明显变化,由大胆泼辣地批判元末社会现实到入明后社会批判锋芒的弱化;由文风自由奔放、主观色彩浓厚到后来的意在规劝讽喻、为文庄重典雅、深婉含蓄(48)徐永明:《宋濂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6页。。宋濂获得了外在的功名富贵,却以内心的自由和愉悦为代价。明初严肃恐怖的政治生态,对于像宋濂这类文臣和士人必然产生深刻冲击。由此,宋濂收敛甚至不愿再写作也就不难理解了。
明洪武十年(1377)正月,宋濂致仕家居,辟一室,名曰“静轩”,终日闭户撰述,告诫子孙毋入城市,试图以此全身免祸。政治之于宋濂已成畏途。随后的洪武十三年,一场胡惟庸案使得宋濂祖孙父子家破人亡,次子宋璲、长孙宋慎被诛。宋濂有赖马皇后援救得免杀身之祸,但全家被发配至茂州。宋濂在发配途中,卒于夔州僧舍。面对专制皇权的淫威,即便如宋濂这样的惟恭惟谨和明哲保身,也免不了招致灾祸。
宋濂暮年心态的转变更多地缘于外部政治生态的严肃化,但这仅是停留于表面的认识。新朝初立,宋濂受传统士人理想的影响,自然有急于行道济世的想法,他的文风与写作内容由此改变也是可以理解的。宋濂是一个典型的“饮水著书”的书生,想象力丰富,感情敏感热烈,在自我思维的世界里可以自由遨游,但对于现实的生活世界却可能近乎无知。宋濂漠视世人斤斤计较的感官享受,却视自己从事的古文辞和哲思为“道”的载体,堪比性命。宋濂“性尤旷达,视一切外物澹如也”,年过三十就以家事托付子侄,自己则如尘外之人般“朝夕唯从事书册间”(49)郑涛:《宋潜溪先生小传》,《宋濂全集》,附录2,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567页。。宋濂这种文人心性,自少及老,不曾有本质上的改换。宋濂晚年的心态调整,只是为了适应日趋严肃化、恐怖化的外部政治环境而作出的妥协和退让,但他的思想底色从根本上说则未见变易,依然故我。宋濂在入仕后遭遇的种种人生困局以及失落的行道理想,致使他的心态在专制皇权下从自由趋于保守。面对朱明王朝的专制统治和忧谗畏讥、动辄得咎的现实境遇,宋濂的政治热情迅速减退,政治理想随之幻灭,只愿早日归隐林泉以图自保。
四、结语
身处元明之交的宋濂是一位相对自由的思想者。原本多元化的思想格局使他笔下的文章蕴含丰富的人生哲理和较高的思想境界,在社会失序的战乱时代更显思想批判力度。这与他成为明朝官员,并为明朝官方话语进行代言,个人思想与文风日趋僵化保守的表现迥异。宋濂之所以有这种文风上的转变,既有来自明朝官方体制话语的有意塑造和推波助澜,也有宋濂为全身免祸而作出的妥协与退让。宋濂带有信实意味的传记文章透露了他这种阶段性的思想变化。
宋濂的思想世界中存在一以贯之且多元互动的思维脉络。他自命儒者,以理学为学术根底,却也曾积极与佛、道两家思想往来沟通;个人行动受到浙东经世致用学术主张的驱动,仕宦用世之心一生未改,却也曾入仙华山,肥遁林泉之思终生见诸笔端。经历了氛围相对自由宽松的元末统治到日趋严肃化、恐怖化的明初政治,宋濂也发生由乡间儒生到帝国重臣的身份转变,他的思想波动因为朝代更迭和身份变化而尤为醒目。其间,他的文风发生了转变,他为全身保命不断妥协退让,原本颇具社会批判力度的思想也日趋保守和缄默,终日劳形于案牍之间,淹没于文字应酬之中,他在自传文字中所发的牢骚忠实地展露了他的生命窘态。宋濂悲凉的人生结局诚然是专制主义皇权的牺牲品,但他一生曲折跌宕的思想波动又何尝不是王权社会下知识人一般性的文化反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