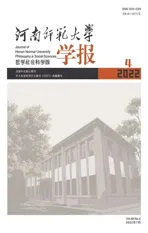先锋小说的当代发生及其与文学群落的关联
2022-03-18张丛皞王雨晴
张丛皞,王雨晴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先锋小说是新时期文学的一座里程碑,“就新时期文学而言,1985年前后兴起的以马原、残雪、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作家为代表的小说创作,由于其自觉的创新实验而被评论家普遍指认为先锋小说”(1)叶立文:《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先锋小说和先锋群体被冠以“先锋”之名似乎已约定俗成。然而,先锋小说家们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标签,马原、残雪和余华等都曾表示“先锋派”是文学史家扣给他们的帽子。对于“先锋”的指称,文学史家和先锋群体之间相互悖反的态度使先锋小说何以被称为“先锋”这一问题显得更加耐人寻味。这引出了与之相关的疑问:文学领域中的“先锋”是一个舶来的概念,新时期文学话语体系中“先锋”语义如何生成,其理据性何在?换言之,“先锋”这个能指符号何以能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批文学青年和文学文本之间建立起语义联系?
对于此问题的探究,一方面,需要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语境中,在“先锋”们所在的文学群体与文学现场的历史对话中去探寻他们如何成为先锋,又何以被称为“先锋”的;另一方面,也需考虑“先锋”的语义内涵,事实上,“先锋”语义在新时期话语体系中的引申就是其语义生成的过程,而其语义中构成了“先锋性”的义素便是连接其指称符号和描述对象的依据。这提醒我们要重新探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马原、余华等人的文学观念和小说文本中是如何潜含着先锋的基因的?其文本中的先锋性又是如何被先锋群体所发掘的?本文秉承质疑与探索的精神,通过追索“先锋小说”的先锋性基因,重返其生长的文化现场,在八十年代的“西藏—上海”文学群体中重探新时期“先锋”语义的生成。
一、“先锋”的基因:“所谓先锋,就是自由”
以上问题所引发出的思考是,当我们在谈论“先锋”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想要真正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生命轨迹、挣脱对它的共名式的认识,就需破解其深层的基因代码——先锋性。陈思和曾经指出:“在中国,‘先锋文学’是一个外来的概念。”“所谓‘先锋精神’,它意味着以前卫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可能性,它以极端的态度对文学共名状态发起猛烈攻击,批判政治上的平庸、道德上的守旧和艺术上的媚俗。”(2)陈思和:《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先锋性》,《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事实上,无论是“先锋精神”,还是“先锋性”,都是指“先锋”语义在文学语境中的隐喻,那么还原“先锋”语义的变迁将有助于对先锋涵义的辨认。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先锋”最早都是军事学上的术语之一。依据《辞海》的解释,“先锋”最早出现在《三国志·蜀·马良传》中:“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892页。在西方,“Avant-Garde”最早也是军事领域的概念之一。诚如陈思和所言,“先锋文学”是一个舶来语,且由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小说与西方现代派文学之间的师承关系,故考察“先锋”一词在西方的语义变迁对于探寻先锋小说的“先锋性”尤为关键。
Avant 有“在……之前、以前”之意,同时具有名词属性,意为“前部、前锋、前线”等;Garde作为名词(阳性)具有“守卫者、哨兵、卫兵”之意,作为动词时,具有“看管、守卫、保护”之意;当二者连为词组时,Avant-Garde具有“前卫、前沿和先锋(军事)”之意(《Dictionnaire Linguee》,2020)。从法语字典Avant-Garde的延伸词条中,可以看到“先锋”的语义由军事领域分别向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等领域拓展的迁移过程,比如:
Dans la théorie marxiste, l’avant-garde est la fraction la plus consciencieuse et la plus politisée du prolétariat.(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先锋是最为认真、最具有无产阶级政治色彩的部分。)
L’avant-garde jazz est un mouvement de jazz des années 1950 et 1960.(先锋爵士是1950年到1960年间的爵士运动。)
L’avant-garde russe est un courant très influent de l’art moderne.(俄罗斯先锋是现代艺术中极具影响力的一个潮流。)
L’avant-garde est aussi un mouvement littéraire et poétique.(先锋也是一个文学和诗歌运动。)
根据以上词条,“艺术”“潮流”“运动”均是与“先锋”密切相关的词语,结合前文所提到的“前卫、前沿和先锋(军事)”的语义内容,我们可以这样概述Avant—Garde的语义色彩:斗争性的、前沿的、激烈的、理想主义的。由此可以辨认,作为在不同语境中的隐喻投射,“先锋”的语义分别在政治、文化等语境内的延伸带有较为浓厚的社会倾向性。“先锋这个隐喻——表示政治、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的一种自觉的进步立场——在十九世纪之前并未得到始终一贯的运用”(4)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104页。。卡林内斯库将以上所得出的先锋的种种隐喻归结为“一种自觉的进步立场”,当我们将这个隐喻放在艺术领域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先锋性体现的是艺术自律性的要求。如卡林奈斯库所言,文学话语中“先锋”的内涵经常是同“现代性”相关联的,“在十九世纪的前半期乃至稍后的时期,先锋派的概念,既包括政治上的也包括文化上的,只不过是现代性的一种激烈化和高度乌托邦化了的说法”(5)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101页。。而“先锋派”——“那些以极端审美主义为特征的运动,如松散的‘为艺术而艺术’团体”(6)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45页。,正催生于现代性(指审美的现代性)的艺术观念中。这似乎指出,当“先锋”从社会语境迁移至艺术语境时,其浓厚的社会性会被极端的审美性削弱。值得注意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表述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纯文学”概念极为相似。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曾因其文本中“高度乌托邦化”的形式探索而被指称缺失社会性意义、深陷形式主义的黑洞。从残雪小说中扭曲变形、纠缠不休的梦魇式寓言,莫言小说中打破感官阈限的魔幻叙述,到余华小说中颠覆常规秩序的暴力书写,均能辨认出文艺语境内的先锋性中所蕴含的审美极端化倾向。
二十世纪初期,“先锋”一词在文艺领域掀起了热烈的创作思潮。我们可以在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俄国左翼文学。以及象征主义文学中看到先锋所特有的自觉斗争性,它们将视野放得尽可能远,不仅要去预见未知,而且要奋起与当时的文艺模式作战。“先锋”与现代性的亲缘关系使得它意识到“现在”即是“过去”的一种形态,因此先锋派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所展示出的前沿性,往往伴随着对历史话语的挣脱和剥离。在西方,达达主义作为先锋派中激烈的派别之一,“既反对艺术作品所依赖的分配机制,也反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由自律概念所规定的艺术地位”(7)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9页。。在中国,前沿性与斗争性相结合的先锋性在马原那里得到了确认,他认为同许多具有即时社会价值的小说相比,他的小说的艺术价值和精神内涵更能做到历久弥新(8)马原曾说:“很多小说在时效性消失以后,就彻底变成了垃圾,被抛弃了。我这些旧书旧作还可以当新书一样面世,还有新的读者去读它,我岂不是反过来占了很大的便宜?”(参见马原,傅小平:《马原:在八十年代,我们彼此是朋友,也都相互敬重》,《西湖》,2020年第1期。)。马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认识到他自己的写作,是一种游走于主流意识形态边缘的具有异质性话语特征的写作,与同时期的知青主题小说相比,马原坚持构建异于普遍性话语诉求的虚构写作,这正是卡林奈斯库所言的“自觉的进步立场”。不可否认,先锋小说的受众是有限的,读者很难从这些小说中寻找出惯常的阅读期待,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这些小说可“带给读者较强的陌生化体验,颠覆读者的期待视野”(9)刘中望,费振华:《论余华小说〈兄弟〉的接受及其异质性》,《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这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真实的状态所在。
由上所述,“先锋”一词在从军事学到社会学,再到文艺领域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偏向审美的倾向已成为其语义的主要侧重,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文艺领域对于艺术自律的极致诉求,应与先锋原义中的斗争性和前沿性有很大关联。在现实的文艺实践中,文艺的先锋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拒绝既有规范,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自我的否定,这两种特征都是通过对极端化的艺术实验所达致的。其中,既有基于危机意识所表达的对于传统的反抗,也有基于对自我不满而形成的精神上的探索。然而,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出现,现代主义以抗争的姿态所建立起来的秩序同样受到了批判,人们借助后现代主义的视野,洞见了先锋文艺在激进姿态下的颓废特征。以此考察1987年以后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等人的先锋创作,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小说中所展示出的神秘性和宿命感,与后现代主义所述先锋文艺的颓废特征不无相似之处。《世事如烟》《褐色鸟群》中断裂的因果和价值链条,《此文献给少女杨柳》《青黄》中无以确信的记忆和在时间交错中颠倒错置的历史,《信使之函》《我是少年酒坛子》徜徉于能指符号的诗意美感与丢失了确切所指的语言,都与指向自我解构的先锋性形成了呼应。
理论家对于先锋文艺的批判已无异议,但这一批判究竟是导致了它的自我毁灭,还是它的生生不息,仍然是一个有待论证的命题。毫无疑问的是,当《百年孤独》的出版震惊世人、当“垮掉的一代”歌唱绝望时,人们已将其特殊的精神内核视为时代的先锋。因此,“先锋”是一个流动的概念,理论上讲,它永远在与自身告别。“先锋性”则是一个永存的基因,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文艺才不间断地走向抗争,即抗争传统,以寻求自由的空间,也抗争它自己所建立的秩序,以保存艺术的自觉。从这层意义上讲,激烈的革新和绝望的颓废就如同“先锋”的正面与反面,它们只有贴合在一起才能拼凑出先锋的完整面目:在对传统的反抗和瓦解中,“先锋”一直在试图靠近人类精神世界和艺术创作上的自由。正因如此,在新时期文学的实践创作中,“先锋小说”指的是一些为探索小说写作多种可能的创作实践,它们是一些敢于背离和反抗既有文学范式的实验文本,正如格非所言:“我所向往的自由……是在写作过程中随心所欲,不受任何陈规陋习局限的可能性。”(10)格非:《格非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3页。后来,这些小说家转向了现实主义写作或新历史主义写作,从表层上看,似乎是先锋写作的衰退,但是从其内里上看,这又何尝不是其自我否定精神的说明,即始终处于动态之中的“先锋性”的说明。
二、西藏写作群体:超现实的文学乌托邦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代小说创作中的先锋因素主要体现在形式探索和语言实验两个方面,而拉萨和上海则是先锋小说家聚集的两个重要地理空间。如果说西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小说变革酝酿发酵的原点,那么,将小说创作的变革和实验发扬光大的城市则无疑是上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一批批大学生的进藏,一个小型的文学群体在拉萨逐渐形成,这是一个囊括了汉藏两地青年作家的创作群。在这个群体中,除马原之外,其他小说家也都有着较强的探索意识。拉萨文学群体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界的影响,主要是通过1985年《西藏文学》6月号集中发表的五篇“魔幻现实主义”(11)在这期《西藏文学》中,有一段编者话语,称“生活在西藏的藏汉族青年作家们……终于有人从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魔幻现实主义中悟出了一点点什么……本期有发表了扎西达娃等五位青年作者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五篇。”作品实现的。这些以藏地生活和藏族文化为背景的小说,将西藏特有的神鬼传说和现代写作技法融为一体,开创出了一种带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写作风格。与此同时,当代文坛正在兴起的文化热,在激起人们对于发掘本土文化热情的同时,也推动了他们关于文化与小说如何联结的思考,正如李陀在评价南美作家时所说的那样:“他们给我们提供一个完全新的视野,把现代主义和他们本土的文化有一个很好的结合。”(12)王尧:《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以“先锋”与“寻根”等文学话语的缠绕为线索》,《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显然,《西藏,隐秘岁月》《幻鸣》等小说的发表,正满足了当代文坛对于小说探索的阅读期待。《收获》的编辑程永新甚至想做一次“西藏专号”的选题策划,足见这些作品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期待的契合程度。曾有学者指出,早在“先锋小说”确立之前,在西藏就已经有了较为成功的小说实验的案例,这显然指的就是以马原和扎西达娃为中心的文学创作群。这些较为成功的小说作品,不只包含1985年6月发表的作品,还包括此前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和色波的《竹笛,啜泣和梦》,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拉萨文学群体中的某一位作家的写作给文坛带来了惊喜,而是几乎每一位年轻作家都能拿得出兼具现代小说技巧和地域文化特色的作品。在信息远不及当下畅通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藏对于当代艺术系和文学系的大学生来说,一直都是令人向往的神秘所在。事实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拉萨的确吸引了包括画家、摄影师、音乐家、诗人和小说家在内的一大批当代艺术家,皮皮曾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在这个小世界中文学艺术娱乐这些很精神的东西是主流,大家能一天一天地谈小说,为海明威的一个小说结尾争得面红耳赤差点打起来……一群年轻的大学生,他们踢足球打篮球搞恋爱,工作的压力很小,生活很有诗意,所以也很不现实。”(13)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01页。一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无需为现实的生计烦扰,在那个离星空很近的地方畅谈诗词歌赋,以一种脱离现实的乌托邦想象来表达他们理想主义的写作态度。从地域发展上来讲,西藏的现代化进程比较缓慢,但正是这种缓慢的生活节奏使得当代的文艺青年将这里视为理想之地,他们用诗歌小说取代柴米油盐,用风花雪月取代失职加薪,从而表现出了与当代文坛主流不一样的创作姿态。马原认为小说写作太关心与“我”有关的事情,因此,他们只想一吐为快而不关心写作的方法。扎西达娃在给程永新的信中展示出了另一种态度:“我的名利思想较之许多人淡泊,我永远不急躁。”(14)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上),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26页。我们似乎可以理解只有淡化创作功利性的态度才能突显文学“自觉的前卫立场”,色波小说中令人头晕目眩的视角转换,扎西达娃小说中现代寓言式的西藏神话,正表明了他们由“写什么”的创作传统转入形式探索的先锋姿态。
另一方面,西藏古老神秘的文化也使小说家们为之着迷。吴亮曾在《马原的叙述圈套》中指出马原不明就里地被西藏奇异的神秘空气所牵引,这使得他的“西藏小说”中充满了剥离了理性束缚的叙述,和无法以常理解释的谜团,比如在《叠纸鹞的三种方法》里,养狗老太的身世在不同人的回忆中变得模糊可疑,而干瘪的杀人老太又为何使他想到了胖乎乎的、为人亲切的酿酒老太?全文中出现的三位老太究竟有没有关联?三个拼贴在一起的故事之间是否能在某条线索上拼合起来?马原所留下的这些疑问,任凭读者猜测却不作解答,一如他着迷于西藏的宗教气息却又无法切近其信仰核心一样。毫无疑问,这种源于西藏神秘文化,却又将之“形而下、具体化”的虚构叙事方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拉萨文学群体中进藏作家的作品常常展现出一种“局外人”的隔膜目光。在这些作家的小说中,“游客”“异乡人”是常用的视角,进藏游历、探险、看天葬、寻亲的故事是常见的情节,我们能感受到异乡人在面对这座神秘的古老高原时的困惑目光,高原上的故事也因此显得奇异而荒诞。在《没上油彩的画布》中,加措偷偷潜入藏族女孩德吉家的帐篷,并在昏暗之中与德吉亲热,但是当酥油灯亮起以后,他突然发现适才亲热的对象竟是德吉的阿妈,而德吉阿爸也在场,此时加措的“惊恐”和“怯生生”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令人感到荒诞的是德吉阿爸的反应,“递给他一串奶渣,地道的藏北货”。面对着潜入帐篷、侵犯妻子的男人,身配长刀的德吉阿爸为何全无怒意甚至以礼相待?这种无从解释的诡吊情景正是异乡人眼中的魔幻现实,正如皮皮所说,“这是一个我无法走进的世界,无论我在那儿待上多少年”。对于异乡人而言,西藏的日常图景都是带有神话色彩的。马原认为他的小说中颇具诗意的神秘感,在很多情况下只不过是照搬了日常生活经验所产生的效果,比如《拉萨河女神》中,一群文艺青年在河心岛露营时,集思广益处理了营地边两具腐烂的死猪,然后该准备野餐的准备餐食,该洗衣服的洗衣服。如果马原不说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读者可能会认为作者是在以怪诞情节来说明生活的荒诞,事实上,这却是马原当年真实的郊游经历。
除了来自西藏本身的馈赠之外,这些沉醉于文学梦的青年还吸收了世界文学的资源。据马原回忆,他在西藏的生活环境完全是文学性的,他和皮皮在拉萨的家里,每天都举办由艺术家、文学家朋友参加的聚会。当马原将胡安·鲁尔福的新书带到这里时,这本书马上就受到了这群文学青年的喜欢,马原甚至断言:“西藏的魔幻现实主义就源于这本书啊。所以他(胡安·鲁尔福)不只是拉美文学之父,还是西藏魔幻现实主义之父。”(15)马原,傅小平:《马原:在八十年代,我们彼此是朋友,也都相互敬重》,《西湖》,2020年第1期。关于当代文坛对南美文学资源的接受,可参照韩少功的记述。在1984年底杭州会议之前,很多与会者都已在报刊上看到了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但是大都只读过其小说的某些翻译片段;另外,在杭州会议上,大家感兴趣的作家是海明威和萨特,根本不是南美作家。由此可以说,西藏的生活环境虽然相对封闭,但是西藏文学群体的阅读视野却不落后,事实上,不论是马原、扎西达娃,还是此一群体中的其他作家,他们的作品中都潜含着南美作家作品魔幻现实的影子,即一种糅合了现代文学手法与地域特色生命力的文学写作。
三、上海文学群体:现代都市的前沿视野
如果说在1985年之前,拉萨文学群体的先锋属性体现在其写作的前沿性,那么,在1985年之后,继起的文学群体则集中在了上海的文学批评界。拉萨文学群体的核心是作家,上海文学群体的核心则是居于《收获》《上海文学》周边的文学批评家。只需粗略整理一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期刊的刊文数据便可看到,在1985-1989年期间,《收获》《上海文学》发表实验小说的数量超过了其他期刊所发表数量的总和。1985年,《上海文学》在第2期上发表了马原的小说《冈底斯的诱惑》。关于这篇小说的发表,马原、李子云和李陀等人都曾对此作过详细的记述,此不赘述。作为参照,陈村的《一天》也发表在这一期的《上海文学》上。短篇小说《一天》极具探索意味,陈村以语言的机械重复暗喻城市生活的机械重复,以个性化的文体引出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思考。《上海文学》同时发表两篇实验性较强的小说,正是其先锋姿态的一种显示。对比马原1984-1985年期间的小说发表情况,更能比较清楚地看到《上海文学》《收获》在小说探索上的前沿视野:《拉萨河女神》发于1984年《西藏文学》第8期,《冈底斯的诱惑》发于1985年《上海文学》第2期,《叠纸鹞的三种方法》发于1985年《西藏文学》第4期,《西海无帆船》发于1985年《收获》第5期,《喜马拉雅古歌》发于1985年《文学月报》第10期。马原的实验性小说写作虽然是在1985年以前就开始的,但是给他带来声誉的则是上海的批评家们,正如马原自己所说,实际上,是《上海文学》把他推上了文坛(16)马原1992年11月在《上海文学》杂志社内与周介人、程德培对话时说:“我说,实际上,是《上海文学》把我推上了文坛,我个人是感谢《上海文学》的。”该对话收于马原所著的《重返黄金时代》一书中。。这些数据表明,上海的文学批评界已经拥有了较为凸显的前沿视野和先锋意识。
如果说期刊的筛选机制能够为小说家的文学探索提供实践平台,那么评论家的阐释功能则可为小说家的文学探索提供理论支持。回顾《冈底斯的诱惑》刚发表之时的批评反应,1985年关于这篇小说的评论只有两篇。吴亮对此解释为:“由于对西藏民族历史、宗教、神话和种种野蛮的风俗所知甚少,也由于对那种怪诞的叙述形式和隐语感到极为生疏,人们只好对之表示沉默。”(17)吴亮:《当代小说与圈子批评家》,《小说评论》,1986年第1期。由于评论界有偏重小说内容主题的习惯,所以,当马原小说中有不明确性的象征寓意时,他们很难运用既有的知识结构去进行阐释。以今天的视域而看,评论家们尚未认识到,对于马原而言,现象本身就是意义。许振强与马原《关于〈冈底斯的诱惑〉的对话》正是对此推论的证实,对话中许振强以“社会性”和“自然性”去判别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方法被马原否定;随后许振强提出小说结尾展开的ABC三种解释是马原用来“搪塞读者的疑问”的“蛇尾”,这种解读显然也与马原的写作构思不符,马原认为这样的结尾是在“最大限度上保持原来故事的弹性”,而且它“不是从情节中引申出来的,是作者自己认定需要这样来结束”(18)许振强,马原:《关于〈冈底斯的诱惑〉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5期。。
真正为马原打开话语空间的,是李劼的《冈底斯的诱惑与思维的双向同构》和吴亮的《马原的叙述圈套》。前者指出了马原笔下悖论叙述后世界的不可知,并以“认知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认知建构的多样性”发掘出作者在小说中设置开放式结构的用意,显然,这种认知较此前许振强的批评逻辑,更能深入艺术内部。后者跳出《冈底斯的诱惑》这一独立文本,进入对马原写作态度和小说意识的整体把握之中,吴亮在这篇文章中揭开马原虚构写作的种种伎俩,将其碎片拼贴式的故事形态解释为非逻辑的经验方式,他特别指出马原的写作是非功利性的,“功利性的目的,只会驱使人的感觉和经验,进入一个被事先限定了的轨道,而马原恰恰是不可能被事先限定的”(19)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由上文可知,文学的先锋性因其自律性的内在规定而与功利性形成了对立,那么,在吴亮对马原写作的阐述中可以断定,吴亮不只对马原现代技法具有专业性的认知,同时,他对马原“不受限定”的自由探索态度也有清楚的认知,不妨说,此时的吴亮对于马原小说的先锋性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而这也正是评论家自身所携带的先锋属性的文学说明。
吴亮和李劼以前沿目光发掘出的小说家并不只有马原一人,他们也不是上海文学群体中仅有的先锋评论家,其他如程德培、蔡翔、李庆西等,也都是围绕在《上海文学》《收获》周边活跃的理论批评家。当许多评论家还沉浸于社会学意义上的主题阐释时,这些新潮批评家们已经关注到个体的精神困境;当许多批评家还在纠缠于“现代派”与“现代主义”的概念区分时,这些新潮批评家们已经注意到了小说的形式意味。为何上海的评论家们会呈现如此突出的先锋意识呢。前文已述,先锋在语义上与“现代”的前瞻性紧密相连,其本质诉求并不是对抗,而是前行,所以,它始终处于流动的状态。无论是先锋作家们的前沿意识,还是先锋小说陌生化的审美体验,均可从这里找到原点。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大都市之一,上海以其改革开放的精神赋予了这座城市现代的特征,居于这里的评论家们在感受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时,也不知不觉地滋生出了前沿性的文学探索意识。1987年,吴亮在《文艺评论》发表了“对城市生活的文学沉思”的系列文章,我们能从中清晰地看到他对现代城市的时间和空间,城市人的精神状态、行为方式以及生存体验的思考。这些都是上海作为一座现代化的都市给一个文学评论者所带来的感受,“城市正是这样一个制造支离破碎人生的大工厂,城市人的最基本心态就是这种支离破碎,一种迅速接纳又迅速遁去的文化价值被草率地对待,没有深入人心的东西。这就是变化太快太频繁造成的结果”(20)吴亮:《城市人精神上的徘徊者:对城市生活的文学沉思(四)》,《文艺评论》,1987年第4期。。在这段独白中,现代城市文明已显出了某种后现代的颓废面貌,速度加快的城市建构最终导致了文化价值的解构,这难道不正是先锋流动的本质,不正是先锋所达致的对自我的否定的特征吗?从这层意义上讲,城市的现代性追求赋予了青年们鲜明的城市意识,而他们又在理解文学时,将它转化为成了具有先锋意识的前沿视野。
综上所述,对先锋语义所进行的重探,以及对居于拉萨和上海的先锋群体所进行的重访,可以揭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历史内涵。一方面,南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西藏的超现实文化氛围,以及上海的现代化追求,为文学青年提供了颇具先锋属性的文化视野;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整体语境中,无论是小说家,还是小说批评家,他们都在糅合了地域文化和现代意识的过程中,比较鲜明地展现出了具有前沿视野的先锋精神。这些既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小说创作的特征,同时也构成了一种新颖话语体系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