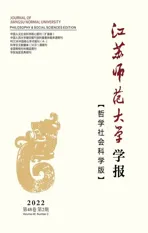政治修辞与用典文本建构
2022-03-18吴礼权谢元春
吴礼权 谢元春
(1.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433;2.湖南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众所周知,人是社会的人,需要融入社会,跟他人合作与交往。为此,人就必须跟他人进行沟通交流。沟通交流有很多方式,其中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语言。应该指出的是,以语言为工具跟他人进行沟通交流,虽然是具备正常思维能力与语言能力的普通人都能做到的,但是沟通交流的效果并不是所有人都一样。沟通交流的效果不同,融入社会,跟他人合作与交往的结果也会有所不同。沟通交流效果好,则合作交往愉快,工作或事业推进顺利,人生境遇顺遂;沟通交流效果不好,则合作交往不愉快,工作或事业的推进会受到阻力,人生境遇可能陷入困顿。因此,只要稍微懂些社会生存法则的人,都会非常重视与人沟通交流,并努力提升沟通交流的效果。
为了提升沟通交流的效果,交际者(亦即“表达者”,包括说话人、写作者)就必然要在语言文字表达上经营努力。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作为自然人的交际者,为了达到其预期的交际目标,往往都会考虑说写表达的效果。为了取得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交际者都会在修辞上用心,讲究表达的技巧,这就是‘日常修辞’。”(1)吴礼权:《政治修辞与比喻文本建构》,《阜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而在政治生活中,作为政治人的交际者,也会“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交际目标而应合特定题旨情境,发挥创意造言的智慧,有效调动语言资源,动用一切有效的表达手法,为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2)吴礼权:《政治与政治修辞》,《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而在语言文字表达上经营努力,这就是“政治修辞”。
从逻辑的层面看,“政治修辞跟日常修辞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种在语言文字表达上的经营努力”(3)吴礼权、高宇虹:《政治修辞与双关文本建构》,《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但是,“从客观事实来看,政治修辞与日常修辞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即使是使用同一种修辞手法建构修辞文本,在所追求的目标预期上也会有所区别”(4)吴礼权、高宇虹:《政治修辞与双关文本建构》,《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这是因为政治修辞与日常修辞的主体不同,政治修辞的主体是政治人(有特定政治身份的非普通人),日常修辞的主体是自然人(没有特定政治身份的普通人)。虽然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人为了实现其交际目标,也非常讲究修辞技巧,但是只是为了提升达意传情的效果而已;而在政治生活中,政治人讲究修辞技巧则就不仅仅是为了提升达意传情的效果,往往还有别的修辞境界的追求。比方说,同样是以用典修辞手法建构修辞文本,自然人在日常修辞中建构用典文本,一般多是为了展现其学识的渊博与表情达意的含蓄优雅;而政治人在政治修辞中建构用典文本,则多倾向于追求表情达意的含蓄婉转,以此规避政治上的风险。同时,还可能有借此展现渊博的学识与优雅的风度,进而塑造自身作为政治人的人格形象。
一、用典的定义及其表达功能
用典,是一种在说写表达中援引古代人事以为佐助的修辞手法。以用典手法建构的修辞文本,称为用典修辞文本。
一般说来,以用典手法建构的修辞文本,“在表达上可以使表达者的达意传情显得婉约含蓄;在接受上,由于表达者在文本意义的表达与接受者的接受之间制造了‘距离’,使接受者只能通过对表达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中的典故进行咀嚼、消化后才能理解其内在的含义,这虽然给接受者的接受带来了一定的障碍,但接受者一旦经过努力破除了接受困阻,便会自然获得一种文本解读成功的心理快慰与欣赏中的美感享受”(5)吴礼权:《现代汉语修辞学》(第四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0-61页。。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在文人的说写表达中,用典修辞文本的建构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例如:
昔草滥于吹嘘,藉文言之余庆。门有通德,家承赐书。或陪玄武之观,时参凤皇之墟。观受釐于宣室,赋长杨于直庐。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盗潜移,长离永灭。 摧直辔于三危,碎平途于九折。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北朝·庾信《小园赋》)
上引庾信赋中的这段文字,虽仅一百多字,却用了十二个典故,分别是:“‘草滥’句,典出于《韩非子·内储说上》:‘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后世遂以‘滥竽充数’指称那些没有真才实学,却要蒙混充数之辈。 庾信这里用此典,是暗指自己原来仕梁时候的优宠。 ‘余庆’句,典出于《周易·乾卦·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庾信这里用此典,是隐指自己仕梁时凭借先世之德的事。‘通德’句,典出于《后汉书·郑玄传》。其传有云:‘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国相孔融深敬于玄,告高密县曰:昔东海于公,仅有一节,犹或戒乡人侈其门闾。矧乃郑公之德,而无驷牡之路。可广门衢,令容高车。号曰通德门。’庾信这里用此典,是喻指其祖父庾易为齐徵士,如汉之郑玄一般位崇德隆。‘赐书’句,典出《汉书·叙传》。其传有云:‘班彪,字叔皮,与仲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庾信这里用此典,是指其父庾肩吾与伯父庾于陵在南朝均有文名,可与班彪兄弟父子相比。‘宣室’句,典出于《史记·贾谊传》。其传有云:‘贾生徵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庾信这里用此典,是说自己仕梁时所受到的知遇之恩。‘长杨’句,典出于汉代扬雄作《长杨赋》之事。扬雄曾为汉武帝郎,常侍武帝,深得汉武帝宠爱,并作《长杨赋》以讽谏武帝。庾信这里用此典,与上句‘宣室’句一样,是暗指自己仕梁时所受的知遇之恩。‘荆轲’句,典出于《史记·刺客列传》。 此传记侠士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知遇之恩,慨然允诺入秦刺杀秦王。临行前,燕太子丹饯于易水之上,荆轲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庾信这里用此典,意在感念仕梁时所受的知遇之恩。‘苏武’句,典出于汉人苏武出使匈奴之事。史载,苏武奉命出使匈奴,其副将张胜参与匈奴贵族的内部斗争,事发投降。而苏武则不为所动,匈奴贵族虽屡欲降之,而终不屈。遂为匈奴拘羁,又迁之北海(今贝加尔湖)牧羊,留二十年不遣还。后汉与匈奴和好,苏武才得以还国。相传,苏武归国前曾与汉降将李陵作别,赠诗中有‘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之句。庾信这里用此典,是暗抒羁宦于西魏与北周而不得回到故国的感伤之情。‘关山’句,典出于古乐府《关山月》。汉乐府《关山月》曲,多写兵士久戍不归与家人互伤离别之内容。庾信这里用此典,是暗写自己羁宦于西魏的乡关之思。 ‘陇水’句,典出于古乐府《陇头歌辞》。其歌有云:‘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庾信这里用此典,与上面‘吴山’句一样,也是暗写自己羁宦于西魏的乡关之思。‘龟言’句,典出于《水经注》引车频《秦书》所记之事。其文云:苻坚建元十二年,高陆县民穿井得龟,长二尺六寸,背文负八卦古字。坚以石为池养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问吉凶,名为客龟。大卜佐高梦龟言:‘我将归江南,不遇,死于秦。’庾信这里用此典,是喻指自己思归江南,不欲如龟之客死他乡。‘鹤讶’句,典见于《异苑》。 其中有文记载云:晋太康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见二白鹤语于桥下曰:‘今兹寒,不减尧崩年也’,于是飞去。庾信这里用此典,是隐指梁元帝被杀于江陵城破之事,有怀念故君之意”(6)吴礼权:《委婉修辞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5页。。庾信赋中所用的12个典故,如果概括归纳一下,“前六个典故,是追忆仕梁时的快乐时光;后六个典故,是叙写羁宦北国异乡的忧苦心情。整个一段所要表达的意思,说白了,就是:‘美好往事成追忆,乡国之思堪白头。’然而,作者没有这样直白地告诉读者,而是通过一系列典故的组合,让人思而得之”(7)吴礼权:《委婉修辞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小园赋》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抒写乡国之思的经典之作,赢得千古无数文人掉头苦吟”(8)吴礼权:《现代汉语修辞学》(第四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6页。,在很大程度上与大量典故的运用有着密切关系。
现代文人也有喜欢以用典手法建构修辞文本的,尤其是在文学创作中最为常见。例如:
面包树的荫凉,在夏天给我们招来了好几位朋友。孟瑶住在我们街口的一个“危楼”里,陈之藩、王节如也住在不远的地方,走过来不需要五分钟,每当晚饭后薄暮时分这三位是我们的常客。我们没有椅子让客人坐,只能搬出洗衣服时用的小竹凳子和我们饭桌旁的三条腿的圆木凳,比“班荆道故”的情形略胜一筹。来客在树下怡然就坐,不嫌简慢。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梁实秋《槐园梦忆》)
上引这段文字,是“梁实秋记其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时夏夜与朋友在家门口纳凉聊天的往事”(9)吴礼权:《现代汉语修辞学》(第四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2页。。众所周知,梁实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儒雅的大学者。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情况,作为大学教授的他,朋友到访,连招待朋友坐的凳子也不够”(10)吴礼权:《现代汉语修辞学》(第四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2页。。这种生活的窘况,不要说是梁实秋这样的大学者,就是一般的中国读书人恐怕也羞于言表。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记述这段往事又不能不提。于是,梁实秋就选择了用典修辞手法,建构了一个修辞文本:“我们没有椅子让客人坐,只能搬出洗衣服时用的小竹凳子和我们饭桌旁的三条腿的圆木凳,比‘班荆道故’的情形略胜一筹”,将往昔窘迫的生活境况“以自我解嘲的笔触婉约地一笔带过”(11)吴礼权:《现代汉语修辞学》(第四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2页。,不仅维护了自己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与儒雅学者的体面与矜持,而且有化尴尬为幽默的风趣”(12)吴礼权:《现代汉语修辞学》(第四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2页。。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效果,完全得力于“班荆道故”四字。它是一个典故,比较生僻,出自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所记这样一个故事:“伍举奔郑,将遂奔晋。声子将如晋,遇之于郑郊,班荆相与食,而言复故。”晋人杜预注曰:“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议归楚,事朋友世亲。”这一典故,经过历代文人的反复使用,后来就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典故义,专指“朋友途中相遇,席地而坐,共话旧情”(13)吴礼权:《现代汉语修辞学》(第四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2页。。其实,梁实秋所要表达的意思,用大白话直说,就是:“朋友到访,没有像样的坐具让客人坐,总比坐在地上好点”(14)吴礼权:《现代汉语修辞学》(第四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2页。。如果真的这样写了,不仅让他本人斯文扫地,也让他的作品读来索然无味了。相反,选择以用典手法建构修辞文本表而出之,则不仅使表意显得婉约含蓄,而且文章读来也别具文采,有耐人寻味的审美情趣。
二、政治修辞与用典文本建构
以用典手法建构修辞文本,不仅是中国古今文人的最爱,也是古往今来中国政治人的最爱。下面我们来看几例政治人的政治修辞文本。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孰察之。(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
上引文字是西汉梁孝王政治幕僚邹阳给梁孝王所写书信的开头一段,大致意思是:臣听说有句话:“忠心之人没有不得好报,守信之人不会被人怀疑。”以前臣常认为此话是对的,现在看来恐怕只是一句空话而已。昔日荆轲仰慕燕太子丹之义,慨然舍身要替他去刺杀秦王,义气干云,遂有白虹贯日之奇观。然而,太子丹却怀疑他迟迟不出发是不愿践诺;卫先生殚精竭虑为秦国谋划灭赵的长平之战,忠义感动了上苍,遂有太白星犯昴星之天象。然而,秦昭王却怀疑、不信任他。荆轲与卫先生的精诚使天地都出现了异象,而他们的忠信却不为二位君王所了解,这难道不是很悲哀吗?而今臣竭尽忠诚,将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希望大王能够了解。可是,大王的左右却不了解臣的忠心,最终还是听从了狱吏审讯的结论,使臣的忠心为世人所怀疑。臣的遭遇,使臣不得不相信,今天即使让荆轲和卫先生重新再活过来,恐怕燕太子丹与秦昭王也是不会醒悟的。希望大王仔细体察臣的冤情。
邹阳是西汉文学家,同时也是政治人。《史记》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记载说:“邹阳者,齐人也。游于梁,与故吴人庄忌夫子、淮阴枚生之徒交。上书而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嫉邹阳,恶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将欲杀之。邹阳客游,以谗见禽,恐死而负累,乃从狱中上书。”可见,邹阳不是一般书生,而是梁孝王的门客,即政治幕僚。他之所以获罪被人诬陷下狱,也是因为同僚之间的政争所致。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与鲁仲连并列作传,说明太史公也认为他不是一般的文学家,而是战国时代的说客策士鲁仲连之类的人物,属于政治修辞学意义上典型的政治人。他给梁孝王所写书信,是为其所受的冤屈辩解,内容无关生活琐事,而是表白自己的忠心与所受冤屈的不公,属于政治话题。因此,这封书信的性质明显是典型的政治修辞文本。
作为政治修辞文本,邹阳这封上梁孝王书的效果如何呢?《史记》记载曰:“书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为上客”,说明邹阳的政治修辞是非常成功的。事实上,邹阳的这封书信确实是非常成功的,表现了政治修辞的高度技巧。我们不必读完全文,仅从上引的开头一段文字,便能管中窥豹。全文第一句“忠无不报,信不见疑”,明明是自己的观点,邹阳却冠以“臣闻”二字,让梁孝王感觉这八个字是来自圣贤或祖宗的见解,使其在权威崇拜与祖宗崇拜的惯性心理影响下第一时间就予以认同。紧接着,突然逆转方向,对梁孝王在心理上已然认同之理予以推翻,说自己“常以为然”的“忠无不报,信不见疑”的公理是“徒虚语耳”(是一句空话)。由此顺势转入自己要表达的主题,为自己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冤屈进行辩解。众所周知,辩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拿出证据。然而,邹阳被梁孝王门客羊胜、公孙诡等人谗言构陷,是找不出证据的,况且他此时人在狱中。那么,如何破解这种终无对证的死局,而让梁孝王相信自己确实是忠信之人而受人陷害,进而解除自己的牢狱之灾呢?邹阳找到了一个好的办法,也是他作为一个满腹经纶的文学家最擅长的办法,就是引经据典,拿历史上的人事来充当逻辑上的论据,以此佐证自己的观点。那么,引什么典故可以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打动梁孝王之心,让他确信自己是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呢?邹阳选择征引了在历史上最有知名度的两个典故:一是荆轲慷慨赴义,为燕太子丹刺杀秦王,却因在等候另一位行动伙伴时而被燕太子丹怀疑,以为他迟迟不出发是不愿践诺;二是卫先生为秦国一统天下的大业而殚精竭虑,替秦昭王谋划灭亡赵国的长平之战计划,在秦将白起大败赵军于长平,正要趁势灭亡赵国,请求秦昭王增兵时,秦昭王却不听卫先生之计,反而听信于应侯范雎的谗言,怀疑白起的动机,迟迟不发兵粮,致使灭赵计划功败垂成。这两个典故所叙之事,离西汉初年时间不算遥远,且属于被证实的信史。邹阳将之择出以为佐证,通过逻辑类比的形式实现了其辩冤自清的证据链接,从而在无需拿出事证的情况下便能让梁孝王在心理上认同其论证的合理性,由此暗度陈仓,顺利实现其政治修辞的目标预期:让梁孝王相信“忠无不报,信不见疑”只是虚语,荆轲、卫先生与自己的遭遇就是证明,希望梁孝王相信他的清白,了解他的忠心与诚信。事实证明,邹阳以用典手法建构的修辞文本是有效的,不仅达到了其辩冤自清的政治修辞目标,而且还赢得了梁孝王的信用,待之为上客。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
孙权大会群臣,……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十九《诸葛恪传》)
上引文字,讲的是这样一个历史故事:东吴大帝孙权一次大会群臣,赐宴饮酒,命诸葛恪担任宴会主持人,劝大家饮酒。行酒到东吴元老张昭面前时,张昭因为先前已经喝了不少,脸带酒色,遂推辞不肯再饮。诸葛恪再三相劝,张昭仍不肯再饮,并说:“你这不是尊老之礼!”孙权听了不乐意,觉得张昭这是在倚老卖老,于是命令诸葛恪说:“卿只要说得好,让张公理屈辞穷,他自然会饮。”诸葛恪听懂了孙权的意思,于是就对张昭说道:“想当年,姜太公辅佐周武王伐纣,开创周朝八百年基业,年高九十还举旗仗钺,冲锋陷阵,也没有说要告老休养。现在,前线有战事,您身为将军,皇上却让您退居在后;朝廷有宴会,皇上却礼请将军于先,这还叫不尊老吗?”张昭被说得哑口无言,于是只好喝尽了诸葛恪所敬之酒。
上述故事中的三个人物,都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人物。孙权是三国时代吴国之帝,东吴基业的开创者。诸葛恪是东吴大将军诸葛瑾之子,是东吴名将与朝中权臣。孙权病危之时,被委以托孤大臣之首的重任。孙亮即位为帝后,加封太傅,执掌军政大权,官拜丞相,爵封阳都侯。张昭是东吴元老,早在孙权之兄孙策创业之时,就是东吴早期政权架构的核心人物,官拜长史与抚军中郎将。东吴所有的文武之事,孙策差不多都委任于张昭。孙策死后,率群僚辅佐孙权,稳定了江东局势。孙权封王后,张昭官拜绥远将军,爵封由拳侯。后孙权称帝,张昭因敢于直谏、性格过于刚正而被疏远。张昭遂以年老多病为由而辞去了官位职事,被孙权改拜为辅吴将军、封娄侯。晚年,张昭曾一度不参与东吴政事。可见,上述故事中的三个主角都是典型的政治人,而且彼此关系非常复杂。故事中的饮酒情节,表面上看是东吴朝廷生活中的花絮,实则是暗潮涌动、机锋毕露的政治博弈。撇开君臣恩怨与政见分歧不论,仅就上述故事中的政治博弈而言,诸葛恪与孙权是得势的赢者,而张昭是失势落败的输者。诸葛恪奉旨劝酒,之所以能让东吴元老张昭吃瘪落寞,从政治修辞学的视角来看,主要是得力于用典修辞手法的运用。
诸葛恪的劝酒语篇,从层次与结构的角度观察,可以分为两个平行层面与结构:其一是“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属用典层面;其二是“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前,何谓不养老也”,属叙事层面。“用典层面说的是:周朝的吕尚(本姓姜,字子牙),有奇才。年七十余,直钩垂钓于渭水之阳。其时周文王将出猎,卜之曰: ‘非龙非彲,非熊非羆,所获者霸王之辅。’文王出猎至渭水之滨,果遇吕尚。与语大悦:‘吾太公望予久矣!’遂号之曰‘太公望’,立为师。后武王尊为师尚父。太公年九十时, 助武王伐纣,秉旄仗钺,指挥万军,灭商而奠周室八百余年江山基业”(15)吴礼权:《唇枪舌剑:言辩的智慧》(修订版),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页。。叙事层面说的是: 昔日张昭辅佐孙策,创立东吴基业有功,号为元老。现在东吴与曹魏、刘蜀逐鹿问鼎,张昭却以年老为由,军旅之事退之于后;今日孙权开席大宴群臣,张昭被尊之为上宾,却抱怨不受尊重。“若将这两个层面分而置于两种语境,则仅是两个客观的叙事语篇,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言外之意。但是,诸葛恪的劝酒语篇则不然。它将用典层面与叙事层面有机地统一于同一语篇之中,由此这一前一后并列的两个层面便产生了强烈的对比与反讽效应。整个劝酒语篇就透露出这样的深层语义指向:吕尚九十高龄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为国效忠,不落人后,精神可嘉;张昭年事不高,却倚老卖老。军旅之事退缩在后,酒食之事一马当先, 反而还要口出怨言,节操不高”(16)吴礼权:《唇枪舌剑:言辩的智慧》(修订版),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页。。正因为诸葛恪以用典手法建构的修辞文本具有高度的技巧,表意虽然温婉含蓄,却又绵里藏针,使张昭不得不喝下被劝的酒,从而顺利地完成了孙权交给的“杯酒显君威”的政治任务。可见,喝酒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喝酒也需要讲政治修辞。
以上说的都是男人们在政争与官场博弈中的政治修辞表现,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例女人的政治修辞表现。
蜀先主甘后……生而体貌特异,年至十八,玉质柔肌,态媚容冶;先主致后于白绡帐中,于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
河南献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侧,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常称:“玉之所贵,比德君子,况为人形而不可玩乎?”
甘后与玉人洁白齐润,观者殆相乱惑,嬖宠者非唯嫉甘后,而亦妒玉人。后常欲琢毁坏之。乃戒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为宝,春秋美之,今吴魏未灭,安以妖玩经怀!凡诬惑生疑,勿复进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当时君子以甘后为神智妇人。(晋·王嘉《王子年拾遗记》)
上引文字,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蜀汉先主刘备的皇后甘夫人,从小就体貌特异,与众不同。年至十八,更是出落得如花似玉,态媚容冶。尤其是肌肤就像玉一般洁白,柔软温润,深受先主刘备喜爱。刘备因为爱其肌肤洁白如玉,常将甘夫人置于白绡帐中,从门外回望,就像是月下聚雪的景观。一次,河南有人给刘备献了一个玉人,高有三尺,跟真人一般。刘备非常喜爱,就将玉人放于甘夫人身后,白天跟将领们讲论军事谋略,晚上就搂着甘夫人而把玩玉人。因怕甘夫人吃醋,常常都会找些说辞,说玉的可贵就像有德的君子,何况有人形的玉就更难得了,怎么不可以欣赏把玩呢?甘夫人与玉人都洁白温润,所有见过的人都几乎分辨不出二者的差别,以致会发生互相混淆错乱的情况。刘备身边亲近宠幸的人,不仅嫉妒甘夫人,也嫉妒玉人。甘夫人因为刘备对玉人太过于沉溺,恐怕他玩物丧志而忘记了恢复汉室大业,遂常有琢毁玉人之念。但是,又不敢贸然为之。一次,得到一个机会,甘夫人就跟刘备进谏道:“昔日宋国贤臣子罕不贪得别人相赠之玉而以为宝,春秋时代的人们都称颂他的人品。而今,孙吴、曹魏未灭,您怎么可以沉溺于妖玩之物呢?以后凡是诬惑令人生疑之物,都不要让人再进献了。”刘备听了这番话,幡然醒悟。于是,立即令人将玉人像撤去了,以前亲近宠幸的小人也被斥退了。当时有见识的君子听说了此事,都认为甘夫人是神智妇人。后来,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称帝于成都,甘夫人被封为皇后。
故事中的甘夫人虽然不是政治家,但却是蜀汉先主刘备之妻,不是普通的妇人。她所进言刘备的事关涉到恢复汉室大业,属于典型的政治话题。正因为如此,甘夫人在进谏刘备的特定情境下便被临时赋予了政治人的角色身份,她劝刘备不要玩物丧志,务必要撤掉玉人、斥退佞臣小人,专心致志于恢复汉室大业的一番话,就成了典型的政治修辞,而不是寻常夫妻之间的闲话家常。从政治修辞学的视角来看,甘夫人的政治修辞之所以奏效,让刘备从玩物丧志的沉沦中幡然醒悟,主要是得力于她以用典手法建构了一个高妙的修辞文本:“昔子罕不以玉为宝,春秋美之,今吴魏未灭,安以妖玩经怀!凡诬惑生疑,勿复进焉!”
我们之所以说甘夫人的用典修辞文本高妙,是因为她所用的典故非常贴切而自然,没有“为修辞而修辞”的生硬感。她所用的典故,对于今人来说也许是比较生僻了,但是对于三国时代的人们来说,可谓是妇孺皆知,社会认同度非常高。其事见于《左传·襄公十五年》的一段历史记载:“宋人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其宝也。’”记载中所提到的子罕,不是普通的政治人物,而是在春秋时代颇具知名度的人物,在宋国更是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正卿(即宋国之相)乐喜。“子罕虽为一国之相,位高权重,却从不以权谋私,而是廉洁奉公,为宋平公所倚重。他不受人之玉的故事,则更是先秦时代中国人津津乐道的美德”(17)吴礼权:《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第二版),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页。。如果我们能够回归到三国时代的历史情境之中,也许更能体会到甘夫人之所以要用“子罕不以玉为宝”这一大众化典故的深意所在。事实上,“甘夫人之所以要搬出春秋时代的子罕来,那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知道,刘备玩物丧志的原因就是因为玉,所以搬出‘子罕不以玉为宝’的典故,对他最有针对性。另外,刘备最倚重的结义兄弟关羽最喜欢读《春秋》,最服膺春秋时代的许多人物,当然包括子罕”(18)吴礼权:《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第二版),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页。。甘夫人作为刘备最宠幸的女人,当然知道刘备最重兄弟之情。刘备曾说过“兄弟如手足”的话,所以,兄弟喜欢的,也一定是他喜欢的。正因为甘夫人“对刘备的心理把握得非常准确,所以一搬出‘子罕不以玉为宝’的典故,立即就镇住了刘备,让他幡然醒悟:要青史留名,要成就大业,就必须学习古之圣人”(19)吴礼权:《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第二版),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页。。今天我们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跟甘夫人的认知也是相同的。可见,甘夫人确实是一个成熟的政治人,其政治修辞能够奏效,也是有原因的。
三、结语
用典,在汉语表达中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修辞手法。从汉语修辞史的视角看,用典修辞法历来最受文人学士青睐,尤其是在文学作品或其他书面语表达中,运用这种手法建构修辞文本更是司空见惯。从修辞实践上看,无论是在自然人的日常修辞中,还是在政治人的政治修辞中,用典文本的建构都是时有所见。不过,在以用典手法建构修辞文本时,政治人与自然人在文本建构的目标预期上是有所区别的。一般说来,在日常修辞中,自然人以用典法建构修辞文本,目标预期往往是为了展现其学识的渊博,或是为了表情达意的含蓄优雅;而在政治修辞中,政治人以用典法建构修辞文本,多数情况下是倾向于追求表情达意的含蓄婉转,以此展现对居于上位的受交际者的敬畏之心,同时也为自己规避政治上的风险留下回旋余地。除此之外,政治人以用典法建构修辞文本,有时还可以借此展现渊博的学识与优雅的风度,进而为塑造自身作为政治人的高雅人格形象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