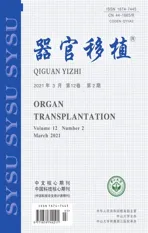多囊肾囊内感染与肾移植
2021-12-31黎雪琳苗芸
黎雪琳 苗芸
常染色体显性多囊肾病(autosomal dominant polycystic kidney disease,ADPKD)是一种常见的单基因遗传性肾病,发病率为1/400~1/1 000[1],主要表现为肾小管上皮细胞来源的囊肿不断地形成并分泌囊液使肾脏进行性增大,肾实质逐渐纤维化,导致肾功能进行性减退。典型患者在中年时期会进展为终末期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肾移植是有效的根治方法。ADPKD在临床中常伴有疼痛、血尿以及囊内感染等并发症,患者一生中可能经历数次囊内感染,抗生素治疗所产生的耐药性问题日益突出。因此,研究多囊肾囊液内的细菌类型、抗生素水平与细菌耐药性等问题,对探寻有效的治疗方案及提高肾移植疗效具有重要作用。
1 肾囊肿起源
ADPKD患者只有1%~3%的肾单位出现病变,但囊肿可以起源于肾单位的任何管状部分,包括近端小管、远端小管和集合管[2]。“二次打击”学说认为,从亲代遗传的PKD1或PKD2杂合子突变(生殖突变)不足以发病,在后天环境因素的“二次打击”下,杂合子正常等位基因也发生突变(体细胞突变)时才会引起囊肿发生[3]。未发病的PKD1+/-食蟹猴模型显示,大多数囊肿首先在远端小管周围形成,这可能反映了ADPKD患者在未发病的杂合子阶段囊肿形成的初始病理学表现,代表疾病的最早表现[4];而在ADPKD疾病快速进展期PKD1-/-小鼠肾脏切片的免疫组织化学(免疫组化)染色表明,最初出现扩张的小管起源于近端小管,而后期大多数囊肿起源于远端小管或集合管[5]。且在疾病后期,起源于集合管的囊肿比其他节段形成的囊肿更严重,体积更大[6]。
囊肿的发育主要涉及两个过程:细胞异常增殖和囊腔内液体积聚。ADPKD中突变的PKD1或PKD2基因所编码的异常多囊蛋白复合物降低了细胞内Ca2+水平,致使细胞内环磷酸腺苷(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cAMP)水平升高,从而激活B-Raf/MEK/ERK、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 以及Wnt/β-catenin 等信号通路,引起细胞异常增殖[7]。细胞内cAMP水平的升高还可导致上皮细胞向囊腔的分泌增多;同时,囊壁上皮细胞高表达囊性纤维化跨膜电导调节因子(cystic fibrosis transmembrane conductance regulator,CFTR)基因,分泌到囊腔内的Cl-增多,使囊腔带负电荷,将Na+和H+吸入囊内,导致囊腔内液体的积聚[8-9]。
2 肾囊肿的分类与囊液来源
2.1 囊肿的分类
以Na+以在囊液和血清中的比值将囊肿分为非梯度囊肿、梯度囊肿及不确定囊肿。其中,比值>0.8的囊肿为非梯度囊肿,比值<0.4的囊肿为梯度囊肿,比值为0.4~0.8或Na+测定量不足的囊肿为不确定囊肿。肾囊肿来源于肾单位的小管部分,其上皮层保持了起源部位的许多组织学特性和功能,其中具有低Na+水平的梯度囊肿可维持典型的远端小管跨上皮溶质梯度,表明其来自远端小管,表现出高Na+水平的非梯度囊肿含有与近端小管液体成分相似的液体,表明其有可能来自近端小管[10]。非梯度囊肿囊液中的Na+、K+、Cl-、H+水平与血清水平基本相等,而梯度囊肿囊液中相关离子水平则远低于血清水平[11]。
2.2 囊液的来源
肾囊肿随小管的囊状扩张而出现,随着囊肿体积扩大而独立于小管[12]。未与小管分离时,囊液来自肾小球滤液;分离后,囊液来自跨上皮的液体分泌。因此,最初的囊液可以认为是血浆超滤液,而后来的囊液则是囊壁上皮细胞自身分泌的水和溶质[13]。囊肿可能来自肾单位的任何管状部分,囊液成分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其管状起源。正常情况下,肾小管可重吸收超过99%的肾小球滤液,囊肿中大量囊液的存在可反映囊壁上皮细胞的重吸收功能异常[14]。
肾囊肿中囊液来源的特点可能有助于解释囊液中不同类型抗生素水平存在差异的现象。由于囊肿不与肾小管相通,囊壁异常增生包裹,囊液大部分来源于跨上皮的液体分泌,因此抗生素运输的主要机制是扩散,脂溶性药物的扩散效果明显,水溶性抗生素则难以渗透进入囊肿,水溶性抗生素和脂溶性抗生素在囊肿中的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导致对ADPKD患者囊内感染进行标准抗菌治疗的效果不佳,病情反复[15]。
Hamanoue等[16]对庆大霉素、妥布霉素、头孢匹林和替卡西林这些常用于严重尿路感染的水溶性抗生素进行研究,分析抗生素的囊液水平与血清水平的差异。实验结果表明,常用的水溶性抗生素的囊液水平远低于血清水平,且非梯度囊肿中抗生素水平远低于梯度囊肿,甚至接近于0。Lantinga等[17]的研究表明,脂溶性抗生素的囊液水平与血清水平的比值均>1,甚至可达到8,水溶性抗生素该比值均<0.5。由此可见,水溶性抗生素的囊液水平远低于血清水平,但脂溶性抗生素的囊液水平则较血清水平高。
因此,在囊内感染的治疗中,应优先选择脂溶性抗生素,其中头孢菌素类、氨基苷类抗生素通常不能穿透囊肿,治疗效果不佳;氟喹诺酮和复方磺胺甲唑对革兰阴性菌具有较好疗效,但复方磺胺甲唑不适用于ESRD患者,因此临床上经常选择氟喹诺酮类药物(如环丙沙星和左氧氟沙星)、复方磺胺甲唑和氯霉素等作为囊内感染的一线抗生素[18]。
3 囊液内细菌类型及其耐药性
3.1 囊液内细菌类型及来源
对囊液内细菌类型的研究发现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最常见,约占75%,与泌尿系统感染情况十分类似。但囊液中也存在泌尿系统感染中较不常见的细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球菌、乳酸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厌氧菌,这些细菌占所有囊内感染致病微生物的15%。囊液内的低氧环境可能导致厌氧菌感染。此外,反复多次的抗生素治疗、引流和手术也可能导致院内细菌感染[19]。
囊内感染的致病微生物类型与泌尿系统感染相似,但同时又存在差异,符合目前对于囊内感染来源的两种理论——逆行感染和血行播散。逆行感染是指泌尿系统的细菌逆行感染囊肿,其理论支持主要是肾脏与泌尿道菌种的相似性及其解剖关系。且由于ADPKD患者多合并肾功能不全、免疫力低下、尿路梗阻、囊肿局部血流量减少和囊液引流不畅,因此肾脏囊内感染的同时常常伴有尿路感染。但尿液培养微生物可能无法反映囊液中存在的细菌,一方面是因为囊肿不与集合管系统连通,另一方面可能是因患者常年服用抗生素使尿细菌培养表现为阴性[20]。
血行播散是指大多数来自肠道的致病微生物,可能从门静脉系统或胆道侵入血流,从而引起囊内感染,其理论支持主要是囊肿不与集合管系统连通,所以尿液培养经常是阴性,而血液培养可能为阳性[21]。既往研究中的一项病例报告显示,1例有静脉注射毒品史的ADPKD患者存在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血症且囊液培养发现了相同的细菌,但尿液培养结果为阴性。ADPKD患者肝脏囊内感染发生率较肾脏囊内感染发生率高,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感染的血行播散[22]。但囊液与血液的培养结果可能也存在差异,这是由于囊肿引流和囊液培养通常在抗生素给药数周后进行,而血液培养通常在囊内感染发生后很快进行,故囊液培养结果通常为阴性,与血液培养结果存在一定差异。通过血液培养检测到的微生物可能反映了引起早期感染的微生物,而通过囊液培养检测到的微生物可能是造成晚期感染的原因。肠道微生物的入侵可能反复发生,抗生素治疗可能导致耐药微生物侵袭[19]。
3.2 囊内感染细菌耐药性问题
不同中心分别对囊液、血液以及中段尿液培养中的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等囊内感染常见细菌进行耐药性检测,结果均提示囊内感染常见细菌的耐药性在囊液、尿液与血液中有高度相似性[22-23]。因此可以通过尿液、血液的分析结果选择敏感的抗生素,减少囊液取样及结果评价的难度。
一项对亚洲17个国家泌尿系统感染患者的病原体和药物敏感性分析表明,环丙沙星的耐药率为54.9%,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为39.0%,头孢菌素耐药率为42%以上。在青霉素家族中,55.0%的病原体对氨苄西林加β-内酰胺酶抑制剂耐药,37.3%对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耐药。在氨基苷类抗生素中,41.4%的病原体对庆大霉素耐药,24.9%对阿米卡星耐药[24]。临床上治疗囊内感染的一线抗生素氟喹诺酮类药物的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表明其细菌耐药性问题突出。引起囊内感染的革兰阴性菌中,大肠埃希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对氟喹诺酮类药物的敏感性极低,因此,医师在临床上进行经验性治疗时,应选择敏感性高的药物,如阿米卡星和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25]。
4 ADPKD患者囊内感染与肾移植治疗
囊内感染是ADPKD患者在ESRD阶段常见并发症。处于该阶段的患者因双侧多囊肾体积异常增大、腹部膨隆、挤压肠道,通常采用血液透析治疗[26]。血液透析过程中肝素钠或其他抗凝剂的作用,会导致血液透析后囊内出血,且往往伴随囊内感染[27]。临床上可见患者出现发热、乏力、腰腹局部疼痛,如破裂的囊肿与集合管系统相通,则患者出现肉眼血尿,同时血象升高呈感染状态。部分患者还有尿量,中段尿液培养结果往往为阴性。此时通常按照经验性用药给予抗生素和止血药物进行保守治疗,感染及出血控制之后,可考虑切除反复疼痛(感染或出血)、经常发病一侧的多囊肾。但患者已发生肾衰竭,凝血功能欠佳,开放手术和腹腔镜手术的风险均较大,切除多囊肾后出现的巨大创面和创腔,在规律血液透析时会加重渗血[28]。进入ESRD阶段的ADPKD患者囊内感染治疗较为复杂,且病情平稳后仍会反复发作,肾移植是较为理想的治疗方案。此时原多囊肾有以下3种处理方式:移植前切除;先切除多囊肾,同期行肾移植;仅行肾移植,保留多囊肾。
若反复发生囊内感染或感染情况较为严重,可考虑在移植前将多囊肾切除或在移植同期切除,以规避术后多囊肾感染灶潜在并发症的风险,更好地控制血压,降低泌尿系统感染率,避免短期内再次手术,提高受者和移植肾的长期存活率。但移植前切除多囊肾会导致患者移植前处于无尿且血红蛋白水平较低的状态,可能导致病死率较高,因此不推荐常规实施,仅适用于严重囊内感染或反复出血、胃肠道压力大或疑似恶性肿瘤、原多囊肾过大导致移植肾缺乏植入空间等情况[29]。相较于移植前切除多囊肾,同期切除可使患者在等待移植期间保留较理想的肾功能和残留尿量,且不会增加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29]。
若多囊肾囊内感染控制较为理想,可以仅行肾移植,保留多囊肾。随着移植肾功能逐渐恢复和稳定,多囊肾的体积会逐渐缩小,高血压、血尿、尿路感染及消化道症状等均会好转[30]。但这种术式不能规避多囊肾感染灶潜在并发症的风险,且由于肾移植术后受者长期处于免疫抑制状态,容易发生囊内感染,表现为发热、乏力,局部疼痛等[31];因肾功能逐渐恢复,凝血功能明显改善,故囊内感染不常伴有出血;血象升高呈感染状态时,尿中白细胞阳性,中段尿液培养可能仍阴性,未能反映囊内细菌感染的情况;囊内感染严重者甚至可出现脓毒血症,导致严重的全身症状[32]。因此,对移植时保留多囊肾的受者,术后需严密监测其移植肾的体积和功能,合理选择免疫抑制方案,防治多囊肾的并发症。对反复感染、并发症严重的受者,除了抗生素治疗之外,可考虑在病情平稳后再次手术切除多囊肾[33]。
5 小 结
综上所述,囊液、血液与尿液所含的细菌类型高度相似但又存在一定的区别,未来的研究可以挖掘三者之间更精确的关系,以提高血液、尿液培养结果对囊内感染诊治的指导意义。目前对囊液的研究多将所有囊肿视为整体进行分析,未来可以考虑将单个囊肿作为研究对象,发掘各个囊肿之间的异质性,利用囊肿的性质对囊内感染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当ADPKD进展至ESRD需行肾移植时,应根据患者的感染情况选择合适的术式,以提高肾移植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