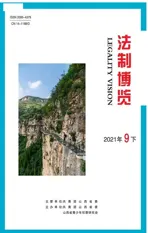自媒体背景下网络谣言的《刑法》治理研究
2021-11-25成瑶笙
成瑶笙
(吉林财经大学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自媒体是一种为个体提供信息生产、积累、共享、传播内容兼具私密性和公开性的信息传播方式。随着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与更新,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等自媒体平台得到了蓬勃发展。在自媒体时代信息呈现爆炸式的增长,同时也为网络谣言的滋生提供了稳定的信息流通条件。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四起,严重污染了自媒体环境,影响自媒体平台的健康发展。不法之人钻法律空子,恶意散布网络谣言,必须要予以《刑法》规制,阻止网络谣言危及社会秩序,营造积极和谐的社会环境。随着网络谣言愈演愈烈,甚至严重污染网络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也接连出台相关法律,治理网络谣言泛滥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减少网络谣言现象,降低网络谣言引发的风险,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中,提出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纳入《刑法》规制范围,要凭借《刑法》的力量遏制网络谣言犯罪行为。即使我国在网络谣言《刑法》规制方面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仍有需要完善之处。
一、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危害
谣言作为一种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言论,在传播的过程中被人利用,便可能会引发负面的网络传播效应,且真正具有危害力的谣言是具有攻击性的,容易产生消极的社会影响。[1]网络谣言在学界虽没有统一的观点,但网络谣言通常被认为是凭借网络平台传播的不实的无中生有的信息,这个信息可以是虚假的,也可能是未经证实的信息。但在刑法学领域而言,《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规定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即“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依据此法律规定可以理解为,《刑法》层面上的网络谣言指的是明知虚假信息却进行网络散布并形成了恶劣影响的信息。自媒体时代网络传播迅速高效,网络谣言传播所产生的危害也是不可忽视的。
第一,从个体角度而言,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严重损害个体利益。因为恶意传播网络谣言,随意捏造虚假信息,对他人进行无端的揣测、谩骂甚至是暴露个人隐私等,对个体造成了心理和生理上的伤害。第二,从社会角度而言,网络谣言若形成一定规模,可能会煽动围观网民的情绪,更有甚者可能会影响现实社会的秩序,危及社会公共安全。第三,从国家角度而言,网络谣言通过自媒体平台传播到世界各地,不实和极端的网络言论,也可能给国家的形象抹黑,在国际上形成恶劣影响。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必须要进行严格规制,杜绝网络谣言的传播,严格打击不法之人传播不实言论。《刑法》作为规制网络谣言的一大手段,必须要贯彻到底,严惩造谣之徒。
二、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刑法》规制现状
(一)网络谣言犯罪主体的范围较窄
我国规制言论犯罪的主体通常限于自然人,但在自媒体时代,独立的个人或是某一单位组织也可能成为犯罪的主体,网络谣言的爆发,可能是一个组织的共同编造和传播的结果,这就说明了我国《刑法》在网络谣言犯罪主体规制方面的漏洞。自媒体时代,具有规模化和组织化的单位,通过输出信息获取流量和利益,在传播谣言方面具有系统的产业链,这也加大了网络谣言传播的范围,扩大了网络谣言的影响,所造成的伤害也是巨大的。但是,我国目前通常按照非法经营罪对单位实施的网络谣言犯罪进行规定,即使是在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这种专门针对网络虚假信息的罪名中都没有将单位纳入犯罪主体的范围。[2]因此,可以看到我国《刑法》在网络谣言犯罪主体界定方面范围较为狭窄,这也影响对网络谣言犯罪的《刑法》规制力度。
(二)网络谣言犯罪的界定标准模糊
我国《刑法》有关网络谣言犯罪的界定,一般采取“新瓶装旧酒”立法模式,认为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并无特殊之处,两者只是犯罪手段和途径有所差异,因此,治理网络犯罪甚至不需要专门的立法,换言之,现有的法律没有专门针对网络犯罪制定的法律,而网络犯罪可以遵循《刑法》规定进行具体处理。[3]但是我国《刑法》并没有对网络犯罪进行特殊的说明和规定,也缺少网络谣言犯罪方面的细则,没有明确的网络谣言犯罪的界定标准,且在审理网络谣言犯罪的过程中,也缺少专门的法律规定,而主要通过对传统罪名进行扩大解释以此来规制网络谣言犯罪。然而在自媒体时代,网络信息传播涉及众多,影响也较为广泛,随着网络谣言犯罪的增多,并且网络谣言犯罪所引起的社会危害和个人危害也严重影响了社会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对社会治理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然而《刑法》却无法精准地解决网络谣言犯罪问题,这就导致法律惩罚与犯罪之间的不协调和不匹配。
(三)网络谣言犯罪的惩罚力度不足
网络谣言犯罪的惩罚力度不足,对不法之人没有起到震慑作用。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惩罚力度偏低。以诽谤罪来说,诽谤罪法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且有期徒刑中只有一个层次的幅度刑。行为人即使造成受害人及其近亲属自杀或者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国家利益等危害结果,最高也只能受到三年有期徒刑的惩罚。[4]违法犯罪成本与获益相比,网络谣言犯罪成本低也给不法之人以身犯险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三、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刑法》规制的完善措施
(一)适当增加部分网络谣言犯罪主体
根据网络谣言治理现状可以知晓,适当增加部分网络谣言犯罪主体,扩大网络谣言犯罪主体范围,是网络谣言《刑法》规制完善的必经之路。一方面,自媒体时代,个体信息传播虽起到助推的作用,但个体的力量远不如训练有素的网络谣言生产与传播的单位,依托网络平台而生的“单位”凭借多元的传播渠道和大量的粉丝团体,能够在短时间内将网络谣言传播到各个平台,从而引起大量网民的跟风与转发,造成恶劣的影响。因此,我国《刑法》网络谣言犯罪规制也需要将“单位”纳入网络谣言犯罪主体部分。另一方面,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和诽谤罪作为网络虚假信息犯罪的两种主要形式,其中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扰乱社会秩序,诽谤罪侵犯个人合法权益,以单位为主体的网络谣言犯罪行为同样对社会和个人造成危害,因此,可以适当增加网络谣言犯罪主体。
(二)推动落实网络谣言犯罪界定标准
网络谣言犯罪界定标准清晰,也能够提高网络谣言犯罪《刑法》规制的效率和力度。以网络谣言诽谤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诽谤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转发五百次”的主体也算作为一般主体。在网络诽谤案件审理过程中,行为主体主要为信息的发布者和转发者,发布者是网络谣言第一发布人,其网络诽谤的主体地位是确定的,但转发者是否能够成为诽谤的主体仍旧存在较大的争议。发布者的诽谤主体地位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出发点是故意为之的,但是跟随的转发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转发造成恶劣影响的也应受到相应的惩处,若是转发者本身了解信息是为他人伪造的,而仍旧选择转发该信息导致谣言影响范围随之扩大,那么可以认定该转发人存在主动诽谤他人的责任。在网络谣言犯罪界定的过程中,还需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分析,但界定网络谣言犯罪标准是《刑法》规制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三)加大网络谣言犯罪《刑法》惩治力度
第一,提高网络谣言犯罪的法定刑。有关诽谤罪的刑罚较轻,而诽谤所造成的受害人的伤害程度较深,罪与罚之间没有得到平衡,因此,需要适当提高诽谤罪的刑罚力度,对造成严重后果的网络谣言犯罪必须要予以严惩。第二,增加网络谣言犯罪的罚金刑。自媒体时代,信息与流量可以变现,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许多不法分子铤而走险,选择以散布网络谣言的方式谋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刑法》应该适当增加犯罪罚金,根据网络谣言所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设立不同等级的罚款。尤其是对犯诽谤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主体普遍增加罚金。第三,增加剥夺网络谣言犯罪者终身权利的刑罚。对传播不实言论影响社会秩序的犯罪主体,予以剥夺终身权利的刑罚,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
四、结语
自媒体时代,虚拟的信息传播环境为不法之人传播网络谣言提供可乘之机,网民可以随意在网络上发布言论,甚至利用不实信息煽动情绪,污染网络信息环境,破坏社会正常秩序。我国《刑法》关于网络谣言犯罪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也取得了实质性的治理效果,但并没有完善的网络谣言犯罪的《刑法》规制措施。因此,在未来治理网络谣言犯罪案件时,还需要根据现有的《刑法》规定,并结合现实的案件情况,合理规制网络谣言犯罪行为,维护个人利益和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