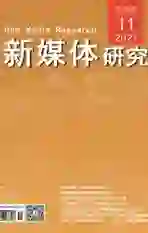技术与遮蔽:海德格尔哲学视域下的算法技术
2021-09-22时盛杰
时盛杰
关键词 算法;海德格尔;技术;集置;遮蔽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1-0020-03
以算法为核心的新媒介技术极大改变了媒介传播形态与社会传播秩序。但是算法媒介却又饱受争议,人们在享受个性化、精确化信息推送服务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算法偏见、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等负面效应。如何看待这一新技术成为了学界的热点话题,本文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出发,探究算法技术的本质、扩张与风险。
德国媒介理论家基特勒曾高度赞扬了海德格尔,认为“只是到了海德格尔时期,对技术媒介的哲学意识才第一次出现,数学与媒介的连接、媒介与本体论的连接也以更加精确的术语而得到阐明”[1]。海德格尔本人虽然并未留下专门的传播学著作,但是其哲学思想却给我们对算法技术的追问提供了启示。
1 集置:算法技术的本质
海德格尔以现象学的视角审视现代技术的本质,他认为“技术之本质也完全不是什么技术因素”[2]。海德格尔并没有将技术的本质归结为某种实体性的要素,而是以 Ge-stell(英文为Enframing,学者译为“集置”或“座架”)作为现代技术的本质。海德格尔认为“集置”是“那种促逼着的要求,那种把人聚集起来,使之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者的要求”[3]。从词源分析来看,Ge-这一词根意为聚集,stell则源于德语stellen,表示摆置、摆放。
可见,海德格尔的 Ge-stell包括了三层含义:一是现代技术的根本性,即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了存在者生存的框架,人们在按照技术的先在框架生活;二是现代技术的普遍性,即现代技术已经完全渗透进入此在的生活之中,人无法游离在技术的“集置”之外;三是现代技术的强制性,德语stellen有“对某人提出要求”之意,Ge-stell所要求的“摆置”与“聚集”带有强制性,一切存在者都要按照技术的要求“摆放”与“聚集”。
“集置”的特点既在于彻底的实用主义,任何存在物都被降格为有用的对象;同时也让存在者自身在这一对象化的过程中将自我也对象化了。换言之,就是海德格尔意识到了现代技术的“异化”——人并没有成为技术的主人而是奴隶。
可以说,海德格尔的论断是对当今算法技术的完美“预言”。算法如今广泛运用于人们的工作生活场景之中,人们被“抛入”算法技术的先在框架之中。普通大众并没有权力编辑算法的程序与规则,只能被动地接受算法程序以做出行为。例如在生產劳动领域,各种CPI考核指标层出不穷,让劳动者深陷其中。2020年9月,《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刷屏社交网络,将外卖员与企业算法系统的矛盾公之于众,呈现了算法技术的“集置”本质。
除此之外,算法技术“集置”本质还体现在社会传播领域。算法传播的个性化推荐产生的“信息茧房”已经在无形地塑造我们的日常观念,甚至已经成为了“生活常识”的最主要来源。而常识往往是人们思考、认识事物的原点,人们在无形之中已经掉进了算法技术的陷阱。人们因为自始至终就生存于这样的数字时代,所以无法做出区分判别,其看待技术的视角也是技术化的。同时算法的重要数据基础都来源于用户自身,用户在享受算法带来的技术便利的同时也在提供数据,实际上将自己对象化、降格化。
2 促逼:算法的扩张方式
算法技术的本质是“集置”(Ge-stell),但是算法技术并非是一种先验存在物,而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的高阶段产物。海德格尔认为“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2],算法技术正是通过“促逼”而入侵存在者的领域。
“促逼”一词的德文为Herausfordern,意为“挑战,挑衅,挑起,引起”。海德格尔用“促逼”一词说明了现代技术的“迫近性”。他认为农民的耕种行为就不是一种促逼,因为他将种子交给自然并耐心等候。而现代技术贯彻着高效、快速、便捷的实用主义哲学,通过“促逼”摆置自然。“促逼”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对自然的压榨,更是人存在状态的转变,“通过促逼着的摆置,人们所谓的现实便被解蔽为持存”[2]。“持存”特指那些被对象化、被榨取、被支配的事物。
作为现代新技术的算法,其“促逼”能力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的工具性促逼;二是社会层面的权力性促逼。
所谓的工具促逼,就是指算法技术凭借其定量化、系统化、精确化的特点击败了传统技术,成为了当代技术中的“显学”。技术时代的人们将世界看作一个与生俱来即可测量与精确认知的,由因果关系相互组合联系的“计算复合体”。精确地认识真理,将哲学“科学化”是西方思想家的普遍倾向。算法的出现与运用无疑让技术乐观主义者看到了认识终极真理的希望。凭借着海量数据、机器学习,算法可以进行精确模拟、分析和预测,算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确在揭示终极真理的道路上击败了其他技术。
而社会层面的权力促逼,则是指算法技术在权力的主导下迅速扩张。有学者提出了“算法即权力”的主张,如英国学者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强调:“在一个媒体和代码无处不在的社会,权力越来越存在于算法之中[4]。”首先,算法本身就是一套运算规则,能够指定规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加之计算机语言的高度复杂性,这决定了算法只能是部分人享有的“权力”而非人皆有之的“权利”。其次,算法长期被笼罩在数字神话的光环之下,具有高度的权威性,表现为一种“软权力”。再者,算法的无处在让人日益“透明化”,在无形之中形成了技术时代的“全景监狱”,让人被动地被驯化。
算法技术通过工具性促逼和权力性促逼不断扩张,实质是一种工具性的合目的论的扩张。海德格尔认识到了技术的“解蔽”并非是流失于不确定性,而是处处得到保障和控制。而控制、保障,正是人们使用算法技术的目的,使算法成为了合目的论的产物。在工具与权力的“促逼”之下,算法成为了“集置”,产生了新的技术秩序并规定着存在者的存在状态。
3 遮蔽:算法技术的风险
技术是人类认识真理、把握规律、改造世界的重要中介,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一种特殊的“解蔽”。海德格尔则将开放领域中的“无蔽”视为真理,“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3]。同时,他认为现代技术在进行强制“解蔽”的同时也造成了“遮蔽”。在现代技术的“集置”中,“人往往走向了一种可能性的边缘……由此就锁闭了另一种可能性”[2]。现代技术带来的危险,就是“在一切正确的东西真实的东西自行隐匿了”[2]。简言之,就是现代媒介技术形成了“被中介的真理”,真理被“遮蔽”了。
在这个“媒介即讯息”的时代,算法技术毫无疑问也在形成一种“遮蔽”,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算法“遮蔽”了人们对于媒介的反思。“追问乃思之虔诚”[2],但是人们长期对技术万能、技术中立的追求已经形成了“技术/数字神话”。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算法技术传递的信息,认为中立客观的算法技术的输出结果是“正确的”。技术规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算法时代的人们往往以算法化的思维去看待算法,关心的只是算法的结果正确与否、算法的效率如何提升。这在海德格尔看来都是一种“遮蔽”,因为这种思维未能触及到技术中立主义的真理观根本——相合性。海德格尔认为追问技术本质应该在与技术领域由亲缘关系但有本质不同的艺术领域进行,因为算法技术追求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确定性、必然性,而艺术则是追求可能性的代表。无限的可能性,才是人应有的存在状态。
第二,算法“遮蔽”了真理。算法具有定量化、精确化优势从而能够揭示真理,这是符合常识的。但是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正在成为对真理的“遮蔽”,算法也不在例外。这主要由于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真理观的颠覆。其一,对于真理与非真理的颠覆。传统观念认为真理的对立面是谬误,人类认知真理的过程就是抛弃谬误的过程。但是,海德格尔并不认为“非真理”就是谬误,而是仍然处在晦暗之中、更为原始的神秘之地,他称之为Gehemnis。而该词的词根heim在德语中是“家”的意思。在技术时代,人们把数学计算的正确结果视为真理,反之就是谬误。这就使得算法技术正在沦为一种强制性、唯一的“解蔽”,这就“遮蔽”了其他的“解蔽”的可能性,甚至遮蔽了真理的原初的源泉。其二,对于相合性原则的颠覆。海德格尔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所认为的“真理是知识和它的对象的一致”[5]的相合性原则。他所问及的是“当我们问及某事物是否是真实的、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真理等问题时,心中所想的东西”[6]。海德格尔注意到了技术时代的真理中介化现象,“真实”与“正确”不断分离。海德格尔认为真理应该是开放无蔽领域的“真实”,而传统真理观只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正确”。算法技术的输出结果毫无疑问是“正确”,但并不一定真实。因为算法模型贯彻了设计者自身的意志和认识,必然在潜意识中忽略某些或大或小的因素,这就导致算法只是对真实的不完全性“拟态”,即中介化的真理。此外,真理的相合性是与“经验”相符,但是算法技术的个性化推荐机制正在塑造一个极其多样的信息环境,这使得每个人的客观经验都不一样。现实生活中也从来不乏有将算法传播的推荐内容作为“客观标准”的现象,如此庞杂的“正确”实际上构成了对“真实”的挤压。
第三,算法“遮蔽”了“存在”。存在问题是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问题,但是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最普遍的、不可定义的、自明的概念,只能通过存在者去把握它。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本性就是“去存在”,即人并非按照某种先在的模板去自我实现,人的本质就是成为自己,人始终是指向未来与可能性的存在。“去存在”人只有处在“本真状态”才能使存在显现。
海德格尔则将语言置于人的存在论地位,做出了“语言说话”的论断,认为“语言是最切近人的本质的”[7]。海德格尔并不将语言看作纯粹的交流媒介,而是存在得以显现的场所,语言规定着人的本质。但是他也提出了人这一“此在”的自始就已“沉沦”,即害怕可能性的境域,混迹于芸芸众生之中。此在以“杂然共在”的沉沦状态来逃避它自己的存在,不断把自己交付给“世界”,为常人所宰治[8]。算法用数据和计算营造了更加庞杂的“常人世界”,人越来越依赖于并倾向于以他人的话语進行表达。算法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再次环境化,让人们寻到了所谓“共同标准”,加剧了人的“杂然共在”。此时“语言说话”的主体就不再是人本身而是算法构建出的虚无缥缈的“常人”。算法技术增加了此在逃避的机会:逃避自我的存在,逃到大家那里去,从而使自己沦落为非本真的存在。
4 结论
从海德格尔哲学思想出发,算法作为现代技术的新发展,同样未能摆脱“集置”的本质,它规定着某一先天存在的技术秩序,将人对象化并降格为有用的“物”。而算法能够如此广泛地运用并渗透入日常生活之中,其扩张方式则是依赖于技术与权力的“促逼”。而“促逼”的后果就是带来了风险,算法在进行“解蔽”的同时也形成了“遮蔽”:算法的“数字神话”无形之中遮蔽着人们对于媒介的反思,算法也遮蔽了真理,同时也遮蔽了本应面向未来与可能性的人的本真状态——“存在”。
但是,海德格尔其实并不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或复古主义者。他并不认为我们在批判技术的同时需要逃避它,也并不怀念着人类历史上的某个“黄金时代”。海德格尔并不能给我们解决算法时代的诸多问题提供具体方法,但是他的反思与追问却给我们提供了可能的救赎道路。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胡菊兰.走向媒介本体论[J].江西社会科学,2010(4):249-254.
[2]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12,16,25,26,37.
[3]海德格尔.存在的天命: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文选[M].孙周兴,编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144,140.
[4]Lash,Scott.“Power after Hegemony:Cultural Studies in Mutation·”Theory,Culture & Society,2007,24(3):55-78.
[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4.
[6]戴维·J,贡克尔,保罗·A·泰勒.海德格尔论媒介[M].吴江,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81.
[7]马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
[8]纪忠慧.高价值言论的法理与哲理[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5):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