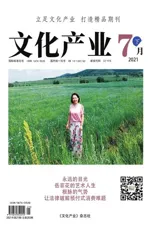永远的目光
2021-09-09本刊专稿王居军
本刊专稿 王居军

因了岁月的洗濯,孩提时代的许多往事,已在记忆中渐渐淡漠,惟有母亲临终时,那满含牵挂而无奈的目光,永恒地烙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如初。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出生在广灵县一个僻远的乡村,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哮喘症。父亲远在大同煤矿下井,一年当中,除了探亲假外,一般很少回家,母亲拖着羸弱的身子,拉扯着我们弟兄俩个,日子过得分外恓惶。那时,我还不到十岁,虽说哥哥只大我两岁,却比我要懂事得多。母亲病重时,哥哥总是很早就起床,扫地擦家,倒灰生炉子,帮妈妈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我小时候特别顽皮,尽管早就醒了,但怕起来干活,便待在床上偷懒。我蒙着头,轻轻地将被子撑开一个缝隙,偷偷向外张望着,只见哥哥先取出一颗生鸡蛋,在碗边磕碎,用筷子边搅动边倒入白开水,鸡蛋泼熟后,洒上白糖,让母亲泡饼干吃。接着,哥哥又抓上几把谷糠加少许玉米面给鸡们煮食,待一切收拾停当,我才装作刚睡醒的样子,伸了伸懒腰,不情愿地离开热被窝,跟哥哥去住在同一小巷的姥姥家吃饭,然后又背着书包一起去上学。
深秋时节,天气渐渐转凉,我和哥哥放学后,常常拿着二齿钉耙和麻绳,去地里刨玉米茬子,或是拿着袋子去树林里搂些杨树叶,晒干后用来煨炕和做饭。我和哥哥小时候在田里拾柴禾的情景,直到现在还常常出现在梦中,那是一幅多么美丽而又迷人的乡村景色啊!秋日的天空,湛蓝而高远。收割后的原野,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清香。晚霞染红了树梢,山雀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吟唱,河里的小水在淙淙地流淌,清澈见底的水流里,时不时会游过几尾活蹦乱跳的鱼儿。我深深地陶醉于眼前这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之中,早就将刨茬子的事情忘到了九霄云外。我一会用树枝去戳水里的小鱼,一会又用土坷垃追打树上的飞鸟,等我玩累了,疯够了,哥哥也早已拾掇好一大堆的玉米茬子,我们将茬子上的土抖尽,码成长方体形状,上下垫着捡来的玉米秸秆,用绳子勒紧,然后,每人一捆,背着回家。那时候,尽管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但有母亲在家,哪怕是卧床不起,我们心里也觉得特别踏实和安全。
母亲本来生就一张鹅蛋脸,身材高挑,模样俊俏,但可恨的病魔无情地吞噬着母亲的健康,母亲每天吃不进几口饭,却在大把大把地喝药,眼瞅着母亲那曾经丰润的双颊一天天消瘦下来,脸色也变得如枯黄的树叶,失去了往日的血色和光泽。母亲虽说身体不好,但特别爱干净,病情稍有好转,母亲就坐不住了,不是打扫家,就是给我们缝洗衣服,将一切家务都料理得井井有条。母亲给我和哥哥做的松紧口布鞋,精致大方,舒适合脚,缝制的衣服、被子,针线细密而又匀称,受到街坊邻里的交口称誉。
母亲对我和哥哥的学习要求甚严,每天放学后,都要亲眼看着我们写完作业,才肯让我们出去玩。听姥姥说,母亲上学时,功课门门优秀,多次被学校评为五好学生。我冬天戴的栽绒棉帽就是妈妈曾经获得的奖品,为此,小伙伴们常常羡慕不已。在那个年代,能戴一顶像解放军叔叔一样的栽绒帽子,实属不易,村里多数人都戴着用山羊猴子皮缝制的棉帽,做工粗糙,样式滑稽,看上去,就像电影《智取威虎山》里的土匪,特不雅观。
母亲不仅生性要强,而且多愁善感,就跟《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差不多。不论做什么,都要倾心尽力做到极致,在常人看来很微不足道的一些事情,往往都能引起母亲的忧虑与愁思。有时候,一家人聚在一起打扑克,每逢出牌,母亲都要寻思再三,生怕自己出错,如果玩输了,母亲会一整天都变得情绪低落。记得有一年中秋节,在空军某后勤部队服役的三舅,特地从外省给我们寄回一盒点心,这在当时的农村可是属于奢侈品。晚上,母亲将月饼、果品放在一个大盘子里,顺便又加了几块三舅给买的点心,摆在院子中央的方桌上,给“月亮爷爷”上供。后来,当我们撤供时,才发现忘了闩街门,点心和供品让人偷去足有一半,那天晚上,母亲心疼得一夜都没睡好。
母亲心地良善,与邻居们相处得特别要好,每次家里改善生活时,母亲都要打发我们先给邻居送去一些,随后,自家人才开始动筷子。因此,左邻右舍的大娘婶子们都喜欢到我家串门,在生活上,我们一家子也常常得到大家的接济和帮助。
由于我和哥哥年龄尚小,病重时,母亲生怕自己失态,会吓着我们,总是咬紧牙关,默默忍受着,实在扛不住了,就想方设法打发我和哥哥出去。那时,我们还不谙世事,竟真的走了,把母亲一个人撇在家里,独自承受着病痛的折磨,我们真傻!
记得有一次,我半夜起来小解,发现母亲正大口大口地吐血,我吓坏了,赶紧去推熟睡中的哥哥,却被母亲拦住了。可怜的母亲见瞒不过去了,便强打精神,一边喘一边安慰我说:“别怕,这种事,妈经得多了,不过是咳嗽震破了毛细血管,吃些药就会好的。”我噙着满眼的泪水,望着面色憔悴的母亲,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和惶恐。
在那个年月里,物资出奇地匮乏。有时,为了弄到几盒维系母亲生命用的青霉素,当“窑黑子”的父亲,不得不四处找关系、批条子,腿都跑细了,药还是常常接济不上,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和控制,母亲的病情变得越来越重了。
一个秋阳暖暖的下午,母亲坐在院子里,抚摸着我和哥哥的头,慢言细语地嘱咐我们:“有一天妈若是走了,你们不要伤心,要听爸爸的话,好好学习,走正路子,多学些本事,长大后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母亲撩起衣襟,擦了擦溢出眼角的泪水,接着说:“凡事多长个心眼,学会自己照顾自己,遇到困难时要想办法克服……”我和哥哥一边流眼泪,一边连连点着头,我们紧紧地抓住母亲的手,依偎在母亲身边,生怕一松开,母亲就会立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那年冬天,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了,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能挽留住她的生命。母亲是大睁着两眼走的。她是带着对我和哥哥的莫大牵挂以及对死神不可抗拒的无奈上路的。
那年,母亲32岁,我刚满10虚岁。
母亲去世后,由于父亲终日在井下作业,实在没时间照顾两个年纪尚小的孩子,便将我和哥哥寄居在姥姥家。我有三个舅舅,两个姨姨,母亲是长女,在姊妹六人中排行老二,大舅最大,六舅最小。姥爷身体一直不好,在我母亲走后的第二年,也不幸病逝。也许是从小没妈的缘故吧,姥姥、姨姨、舅舅们对我和哥哥特别疼爱,尽其所能地呵护着我们,就这样,我和哥哥一直到完成学业、参加工作为止,才跟姥姥分开。
母亲刚离开的那几年,我和哥哥都是结伴去给母亲上坟,每次我们都跪在地上,声嘶力竭地哭喊着“妈妈”,在田地里干活的人们,看着两个没娘的孩子哭得如此可怜,便动了恻隐之心,往往会走过去将我们搀扶起来,并好言安慰,我和哥哥方才止住悲声。
记得母亲过三周年时,正值数九寒冬,哥哥刚好参加考试,姨姨舅舅们又有事都不在家,我只好一个人去给母亲上坟。我们村的坟地一般都在离村子很远的山坡上。那天,天阴沉沉的,西北风夹杂着雪花呼啸而来,吹打在人脸上像针扎一样的疼痛。我边走边四处张望,四野一片苍茫,空无一人,我好不容易跌跌撞撞地来到母亲坟前,摆好供品供菜,跪在地上点香烧纸时,却怎么也点不着火,风刮得田里的玉米杆子哗哗作响,一阵旋风迎面吹来,枯叶碎屑被风旋到空中一圈一圈地打转。眼前的情景,使我不由得联想起老人们讲的那些吓人故事,我突然感到十分的恐惧,心跳急遽加快,仿佛随时都有可能从高高的田埂后面扑出一只饿狼来。最后一根火柴划完了,也未能点着个火,我顾不上再讲究什么了,匆忙收拾好供碗、供筷,㧟着竹篮,连滚带爬地往村里跑去。

由于母亲走得早,村里人对我和哥哥格外关照,生产队分东西时,人们总是争先恐后,乱作一团,但只要队长站在高处一喊,谁也不要拥挤,先让俩孩子领,于是,大家马上安静下来,纷纷给我和哥哥让路。多年以后,每当我回想起这一幕幕往事时,总会被纯朴善良的乡亲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日子在不经意间一晃而过,转眼之间,40多年过去了,伴随着“没妈的孩子像根草”这支忧伤的曲子,我在远离母爱的荒原上,艰难地跋涉。颓废时,想起冥冥之中,母亲那牵肠挂肚的目光,便会于陡然间平添一种无形的力量,鞭策我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同多舛的命运进行一次又一次顽强的抗争。
值得告慰母亲的是,在经历了生活的凄风苦雨之后,我们渐渐地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哥哥大学毕业后,在机关工作,我上完中专,被分配到化工行业。现在,我和哥哥的孩子们也都学有所成,走上了工作岗位。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业余创作,稿件常常被各地报纸、杂志和网络平台采用,并多次获奖。成绩面前,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为,在我的身后时时刻刻都有一束关注我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