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之所在
2021-08-26聂震宁
聂震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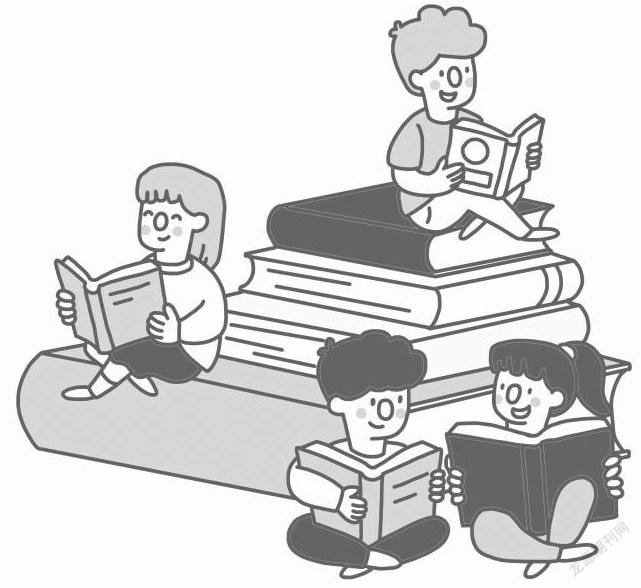
说到读书之所在,首先想到的是书房。
说到书房,中国人的传统中较之于欧美人显然要讲究得多。就拿称谓来说,欧美人称书房很是直白简单,英文直称为“book room”,再大一些的书房就称为“library”(图书馆)。而汉语中的书房称谓,则不一而足,如“斋、轩、阁、楼、堂、馆、房、庐、庵、居、室、园、舍……”可见汉字的层次感、多样性要优越于许多别种文字。
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书房称谓不仅多样别致,更值得玩味的还在于许多置于这些称谓前的书房名号。
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书房名号来说吧。“陋室”,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书房名号,一篇《陋室铭》,让诗人高洁的情愫和超然的情怀传诵古今。“老学庵”,是南宋诗人陆游晚年的书屋名称,一看就知道取“师旷老而学犹秉烛夜行”之意,宣示“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聊斋”,自然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的书房了。作家在路边设座,招待路人烟茶,以备歇脚聊天,凡听到有趣的故事传闻,便回“聊斋”整理成文,加以想象,写成小说,于贫困中写作达20余年之久,著成“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的孤愤之书——《聊斋志异》。“饮冰室”是梁启超的书房名,语出《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吾其内热舆。”以此表达个人读书思考解惑的愿望。“北望斋”是作家张恨水在抗日战争中对自己书房的命名,寄托对故乡的怀念和对抗战早日胜利的希望。最为土俗而怪异的书房名号是“琅環福地”,这是天上玉帝的书房名,典出元代奇书《琅環记》。书中杜撰天上玉帝有书房,“每室各有奇书”“历观诸室书,皆汉以前事,多所未闻者,问其地,曰:琅環福地也。”《现代汉语词典》里就收有“琅環”一词,专指“天帝的藏书处”“天帝的书房”。
为书房选择高雅追求的名号,表明读书人高度珍视自己的读书所在。拥有书房,一直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和追求。梁实秋先生撰文称:“书房,一个多么典雅的名词!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一个书香人家。”我们常常看到,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家,稍有能耐觅得栖身之所,但凡家中有希望读书的成员,总会想到开辟出一处,建设成一个书房来。哪怕是一套“陋室”,只容纳得下一家人睡觉吃饭,只要家中有人读书识字,但有一点可能,主人也会尽其所能,特辟出一个与书相关的角落来。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介绍当代作家赵丽宏称自己的书房为“四尺斋”,状其逼仄,令人感叹。我还没来得及请教丽宏兄此“四尺斋”的年代,估计是早年间的住宅吧。
既然说到读书之所在,那就不会只局限于书房一隅。古代名人常在山水之间留下读书足迹。前几年去江西,南昌西湖边上有一景致称为“孺子亭”,是为纪念东汉高士徐孺子在此读书而建。徐孺子姓徐名稚,字孺子。徐孺子是东汉豫章南昌人,相傳一生博学多识而淡泊名利,豫章太守陈蕃极为敬重其人品而特为其专设一榻,去则悬之,别人不能享用。王勃的名篇《滕王阁序》中便有“人杰地灵,徐孺子陈蕃之榻”这不朽的名句,传为千古佳话。后人为了纪念这位贤人,在徐稚当年读书处修建了一座纪念亭,初时冠以“孺子台”之名,三国、西晋、隋、唐、宋等朝都曾进行兴修或重建,并先后更名为聘君亭、思贤亭,最后以孺子亭命名至今。庐山上有一处颇为著名的读书名胜——白鹿洞书院,原址是唐代诗人李渤兄弟曾隐居读书的地方。后来李渤就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旧地重游,于此修建亭台楼阁,疏引山泉,种植花木,成为一处游览胜地。由于这里山峰回合,形如一洞,故取名为白鹿洞。至五代南唐升元年间,后人曾在此建立“庐山国学”,宋代初年,经扩充改建为书院,定名为白鹿洞书院。庐山还有一处读书名胜,即南唐李璟做太子时读书的地方,筑成了一处读书台。那读书台坐落在如今被游客称为庐山最美处的山南秀峰景区。遥想古人背依大山,看云卷云舒,研读古今贤人传世经典,吐纳开阔山野丰富的负氧离子,真是最为绿色最为低成本的文化享受。
图书馆则是现代人最应该利用的读书所在。相传老子进入周王朝宫中,被周景王任命为守藏室之史,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馆长,在周朝的图书馆里,老子写出了流传至今的《道德经》。马克思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读书和写作《资本论》的故事,至今仍为游客所津津乐道。青年毛泽东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在那里他读了许多影响其一生的中外名著。当代哲人顾准先生,在他最为艰难的岁月里,就是凭借在北京图书馆的借阅进行自己的读书和思考。现今大中城市漂着千千万万的务工青年,他们在工棚、租借房里自然不可能有书房,他们读书最应当去的地方就是当地的图书馆。
去图书馆借阅要稍微麻烦一些,因此,在我看来,当下最为便利的读书所在还是书店。我读初中时,没钱买书,就经常放学后去县新华书店读书,北京话称之为“蹭读”。“蹭读”的时间长了,我也有被售货员驱赶过。安徽桐城派后人舒芜先生曾回忆,抗战时期,他和许多青年流落重庆,书店就成为这些“蓬头垢面”流浪青年“蹭读”的地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总编辑徐惟诚先生对我说过他少时在书店“蹭读”的经历。徐先生早年家住上海,少时家贫,他常常在星期天怀揣一个冷馒头,从徐家汇去往设在复兴路上的生活书店看书,因为无钱乘电车只能徒步走很长的路。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书店宣示要竭诚为读者服务,故而从不驱赶“蹭读”者,致使徐先生当时能够在书店里饥餐馒头,饱读终日,直到书店打烊才作罢。老先生说,为此至今还感激邹韬奋先生和他的生活书店。
现在的书店也都开架服务读者,对“蹭读”者也越来越友善。2012年7月24日的《中国新闻出版报》头版载文《书店变成阅览室——青少年暑期阅读环境调查》,文称:“在京城各大书店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书架之间、过道边沿的空地坐满了捧着书的孩子们,大点儿的孩子独自或结伴而来,小点儿的则由父母陪着,营业员们推着车,四处搜索找不到‘家’的书。”文章比较生动详细地介绍了书店善待读者“蹭读”的事例,令我很是感动。在书店里“蹭读”,还不时会有一些读书以外的收获。譬如,不少稍微大一点的书店现在经常举办敞开式的专家作者新书讨论会,读者们不费事就可以在现场“蹭读”其书、“蹭观”其真人、“蹭听”其高论,实则是一番丰富的文化享受。
责编:王晓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