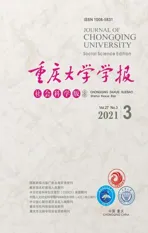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型动力机制与传导路径研究
2021-06-21曾德珩陈春江杜永杰
曾德珩,陈春江,杜永杰
(重庆大学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重庆 400044)
随着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建筑业蓬勃发展,建筑农民工数量持续增长。《2018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8 836万人,其中建筑业农民工占18.6%,仅次于制造业的27.9%。我国建筑农民工普遍存在流动性大、老龄化严重、技能素质低、合法权益无法有效保障等问题,严重阻碍着建筑业的持续健康发展[1-2]。2017年11月,住建部颁布的《关于培育新时期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中级工以上建筑工人要达到1 000万人,要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建筑业产业工人大军。
推进建筑农民工(1)本文所指的“建筑农民工”,是指从事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型需要实现其职业身份与社会身份的双重转化。建筑农民工的职业身份具有“工”和“农”的二元结构特征[3],需要将“半工半农”的非稳定状态转化为职业化水平较高的工人身份;建筑农民工的社会身份也具有“亦城亦乡”“非城非乡”的二元结构特征,属于城市边缘人[4],需要保障其享有平等的市民权。所以,建筑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型的本质是建筑农民工职业化与市民化并举的动态过程。通过借鉴已有农民工职业化及市民化研究,本文综合分析建筑农民工产业工人化转型的影响维度,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以厘清不同结构要素对建筑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作用效应,探索建筑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型的有效路径。
一、文献回顾与述评
农民工职业化是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经过市场竞争,成为具备一定从业技能和职业资格的新型产业工人,农民工职业化是实现建筑产业转型、创新驱动发展的人力资本保障。农民工面临着自身素质低、二元分割劳动力市场制度、城市歧视性用工政策等困境[5],制约了农民工职业化的推进。冯虹和沈自友提出建立人力资本投入机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构建职业化就业体系[6]。沈自友和陈井安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提出实现农民工职业化的路径选择[7]。崔晓明基于“交易成本”视角,探讨建筑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化道路及职业化突破路径,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化水平受到个人素质方面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从业时间,行业特征方面的技能培训情况、年收入状况及工作强度,制度环境方面的合同签订、社保参与及专职化程度等的影响[8]。杨秀丽、李录堂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农民工职业化的影响因素,发现文化程度、月平均收入、劳动合同等因素对农民工职业化具有一定的影响[9]。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向市民转变时,获得并运用市民权的基本资格和能力,适应城市并具备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现阶段,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主要聚焦于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其一,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研究。农民工市民权缺失主要表现为非正规工作、社会保障的有限性与不平等性、政治参与和利益代表不足、家庭分离的居住形式、平等教育权的缺失[10-12],农民工市民化的出路在于外部“赋能”与自身“增能”。刘小年分析市民化政策的执行效果,发现农民工落户城镇面临着户口迁移手续繁琐、城镇社区排斥、乡村社区农地等财产权利保全等问题,影响农民工落户城镇的进度和质量[13]。黄佳豪基于社会排斥视角,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福利和空间等多重困境,并从功能性排斥与结构性排斥路径分析其运作机制[14]。其二,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姚植夫和薛建宏基于资本和认知视角,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家乡及家庭的经济水平等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15]。赖作莲等采用层次分析法,基于居住条件、经济状况、职业发展、社会关系、基本权利和心理认同等6个维度构建评估指标体系,测算多个城市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以探讨不同地区农民工市民化差异和影响因素[16]。李练军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农民工融入中小城镇的市民化能力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和土地处置方式对市民化能力影响最为显著[17]。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导致城市内部严重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农民工在子女教育、就业、医疗、养老和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已极大阻碍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18-19]。
首先,子女教育制度。虽然2018年我国农民工随迁子女幼儿园与义务教育阶段的就读率较高(分别为83.5%与98.9%),但是本地升学难、费用高依然是进城农民工家长反映最多的教育问题[20]。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拨付的依据是“户籍人口”,在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制约下,农民工流入地政府会制定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就学接纳标准,要求出具繁杂的入学证明,或通过收取赞助费、借读费等转移当地政府的教育财政支出[21]。此外,随迁子女大部分就读于政府指定的农民工子女入读学校,其教学质量通常处于当地教育的较低水平。
其次,就业制度。农民工长期徘徊在城乡之间,大多在次属的低级劳动力市场流动就业,难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就业权益与失业保障。由于城镇管理部门明确要求农民工办理务工证、暂住证等诸多证件,缴纳各类管理费用,致使农民工流动就业成本较高,提高了流动就业门槛[22]。同时,农民工还遭受着劳动安全条件差、劳动保护缺失、职业病和工伤事故比例高等危害,工作环境较为恶劣[23]。
再次,社会保障制度。我国部分城市已逐步为农民工提供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但是农民工普遍存在参保比例低、参保受益少、转保难度大、退保比例高、退保受损大等问题[24]。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统筹单位为省(区、市),不同单位的社会保障政策不统一、费率不统一,使得农民工社保跨地区转移与接续困难,无法适应其流动性大、工作转换频繁的特点。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民工跨地区就业时,往往由于保险档案不能顺利转移而只能退保[25]。
最后,住房制度。2018年,我国进城农民工的租房居住比例为61.3%,单位或雇主提供住房的比例为12.9%,仅2.9%能享受保障性住房[19]。其中,大部分农民工聚居于城乡结合处或城中村,或选择蚁族式群租,基本上以单位宿舍集中居住与租赁居住为主,居住环境不佳,人均居住面积低,配套设施较为简陋[26]。此外,城市住房保障一般以本地户籍为申请基本条件,使不具备本地户籍的农民工被排除在保障性住房体系之外[27]。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主要聚集于农民工市民化,其中又以制造业农民工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建筑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的相关研究仍停留在概念框架层面。因此,本文基于问卷调查结果,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建筑农民工产业工人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具体分析建筑业发展水平、建筑企业用工管理、政策制度环境、建筑农民工人力资本、建筑农民工职业化水平与市民化水平6个外因潜变量对建筑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程度的影响,以期为建筑农民工转型提供有效建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模型
建筑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型,本质是其职业身份与社会身份的转化,是建筑农民工职业化与市民化并举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是涉及多元主体的系统工程,行业、企业、农民工等主体均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与建筑农民工人力资本及政策制度环境密切相关。所以,本文通过借鉴已有农民工职业化与市民化研究成果,依托于住建部《建筑业农民工向产业工人化转型顶层设计》课题的问卷调查结果,构建了建筑农民工产业工人化转型的动力机制模型,见图1。

图1 建筑农民工产业工人化转型的动力机制模型
(二)研究假设
1.建筑业发展水平
建筑业发展水平是建筑企业用工管理的前因变量。已有研究表明,建筑业发展水平显著影响建筑农民工的职业化水平,进而影响其产业工人化程度。吴书安等[28]、李亚静和刘玉明[29]、黄居林[30]等学者认为建筑行业的总体工作强度、安全保障与行业结构等的改善,有利于提升建筑农民工职业化水平,促进其产业工人化转型。与此同时,建筑业实行的不同制度,如转包分包制、包工头制度、工程总承包制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建筑企业对农民工的使用模式与工资发放方式[31]。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建筑业发展水平与建筑农民工职业化水平呈正相关。
H2:建筑业发展水平与建筑企业用工管理呈正相关。
2.建筑企业用工管理
建筑企业用工管理在建筑农民工产业工人化转型中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建筑企业的用工状况影响着建筑农民工的职业化水平。企业的职业发展激励、劳动权益保障、职业技能培训共同影响着农民工的职业化意愿[32];建筑企业的工资发放及劳务合同签订情况也会影响建筑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间接影响其职业化意愿[33]。另一方面,建筑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企业用工管理密切相关。企业层面的技能培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匹配性,有利于提升农民工的专用性人力资本[34];建筑企业的职业晋升机制则是建筑农民工积极提升人力资本的内在驱动力[35]。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建筑企业用工管理与建筑农民工职业化水平呈正相关性。
H4:建筑企业用工管理与建筑农民工人力资本呈正相关性。
3.政策制度环境
农民工的就业、社保、住房及教育等社会保障状况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因此相关政策制度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因素[35]。地方政府将户籍作为一种资源,仅少数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和经营才能的农民工才能实现市民化[37]。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城市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制度都将农民工排斥在城市资源配置体系之外,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25]。与此同时,根据农民工面临的现实困境,李仕波和陈开江提出构建覆盖农民工群体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改革创新公共服务制度,剥离公共服务的户籍绑定属性[38];吴庆国提出“就业政策的倒逼机制”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以提高其人力资本[39]。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5:政策制度环境与建筑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呈正相关。
H6:政策制度环境与建筑农民工人力资本呈正相关。
4.建筑农民工人力资本
建筑农民工的职业化与市民化都与其人力资本状况密切相关。农民工个体因素中的年龄、教育程度和月平均收入等人力资本状况均对农民工职业化意愿有一定的影响[9]。与此同时,陈昭玖和胡雯基于人力资本迁移理论,提出受过良好教育、有专业技能、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市民化[40];梅建明和袁玉洁认为农民工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生活状况等因素能够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41]。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7:建筑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建筑农民工职业化水平呈正相关。
H8:建筑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建筑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呈正相关。
5.建筑农民工职业化与市民化水平
建筑农民工的产业工人化转型应实现其职业身份与社会身份的同步转化。建筑农民工的职业身份具有“工”和“农”的二元结构特征[3],需要将“半工半农”的非稳定状态转化为职业化程度较高的工人身份;建筑农民工的社会身份也具有“亦城亦乡”“非城非乡”的二元结构特征,属于城市边缘人[4],需要保障其享有平等的市民权。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9:建筑农民工的职业化水平与产业工人化水平呈正相关
H10:建筑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与产业工人化水平呈正相关
三、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问卷设计
根据建筑农民工产业工人化转型的动力机制模型,本文设计了中国建筑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动力机制的调查问卷,建筑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程度(IWL)的影响因素为6个外因潜变量,分别为建筑业发展水平(CID)、建筑企业用工管理(CEE)、建筑农民工人力资本(CWH)、政策制度环境(PSE)、建筑农民工职业化水平(CWPL)及建筑农民工市民化水平(CWCL)。每个潜变量设有1~7个题项,共29个题项。问卷涉及的题项借鉴大量国内外学者关于建筑农民工及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并通过小规模访谈消除题项的不明确和不全面之处,最终得到各潜变量的测量题项(见表1)。本文的评分尺度采用5级Likert量表,从“5”到“1”分别表示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重要、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

表1 中国建筑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动力机制的验证要素量表
(二)数据来源
本次问卷调查采用两种方式收集问卷数据,累计发放调研问卷350份,其中有效问卷312份,有效回收率为89.14%。第一种是现场回收,调研对象是建筑企业与建筑业科研单位的工作人员。其中,大多数调研对象具备建筑企业或建筑相关行业从业经验,能反映建筑业实际需求。该方法累计发放问卷150份,有效问卷144份。第二种是通过问卷星网站的网络问卷调查,调研对象主要是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科研单位的工作人员。该方法累计发放问卷200份,有效问卷168份。
四、数据分析
(一)信度检验
变量测量的信度检验可以确保模型拟合度评价和假设检验的有效性,Cronbach α系数是使用最普遍的同质性信度检验方法。Churchill提出,如果指标相关度(CITC,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小于0.5,则须删除该指标;如果Cronbach α值大于0.6,说明指标可靠性满足要求,否则应当予以删除;如果删除某一题项后的Cronbach α值大于原Cronbach α值,也应予以删除。表1中,所有题项的CITC值均大于0.5,6个潜变量的Cronbach α值均大于0.7,说明样本数据的信度较高。此外,各个题项“删除题项后的Cronbach α值”(具体数值未在本文呈现)均小于原“Cronbach α值”,所以保留建筑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动力机制测量量表的所有题项。
(二)效度检验
探索性因子分析中,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KMO样本测度及巴特莱特球形检验(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以检验是否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调查问卷中29个量表题项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KMO值为0.886>0.50,且显著性水平为0.000<0.001,因此该量表适合因子分析。

表2 测量量表的效度检验
未旋转的因子载荷一般不能明确呈现各个因子代表的真正含义,所以本文采用Kaiser标准化正交旋转法,旋转后的因子载荷见表3,其中空白处表示因子载荷小于0.4。结果显示,各个题项的交叉负载程度较低,且每个潜变量的因子载荷均超过最低可接受水平0.5,因此各个题项的归类符合理论预期,测量量表整体拥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表3 旋转因子成份载荷矩阵表
(三)模型假设检验
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只能通过观测变量间接反映,无法被直接观察或测量,即属于潜变量。传统统计分析方法一般只能有效处理一个潜变量,因此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该方法可以同时探索和分析若干潜变量,允许因变量与自变量存在测量误差。本文利用Amos17.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性分析,以验证假设模型与数据的一致性程度,结果见图2。

图2 建筑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注:虚线表示变量间的作用关系不显著,实线表示作用关系显著;箭头指向表示变量间的作用方向
1.模型的外在质量评价
整体适配度指标包括绝对适配度指标、增值适配度指标和简约适配度指标,用以衡量模型的外在质量,结果见表4。在绝对适配度指标中,卡方值为0.206>0.05,满足要求;卡方与自由度之比为1.062<3,满足要求;拟合优度指数为0.927> 0.9,满足要求;调整拟合优度指数为0.850>0.8,满足要求;近似残差均方根为0.018<0.08,满足要求。在增值适配度指标中,比较拟合指数为0.993>0.9,满足要求;规范拟合指数为0.901>0.9,满足要求;不规范拟合指数为0.918>0.9,满足要求。简约适配度指标中,简约拟合优度指数为0.666>0.5,满足要求;简约规范拟合指数为0.772>0.5,满足要求。因此,根据各个指标与参考值的比较结果,结构方程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为理想。

表4 模型整体适配度指标
2.模型的内在质量评价
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和平均方差变异抽取量是结构方程模型内在质量的主要评价指标。如果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大于0.60,或平均方差变异抽取量大于0.50,表明模型内在质量较好。由表5可知,6个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均大于0.60,且平均方差变异抽取量均大于0.5,说明模型具有良好的内在质量。

表5 模型内在质量评价
(四)模型实证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的各路径系数、T值和假设检验结果见表6。建筑业发展水平对建筑企业用工管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当建筑业推行工程总承包模式、加强工业化建造、降低农民工工作强度时,将推动完善建筑企业的劳务合同签订、工资发放及技能培训等,所以验证了假设H1;建筑业发展水平对建筑农民工职业化水平无显著影响,表明假设H2不成立。建筑企业用工管理对建筑农民工人力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建筑企业的职业晋升通道、技能培训、劳务合同签订与工资发放方式等的完善,有利于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验证了假设H4;然而,建筑企业用工管理对建筑农民工职业化水平无显著影响,表明H3不成立。政策制度环境对建筑农民工人力资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政策的改革与完善,有利于提升建筑农民工的健康人力资本,验证了假设H6;同时,政策制度环境与建筑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即更加完善的住房、社会保障及教育等政策制度有利于提高建筑农民工市民化水平,验证了假设H5。建筑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其职业化水平和市民化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即建筑农民工的人力资本越高,建筑农民工的职业化水平与市民化水平就越高,验证了假设H7与H8。建筑农民工产业工人化转型受到其职业化水平与市民化水平的正向作用。总体上,建筑农民工的职业化水平越高,其产业工人化水平就越高;建筑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越高,其产业工人化水平也越高,验证了假设H9和H10。

表6 标准化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
综上所述,建筑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与职业化水平是其产业工人化程度的直接前因变量;建筑业发展水平直接作用于建筑企业用工管理,而建筑企业用工管理、政策制度环境共同直接影响建筑农民工人力资本;建筑农民工人力资本作用于其职业化水平和市民化水平的提升,政策制度环境直接影响建筑农民工市民化水平。
五、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需要推动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及住房制度等的改革。其一,户籍制度。坚持积分落户政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适当放宽建筑农民工落户条件,简化落户手续;制定适用于建筑农民工的落户政策,如为具备专业技能的农民工开辟绿色落户通道。其二,就业制度。加强以“技能+安全知识”为核心的建筑农民工职业培训,注重社会文明素养培训与技能培训并举,建立并完善建筑农民工的严格职业准入制度与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提高建筑农民工维权意识,加强监督建筑企业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不定时抽查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安全管理与劳动保护。其三,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将原有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至全部建筑农民工,降低申请门槛,简化申请流程,缩短申请时间;推行强制社会保险政策,实行政府、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加大社会保险的宣传和推广;建立全国社会保障登记制度,积极推行社会保障转移制度,尤其是异地就医报销制度,实现社保跟人走。其四,教育制度。改革教育拨款政策,取消借读费制度,降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入学经济负担;建立义务教育登记卡制度,即随迁子女可依据登记卡就近入学,避免就学歧视和拒绝入学问题;建立适合随迁子女的学校,扶持民工子弟学校。其五,住房制度。改革住房保障和补贴政策,将原有保障性住房体系覆盖至具备稳定经济收入的建筑农民工,给予家庭成员较多且收入较低的建筑农民工一定的住房补贴;解决建筑农民工公积金异地转移困难等问题,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简化提取手续。
第二,建筑业发展状况是建筑农民工产业工人化转型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其一,推广工程总承包模式,完善工程总承包管理体系,加强工程总承包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工程总承包模式的示范引导作用。其二,建立实名制管理信息一体化平台。建立统一的“政府—建筑企业—工人”实名制管理信息系统,制定实名制管理办法与标准。其三,发展专业分包与小微型专业制造企业。引导劳务企业与中小型施工总承包企业走专业化发展道路,鼓励包工头转型创办小微型专业分包公司,严禁专业制造与专业分包企业进行劳务分包。
第三,企业是建筑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实践场所。其一,推行薪酬总付一体化。推动全费用工资的薪酬结构,即“基本工资+奖金+保险+福利+津贴”,建立以个人为单位的强制劳动保险制度;实行规范的用工管理,实现标准的合同化工资价格核定;推动银行代发工资制度,明确由施工总承包企业对农民工工资支付负责,取消分包企业的参与,解决建筑农民工的欠薪问题。其二,推广简易劳动合同示范文本。制定统一的建筑业简易劳动合同示范文本,动态检查简易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立法保障简易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其三,拓宽建筑农民工职业化晋升路径。建筑企业除培养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外,还应建立合理的考核标准、健全职业化激励制度,为建筑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提供路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