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驰“无厘头”电影中的“无”之审美蕴含
2021-05-27王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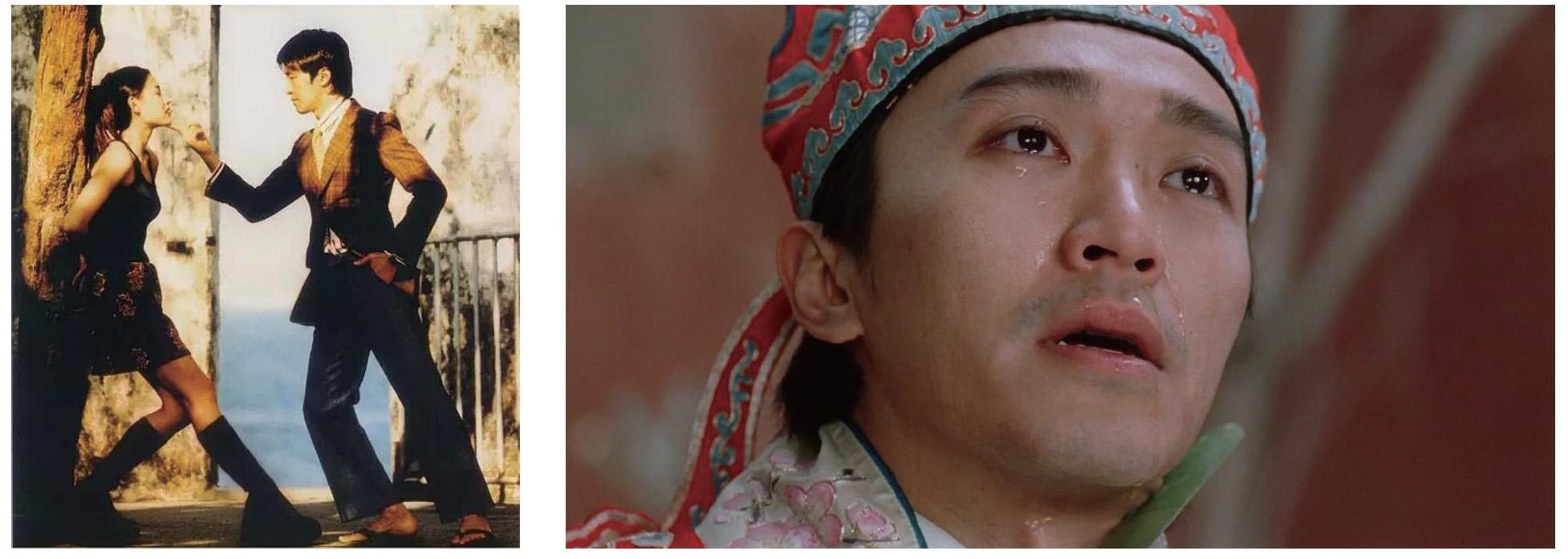
摘 要:周星驰电影以“无厘头”式表演方式和语言表达、情节编排为主要风格,电影语言诙谐、通俗、夸张、无深度甚至粗俗;在电影情节上以突破常规的叙事模式,打破逻辑枷锁,达到“无”之乐趣。在电影叙事上,周星驰解构传统爱情叙事、英雄叙事,以小人物叙事、戏仿叙事、狂欢叙事获得后现代语境中的大众青睐,获得“无”之美感。其喜剧在存在主义哲学理论视域中完成自我,以上述特征最终达成“无”之超越、“无”之自由,在荒诞中显现存在的真实,在笑声中自我超越,展现出了周星驰“无厘头”电影独一无二的“无”之审美蕴含。
关键词:周星驰;无厘头;喜剧;解构;后现代;荒诞
周星驰电影独具匠心的喜剧风格使其成为一代经典,其突破传统的电影模式,抛弃以往喜剧的固有套路,形成独具一格的叙事方式和喜剧风格——“无厘头”。关于其喜剧中“无厘头”风格的审美研究,刘鹏燕在《“无厘头”与现代喜剧之旅》[1]中从三个方面阐发“无厘头”电影的喜剧观念及其表达特点。唐果在《论周星驰电影的喜剧风格与审美意义》[2]中提到“无厘头”式的语言风格以及语言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刘腾在《周星驰电影与后现代主义文化》[3]中将“无厘头”的表现方式簡单分为八种,如:幻觉、男扮女装、恶搞,等等。高字民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解构与狂欢——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电影的阐释》[4]中,从法国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和前苏联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来分析周星驰电影的喜剧性特征。本文主要从电影风格、语言风格、叙事风格分析周星驰喜剧所蕴含的虚无美以及“无”在喜剧中的意义,探索“无”之乐趣,“无”之自由。
一、话语-情节的“无”之乐趣
周星驰电影的“无厘头”风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话语意义上的“无厘头”及行为表现上的“无厘头”。“无厘头”本是岭南文化地区的俗谚,指某人的言行表现没有由来,无明确的目标,做事情不分主次,语言表达鄙俗任意、颠三倒四、莫名其妙,但也不是完全不存在道理。
(一)话语意义的“无厘头”
1.语言的陌生化
俄国学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理论强调:在内容与形式上,违背我们所常见的一切事物或规则情理,并且在艺术上也超出常境。表面彼此不相联系,内部相互联系的种种要素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种矛盾造成了“陌生化”的特征,能够给人以感官的刺激或情感的震撼,是形式主义者的陌生化理论的核心所在。
在周星驰的电影中,“无厘头”式的语言占有重要地位,语言原有的意义以崭新的方式被消解。我们所熟悉的语言在影片中被陌生化处理,常用语言规则被打破,读者和观众按照语言习惯、思维定势思考而导致期待落差,从而产生强烈的滑稽效果。电影将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用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错位使用,例如《唐伯虎点秋香》中,船夫:“……这么多船偏挑到了我这艘船,我可是出了名的快啊!”唐伯虎:“是吗?啊,你的船在下沉啊。”船夫:“沉也沉得快啊。”在此语境中,“快”应是为船行驶的速度快,但在电影中却将其荒唐的理解为下沉的速度快,变成了行驶速度中“快”的一种,这便是与通例表达的偏离,让接受者对语言的接收有一种阻断,这个过程即是产生陌生化的过程,形成诙谐幽默的喜剧效果。
除此之外,中英文共现、语序颠倒、谐音等手法在周星驰喜剧中随处可见,使欣赏者感到强烈的新奇感和陌生感。例如:《大话西游》中至尊宝为了穿越时空救白晶晶,二当家在洞口看到随即说:“娘子,快跟牛魔王一起看上帝。”但将“牛魔王”跟“上帝”这两个在常规语境下不能相提并论的形象放置在一起,便显得荒谬。“上帝”是基督教宗教信仰中的神,与《西游记》中的角色“牛魔王”共同出现在电影语境中,无疑是一种没有来由、没有逻辑、没有意义的“无厘头”。在《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希望博得秋香的同情以进华府,和另一个装惨的人比惨:那人的狗突然死去便用“有情有义”“肝胆相照”来形容狗与他的关系,唐伯虎随即对一只死去的“小强”(蟑螂)做出回应,用“同甘共苦”“相依为命”“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词来对一只蟑螂哭丧。这些词原本是来形容人们之间崇高的感情,多用在较为严肃的情景中,但在这个语境中却是形容人与死去的动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唐伯虎与其死去的宠物蟑螂)。一方面,这些语言在这个语境中使用十分荒诞陌生;另一方面,人人喊打的蟑螂竟成了唐伯虎情深义重的宠物,显得十分荒诞,也正因此才使得观众捧腹大笑。再比如大众在日常中说法是“我先走”,而在周星驰电影中的则是“我走先”;“先给我一个理由”换成“给个理由先”,而“我服了你”变成“I服了You”;《唐伯虎点秋香》里唐伯虎还冒出了英文“follow me”;《大话西游里》中唐僧将“仁慈”与“人妖”谐音互换,等等。
2.无意义的对白
在一种无意义对话的场景中制造喜剧效果是周星驰影片中经常发生的,这也是“无厘头”语言表现方式之一,话语可以被随意的拼贴歪曲。《大话西游》中的唐僧一改往日严肃形象,转化为一个“话唠”形象,比如在影片开头唐僧的一段对白中:唐僧让孙悟空不要乱扔东西,当孙悟空扔掉月光宝盒时,唐僧又说随意丢东西会破坏环境、砸到小朋友、树木花草。当孙悟空受不了唐僧的啰嗦想要抢走月光宝盒时,唐僧并没有给悟空,而是一直念叨着:“悟空,你想要的话你就讲出来嘛,你要说出来我才能知道……不说我就不知道……你要说出来啊……是不是想要……”“无厘头”式的对白往往令人意想不到,月光宝盒是个贵重宝物,在被孙悟空扔掉时,唐僧却说乱扔东西会导致坏境被破坏、小朋友被砸等后果,但是环境污染并不属于那个时空中的概念,而现场也没有任何“小朋友”出现。其次,对话屡次反复一个意思,唐僧以不同的语言组织形式重复述说着一句话就能够表达的意思。这种“无意义”的对白表面上看似没有任何含义,话语的意义被消解得残缺不全,加上唐僧原有的严肃人物形象,形成对原有规则的颠覆和反叛,以“无厘头”独具的语言风格,从而达到娱乐大众的效果。
在《喜剧之王》中一帮坐台小姐想要学习如何装作学生,便去找尹天仇学演戏:当尹天仇说“如果你们出来卖的时候……”时,听到的刘飘飘非常生气,转身走到后面先拿起羽毛球拍左右挥动,尹天仇看了看,带头的大姐对他说:“没事的,她是这样的。”此时的柳飘飘又拿着一个大夹子挥了挥,那个大姐还在说:“没事,没事。”最后柳飘飘拿起来一个凳子朝尹天仇走过来,不停的拍打尹天仇。而那个带头的大姐却还一直在说:“没事,没事。”在这个场景中,人物之间的对白与行为逻辑混乱,不相匹配,但几个人物分别的行为互不影响,而带头大姐的“没事”也成为一句没有意义的对白,增强了电影的娱乐效果,“无厘头”风格显著。
3.粗俗语言的狂欢
周星驰影片的台词大多粗俗直露,有时通篇都是叱骂,充满着讥讽戏弄,这与狂欢节的广场语言有着某些连通的地方。广场语言是指狂欢节庆中流行的、狂欢的、自由而不受抑制的语言。在其电影中出现大量叱骂词汇,这些鄙俗、不登大雅的词汇在官方语汇中绝对不可能呈现。这与教条式的官方格调更是格不入,但在周星驰的电影中都显得不足为奇,电影中正是这种粗俗的语言使角色之间关系更加紧密,过于谦恭的语言则暗示着角色间的距离感。
周星驰与吴孟达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虽常常污言秽语,但关系也是最为亲近的。在《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为了不被發现身份,编造了一段痛斥“自己”的故事,而这段说辞让夫人与丫鬟们听得飘飘欲仙,看见此刻武状元想要模仿唐伯虎“惨,吃了拉,拉了撒……吃喝拉撒”,众人被这样几句没有任何才华水平的话拽回现实。而这些对话具有怎样的意义很难说清,对于影片情节的推进以及角色塑造并没有起到现实意义,只是在夸张、粗俗的言语繁复中呈现一种茫无头绪的嘻弄、发泄作用,但这正是周星驰喜剧的表现方式。周星驰的喜剧作品是反抗传统的手段和工具,作为一种新型喜剧,以“无厘头”式的滑稽和欢愉,为大众创造了一个寻找自由、宣泄和寄托的出口。
(二)行为表现的“虚无”
1.期待落空的虚无
在周星驰影片中,作者故意设置镜头误导观众,随着镜头缓缓移动,观众才茅塞顿开。以一种违背常规思维习惯来使观众掉入作者预先挖好的陷阱里,创作者刻意与常识规律相背离,常识的因果关系被打破,从而形成期望与实际的差距,创造出喜剧效果。这种表现即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言之“预期失望说”。康德认为,喜剧之所以可笑,多数是因为非常规、无意义、非僧非俗式的配合,当人们根据常理所做的理想是这般,而结果却非这般,甚至和预料的相反,这时就会产生喜剧效果。《唐伯虎点秋香》中,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唐伯虎提笔蘸墨挽袖,神色严肃认真,然而画面突然下拉,镜头中有几串鸡翅,唐伯虎就开始给鸡翅刷酱,观众这才茅塞顿开。《食神》中的史提芬周的师傅在食神大赛中的行为表现,以及《济公》中朱大常和小玉磨豆腐的场景,均是如此。
这种“出乎意料”的表现在周星驰电影中俯拾皆是,当对象不符合常规、不和谐,就构成了遵守常规做出判断人的可笑的对象。这也是“无厘头”善用的一种技巧,突破惯常思维模式,不按常理,独辟蹊径,增强了喜剧效果,往往给观众留下深刻。《九品芝麻官》中包龙星的母亲给他的尚方宝剑,在办案这个十分紧张的时刻,抽出的剑居然只是一条咸鱼。在惊悚喜剧电影《回魂夜》中,Leon是一位捉鬼大师,在电影开头他赶走了藏在大楼里的鬼魂,后来在与保安交谈中,他说大楼中还存在鬼魂,说着突然又问这附近有公交站吗?又说:“你去买瓶护发素吧,鬼最怕有精神的人。”临走之前问保安队长借五百元打车,保安认为他说的话驴头不对马嘴,觉得他有神经病,随后就有真的精神医生来找Leon,并把他抓走,此时,保安感叹:“原来是神经病。”两种形象的快速转变令人猝不及防,给予了观众很大的心理落差,这种落差从而使观众产生笑。
这些表达对于影片的叙事发展以及内部深度的含义都没有什么具体影响,但却是周星驰电影中必不可少的喜剧元素。影片中与周星驰对话的人物也常常感到莫名其妙,观众虽然也感到稍显混乱,但却会产生“笑”,因此也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是周星驰电影的标签。
2.夸张怪诞的动作行为
周星驰夸张、狂荡不羁的行为表演也是其影片的标志性特点。“夸张”原为语文中一种修辞手法,在周星驰喜剧中则是对无厘头的一种“修辞”,比如《九品芝麻官》里包龙星努力学习吵架的本领,在一次练习中竟然能把弯的铁杆骂成直的,对河骂出鱼虾,骂活已经死去的人。《少林足球》里星仔在比赛时踢得最后一脚,十分厉害,踢出球像一阵龙卷风,把对方守门的球员的衣服刮得开裂、全身赤裸,最后少林队取得胜利。《破坏之王》里何金银眼看着阿丽被欺骗,而他却无法证明自己才是救阿丽的人,看到阿丽在发布会上与师兄唱歌跳舞,居然难过悲伤到七窍流血。在《行运一条龙》中一女护士给何金水打针,拿着一根极粗的针管,对着何金水的胳膊用力的扎下去,动作十分夸张,随着拔针的动作,何金水疼痛得大叫,配合这画面出现的卫星定位图,说明何金水的喊声已经直冲云霄。《唐伯虎点秋香》中秋香被夺命书生踢得面目全非,而唐伯虎的一招“还我漂漂拳”,把秋香的脸给“打”好了,这种无来由的夸张更是给影片增添了荒诞滑稽的味道。
二、解构-重构的“无”之美感
法国雅克·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理论的领袖人物。解构主义反对传统、反中心、反非对即错的论题,还强烈反对基于常规思维上的理念冲突。因此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攻击“逻各斯中心主义”,打破这已有的不可动摇的规则。浅显一点地说,“解构”就是对现存的所有一切表示怀疑:所有都可以颠覆和反叛。在周星驰的喜剧中,主要是对严肃与传统的解构,往往戏谑化爱情以及英雄主义,在解构后重构,达到独特的审美效果。
(一)消解崇高与权威
爱情是我们最真挚的情感之一,英雄是人人尊敬的救世者。巴尔扎克曾说过,爱情不单单是人类的一种珍贵的情感,站在另一种角度上看爱情也是艺术。古往今来有多少唯美的爱情故事令人震撼,结局或凄惨,或圆满。中国有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梁祝化蝶,西方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这些著作中的男女主人公对爱情忠贞,让人感叹爱情的力量,这种力量让人对爱情产生一种独特的崇高感。英雄主题是古往今来人们歌颂的焦点,自从有了文明就有了英雄崇拜,古希腊悲剧对英雄的描写无疑为英雄描摹上了悲壮、崇高之感,我国古代亦有大禹治水、夸父逐日等英雄故事,英雄叙事在人们眼中自然是严肃庄重的。无论是爱情话题还是英雄主题在各种形式的艺术表现中都是神圣的、权威的,周星驰在其喜剧中却将其解构,游戏化,反而达到一种“无厘头”式的审美感受。
1.爱情的戏谑
爱情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主题之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诗词歌赋、文集电影还是绘画雕塑,都有对爱情的描绘,包含爱情主题的电影的类型也数不胜数,战争片、科幻片甚至是惊悚片等,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商业电影的主要卖点之一。爱情主题在周星驰喜剧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但就其表达形式来看,与以往传颂的爱情故事中的表现却是背道而驰,“爱情”是神圣崇高的,无论是悲惨结局还是大团圆式的爱情,其表现方式基本都是正统庄严的,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许仙与白娘子、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这都是让人十分感动的爱情故事。但是在周星驰电影中,爱情不再是严肃的,反而是被解构的对象。
影片《大话西游》中,至尊宝为了得到月光宝盒,在紫霞刺向他时,随即编出一段感人的骗词,还偷偷背过身往眼睛里滴了几滴水,十分深情得对着紫霞说“爱你一万年……”之类的假话,内心却是想着,这个谎话是生平中最完美的。这段“告白”的台词后来也成为大众熟知的流行语。周星驰为观众呈现出了一个荒诞的爱情故事,原本应是神圣温情的表白却以这种虚伪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滴假“泪水”和一段谎言消解了爱情的神圣,周星驰提醒着观众:泪水与谎言构成了爱情,并以喜剧的表达方式缓解情绪,看穿爱情本质后的“本应悲伤”也被笑声冲击、消解,再与影片最后的“城墙之吻”遥相呼应。周星驰显然认为爱情仍是存在的,只不过在后现代语境中,“神圣”“庄严”反而使爱情虚伪——解构的目的在于重构,消解了爱情与誓言的神圣性后,周星驰还爱情以“个人情感”的平凡和质朴,并在平凡中凸显爱情的可贵,例如《喜剧之王》《破坏之王》等,都描绘了小人物在面对不同的困难、坚定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爱情,小人物叙事则取代了英雄叙事成为了后现代语境中大众精神寄托的选择。
2.英雄的落幕
周星驰影片中所有的形式、法则、理论都被毫不保留地解构,是对权威的蔑视、反叛、颠覆与破坏。以游戏和放荡不羁的解构姿态,搜寻无所不在、包罗万象的解构对象,并且以从心所欲、绝对自由的精神去解构原有对象,从而产生巨大的落差,这种心理上的差距便促使笑腺扩张。以一种嬉戏姿态的解构者,站在“理性”之外,对标准、艺术、伦理等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反叛和戏谑。
在周星驰影片中,对英雄主义的消解也是其表现方式之一。英雄主义作是人类文化精神之一,自古就流贯在人类的文化之中,是高尚庄严的,在以往的电影中凡是涉及英雄人物,都是与传统形象保持一致或更加突出其英雄品質,而在周星驰的电影中不仅没有着重表现还将人物形象所具有的英雄气概消解了。周星驰喜剧影片中的“英雄”实际都是普通人,处于一种窘迫的境地,虽然不像英雄人物那样具有高尚的品格,也不令人崇拜,但他们却具有一颗善良的心,刻守道义,努力执着。这与周星驰的人生经历以及香港的文化坏境密不可分,周星驰影片中的英雄叙事常常分为两种模式:小人物英雄的成长及对经典化英雄的调侃。
主角常常开始时还仅仅一个普通的无名小卒,生活在社会底层,但这个“nobody”在最后紧急时刻总会误打误撞,以某种方式击败坏人,从而拯救众人。周星驰喜剧的这种“降格”以及将小人物英雄化的表现方式,与巴赫金提到的“脱冕”“加冕”理论相通。在周星驰喜剧中常常会出现这种小人物的英雄叙事,如《破坏之王》中何金银是一个胆小懦弱送餐小子,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人,决定改变自己的懦弱拜师学武,不但没有学到真功夫,还被骗了钱,但歪打正着创造出了“无敌风火轮”的招式,最后还打败了武术高强的大师兄,获得了爱情。在《功夫》中,星仔是一个混混,他能言善辩、为人圆滑,但却没有坚定的意志,百无一成。他做梦都想能够成为斧头帮中的一份子,向往黑社会的生活,成为一个大人物。自荐去帮斧头敲诈居民,没想到居民个个身怀绝技,使出浑身解数进行反抗,本性并不坏的星仔逐渐转变了思想,帮助居民,在被打得筋脉尽断时,居然练得了如来神掌,成为英雄。
另一种是以对大众所熟知的英雄形象的推翻与反叛。在周星驰的影片中常常解构人们心中已经定型的固有形象,尤其是对崇高、神圣、令人崇拜的人物颠覆并伴随着嘲笑,塑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物形象,从而达到娱乐大众的效果。这在《唐伯虎点秋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江南四大才子“唐祝文周”,在经典叙事中是才高八斗且性情洒脱的知识分子。但在周星驰电影中的“四大才子”衣衫不整,伴随着浮夸的走姿,吟出“回家玩老婆”这样粗俗字眼的诗句;祝枝山请求帮忙,便用其裸体画出一副巨作;唐伯虎为了靠近秋香装成乞丐,为了进入华府卖身葬“小强”,对出“你老娘”等字眼的粗俗对联,为了化解华夫人的怀疑伴着模仿架子鼓的配乐说了一段凄惨的身世快板,等等。影片从头至尾都是在颠覆人们对传统唐伯虎形象的印象,周星驰电影中的唐伯虎是一个无赖混混、又是一个极具浪漫的诗人以及武功高强的大侠,亦或者说他只是借助于唐伯虎的名号塑造出得“唐伯虎”。才子祝枝山则被解构为一个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的赌徒。传统的才子形象被描绘得支离破碎,让人忍俊不禁,在周星驰电影中这种的解构也是屡见不鲜。
(二)解构传统的的叙事模式
周星驰的影片中除了对于传统爱情主题以及英雄人物的解构,还通过运用各种戏仿、狂欢等方法创造出许多喜剧元素,把以往传统的故事演绎为了滑稽搞笑的效果或是带有讽刺式的嘲弄,消解严肃、深度,将其转变为粗俗、荒诞、娱乐至上。对其传统的叙事模式的解构,将杂乱无章、反理性进行到底。
1.戏仿经典
“戏仿”又称“戏拟”“谐仿”等,是把其他作品或其经典片段借鉴过来,用在自己作品中,从而对其进行戏谑、嘲弄以及致敬。通过戏仿,将某些经典作品拼贴为全新的新剧作品,是一种解构经典的方式。
其一是对经典电影的戏仿。周星驰的喜剧电影往往通过对其他经典电影情节、人物语言的模仿使观众得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新的场景下,观众忽然回想起原文本从而忍俊不禁。如周星驰的《回魂夜》里面的元素就是在戏仿法国吕克贝松导演的《这个杀手不太冷》。两个影片开头场景相似,Leon的着装打扮和造型就是在模仿里昂,两人都随身携带一盆花并将其视为好朋友等等。《国产凌凌漆》中总是发明一些无用的东西的发明家达闻西模仿了美国无厘头电影《白头神探》中的博士。《家有喜事》中,常欢为追求喜欢模仿影视剧人物的何里玉,在看到电视上播放《人鬼情未了》中做陶瓷的经典片段,两人也滑稽地模仿了这一画面。周星驰许多影片中很多的搞笑桥段是对卡通片《IQ博士》《忍者小精灵》的写照,比如《九品芝麻官》中,杂戏团中的师兄误将包龙星当成女人,在饭桌上给包龙星的碗里夹得菜足足有五十公分高,就是对卡通片的模仿,将漫画式的元素运用在电影中,从而收到独特的喜剧效果。
其二是对流行元素的戏仿。流行元素顾名思义就是当前比较盛行的大众文化。周星驰有几部电影中的某些情节对于现代流行元素的模仿让人印象深刻。在《大内密探零零发》中“戏仿”了一段如今非常流行的颁奖典礼,零零发为了抓住无相皇假扮的琴操与一家人演了一出戏。在抓住琴操后,零零发模仿主持人的口气,伴随画面回顾发嫂“演戏”的镜头,并且加上解说发嫂“演戏”中刻画的细节,而被灯光照射的发嫂像演员一样走来,发表“获奖感言”,言语表情都在模仿现实颁奖典礼上获奖人所说过的“感人”台词:“谢谢我的老公,我的家人……”最后由皇上对其颁奖,整个场景无不是在对颁奖典礼的戏仿。
在《唐伯虎点秋香》中最经典的片段之一就是华夫人和唐伯虎戏仿了一段现代广告,俩人在争论谁的毒药更厉害时,转头朝着镜头开始介绍自己的毒药是由怎样的配料而制,最后异口同声“必备良药”,让观众在摸不着头脑中啼笑皆非。周星驰电影通过解构的手段,对经典的片段或流行元素的模仿,加以独特方式游戏化,从而达到娱乐大众的效果。影片常常给人以新颖的方式,虽是在解构意义,同时也在建构一种崭新的喜剧模式。
2.狂欢化叙事
狂欢理论是由俄国学者巴赫金提出的。所谓狂欢化就是指:狂欢节式的各种形式在文体中转换和渗入,狂欢化的来源即是狂欢节本身。在这个狂欢世界中,大家一律平等,没有空间的界限,超越了世俗的等级制度、等级观念以及各种特权禁令,超越了日常生活,回到主体的生活世界,从而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功利性和严肃性。在这里,生活中的疯癫、小丑等形象反而成为最有活力的人。消解所有权威,赞扬和谩骂交错,黑白同体,不存在二元对立,与周星驰的喜剧电影中的表现有异曲同工之妙。周星驰与其他喜剧一样都遵循着使人愉悦自由的原则,但作为“无厘头”的代表,影片中的人物行为语言往往体现一种乖觉夸张的癫狂状态,就是这种狂欢化状态,增强了喜剧效果。在《济公》中,由周星驰饰演的济公,行为乖张荒唐,与传统形象相差甚远,在电影开头,众神仙聚在一起纷纷向玉帝告状,王母说:“降龙罗汉把我蟠桃上的蟠桃全都偷去给牛郎的牛吃了。”一神:“岂止,他还串通喜鹊搭起鹊桥让牛郎织女幽会,已经生了一打孩子。”月老:“他来到我这乱搞一通,让皇帝去追求风流女子,公主跟乞丐私奔跑了”……更离谱的是他把哮天犬给炖了,弄瞎了二郎神的眼睛。
这种狂欢式的表演曾一度被人鄙夷,刚开始那些还固守传统思维的人将其看做是“不雅”“不文明”“十分恶俗”的喜剧电影。当人对现实生活不满却又无法做出抵抗时,常常会通过隐性意识来寻找突破口,周星驰电影中的通过人物往往以各种荒诞的幻想或者梦境以寻求理想世界,进入狂欢的自由境遇,周星驰电影中人物就是常常不满现实从而逃脱出来,进而钻进自己想象的空间获得慰藉。在《唐伯虎点秋香》中的一个狂想场景,唐伯虎帮秋香捡风筝,幻想自己为秋香而摔断胳膊,秋香十分感动,与他热烈的拥吻。然而,镜头突然一转,直对唐伯虎的脸,其怪嗔的狂笑显得十分夸张,原来这只唐伯虎自己的幻想,结果当然事與愿违,不仅没有抱得美人归,反而摔坏风筝落得狼狈不堪。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创造存在于无意识的领域之中,这就是人的本能欲望,即“力必多”。由于现代社会的理性限制,才有了“力比多”的转移与潜藏。周星驰电影中有关乎两性问题也丝毫不避讳,这也符合解构与狂欢的目的,当人们在看惯了各种高雅艺术后,这种“低俗”文化则让人耳目一新。在影片《国产凌凌漆》的最后,凌凌漆与女主在肉摊的帐篷里行雨水之欢,这些画面设置的目的并不是要赤裸地表现“性”行为,只是对其的一种恶搞,达到一种狂欢的效果,回归到人类本原,挖掘人性中隐藏的、被忽略的一面。
三、存在-选择的“无”之超越
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没有什么是规定性的,每个人的人生如何都取决于自己的选择,人在选择中找寻自己的本质。正处于本质的缺失之中,人生才不断地去追求、去超越自我,这个过程便就是从不完满到完满,不竭不息,以求最终能够获得自由。喜剧的本质就是超越之后的轻松和欢快,周星驰电影中的“无”与超越的最终目的同向,都意图使人超越自身存在、自我造就,获得一种精神上的绝对自由。
《喜剧论纲》中明确提出:喜剧来自于笑。其感性结构是由“可笑”的事物与笑组成的。当笑者在一定意义上超越被笑的对象,在此时就会产生笑,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情感表现,常与喜剧联系在一起,喜剧来自于笑,同时它所产生的作用也是笑。笑的意义众多,有开心快乐的笑,也有嘲讽的笑以及无奈大笑等。因此喜剧所产生的笑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正面积极的带有肯定性的笑,另一种是都有讽刺意味的嘲笑他人的否定性的笑。肯定性的笑中包含着的是赞颂与肯定,是最具有笑的本义,而周星驰喜剧以“无厘头”式的幽默来产生笑的意味,这种笑最终带给人的是自由与超越。
笑本身就具有解脱的意味, 喜剧精神的最大特点就是超越,在周星驰电影中这种超越精神通过以一种非常平静的叙述语气通过对权威力量进行展示戏谑完成。在《少林足球》中强雄提出如果“黄金右脚”给他擦鞋,他就可以让他们的球队参赛,众人争抢擦鞋,此时众人争夺鞋子走远,只有强雄穿着一只鞋尴尬的留在原地,此时镜头对他的破袜,以及露在外面的脚趾。众人以一种看似服从的方式既得到了参赛机会,又令强雄出丑。周星驰的电影人物在屈从中抗争,在沉静中超越。
在周星驰喜剧中,不仅具有喜剧的“嘲他性”,还带有许多自嘲色彩,以一种“黑色幽默”来体悟人生,揭露荒诞。《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家世显赫,又是“四大才子”,名声大噪。府中又迎娶了八位貌美如花的妻子,这令不少人都羡慕不已。然而他自己心中十分清楚自己的八位妻子花颜月貌,可是个个都好玩贪赌,家中整日乌烟瘴气,没有一位真正懂他的人。当面对其他人的夸赞与羡慕,唐伯虎无奈地狂笑自嘲。周星驰的这种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荒诞喜剧的“嘲他性”与传统喜剧不同,传统喜剧是以理性嘲笑反理性、非理性,而周星驰喜剧是用反理性、非理想的形式去嘲笑传统理性以及人类的一切欲望。而对于这种嘲笑之后的放肆大笑是一种超越的笑。
四、结语
周星驰的电影被认为是中国喜剧电影中一抹亮眼的色彩,“无厘头”这种特立独行的喜剧风格从开始不被接受到最后成为中国喜剧倍受追捧的宠儿,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是现代人生存境遇的幽默化表达。无论从其表达方式还是情节叙述都以“无”为中心,无意义、无逻辑,娱乐至上,观众在欣赏时,得以卸除疲劳,放松身心,在狂欢大笑中回归本身。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喜剧形式触发了观众的笑神经,在一种反抗、游戏及近似粗鄙的嬉笑怒骂中对于正统的社会规则与价值理念进行消解,让观众在“无”中生笑。周星驰喜剧中“无厘头”的语言风格,其特点就是反常规、背离语法逻辑、前言不搭后语。在凸显娱乐性之外,解构语言意义,反叛原有秩序,消解所叙之事的意义和深度。在周星驰的诸多电影中,都以其“无厘头”式的手段解构语言,似乎语言不具备常规意义,说出来也与没说无异。人物行为表现在夸张、怪诞中产生一种无由来、无中心的娱乐和发泄,表面看似没有意义,反而呈现出一种极致快乐的美感。“解构严肃”是周星驰在情节设置的一大亮点。解构方式新颖、抓人眼球,塑造边缘人物,解构程度并未彻底推翻,给予英雄人物社会俗气却并非完全否定,反而更加贴近大众。周星驰电影在笑声背后体现的是人的理性精神的分裂,以及对自我身份认知的失落,也渗透着人类生存与大地之上的诗意特征,周星驰在其电影中所传达的是超越意味,以喜剧的形式传达的是一种人的相对自由和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让观众在“无”中生笑,领悟“无”之自由,从而形成一种独具风格的美。
参考文献:
[1]刘鹏艳.“无厘头”与现代喜剧之旅[D].合肥:安徽大学,2007.
[2]唐果.论周星驰电影的喜剧风格与审美意义[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0.
[3]刘腾.周星驰电影与后现代主义文化[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11.
[4]高字民.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解构与狂欢[D].西安:西北大学,2003.
作者简介:王童,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电影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