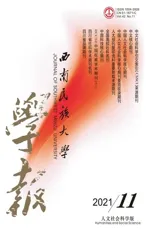乡村振兴语境中公益直播带货的叙事意义考察
2021-04-17陈笑春唐瑞蔓
陈笑春 唐瑞蔓
[提要]通过观察2020年、2021年公益直播带货的典型样本,文章阐释了媒介叙事力量在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战略推进中通过“连接”对文化与社会的整合意义。研究认为,经由商业型叙事者、基层官员叙事者、主流媒体叙事者的协同塑造,公益直播带货构建出“好物”“景观”“价值观”等多个维度的连接,有助于解决因空间距离、疫情影响、(媒介)语言不通、平台区隔等造成的生产生活和价值观传播问题。这既是聚焦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举措,也是推进媒体深度融合与讲好中国故事的积极探索。
网络直播,作为一种社交媒介,其叙事程式、文本身份、传播功能等随着媒介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与更新。2016年,直播与电商的合作所催生的直播带货,成为直播这种媒介形态的主要垂直细分领域之一。直播受众变成了直播带货的消费者,推荐、促销商品成为直播叙事的主旨。同年,薇娅等电商主播就以助农直播的形式帮助农产品滞销的农户卖货,开启了直播带货公益应用的先河。①2018年,一些基层官员走进直播间,帮助推荐地方农产品,便兴起“政务+直播+助农”的融合模式。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的销售和农村产业的增收。为了让滞销的农副产品打开销路,促进经济复苏,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的号召和组织之下,社会各界通过参与公益直播带货为乡村发展助力。在这一历史契机中,直播带货的公益价值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显出来,被更广泛的人群看见和接受。
党的十八大以来,解决好“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强化举措,扩大成果”。[1](P.99)建构“大扶贫格局”,“凝聚‘全民扶贫’合力”[2](P.16),形成有益于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环境,就要激活或重建贫困者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连接。从媒介视角来看,“连接先于存在”。[3](P.31)贫困者,往往是“身体被局限于边缘社会空间”的人,他们“在媒介空间中的表征也是被边缘化或被排除在外的”。[4]因此,若要扶贫效益持续发挥就需帮助网络外围的贫困者保持良好的连接关系。[5](P.XIII)直播这一媒介技术可以在时间、空间和语言上为贫困者与其他社会成员的连接提供极大的便利。然而,面对互联网上难以计数的直播带货,如果没有主流媒体、基层政府、商业平台等其他行动者的帮扶,仅仅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其实很难驾驭直播这项“新农活”。当“以直播为媒的社会互动实践全方位渗透到各领域中,以传播逻辑重构社会”[6]时,公益直播带货的首要价值就在于:为农民、农村、农业提供进入“连接媒体系统”②的有效路径,通过媒介叙事的力量,让那些原本不在直播景观之中却需要被“看见”和关注的物、人、价值观能够置身于直播景观的中心。
针对公益直播带货现象,传播学界已经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向:一是从工具视角展开的对直播平台助力脱贫攻坚的实践描述、策略总结和模式探索;二是从媒体融合视角对主流媒体直播带货进行背景分析和效果评价;三是从媒介景观、互动仪式链等理论视角对主流媒体直播带货、地方官员直播带货等媒介现象的诠释与反思。通过对2020年、2021年公益直播带货典型样本的观察,我们试图探索媒介叙事力量在从精准扶贫到更为整体性、系统性的乡村振兴战略过渡中对文化与社会的整合意义。本文将基于两方面问题展开:一是作为媒介的公益直播带货,连接了哪些曾经看似无关的行为与场域;二是在这种因跨域连接而生成的混合式的媒介景观中,叙事者的作用与意义是什么。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研究的公益直播,可以是一个公益专场,也可以是某场带货直播中穿插的公益行为;界定直播的公益程度,并不在于这场直播为扶助对象提供了多少“让利”,而在于直播是不是指向助农扶贫、复工复产、乡村振兴等公益目的。
一、理论视角:叙事者与景观
叙事是本文观察公益直播带货之“连接”作用的切入角度。叙事,即讲故事,作为一种融贯经验、建构意义的经典方法,叙事深刻影响着媒介内容的生产以及受众对媒介内容的认知与记忆。公益直播带货建构的各种维度的连接,离不开叙事的塑造。同时,其连接的广度、深度与温度也经由叙事的变迁图景获得充分的显现。叙事者,是叙事的主体,叙事的发出者,决定着叙事文本讲什么以及如何讲。赵毅衡认为,叙事者是一种“表意功能”,呈现“人格-框架”的二象形态;“当此功能绝对人格化时,他就是有血有肉的实际讲述者;当此功能绝对非人格化时,就成为构成叙述的指令框架”。[7](P.92-99)然而,无论是人格化还是框架化的叙事者,始终被叙事体裁的规定性指引着或约束着。叙事者与作者的关系也颇为复杂,有时分裂,有时合一。在所有纪实型叙事中,作者与叙事者是合一的,“作者即是叙述者”,作者本人要对文本中的所有叙述负责。[7](P.94)直播带货是一种作者与叙事者合一的纪实型叙事,带货主播及其团队必须为与产品相关的所有叙述的真实性负责。正是基于这种合一性,变化的作者与相对稳定的叙事者之间有一种互塑的张力。驯服于叙事者的作者,生产出符合叙事惯例的内容;而塑造叙事者的作者,会突破既有的叙事框架,追求表达方式的创新,让受众在熟悉的世界中收获陌生的惊喜。不难发现,叙事者是在叙事框架与作者之间的中介,是观察叙事变迁的一个灵活且适宜的基点。
整体来看,公益直播带货的叙事者主要经由三类作者塑造。首先,商业平台将直播场域的“好物”框架置入公益叙事之中,以期将公益与商业协调统一。其次,基层官员通过打造具有个人特质的媒介形象,生产出各具创意的叙事者。他们一边为农户带货,为消费者推荐“好物”;一边通过构建新奇独特的媒介景观去丰富公益直播带货的叙述内容与连接维度。最后,主流媒体叙事者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公益直播带货创造共识、构建认同、传播价值观的功能。在分析官员直播带货时,本文借用了“景观”一词。居伊·德波将景观界定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它既是现存生产方式的结果,也是该生产方式的规划”。[8](P.4)道格拉斯·凯尔纳又对德波提出的景观概念进行了更细致的界定,将媒介景观(又译媒体奇观)指认为“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9](P.2)上述两种不同层次的景观概念共同描述出景观的视觉性、中介性和戏剧性特征。本文使用“景观”这一术语,仅旨在提取这三种景观特征去阐释官员直播带货的传播功能,而非对两种景观理论的全部套用;同时,互动特征突出的直播媒介,也让媒介景观原本指涉的被动观看性大大削弱,而社交性更显突出。此外,虽然商业平台和主流媒体主导的公益直播带货也具有视觉性、中介性、社交性和戏剧性的景观特征,但这些对于作为媒体平台的二者来说并不是新鲜事,而且也并非它们塑造公益直播带货的核心方式,因而本文未从景观维度对二者展开细致分析。
二、商业型叙事者建构“物的连接”
乡村振兴背景下,一些农民积极发挥自身主体性,通过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渠道创业致富。巧妇9妹、李子柒、华农兄弟、蜀中桃子姐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通过或原生态或精雕细琢的乡村叙事打动了大量网友。个别先行者的成功虽然显现出数字经济对于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意义,但却不具备普适性,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要通过直播带货等互联网媒介形态提高农村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就要积极创造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被看见、被需求的连接环境。公益直播带货就是创造这一连接环境的有效路径之一。它通过汇聚商业平台、行业专家、媒介技术等市场资源,为优质农产品聚集“注意力”,为乡村振兴中的农民、农村和农业提供宝贵的连接资源。
从发展进程来看,公益直播带货最初的叙事框架由商业平台生成,来自商业平台的带货主播就是其中人格化的叙事者。在直播带货领域,“电商主播中的头部主播撑起了半壁江山”。③基于影响力造就的资源整合力,“头部主播”在商品选择上比较全面且有品质保证,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因而更容易连接到不通圈层的用户,也更容易收获用户的持续信赖,成为能够影响消费大众的“关键意见领袖”。从某种程度上说,“头部主播”就是网络直播文化制造的时代偶像,并被赋予了塑造直播叙事范式的影响力。其中,薇娅和李佳琦又是“头部主播”中的代表性人物④,他们也是公益直播的积极参与者。李佳琦与央视主播朱广权合作的“小朱配琦”系列公益专场,就曾引发过广泛关注。薇娅则在2016年就开始尝试助农直播,是“全国脱贫攻坚奉献奖”“阿里巴巴2019脱贫攻坚公益主播”“淘宝十大公益主播”等荣誉的获得者。⑤通过对薇娅、李佳琦的公益直播的观察,本文发现,公益直播带货最初的叙事框架是在公益与商业的协调与平衡中逐步确立起来的。
直播间是一个商业空间,直播带货本是一种商业行为。公益和商业是两种文化,各有各的场域和逻辑。只有找到它们的交集,公益直播带货的连接功能才能有效发挥。直播带货其实是以直播媒介为形式和渠道促动的消费者与商品之间的连接。这种商品,在直播带货的语境中被称为“好物”,它代表着直播带货的商业规则——价格优惠、所见即所得、售后完善等。公益性的直播带货也要建立在“好物”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好物”就是公益与商业的交集。最初以公益之名出现在商业直播间的农产品,就曾因定价、质量、售后等方面没有达到直播带货的“好物”标准,引发过消费者的质疑和不满。对此,薇娅总结道:“公益直播既要考虑公益,也要考虑顾客……既要帮助农民销售产品,又要为粉丝提供性价比高的好物……我们要让观众购买的,是那种即使没有‘助农’的标签,他们也愿意买的好产品”。[10](P.155-158)“头部主播”及其背后的平台在公益直播中建构的叙事框架要同时兼顾助农与“好物”两种主旨;既要从道德向度叙述购买一种农产品,帮助一些农户和农产品经营者的公益意义,又要从商业向度叙述这一购买行为对于消费者的现实意义,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基础。
“好物”标准,为能够进入公益直播带货的农产品设定了门槛。系于自己的品牌效益和意见领袖身份,“头部主播”及其所在的直播间不可能对所有农产品敞开怀抱,他们更青睐于那些已经完成了标准化、品牌化,拥有完善售后体系的优质农产品。这其实是一个悖论。因为大部分需要扶助的农户恰恰缺少这种标准化、品牌化的能力。因此,在连接农产品和消费者,用直播平台提振农产品的销量之外,直播助农还必须包含另一个更为基础和持续的层面,即连接农产品与电商标准,促进农村产业升级。前者发生在直播间,是可见可感可参与的“前台”,对所有人敞开,以媒介的效能发挥着商业上组织和校对方向的功能(如前所述,薇娅正是从消费者的负面评论里发现早期公益直播存在的定价、质量和售后等问题,进而纠偏、提升);后者发生在直播间外,是支撑和维系着直播间助农叙事的“后台”,因具有专业性的门槛而较为隐蔽。这两个层面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携手”把滞销的或初级的农产品升级为直播间的抢手好物,从而促成公益与商业基于叙事者基点的合作。
三、基层官员叙事者生产“景观的连接”
继电商主播参与公益直播带货之后,商业平台又开始邀请本来处于直播外围的县长、区长等基层官员走进直播间,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促进本地的农业开发工作。据相关资料显示,早期邀请基层官员参与直播带货并为公众熟知的是淘宝平台。2018年下半年开始,“县长扎堆儿玩直播”成为新趋势;2019年,全国超过100位县长走进村播直播间,帮助推荐地方农产品,成为地域产品代言人。[11]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快手”“抖音”等平台也开展了多场官员直播带货,破解农产品的滞销困境。当基层官员走进公益直播间,他们的一言一行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物质层面的带货行为,还在讲述着当地政府与时俱进地利用新媒体盘活地方资源,多举措促进乡村发展的故事。这些关于乡村振兴的叙事,丰富着公益直播带货的既有内容和连接维度。能否讲好这些故事,考验着基层官员和基层政府的叙事能力。
与电商主播相比,官员直播带货的景观特质更为凸显。这种景观性首先体现在政府官员与带货主播两种身份于同一个身体媒介中的并置。从早期直播带货的实践来看,许多官员尚未适应社交媒介的新型互动方式,要么依然保持官员严肃稳重的形象,要么模仿其他人气高的电商主播的风格,缺乏个人特质的展现和个人体验的分享。带货的官员与被推荐的好物之间隔着遥远的距离。两种身份的冲撞,可以带来短暂的新奇感和流量,但很难维持长久的影响力。在适应商业平台的叙事逻辑后,一些基层官员开始从机械的模仿型叙事者转变为主动的创意型叙事者,他们精心打造出具有个人特质的媒介形象,持续性地在商业平台上制造出“雪地红衣策马”“旗袍汉服赏景”“布衣灶台做菜”“田间地头务农”“青山绿水制茶”等景观。⑥这些各具意向的景观生产出海量的与其执政所在地相关的社交话题。这些基层官员们遵循了商业平台制定的“好物”框架,但又未为其所困,反而通过多种媒介叙事的互文与联动,协同生成出新的焦点,拓展了屏幕前的观看者对于基层政府工作和地方自然人文风貌的想象空间。进一步看,以公益为目的的内容生产也激发了社交媒体内容的新形式。随着基层官员的叙事主体性和内容创造力的不断提升,关注基层官员直播的“粉丝”群体也在从点到面地构建起来,有助于激发和维持公益行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更广更深的连接。
当纯粹的带货变为带风景、带家乡、带文化,叙事的作用就更加凸显。这对于官员个人、基层政府、地方文化等皆有一种形象传播的意义。有研究指出,从本质上讲,政府形象传播的最佳模式是“政府行为和解释政府行为的同时并举”,即“从‘做’和‘说’两个方面去进行”,但“做”在“说”前,“行”胜于“言”。[12]在报纸和电视的时代,“说”的工作主要由大众媒体完成。随着“两微一端”的兴起,政府不仅需要“做”,还要实时通过政务号等媒介形式去“说”,逐步承担起在媒介平台上与公众沟通、互动的职责。在直播和短视频等社交媒介塑造的环境中,叙事对现实的参与和建构,或者说“以言成事”[7](P.35)的意动效果分外直接、迅速、鲜明。比如,有位基层官员在接受央视“新闻周刊”采访时坦言,自“雪地红衣策马”的带货视频走红以后,她所宣传的地处边远的县城游客量暴增,她单场直播的带货量也可达到两百万元以上,能够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⑦
总体来看,与“物的连接”相比,“景观的连接”更具可塑性和延展性,同时也更虚拟、更脆弱。“景观的连接”必须扎根于“好物的连接”。如果出现虚假宣传或质量问题,不仅会扰乱直播带货的市场生态,官员形象和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损。然而,基层官员毕竟不是专业主播,如何有效规避随之而来的各种风险,是他们正在面临的巨大挑战。
四、主流媒体叙事者引导“价值观的连接”
面对影响力日益广泛的直播带货,行进于媒体深度融合中的主流媒体,自然要进入这一新的场域去提升自己的影响力。然而,主流媒体是“面向社会主流人群、代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重要公共信息、具有较强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媒体”[13],生成于商业平台的直播带货所形塑的消费文化与主流媒体所倡导的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这种文化差异要求主流媒体首先要讲清直播带货与传播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比如,以扶贫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复工复产、追求美好生活为旨向。其次,主流媒体要在带货直播情境中建构符合自己身份与立场的叙事者,以此实现对带货直播的善用,而不是被带货直播所用。
2020年4月,在“加快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扩大居民消费,并指出要制定专项支持政策,支持湖北经济社会发展”⑧的背景下,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纷纷以公益直播的形式进入带货场域,“助力湖北”成为它们共同的叙事主题。凭借强大的传播力和号召力,主流媒体集结了主持人、记者、演员、歌手、湖北地方官员、带货达人、农产品的经营者和农户,多个知名电商平台,以及观看、下单的海量用户等行动主体,形成了一个宏大的行动者网络,让公益直播带货的动员力从电商主播和基层官员有限的“粉丝”圈扩展至四面八方,充分激发出公益直播带货创造共识,进而建构认同、传播价值观的功能。在主流媒体发起的多场“助力湖北”的公益直播中,香菇、茶叶、莲藕、小龙虾等农副产品依然是重点帮扶品类,滞销农产品的经营者和农户也是重点帮扶对象,再次显现出乡村振兴这一国家大事对于媒体叙事的结构性力量。继“助力湖北”之后,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因势利导,继续设定新的叙事主题,发挥直播带货的价值观连接功能。从2020年4月的“谢谢你为湖北拼单”系列公益活动,2020年7月启动的“买遍中国·助力美好生活”全国31省份巡回专场,2020年11月的“足不出沪,享购好物”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欧洲专场,到2021年3月的“我为新疆棉花代言”专场等,直播带货几乎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在重要时刻发声的一种途径。这些直播文本的主题,彰显出主流媒体直播带货的叙事策略:用主流价值观引导消费行动,让消费行动传播主流话语。消费是人的日常所需。当直播带货以种种创新优势满足了人们的消费需求,塑造了人们的消费习惯,直播带货也就慢慢变成了一种深度融入日常生活的媒介叙事。在主流媒体不断提升传播力和引导力的过程中,这种媒介叙事是其连接到人民群众,并在人民群众中传播主流价值观的有效路径。主流媒体扩大了“带货”的意涵,“带货”成为了一种价值观传播的中介。
在“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以及“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关头,[14]主流媒体高度自觉地发挥媒介叙事力量,克服疫情影响,顺势而为地将公益直播带货原本偏向于微观层面的“物的连接”,中观层面的“景观的连接”,提升为更具系统性和整体性的“价值观的连接”。经由主流媒体叙事者的引导和塑造,公益直播带货的社会动员力和资源整合力被充分激发出来,为未来公益直播带货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主流媒体的参与,也让商业平台及其推广的直播带货走进了更大范围的公共空间。但直播带货在发展中暴露出来的数据流量造假、虚假信息发布等违规行为,及其隐含的算法操控、隐私泄露、消费异化等种种问题,也为公益直播带货和参与的各行动主体带来了风险。如何避免这些问题影响公益直播带货的公益本位诉求,维护其对于提高社会公益认知,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积极意义,是主流媒体在价值观引导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五、结语
公益直播带货是商业平台、基层政府、主流媒体等行动者参与乡村振兴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打通了公益与商业、政务与直播、主流价值引导与商业消费文化等不同的场域,建构了多种维度的连接。从叙事视角来看,首先,商业平台将直播带货场域的“好物”框架置入公益叙事之中,以“物的连接”兼顾公益与商业的平衡。其次,基层官员推动了叙事者的样态创新,纯粹的带货变为带风景、带家乡、带文化,从而丰富了公益性带货的既有内容,将单一的“物的连接”拓展至更具可塑性和延展性的“景观的连接”。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政府振兴地方经济与文化的积极行动也获得了充分的展示。最后,主流媒体叙事者通过扩大“带货”的意涵,让“带货”本身成为了一种价值观传播的中介,提升了公益直播带货创造共识、构建认同、传播价值观的功能。经由多个叙事者的协同塑造,公益直播带货让那些原本不在直播景观之中却需要被“看见”的物、人、价值观能够置身直播景观的中心,有助于解决因空间距离、疫情影响、(媒介)语言不通、平台区隔等造成的生产生活和价值观传播问题。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基于公益直播带货这一融合媒介形态,消费行为成为了公益行动,在不断累积的上亿的销售数额中,媒介叙事激发的连接力量也不断彰显出来。
与此同时,为了网络直播这一影响力愈益广泛的集社交、消费、娱乐、宣传、公益等功能于一体的媒介能够被更多地善用,须要警惕这一媒介技术可能带来的算法操控、隐私泄露、数据造假等诸多问题。正是基于这种警惕,才更需要其他行动主体的参与和介入:一方面在叙事的差异性中发现裂隙与症候,进而洞悉“连接”的深层结构;另一方面,在叙事的多样性中发展“连接”的新维度,实现对既有模式的创造性超越。与此同时,公益直播带货需要处理好“景观的连接”“价值观的连接”与“物的连接”之间的平衡。既要避免商业叙事框架对公益叙事框架的挤压,也要避免让消费走向意义、情绪等非实物产品领域。脱离“好物”维度的带货可能带来消费的异化,这无论对于公益还是商业都不是长久之计。
注释:
①参见:《“80后”电商主播薇娅:相信奔跑中的汗水和眼泪》,新华社客户端,https://xhpfmapi.xinhuaxmt.com/vh512/share/9956298,2021年5月4日。
②在何塞·范·迪克看来,所有平台的组合构成了具有基础设施意义的“连接媒体的生态系统”。参见:[荷兰]何塞·范·迪克《连接:社交媒体批评史》,晏青、陈光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4页、第22页。
③2020年10月12日,毕马威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直播电商报告显示,2020年,直播电商整体规模将达10500亿元,正式进入万亿时代。而根据测算,2021年直播电商行业将继续保持较高速增长,规模有望接近2万亿元。参见: 张燕《电商主播:头部主播撑起半壁江山》,经济网—中国经济周刊,http://www.ceweekly.cn/2020/1231/327163.shtml,2020年12月31日。
④截至2021年10月17日,灰豚数据(淘宝版)显示:薇娅和李佳琦的“粉丝数”分别为0.77亿和0.51亿。参见:灰豚数据,https://www.huitun.com/app/#/app/anchor/talent_ranking,2021年10月18日。
⑤参见:薇娅《薇娅:人生是用来改变的》,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封面介绍。
⑥与以上景观对应的基层官员都在“抖音”平台上开通了实名认证账号,并且得到了中央电视台、澎湃新闻等主流媒体的关注。其抖音名称分别是“贺局长说伊犁”“唐县长爱太湖”“向县长说古丈”“金县长爱山阳”“陈县长说茶”。
⑦参见央视“新闻周刊·本周人物”报道:《贺娇龙:“马上”成名后》,央视网,https://tv.cctv.com/2021/04/17/VIDEV P4oSul5 aJSCnCIfYDLd210417.shtml,2021年4月17日。
⑧这是央视主播海霞在2020年3月27日《主播说联播》节目中对中央政治局会议部分内容的引述,也是在此时,海霞提出了“为湖北拼单”的倡议。参见:《主播说联播 海霞今天要带货!》,央视新闻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n9jBns21j0xUB qNd4Va73g,2020年3月27日;《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中央部署做好这些事》,新闻联播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b-HHzoeSxZgPZwX7 MYjBdA,2020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