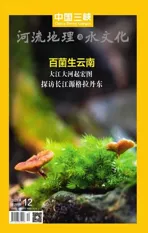探访长江南源当曲
2021-02-21王剑冰编辑孙钰芳
◎文|王剑冰 编辑|孙钰芳

长江南源当曲的国家地理标志 摄影/图虫创意
吉曲河畔,江源人家
在杂多举行过座谈会之后,考察团踏上了探寻长江南源当曲的源头之旅。才旦周书记安排吉多乡乡长尼玛及三位工作人员陪同我们。
道路不宽,但还算平坦。
路上遇不到什么车辆。途中路过一座扎拉达山,车队停了下来。
山峰紧靠路边,仰头看去,断崖峭壁,高插云端。尼玛说格萨尔王曾将神箭射入山石。他指着一个地方,说眼力好的人可以看见留在外边的箭羽。这个时候,有人说看到了,有人说看不到。反正大家都信,因为这个传说已经很多年。
在吉曲河畔,车队又停下了,尼玛让大家看一片神奇的草场。那草葱翠挺拔,招摇过膝,远看如大块的翡翠。尼玛说这草一年四季都是这样颜色,传说是格萨尔王的王妃珠姆种的羊饲草,而此地也正是《格萨尔王》史诗中的绵羊基地。众人直呼神奇。
在一片草场上散落着牛羊,看不见那些牛羊的主人。主人许就在哪个水边的帐篷,守着他们选择的孤独。
有时见到单个的人放着一群牛羊,只有一个小小的帐篷,在远处等着他的夜晚。
还有带着女人的牧人,那女人带着扎着小辫的女孩。女人守在帐篷周围,做着这样那样的事情,使得牧人有一种像牛羊一样的幸福感。在夜像山一样笼罩四野时,牧人会赶着牛羊回来。太阳重新滑进帐篷某个缝隙,他又会带着他的伙伴没入原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伙伴在不断地变换,而生活还是原来的样子。
这样说来,有一种人是人的另一种状态,他们自由着、单纯着、满足着、快乐着。
下起了雨,路变得不大好走起来。
文扎打开了雨刷器。透过车窗看到前面的路,到处都有积水,好像这一带一直没有晴过。车子躲着积水走,躲不过的,就冲压过去。

接山泉水的藏族女孩 摄影/王剑冰
车队的速度缓慢下来。走着走着,看到雨飞扬起来,原来已经变成了雪花。
渐渐地,路面白了。路更不好走。有时路上的坑洼太大,车子只能拐下道路,顺着流水走一段。流水中大都是沙石底子。
车队又停下了。
看到一个河谷,人们朝下面跑去。一会儿有人回来,说那里有一堆绛红色岩石,同姜黄色岩土摞起来,传说是王妃珠姆的排泄物。多少年,人们已经为这堆土赋予了神圣色彩,上面还缠裹着哈达。前面又是一段难走的路,没有办法,车子下到了冰河中。
这里的河水早已结冰。我们裹着厚厚的装备从车上下来照相。大家的兴致还是很高的。这个时候,中原已经热得穿短衫短裤了。
我拉着文扎一同起跳,让索尼蹲着照相,这样可以照出更高的感觉。早忘记了高原反应,上到车上有人提醒才想起来。
中午,考察团的车子再次停下。不远处有一户牧民。
首先看到的是两个孩子,姐姐大约五六岁,弟弟也就两三岁。这两个孩子正在接水。他们在一个山泉前,用勺子往五公斤容量的塑料桶里灌水。两个孩子穿的都不多,弟弟吸溜着鼻涕,不住地看我们。
大家说这两个孩子真好看,姐姐还穿着藏式的小裙子。有人上来给他们照相。连欧沙都加入进来。这两个孩子被众人要求:别动别动,好,就这样。就这样,好,可以舀水了。对,往桶里舀水。
而后姐姐提着装满水的桶艰难地往上走,那只桶甚至有些拖地。弟弟跟在后面,姐姐不时地回头看看弟弟。我起先以为姐弟两个在玩水,后来才知道是在帮大人干活。因为两个大人此刻正在屋棚里忙活。
大家被尼玛乡长邀请进屋。屋里暖暖地生着大炉子,上面烧着奶茶。
一会儿主人便提着被熏黑的奶壶挨个儿倒茶。索尼他们拿来了团队自己准备的干粮,大家就着主人家的热茶简单地吃着午餐。这个时候姐弟两个从另一间屋子门口露出头来,看着桌上的食物。
有人要拿给他们一块,被他们的父亲给说得缩了回去。但是我们坚持让他们接住,他们才吃起来。那个小姐姐提过来的水,被母亲倒在空了的茶壶里。
这是江源路上少见的一户人家,让人想到,无论谁从这里过,都会到这户人家里歇歇脚,喝口热茶,甚至还会借宿一晚。而他们,就是这样,笑着给你倒上奶茶,并不说多少话语。两个孩子,也就常常地冒着滑倒的危险,迎着寒风到五十米远的地方去提水。
走的时候,乡长尼玛指着靠近路边的地方说,原来这里有一块很有型的石头,有时会觉得挡道,就有人把石头抬到高处。可是第二天,这石头就像长了脚,又跑到路边碍事。连这家主人都说,半夜是留着长辫子红头发的人把石头搬到了原位。不知道为什么认定那个位置好。人们以为奇,就带着铁链子来,把这石头拴在那里。这不,刚才听这家主人说,拴着的石头不见了。应该刚被人盗走。
有的说,可能是玩石的盗走了。也有的说,可能是搬走镇邪去了。看来乡长十分在意这块石头,说明这石头被人们传得很广。要知道,这里可是人迹稀少的高原。那么,这块大石的遗失,会对这户人家有影响吗?不得而知。
长江南源科考纪念碑
众人告别热情的主人,继续行进。
雪却是慢慢停了。好在并没有怎么盘山,一路还算顺利。文扎说,长江南源有三座神山,像宝光一样散射出三条河流。一条是长江的南源当曲,一条是澜沧江的支流阿曲,还有一条是昂曲的源头吉曲。
从车窗里可以看到丰沃的山野。谁叫了一声,说快看,野马。果然,不远处,四匹矫健的野马悠然地跑过。
谁又说,那是什么,是野鹿吗?说话功夫,看不到了。
文扎说,这一带的野生动物很多,说不定还能见到雪豹和棕熊。
下午四点,开始进入源区。道路显得更窄,能够感觉是在上坡。
在这片广袤的高原,高峰是相对来说的,稍微有些变化,就能感觉出来。到了当曲源头的山脚,车子又往上走了一段,就再也无路可走,停在了半腰。
有人用手机测了一下,停车处海拔4900米。
而后徒步往上攀,实际上还没怎么攀,就已经气喘吁吁。
一道不宽却清澈的水流,从哪里极快地流下来。远处看,那水是黑色的,实际是被绿色的野草烘托的。水流就像一支画笔,弯弯曲曲地将草原分开,也将那些块状的沼泽分开。
是的,再往上就是大片的沼泽地,据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泥炭沼泽地。哪怕世界上最先进的越野车,到了这里也会望而却步。
在当曲源区,远处耸立的就是唐古拉山。在蒙古语里,这座山意为“雄鹰飞不过去的高山”,但在这里看唐古拉山,也就是比地平线稍高一点的小山。要知道这里的海拔已经是5000米。
作为长江的南源,当曲流域是高寒沼泽湿地的集中分布区,也是长江源地区湿地面积发育最大的区域。平均海拔在4600 米以上,最高发育到了海拔5600米,这个数字,是青藏高原湿地的上限。
当曲之名,来自藏语“沼泽河”的音译。多年冻土的广泛发育和分布,是当曲流域高寒沼泽形成的重要环境之一。这里自然条件恶劣,网状水系复杂,流经数百平方公里的地域,基本为无人区,处于原始状态。
连片的沼泽,简直无法下脚,一个个突出水面的坚硬土块,并不是规则的,左一个右一个,让人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不规则图形。
一凼凼水洼,透着千百年的清纯。这么多年,没有什么打搅它们。它们捧着一颗清心,冲着蓝天。
天什么时候晴了,并且有了阳光,连片的沼泽和泉眼,在阳光照射下,波光粼粼,忽绿忽蓝。
水凼间行走,一会儿就眼花缭乱,如果按照惯性踩踏,保不准哪一脚就踩进水里,那水可是瓦凉瓦凉。这样走不是走,跳不是跳,宽一脚,窄一脚,一会儿就疲惫不堪,眼目生疼。这简直是考验你的视力,你的实力,你的耐力,你的能力。如此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没有头,无边无际。
大家像撒了欢的鸭子,歪歪扭扭,晃晃悠悠地走“地雷阵”,谁也没有速度。不见进度,唯有难度。
本来以为走到前面那个制高点就到了。到了那里发现制高点又前移到了前面很远的地方。那只是一条暂时的地平线。
不甘心,再次攀去。攀到了那里,还是一样。还是另一个制高点在很远的地方等着你。
没有一个人不在这个时候失望地停下来,思考着天圆地方的问题,思考着大境界与小境界的问题。
终于看到了一块矗立于沼泽之中的长江南源科考纪念碑。立碑处实际上没有水源,周围看看,仍然是一片山体。立碑处也不是最高的山脚处,那就是山野中稍高一点的地方。
石碑所标示的源头海拔是5039米。远处耸立的唐古拉山,为当曲这片高寒的沼泽湿地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冰水,那么,形成下面细流的水源,就是这一片沼泽。这样想来,水源的确定,也是人为,不是上天旨意,不由造物主决定。如果再往上走,可能还会看到这样的沼泽和细小的水流,那样较真,这块碑石,很难找到一个下脚处。
想象中水源处是一个最顶尖级的所在,或是一条最细最细的水源,现实与想象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绝对,只有相对。而这个相对,也是大致,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发生了改变。科学无止境,一切仍在探索中。
这块光秃秃的石碑,是怎么弄上来的?汽车拉不上来,坑坑洼洼的沼泽,寸步难行。人抬上来,也不可能,走还大喘气呢。只有牦牛或者马驮,大概是雇了当地的牧民,从下边的车旁起运。

长江源区水系 制图/Roxie
献给江源的颂辞
大家停驻在“长江源”的石碑前,旁边有“国家地理标志”地标。文扎在这里用藏语吟诵了献给江源的颂辞。他的颂词我听不懂,我知道那是深情的诉说。作为这次考察团的领队,他总是显得执著而认真,深沉而含蓄。
看着他的表情,让我想起他说的话,因而也就深切理解他为什么如此正式与庄重。他说,这次考察的命题广,涉及的范畴大,打破了地理限制。源文化关涉到的是整个人类文化的源头,我们要用细致谨慎的态度对待这次考察活动,面对如此大的课题,像面对一片汪洋大海,我们就如一叶小舟,要横渡穿梭,探索一个个未知的答案,梳理众说纷纭的复杂问题,从地理上、视觉上、心理上来一次印象“源文化”。
有人还在赶过来,每个人都显得激动,或者因高寒缺氧,大张着嘴,呼出一口口热气。
有人捧起水喝,有人用水洗脸,有人在照相,照相时还欢呼跳跃。
一切都做完了,各自散开,开始往回走。有的却流连忘返,或站或蹲,或找个地方歪斜下来,也不怕潮湿。刚才谁过沼泽湿了鞋子,这会儿还是顾不得去管。
我看见粉红的格桑花,在坚硬的绿草间微笑。还有一种黄色的花,高高地越过蔓草的头顶,但不是成朵地开放,而是抱成一团,远看是一朵花,近看像一团叶子。它是有叶子的,那叶子是绿色,簇拥在它的下面,将它高高地烘托出来。还有好大一片紫色,如紫的焰,放射在天地间。走到跟前才知道是花,那种并不大的小花,可能在山顶草原显现不出个体形象,那么,就聚拢在一起,开成一个氛围,一个场面,一个更大的花。
当然,另有一种深紫的花,开在扑散开来的叶子中央,显得尤其尊贵,似是坐在一大片柔软的绒毯间。在绒毯的外围,是层层叠叠簇拥的绿草。只两朵这样的花,就铺排出好大一个场面,就像帝王与皇后在俯视着他的臣民。
大片的无名的绿草,一根根针刺一样,一片片竹尖一样,还有一种肥厚如兔耳却少有毛的草。
这里的草拒绝纤柔,一棵棵都突出高原性格。耿直、泼辣、不屈。长就长个样子,开就开个别致。
太寂静,没有一点喧嚣,没有方向指南,没有人间烟火。在这里似乎又回到原始时代,吃就手撕手抓,喝就喝随便哪里流出的水。可以歪歪斜斜、四仰八叉地躺倒,可以敞开胸怀地呼喊,可以尽情地奔跑,愿意跑多远就跑多远。可以放声地大笑,放声地大哭,把一生的郁闷都倾泻。
没有灰尘可以到达这里,没有污染在这里挥发。这里可以盛下所有,包括你的泪眼。
水流,千万道
直到太阳将落,大家才意犹未尽地往山下走去。
车子离开以后,莽莽山野又将陷入永久的寂寞。但是莽莽山野的生命,却仍然自由自在地生长和开放。

岸边的孤狼 摄影/税晓洁

岸边宿营 摄影/税晓洁
又看见那一道水流。刚才我进入沼泽后,将它忘记了,只顾着寻找立有石碑的源头。现在想起来,它不定是在哪里,将一部分沼泽的水源汇聚,只是汇聚了一小部分,就向下流淌。它似乎是沿着我们进入沼泽的边缘地带曲折行走,一边走,一边召唤。
现在,它已经“召唤”得相当有规模。它就在我们的右边。一忽出现,一忽隐没。我们的车子要顺着路走,那路还是一忽上一忽下地盘来盘去。
走出好远,谁喊了一声,看呀——就看到远处一道金光,长长地闪烁在天边。随着车子的临近,金光在变化,一会儿金黄,一会儿浅黄,一会儿又泛出了炫红。初开始以为是云团,再近了,却发现是一条水流,啊,不就是隐没不见的那道流水?
再往前开,简直惊呆了。在我们的前方还有右侧,出现了幻觉一般宏阔的水流。水流不是一道,而是千万道。
这片土地如此慷慨,让它们尽情地舒展、恣肆、漫漶成了一泓海波。这海样的波,丝绸一般细腻柔滑,闪现着五彩霞光。是的,刚才还是金色的、红色的,现在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甚至还出现了青色、银色,最后又变成了蓝色。这是我见到的最美丽的锦缎,简直不敢相信,这颜色是由河流变幻而成。
由于地理和沙石的原因,使河流构成了千万道波光,而且波光是不一样的。如果歪起头看,或者将它们竖起来看,会看到千万种旗袍包裹的身段。是了,是一场风华绝代的旗袍秀。一定不是秀给我们,它们是在自享自乐。在没有人经过的日子,每天都是如此张扬,如此浪漫,如此炫丽。
太阳为它们打着追光灯,一直到电能耗尽。
我们的团队,不知有多少人按动了快门,大家惊呼着,最后满足地上车离去。
随着车子的前行,晦暗的光线下,终于发现,那水,渐渐地归为了一条大河。
那就是当曲。
我现在知道,当曲在囊极巴陇与沱沱河汇合,就成了通天河。通天河流出玉树巴塘河口之后,称为金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