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灾难的科学预测与人文感知
2020-12-11刘华杰
刘华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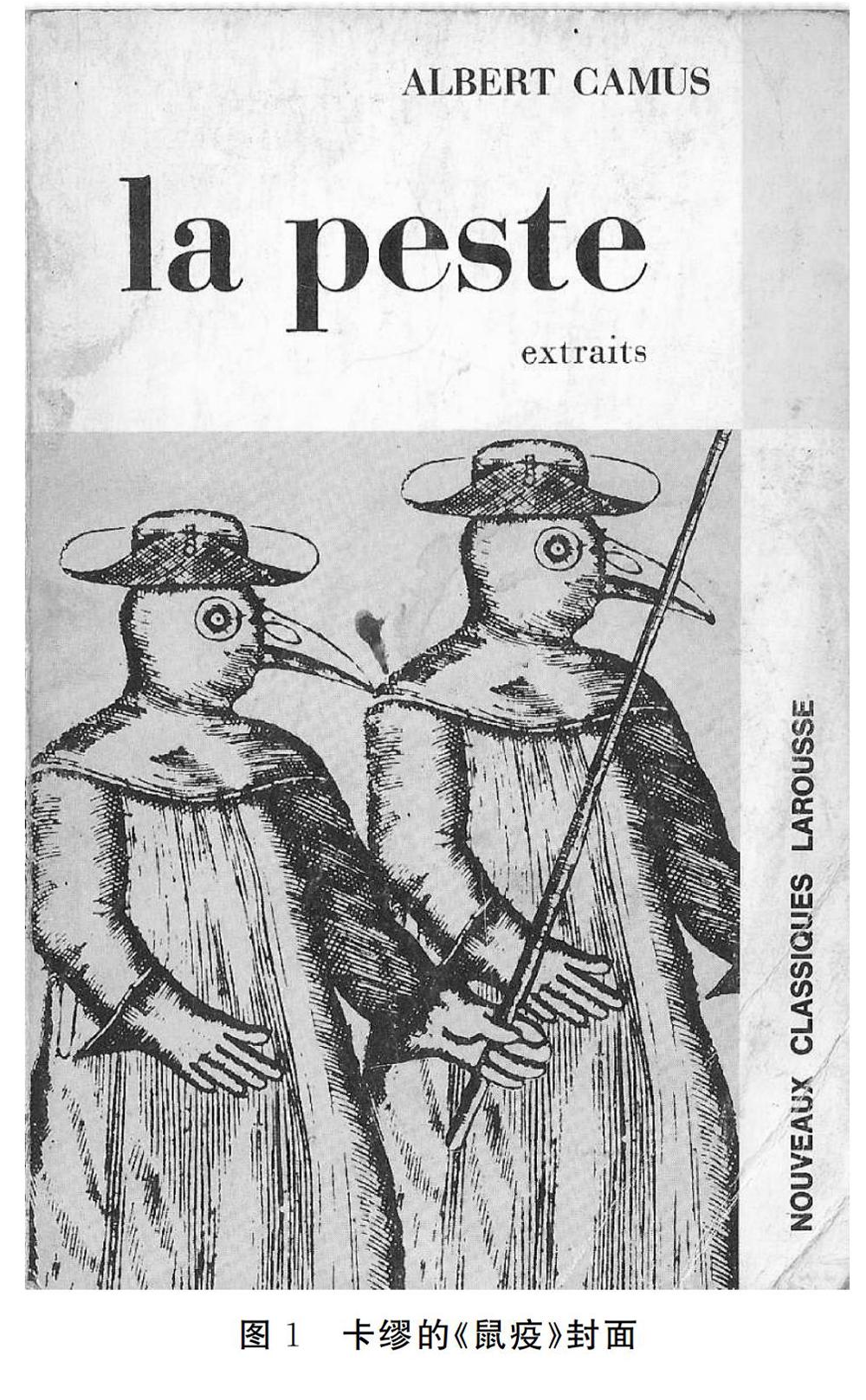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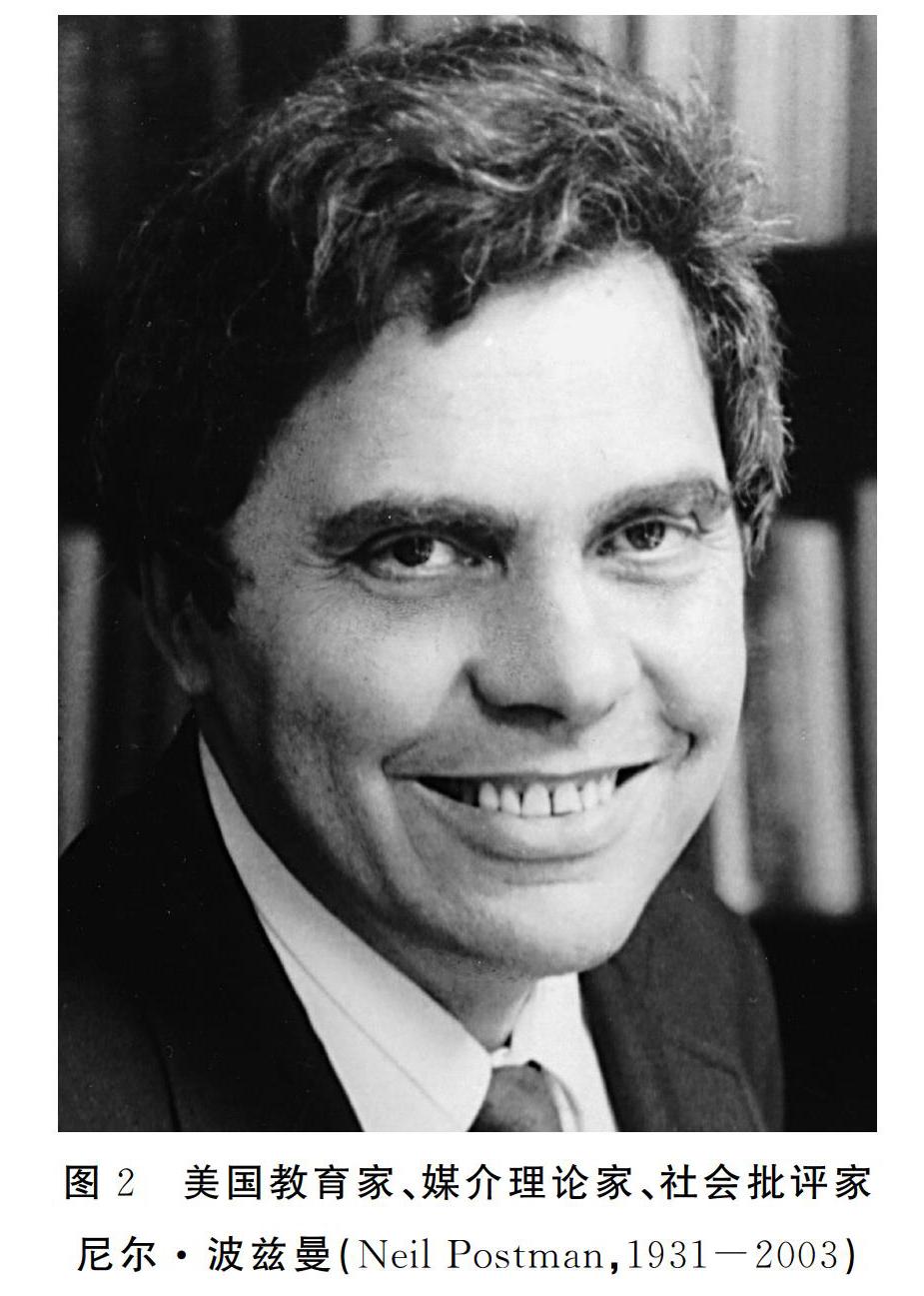
17年前的2003年,SARS在中华大地肆虐。当年5月份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我曾说:“明天、明年,或者100年以后可能还会有比非典更厉害的东西,人类做好准备了吗?”
多年过去,新冠疫情席卷而来,显然人类并没有做好准备。甚至可以说,人类根本就没有准备,也不想准备,大家都觉得灾难跟自己不会扯上关系,侥幸是现代人类生存的特点之一。哈佛大学的史蒂芬·平克教授在《当下的启蒙》中甚至提醒大家不要夸大灾难:“高估灾难本身就是一场灾难”。
有首老歌叫《世事不可强求》(Que SeraSera),朴素轻快的吟唱中表达出“未来不可完全预测、不完全可控”的常识。但用文明武装起来的现代人,不愿意相信这个基本事实。
自近代科学以来,哈雷彗星回归、每一次日食和月食发生的提前告知、火箭一次次的成功发射,都让人们误以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当然,为了更好地生存,人类发展出来的各种学问,特别是自然科学,目的之一就是预言明天,提前把握还未到来的事情。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是高度非线性的,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关系。根据非线性动力学和复杂性科学,系统的长期行为是不可预测的。
通过自然科学努力把握明天,没有错,但仅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考虑仍然不够。只有各尽所能、恰到好处地将科学预测与人文感知结合起来,才有希望应付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
那么,到底如何才算是“恰到好处”?
一、非线性世界与科学预测
做预测,要先讲明时间限定。通常短期邻近的预测可做,时空范围大了就不好办。不讲明这一点,就不能算在理性地思考问题。
仅以时间长短来考虑,预测多久合适?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尺”大一些,“寸”小一些,但它们是相对的,对预测而言,时间的长短也是相对而言的。
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时间一般都是以天、小时、分钟来衡量的。在科学中,运用多种计量单位。比如在信息时代经常会提及“纳秒”,l纳秒是十亿分之一秒。光在真空中1纳秒能走30厘米,光跑得很快,由此可想象1纳秒是很短的时间。另一方面,在宏观和宇观领域,一万年可能并不算很久,天文学家可以提前编出一万年的历书,一万年日月食的初亏、食既、食甚、生光、复圆等时间都可准确提前计算出来。
对于一个要预测的系统,可预测的时间长短是相对的。一万年对我们普通人而言太久,但对天体系统科学来说很短,可以准确推导。而对于微观粒子尺度的事件,一纳秒的时间就可能是很久了,预测也不容易。
那么,对于生活世界中个体的人呢,人的一生可以预测吗?
严格讲,人生在科学意义上不可精确预测,我们没法精确描述这类非线性的復杂系统,“人生”的尺度也超出了科学预测的限度。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十年后会怎样,一个小孩从出生到长大会变成什么样。
但是,人类仍然要为未来着想。以养孩子为例,养孩子也讲规矩、习惯,要读好的托儿所、好的小学中学大学等等,这里边涉及到多种预测,预测时间也有不同的量级,非常复杂,既有科学预测也有别的预测。我要说的是,需要把科学预测跟别的预测方式有机统一在一起,事实上人们也不自觉地这样做的。
首先,科学预测要求非常严格,不能打马虎眼、混水摸鱼,要用可检验的语言描述预测过程。19世纪时,人们已知天王星的运动不符合按牛顿力学所计算的轨道,科学家猜测,可能有什么东西干扰了天王星的轨道,很可能存在未被发现的新行星。
1846年8月31日,法国科学家勒威耶发表一篇报告《论使天王星运行失常的那颗行星,它的质量、轨道和现在所处位置的结论性意见》,来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报告题目是不是太长太哕嗦?是有点长,但并无废话,似乎第一眼就会让人觉得作者勒威耶颇有诚意,即他不想诓别人。他的报告“可证伪性”非常强,他假设了一颗谁都不知道的行星,认为它可以对天王星轨道的偏差负责,他推测了它的质量、轨道以及现在所在的位置。给“领导”提交这样的报告,领导可能被感动,决定试一试,不是吗?当时德国天文学家伽勒按照这个报告的内容在太空中展开搜寻,果然,当年的9月23日就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海王星!
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假如天气预报员说:“本市明天天气晴或阴,最低气温可能零下20摄氏度,最高气温可能零上40度,局部地区有大雨,个别地方会出现暴雪天气。”什么感觉?预报员说的不对?不是不对而是太有把握了!所述区间太大,对我们没有意义,相当于废话练习。科学预测跟街头算命不一样,它要求用科学语言表达,其预报应具备可检验性、可证伪性,要提供用户需要的特别信息。
有诸多限制,科学预测就很难做。除自身的限制外,还有其他方面的限制,我大致列举科学所面对的限制:其一,现在做科学是一种职业,任何职业都很难脱离功利化、行为短期化的特点;其二,科学家进行研究、预测必须建立模型,必须大规模地化简外部的非线性世界,这是方法论上的一个限制,不会化简就做不了科学;其三,科学研究要求尽可能定量化,因而考虑的时空尺度就大受限制,因为尺度一变大就很难量化;其四,现代科学分为很多学科,各个学科领域之间沟通不够,这是体制上的限制。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还讲过一个麻烦:要想预测明天会怎么样,就要用到明天才可能获得的知识,而明天我们能获取什么知识此时无法知晓。这意味着,从逻辑上看我们无法对未来做精确预测。
我也愿意顺便提及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一批数理科学家,如“七机部小组”宋健、于景元、李广元等,对中国人口的“精确预测”。他们采用了人文学者、官员搞不清楚的控制论、微分方程、差分方程、抽象函数等数学工具,发表了《人口发展问题的定量研究》《三十年来中国人口学方法发展的三大特点》《人口与教育》《人口系统稳定性理论评论》等论文以及专著《人口控制论》,为中央政府制订严格的一胎政策起了决定性作用。结果怎样呢?预测并不准确,导致国家宏观政策制订失误,这并不能归结为科学家不努力或者不严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社会系统太复杂了,生育受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个案例很说明问题,葛苏珊(SusanGreenhalgh,哈佛大学教授)和金度经(1974-,韩国首尔人,复旦大学博士)对此进行了有趣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现在大家都知道,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了重大变化,开始鼓励二胎和三胎。怎么会这样?能生时不让生,不能生时鼓励生。当年有多少家庭被迫只生一个孩子,现在跟谁讲理去?个体家庭有损失,国家也有重大损失。
二、人文社会科学感知未来
科学预测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的该做而没有做。
就拿眼前的事情来说,2019年时谁科学地预测到不久后会爆发新冠肺炎疫情?谁能预测到美国这个科技、医疗十分发达的国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过百万?谁能预测到中国最近两次火箭发射都不顺利?谁能预测到2020年4月24日纽约期货交易原油期货价格跌为负值?
没有预测到。人们特别需要提前感知风险,怎么办呢?除了自然科学,还要靠人文、社会科学,而且它们有这个本事!
部分科学家对人文、社会科学持有偏见,觉得它们不严格。但是,要重温一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句话,不是在刚才说的尺度相对性的意义上,而是在更大范围的行事方式上考虑。
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科幻小说家提前在他们的作品中十分形象、逼真地讲述过类似场景。我们从小说中看到类似的东西,可能都不会太当真,因为它是文学描写,是一种想象、虚构。但是,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真正遇到类似事情时,就会不自觉比较、借鉴、利用那里描述过的情节。那时这些“虚假”的小说几乎相当于“预言”。
几年前,我的好友田松(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为南方科技大学教授)跟我唠叨过:“现代社会系统要崩溃,最近就会”。我不相信,多数人可能也不相信。但是现在看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他以一个人文学者的身份通过对社会对世界的长期观察,发现系统中存在很多问题和风险。或者翻译一下,系统的非线性作用已经非常强烈,出现点异常是极有可能的。
著名科幻作家韩松曾说过,从玛丽·雪莱开始,科幻就在写瘟疫。《最后的人》写整个人类文明被瘟疫灭绝。还有克莱顿的《安德洛墨达菌株》、王晋康老师的《十字》、卡缪的《鼠疫》等,也都表达了对这类问题的高度关注。韩松认为科幻作品有这样的功能:“通过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人们重新审视与自然界和其他物种的关系,推动科学启蒙和科学研究,同时会促进社会治理、人文关怀和伦理建设。”
可能会有人问,为什么提前描述现在发生的灾难场景的往往是科幻作家、小说家和哲学家,而不是科学家?难道他们比科学家还厉害吗?
当然不是。他们不是神人,也不想跟科学家较量,但他们确实对未来有一定的感知能力。注意,不是科学预测,而是感知。为了与科学预测对照,叫它“人文感知”吧。
在高度非线性的世界中,经常无法预测未来,如果强行去计算、预测,就会出现科学家所说的欺诈现象,即假科学、伪科学。而人文、社会科学家(包括文艺工作者)是在构建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中的情节不是必然发生的,只是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文、社会科学家在推理、构建故事时,不严格受自然科学的限制,回想一下上面我提及的自然科学面对的限制。因为不受上述限制(当然还会面对其他的限制),它们相比于自然科学,就有了某种优势!
如果平时多品读经典作品,对我们感知未来是会有帮助的。即便不是为了预测未来,仅从欣赏世界、改善自我生活这个出发点来看,也是有好处的。
三、人文与科学如何统一起来?
1984年,尼尔·波兹曼发表了一篇名为《社会科学作为神学》的文章,文章中他认为,现在的社会科学不是科学而是神学。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举例了行为科学家米尔格拉姆电击条件下“对权威的服从”实验及研究论文,并表示米尔格拉姆的研究方式有相当多的伪科学特征。在波兹曼看来,在非自然条件下做这种实验并不代表自然状态下人们对权威的服从就是这样演化的,米尔格拉姆这样做只是为了模仿自然科学家,把一个复杂的系统化简到一个可控的简单系统中,这样的做法没有意义。
波兹曼认为,弗洛伊德、马克思、韦伯、芒福德、荣格、米德、汤因比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师所做的工作,不是科学,而是在“讲故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目标就是讲一个很好的故事。判别大师和普通人,关键就在于他能否讲出一个很特别且人们愿意相信的故事。
不同时期,人们展现同一类问题的方式可能不同,人们愿意相信的版本也不一样。1928年,著名小说家劳伦斯发表长篇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描述了在特殊场合下一位女性对“性”的看法,以文学手法展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压抑。放在今天,社会学家们可能会通过调查问卷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研究,金赛就这样做了,发表了“科学”报告,而在波兹曼看来金赛这样研究只是模仿自然科学而已。
在波兹曼看来,这两种形式并没有孰高孰低之分。大家都知道小说是在写故事,不必当真;而问卷调查看似客观,实际也隐含了很多前提假设。其实都不必太当真,都可以当作故事来了解一下。
换句话说,小说家和当代行为科学研究者都普遍使用了一些本行业内认可的手法,他们都可以“写”(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但因为系统都太过复杂,都是在尝试、猜测。文学家不可能完全精确地描画实际上将发生什么,他们会借用各种隐喻来塑造类型清晰的典型形象,就像好莱坞影片做的那样,观众也习惯按相关套路期望、接受其模式,会觉得那是一个好的故事。有没有用呢?当然有用,否则人们不会浪费时间看电影。
从这个角度出发,波兹曼认为,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其实是“道德神学”的一个分支,现代的人文学者跟佛陀、孔夫子等一样,都是在努力讲好故事。
在波兹曼看来,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讲好自己的故事就可以,没必要硬往自然科学方面靠,没必要冒充科学家。一位好的人文学者不必成为一位自然科学家,类似的,行为学家、经济学家也是如此。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小说家、人文学者跟自然科学家做的是同类的事情,都是想把握明天。前者可能是布道者,而后者可能是当代人认可的学者,这两者的界限其实可以适当模糊一下。
总之,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不要气馁,没必要假装科学,强行模仿科学反而把自己的优势弄没了。人文社会科学感知未来是讲各种各样的可能的故事,它并没有说下一步直接切换到哪一个场景,这就像你多镜头拍一个视频,我们虽然不知道总导演下一步会切换到哪一个镜头,但是你准备的剧本、素材、方案(scenarios)多了,未来能够应对的可能性就多了。
以经济学为例,现代西方经济学观点众多、学派林立,谁代表真理?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颁给了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瑞典福利经济学代表纲纳·缪达尔。他们两人立场、观点很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经济学一般被认为是很接近于自然科学的学问,所以经常称经济学为科学,但这两个观点相异甚至相反的人,却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A和非A会同时成立呢?
嚴格讲不是“同时”,他们只是同时领奖而已,在现实中其学说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场合分别成立的!只要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条件接近某一学说的前提,其主张就有意义了。所以矛盾的学说,各有各的用处,它们都是真理,相对于自己要求的条件而成立。
四、反事实条件句
说清上述经济学的案例,要用到科学哲学里的“反事实条件句”,刘易斯和古德曼仔细研究过这类句子。
自然科学中最客观、最牢靠的科学定律,实际上与反事实条件句相伴随。科学定律不是自然定律,我们知道前者而不知道后者。任何科学定律的得出和成立,都是有条件的。比如,牛顿第一定律说,一个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的作用下会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
请注意,这个条件根本不成立,根本不存在没有外力作用的物体。但是能构造这样的反事实条件句,也正是牛顿及牛顿定律伟大之处。汉语中不大使用反事实条件句,杞人忧天之类的剧本不受欢迎,科幻故事在中国也没市场,中国人发现(发明)的自然定律也不多。据说好不容易找到一条郑玄一虎克定律!我相信还有一些,但不多。
科学要发达,就要多方构造有意义的反事实条件句。从反事实条件句可以一窥自然科学中科学定律的性质。科学家借科学定律驯服大干世界中的各种偶然性、不规则性。从反事实条件句看,自然科学也是在讲故事,当然,自然科学讲不了很不一样的故事。但是无论如何特别、如何好,这样的故事依然没有必然性。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基本信条就是,综合陈述没有必然性,科学定律给出的是综合陈述,因而本身也没有必然性。是不是有点反常识?
通过反事实条件句,我们可以把波兹曼所说的人文社会科学讲故事,与自然科学家对复杂系统之未来的预测等,联系起来,做统一的解释。统一到哪呢?统一到自然科学还是统一到人文?为了避免抢功,我提供科学与人文之外的第三方选项:讲故事。为了论证这一点,要请出重量级人物威尔逊。
美国生物学家、博物学家、蚂蚁专家、两次普利策奖得主威尔逊(Edward O.Wilson),在写《创世纪》这本小书时引用了一项人类学家的研究,该研究2014年发表到美国科学院的院刊PNAS上,说的是非洲某部落晚上围坐在篝火旁讲故事的事。
可能会有人问,篝火晚会我们也见识过,大家在那种场合玩玩而已,还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吗?
威尔逊认为,非洲部落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篝火旁讲故事,有着重要的认知含义。很多非洲部落没有自己的文字,没有书面语言,没有书本、电脑,文明怎么传承?就靠一代一代讲故事。
那篇人类学论文通过详细的调查显示,他们白天大多都是谈论经济、收入问题,或者抱怨,或者讲一些笑话;而到了晚上,就比较安静、严肃,讲的多是家族的起源、人类经历过哪些风险、时代的发展、未来可能会怎样,等等。
这种讲故事,对于人这个物种的社会化,起着关键的作用。通过讲故事,积累了见识,传承着文明。在某种意义上说,要认知、理解、利用这个世界,要传承文明,就要学会讲故事。
五、讲故事与“自我实现预言"
综合波兹曼的观点和科学哲学的观点,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在讲故事!
通常情况下,大部分人认为自然科学家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生产真理。谦虚一点,也会承认在讲故事,只是故事更客观,可信任度更高。科技工作者为了讲好自己的故事(当然也为了我们)做了大量研究,政府、资本家、百姓也愿意资助他们。而人文学者讲的故事,本来就是故事,大家早就明白。其故事可信度较弱,学者在现代社会要生存下去,继续讲故事,就得拿出新的理由。
讲故事和社会科学中的“自我实现预言”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研究过“自我实现预言”。简单说,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希望未来怎样,最后这个世界真的就变成了什么样。比如,人们说狼来了,最后狼真的就来了。这和自然科学很不一样,其实自然科学也在期望。
人类是理性的动物,可以协商、可以计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成“自我实现预言”的实现。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在我们生活的非线性世界里,系统中充斥着大量的不确定性,这当然不会令人停止不前、无所作为。它促使人们不得不做一些事情、准备一些故事,学会适应大自然的发展。
大自然拥有自我调节的机制,人类仅是其中一个物种,虽然我们很聪明,有科学的知识、有文明体系,但也要有风险意识,特别是警惕科技本身可能带来的风险。
我们要更加强调博雅教育、文理教育,对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有更多切身的理解。人类今天的行为会影响到明天,普通百姓经不起太大风浪,但有权有钱有技术的人可以,所以要通过科学、人文的博雅教育,对这些不确定因素进行本能的防范。
非线性世界的下一刻会是什么样的?严格来讲没有人知道。但是有准备和没准备,是完全不一样的。
人是一个有知识、有科学、有文化的物种,不同于花鸟虫鱼那样只会作出本能应对,但演化论讲的“适应”本质上看都是被动的,对人这个物种而言有一点点主动的成分却不可得意忘形。人类不宜贬低其他生命的应对“策略”,其实它们的应对更加自然,也更合天理。人类的确具备能动性,这一特质令人类不断通过学习,以更好地应对下一刻、长远发展的可能局面。正确的做法是,通过一定的学习,不是把你带进沟里的那种,讲好自己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天人系统的故事。
我从不否认人文与科学有诸多不同,但今天只想强调它们的一致性。
(根据2020年5月7日晚混沌大学线上讲座《非线性世界的下一刻:科学预测与人文感知》记录整理。2020年7月23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