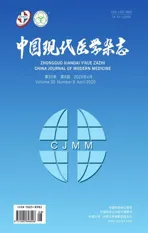体外循环和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中患者脑氧饱和度的变化趋势分析
2020-09-22庄燕萍窦雯玥周兴梅张敏
庄燕萍,窦雯玥,周兴梅,张敏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危重病科 上海 201600)
对于心脏手术患者,尤其是年龄>60 岁老年患者,术后早期发生认知功能障碍(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 POCD)的风险较高[1]。VEDEL 等[2]学者通过多中心临床调查发现,体外循环心脏手术者术后5 ~7 d 的POCD 发生率可达33%~83%,甚至部分患者POCD 为永久性损伤。有研究证实,术中通过监测脑氧饱和度(cerebral regional oxygen saturation,rScO2)可反映脑组织氧供需平衡状况及脑血流量变化,对于术中和围手术期个体化管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3]。近年来,利用反射性红外光谱技术监测术后rScO2变化趋势逐渐在心胸外科手术中大力推广。但是POCD 的发病机制和影响因素尚不明确,因此目前对于监测rScO2的临床价值也一直存有争议。YU 等[4]学者认为,监测术中rScO2变化并不能预测体外循环下心瓣膜手术患者术后早期POCD 的发生风险,只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患者住院时间的长短。本研究拟在相同麻醉条件下,监测体外循环和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术中rScO2变化趋势,以及早期POCD 发生率,从术中rScO2水平变化角度评价体外循环和非体外循环对POCD 发生风险的影响,希望为POCD 发病机制的研究及临床防治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2月—2019年6月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择期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105 例患者。其中,男性62 例,女性43 例;年龄18 ~80 岁,平均(54.04±14.57)岁。纳入标准: ①术前经查体、超声心动图、心电图、胸片等综合检查确诊,符合心脏手术指征;②择期行心脏手术者,包括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off-pump coronary artery bypass,OPCAB)和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nvention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CCABG);③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 ASA)分级Ⅱ、Ⅲ级[5],美国纽约心脏病学会(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 NYHA)心功能分级Ⅱ、Ⅲ级[6];④患者或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①术前存在认知功能障碍;②术前有心肌梗死、血栓栓塞、恶性肿瘤或心脏手术病史;③存在颈动脉斑块、颈动脉闭塞、颈动脉支架植入史;④急诊手术者;⑤术中由OPCAB 转为CCABG。本研究严格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批号: SH20180015。根据麻醉体外循环方式,105 例患者分 为OPCAB 组56 例 和CCABG 组49 例。OPCAB 组男性33 例,女性23 例;CCABG 组男性29 例,女性20 例。
1.2 治疗方法
1.2.1 麻醉方法及术中监护所有患者采用静吸复合气管插管全身麻醉。进入手术室后面罩吸氧,开通静脉通路,行右动脉穿刺置管,静脉滴注瑞芬太尼(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H20030200)0.5 ~1.0μg/kg、顺式阿曲库铵(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60869)0.15 mg/kg、咪达唑仑(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31071)0.05 ~0.10 mg/kg、依托咪酯注射液(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32022379)0.2 ~0.6 mg/kg 进行诱导麻醉。气管插管后连接麻醉机,实施机械通气。输注丙泊酚注射液(德国Fresenius Kabi 公司)1.0 ~2.0μg/ml,吸入七氟醚(上海恒瑞医药公司,国药准字H20070172)1.0MAC 维持30 min,术中监测麻醉深度,维持脑电双频指数在40 ~50。
1.2.2 手术①OPCAB 组患者麻醉后进行全身半量肝素化处理,安置心脏固定器,切开冠状动脉并阻塞吻合口血流,行左乳内动脉与前降支吻合,桡动脉远端、大隐静脉桥近端与冠状动脉的端侧吻合,使用侧壁钳钳夹部分升主动脉作血管近端吻合处理。②CCABG 组患者进行全身肝素化处理,使用膜式氧合器和滚压泵平流灌注,经升主动脉、右心房插管建立全流量体外循环,监测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手术期间调节氧合器气体流速以维持正常二氧化碳CO2。心脏停跳后作桡动脉远端、大隐静脉桥近端与冠状动脉的端侧吻合,随后作左前降支与乳内动脉吻合。开放升主动脉,待心脏复搏后,钳夹升主动脉,完成主动脉吻合。
1.3 rScO2 测量
记录入室后(T0),麻醉诱导后(T1),OPCAB 组半肝素化/CCABG 组肝素化后(T2),OPCAB 组放置心脏固定器后/CCABG 组完全心肺流转(T3),OPCAB组吻合桥血管/CCABG 组心脏停搏后(T4),OPCAB组吻合桥血管远端/CCABG 组停止降温10 min(T5),OPCAB 组桡动脉远端、大隐静脉桥近端与冠状动脉的端侧吻合后/CCABG 组复温(T6),OPCAB 组钳夹部分升主动脉作血管近端吻合后/CCABG 组复温10 min(T7),OPCAB 组停机/CCABG 组测量桥流量时(T8),手术结束时(T9)rScO2,NIRS 脑氧饱和度监测仪购自丹麦福斯公司,型号DS2500。
1.4 手术指标及短期预后
记录患者手术时间、术中最低鼻咽温、术中最低红细胞比容(HCT)、术中最高血糖(Glu)、术中最高血乳酸(Lac),以及术后死亡和POCD 发生率。
1.5 MMSE 评分
术后5 ~7 d 评估MMSE 量表评分,若量表评分低于术前基础值2 分或者<26 分,则视为POCD。
1.6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SPSS 17.0 软件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比较用t检验或重复测量设计的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构成比(%)表示,比较用χ2检验;相关性分析用Pearson 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资料比较
两组年龄、性别构成、体重指数(BMI)、合并疾病、吸烟史、饮酒史、文化程度、ASA 分级、NYHA 心功能分级、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 两组临床资料比较
2.2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最低鼻咽温、术中最低HCT、术中最高Glu、术中最高Lac 比较,经t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CABG 组手术时间长于OPCAB 组,术中最低鼻咽温和HCT 低于OPCAB组,术中最高Glu 和Lac 高于OPCAB 组。两组患者术中最低rScO2比较,经t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术中rScO2 变化趋势
OPCAB 组 与CCABG 组 在T0、T1、T2、T3、T4、T5、T6、T7、T8、T9时间点测量rScO2水平比较,采用重复测量设计的方差分析,结果: ①不同时间点的rScO2水平比较有差别(F=12.068,P=0.000);②两组rScO2水平有差别(F=20.197,P=0.000),OPCAB组与CCABG 组相比在较晚时间达到最低rScO2,随后上升;而CCABG 组在T3时间点达到最低rScO2后随即上升,在T7时间点时又再次下降,随后上升。③两组rScO2变化趋势有差别(F=37.465,P=0.000)。见表3。
表2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比较 (±s)

表2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比较 (±s)
组别 n 手术时间/min 术中最低鼻咽温/℃术中最低HCT/% 术中最高Glu/(mmol/L)术中最高Lac/(mmol/L) 术中最低rScO2/%OPCAB 组 56 181.47±46.85 34.71±0.50 33.34±2.76 138.95±36.63 1.12±0.32 60.53±3.34 CCABG 组 49 217.83±57.62 31.23±0.78 24.50±3.45 162.28±47.31 1.54±0.48 61.74±2.97 t 值 3.564 27.549 14.571 2.843 5.334 1.949 P 值 0.001 0.000 0.000 0.005 0.000 0.054
2.4 两组患者rScO2 与鼻咽温、HCT、Glu 及Lac 的关系
经Pearson 相关性分析,CCABG 组rScO2与鼻咽温、Lac 呈正相关(P<0.05),而OPCAB 组rScO2只与Lac 呈正相关(P<0.05)。见表4。
表3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rScO2 水平比较 (%,±s)

表3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rScO2 水平比较 (%,±s)
注: †为术中最低值。
组别 n T0 T1 T2 T3 T4 OPCAB 组 56 66.92±2.48 67.28±3.11 65.79±2.12 61.85±1.93 60.53±3.34†CCABG 组 49 65.87±2.97 66.46±2.48 66.33±2.34 61.74±2.97† 65.56±3.00 t 值 1.974 1.479 1.241 0.228 8.071 P 值 0.051 0.142 0.218 0.820 0.000组别 n T5 T6 T7 T8 T9 OPCAB 组 56 60.77±3.02 61.03±3.12 65.15±2.46 68.38±4.24 68.16±3.62 CCABG 组 49 68.91±3.15 69.93±3.54 61.95±2.92 67.41±4.10 65.78±2.97 t 值 13.498 10.621 6.094 1.188 3.467 P 值 0.000 0.000 0.000 0.238 0.001
2.5 两组POCD 发生率及与术中最低rScO2 的关系
两组术中和术后7 d 内无患者死亡。术后5 ~7 d,OPCAB 组POCD 发生率为39.29%(22/56),CCABG组为32.65%(16/49),经χ2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498,P=0.481)。
OPCAB 组中POCD 患者与非POCD 患者术中最低rScO2分别为(59.86±2.87)%和(61.28±3.16)%,经t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706,P=0.095),说明OPCAB 组患者最低rScO2值与POCD 无关。CCABG 组中POCD 患者与非POCD 患者术中最低rScO2分别为(60.54±1.63)%和(63.95±1.94)%,经t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061,P=0.000),CCABG 组中POCD 患者最低rScO2低于非POCD 患者。
3 讨论
POCD 是心脏手术后最常发生的暂时性或永久性的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之一,属于医疗处理引起的轻度神经认知障碍,与谵妄、痴呆、遗忘等临床类型存在一定的差异,目前国内外指南中尚缺乏统一的诊断标准和诊断时间。从POCD 的发病机制、起病原因等方面进行研究对于改善患者预后,降低POCD 发生率有重要帮助。众多研究证实,术前合并脑神经病变、中枢神经系统疾病、颈动脉粥样硬化、术中麻醉和循环因素等是影响POCD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7]。体外循环是目前大多数心脏直视手术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之一,但是体外循环中血液与外源性生物材料直接接触,以及心脏手术中产生的缺血再灌注损伤等都是引发全身炎症反应的重要原因[8]。除此以外,血液稀释、脑内毛细血管固体微栓和液体微栓因子的形成,导致脑组织局部缺血缺氧,易引发POCD。谭金等[9]学者证实,CCABG 患者术后3 个月POCD 发生率高于OPCAB 患者,但是在术后早期(≤7 d),两组患者POCD 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MOLLER 等[10]学者曾经对1 128 例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发现术后7 d 内POCD 发生率约为26%,而术后3 个月POCD 发生率降为10%。而且HOLMGAARD 等[11]学者认为,术后早期发生POCD 的患者5年内发生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大大增加。因此本研究着重探讨105 例心脏手术患者术后7 d 内POCD 的发生情况。
rScO2是反映手术过程中脑氧合状态和脑血流变化的重要指标,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重视术中rScO2的变化趋势。虽然有研究证明,在心脏手术中,纠正术中rScO2降低可能会改善患者预后[12],但是关于rScO2与POCD 的关系尚缺乏可靠的实验证据支持。本院引进近红外线光谱分析脑氧饱和度监测仪,用于术中监测rScO2的变化,希望从rScO2变化的角度分析OPCAB 和CCABG 造成术后POCD 发生率差异的原因,从而为防治提供一定的参考。结果发现,手术过程中OPCAB 组和CCABG 组最低rScO2值比较无差异,但是术中T4、T5、T6时间点CCABG 患者rScO2高于OPCAB 患者,T7、T9时间点CCABG 患者rScO2低于OPCAB 患者,而其他时间点OPCAB 与CCABG 患者rScO2水平基本一致。可能是因为T4、T5、T6时间点是OPCAB 组安放固定器后,行心脏桥血管吻合时,此时由于固定器的安放和心脏搬移影响心输出量,使静脉压升高,从而导致rScO2降低。而CCABG 组在流转开始时会出现血压急剧下降,从而使rScO2降低;但是随着灌注量增加,rScO2又逐渐上升。但是随着血液复温,机体代谢有所升高,导致rScO2变化会再次出现一个低谷。在停机时,HCT 升高导致动脉压升高,心输出量增加,rScO2也随之升高。CCABG 组患者rScO2与鼻咽温、Lac 呈正相关,OPCAB 组患者rScO2只与Lac 呈正相关。两组rScO2变化趋势不同,主要是由于CPCAB 组属于非体外循环手术,不涉及变温过程,而CCABG 组需要通过血液稀释达到降温目的,因此会影响机体代谢率。而且OPCAB 和CCABG 搭桥血管顺序不同,对血压的影响也会有差异。
通过分析OPCAB 和CCABG 术中rScO2变化规律,未发现OPCAB 与CCABG 患者存在差异,而且两组术后早期POCD 发生率也无差异。POCD 的发病机制是由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rScO2只是其中一项指标,虽然灵敏性较高,在临床应用中存在较大潜能,但是容易受到年龄、体温、吸入氧浓度、颅骨厚度及手术操作的影响[13],而且目前尚缺乏统一的检测标准[14],最重要的是rScO2并不能完全反映脑组织中氧气的利用度[15]。因此本研究只是从术中rScO2水平变化角度证实OPCAB 与CCABG 术后早期POCD 发生率无显著差异,至于2 种不同心脏手术方式是否存在发生早期POCD 风险的差异,仍需要大样本研究及从其他发病机制角度作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