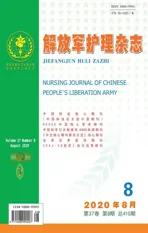围产儿死亡妇女创伤后成长轨迹的质性研究
2020-09-21高伟王琳李红
高伟,王琳,李红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护理部,上海 200030;2.中国医院发展研究院 护理管理研究所, 上海 200025;3.上海交通大学 护理学院,上海 200025)
据统计[1], 2017年全球有250万围产儿死亡。国内围产儿死亡的诊断按照围产I期诊断标准[2],即妊娠达到或超过28周至产后1周所发生的死胎、死产和新生儿早期死亡。2018年,我国围产儿死亡率为4.26‰,上海市围产儿死亡率为2.38‰[3]。围产儿死亡是妇女经历的一种突发特殊情况,由于身心处于应激状态,妇女易产生孤独、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有的甚至可能出现自杀[4]。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创伤后成长受到了各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创伤后成长理论认为,成长与精神痛苦共存,创伤经历不仅会导致消极的心理问题出现,也会给个体带来积极的心理变化[5]。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围产儿死亡妇女创伤后的成长经历,以期为创伤后不同阶段的干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7年7月至2019年12月,目的抽样法选取上海市某三级甲等妇产科医院产科病房曾收治的围产儿死亡妇女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18岁以上;(2)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存在精神障碍、认知障碍、交流障碍者。根据研究目的和抽样的最大差异原则,本研究在选择样本时考虑了不同年龄、学历、职业、生育史、妊娠方式、围产儿死亡原因等,以充分体现差异的最大化。当资料出现饱和时,结束收集和分析资料,共访谈围产儿死亡妇女10名。受访者的一般资料见表1。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1.2 研究方法
1.2.1 资料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使用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扎根理论主要致力于研究行为与过程,是一种探索现象的归纳性研究。通过采取面对面、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收集资料,访谈均采用开放式问题,“您能谈谈当您得知胎儿发生意外时的情况吗?”、“这件事发生后您有哪些改变?这些变化对您的家庭、生活、工作等有何影响?”、“您未来的人生有何打算?”等。本课题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与患者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并与患者充分沟通,告知本研究的目的,承诺对其的隐私保护,获取研究对象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访谈过程中做好录音和笔记,访谈时间50~60 min。对访谈录音进行逐字逐句转录,采用Strass和Corbin的扎根理论分析的方法[6]对资料进行开放式登录、轴心式登录、选择式登录。
1.2.2 质量控制 为避免研究者个人先前观点对资料的主观影响,研究者尽量悬置个人已有的观点和想法,以确保轨迹形成是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以研究者固有观念形成的。资料分析与课题组另一名老师共同完成,以尽量避免因为单一研究者所产生的偏差。访谈结束后,在进行资料整理和分析时,对出现信息遗漏的资料,进行进一步追问。回访受访者确认研究结果是否符合她们的真实经历。
2 结果
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分析资料,共形成13个代码,3个类属和10个下位类属,最终提炼出核心类属是围产儿死亡妇女创伤后成长轨迹,见图1。

图1 围产儿死亡妇女创伤后成长轨迹
2.1 应激期 指妇女从入院面对突发的“胎死宫内”这一诊断,在住院期间接受检查、经历死胎分娩的时期;此阶段妇女心理遭受巨大打击,深陷痛苦。本研究结果显示,这一时期平均持续时间为2个月,主要呈现以下4个特征。(1)震惊。妇女均表示当得知诊断时感到震惊,不知所措。N6:“当时就呆住了,没想到快生了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整个人都是蒙的。”(2)否认。妇女对围产儿死亡的事实没有心理准备,难以接受,试图通过复查等方式证实诊断。N9:“其实已经知道没有胎心了,但对这个事实我是不承认的,还抱有一丝希望,第二天又换了一家医院检查,又确认了一下。”(3)崩溃。妇女住院后在承受精神打击的同时,又面临着分娩时的生理性宫缩痛,内心绝望而无助。N5:“整个发动的过程中我情绪都很崩溃,待产室只有我一个人是没有胎心监护的,还有孕妇跟我聊天,问我是什么情况?”(4)殇痛。分娩后妇女未能正视丧失胎儿的现实,在心理上未完成健康分离,殇痛持续存在。N8:“宝宝生好后,当时医生也不给我看,我觉得特别遗憾,感觉冰冷的她好可怜,我都没有抱她一下。”
2.2 恢复期 这一时期妇女仍很痛苦,但在良好的社会支持下,通过深层次的认知加工,妇女渐渐关注当下生活,并有所行动,努力与创伤进行抗争。本研究结果显示,这一时期平均持续时间为2年,主要呈现以下3个特征。(1)认知加工。妇女自身不断反思不良妊娠的结局归因,在痛苦中寻找力量。①宿命观:N9:“我想这就是我的命吧,命中注定我和这个孩子的缘分太浅了。”②结局反思:N5:“一直在想是不是没有及时发现胎动异常造成的,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她,就是自己的原因。” ③意义构建:N10:“我心情再这样郁闷下去的话,会不会对我的家庭带来更加不好的影响,与其这样不如我自己调整好心态,迎接后面一个宝宝。”(2)主动应对。妇女试图通过注意转移、精神寄托等行为主动回避容易引发创伤体验的活动或情境。①规避刺激: N10:“我把工作单位换了,住的房子也换了,能换的环境我都换了一遍。”N3:“宝宝的衣服全部都送掉了,一件都没有留。”②注意转移:N7:“周末报了一个班去学车,尽量不要让自己空很多时间来想这件事情,事情发生后会刻意的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工作。” ③精神寄托:N7:“我每日礼佛,为宝宝祈福,许完愿之后得到一定的释然。”④关注当下:夫妻双方渐渐聚焦当下生活,并有所行动,如通过孕前检查、积极锻炼等方式争取早日怀孕。N2:“我办了健身卡,好好调理身体备孕下一胎。”N5:“我们去做了孕前体检,还接种了麻腮风疫苗。”(3)社会支持。本研究中社会支持主要来源于医护、家庭及同伴。①医护支持:N7:“医护人员的鼓励作用特别大,特别迷茫的时候,就用微信联系一下医生,我们就安心好多。”②家人支持:N5:“我老公对我鼓励也很大,孩子没有不要紧的,我觉得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你。”③同伴支持:N8:“病友之间相互联系的,病友说出的话不一样,因为我们都有切身体会的。”
2.3 成长期 此阶段痛苦虽在,但已能坦然面对,妇女能以一种平静的语气陈述过往,在自我陈述中更倾向于表达其在创伤过程中的体验和感受,这一阶段作为成功应对的各种成长结果已凸显出来。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对象平均在创伤事件发生后的第3年进入成长期,这一时期主要呈现以下3个特征。(1)人生哲学变化。创伤后个体重新审视生命,对生活事件进行重新排序。N8:“经历这么大的事情,现在工作中、生活中的琐事看得很开,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难过,每天开心最重要。”(2)个人力量增强。创伤后个体产生正性的生存意识,主要表现为更高的自我效能。N9:“这个过程是痛苦的,经历了以后就成长了,我都到最低谷了,还怕什么呢?后来我就积极面对一切。”(3)与他人关系变化。在与他人的人际互动中,伤者认知到与他人关系的转变。①夫妻关系更加亲密:N10:“两个人以前就是吃吃喝喝什么的,现在两个人的感情更加深了。”②同理心与利他意识:N2:“病房里看到同样的患者同情和怜悯会多一点,看到她哭我也想哭,家属有什么要求的话,我都会尽量满足。” ③人情的美好:N7:“住院的时候来看我的同事很多,觉得同事之间的友谊还是很重要的,回想起来她们安慰我的样子,觉得很温暖。”
3 讨论
3.1 探究围产儿死亡妇女创伤后成长轨迹的意义 了解创伤后妇女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变化,是临床医护人员实施干预方案的前提。本研究发现,围产儿死亡妇女早期存在较强的负性心理体验,主要表现为震惊、否认、崩溃与持续性哀伤等,这与Pabon等[7]研究的创伤后成长体验相符。有研究[8-9]显示,围产儿死亡事件在给妇女带来负性心理体验的同时,也能使她们感受到生活中的积极改变。创伤后成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该过程中妇女能摒弃负性心理情绪、想法和判断,重新认识自己并做出积极正确的应对,找到归属感,重塑对生活的信心,这将对疾病的康复产生重要作用[10]。王艳波[11]将创伤后成长轨迹定义为“毁灭期、接受期、重建与整合期”等3个阶段,并指出其对应的心理体验为“深陷痛苦、努力成长及实现成长”。本研究显示,围产儿死亡妇女创伤后成长轨迹是一个持续的动态变化过程,创伤后成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步发生的,主要可划分为应激期、接受期、成长期三个阶段。医护人员了解围产儿死亡妇女创伤后成长发生的时间轨迹,理解创伤发生后经历怎样的阶段性心理变化,根据患者的需求有针对性地给予积极、正确的引导,对于促进其创伤后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3.2 围产儿死亡妇女创伤后成长轨迹各时期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历围产儿死亡的妇女,不同时期的情绪及照护需求不同。(1)应激期:这一时期妇女的负性情绪很强烈,不知如何面对当下及未来,有研究[12]表明,医护人员的专业支持可以增强患者个人力量。此时,医护人员应感知到妇女心理状态并判断其心理需求,为其提供一个安静的病房,将正常分娩妇女与其分开,避免环境刺激,并给予同理心和专业的指导。引产过程中,面对患者的绝望情绪,助产士的支持非常重要,要帮助其在痛苦中寻求意义,找到精神支撑并给予殇痛关怀。分娩后,为避免妇女日后的回忆,助产士常拒绝妇女见新生儿遗体。有研究[13-14]报道,通过追悼、鞠躬、拍摄照片等仪式活动,可以帮助失去胎儿的家长正视丧失胎儿的现实,在心理上完成健康分离,引导新的出发。(2)恢复期:此阶段妇女在创伤与调适中逐步迈向成长,帮助伤者在痛苦中“寻求意义”、促进有效应对、营造良好的人际气氛,是激起其自我成长的动力。研究[15-16]显示,社会支持对个人的创伤后成长具有积极影响。本研究中围产儿死亡妇女创伤后的成长,离不开医护人员的专业支持、配偶和同伴的支持。妇女对创伤事件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思考怎么做才能有利于自身康复并计划孕育新的生命。有研究[17]显示,对不良妊娠结局妇女提供产前咨询和心理支持不仅可以减少其焦虑和抑郁症状,而且还能提高其身心功能及再次怀孕的概率。(3)成长期:尽管创伤后妇女早期存在诸多心理问题,但认知加工、主动应对、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促发其创伤后成长的发生,最终实现自我、与他人关系、人生哲学3个方面的成长。本研究显示,创伤后成长的发生是一个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这与刘冈等[10]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3.3 个人认知加工是创伤后成长产生的重要因素 个体对创伤信息的认知加工是个体走向成长的关键环节[18],认知加工指创伤事件发生后个体经历的反思及积极释意等过程。Davis等[19]在其质性研究中也发现,获得个人成长者均易从创伤中寻找到意义,而未获成长者多不能从创伤中发现意义。本研究中,创伤个体在认知层面展开对创伤的意义搜寻,寻找的精神支持包括对新生命的渴望、对家庭的责任意识等。认知与应对密不可分,随着个体创伤后认知的变化,患者会出现相应的行为层面的改变[11]。本研究中进行深层次认知加工和积极沉思的妇女,同时采用了积极的应对策略,具有更好的创伤后自我恢复和发展的潜能,如通过注意转移、规避刺激等行为主动回避容易引发创伤体验的活动或情境;当妇女出现关注当下、积极备孕的行为层面转变时,是其努力成长的重要标志,医护人员应肯定其表现出的勇气。因此,如何促进伤者在认知层面从痛苦中寻求到意义,从悲伤无助到主动应对的转变是实现其成长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