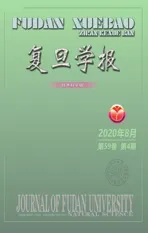福建省建设用地空间差异与溢出效应的耦合特征
2020-09-14余卓芮李登辉张丽君刘岱宁
刘 钰,余卓芮,李登辉,张丽君,刘岱宁,张 浩
(1. 河南大学 土木建筑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3; 2. 河南大学 中原发展研究院,河南 开封 475003;3.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3; 4. 河南大学 环境与规划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3;5. 复旦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上海 200438)
当前世界范围内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已成为全球土地利用变化的突出特征,建设用地在全球陆地的占比从1992年的0.23%上升至2013年的0.53%[1];在此期间,我国建设用地的增速首冠全球并呈现明显的地域空间失衡特征,主要表现为各个城市的建设用地规模差异巨大[2];此外,建设用地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市具有溢出效应,以其为中心形成了建设用地聚集区[3].建设用地在空间上的非均衡扩张不仅影响到经济发展效率和社会公平[4],造成重点建设地域的生态压力过大[5],引发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加剧等城市问题[6],因而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现有的对建设用地空间失衡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包括建设用地规模[6-7]、开发强度[8]、利用效率[9]和供给政策[10]等多个视角;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遥感监测[1]、驱动力分析[11]和情景模拟[12]等多种技术手段;在实证案例上,包括国家[2]、城市群[13]和省级[14]等多个空间尺度;在失衡特征上,空间差异和溢出效应是相关研究关注的主要维度[2,14-15].但是现有研究对建设用地这两种空间维度的分析基本上都是独立展开,缺少对空间差异和溢出效应的耦合分析.例如,在空间格局层面,Wei等基于Gini、Theil和变异系数测度了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空间差异[2],也有学者通过空间自相关系数分析了建设用地的空间溢出特征[15],但相关研究很少关注建设用地空间差异和空间溢出的格局是否存在关联和耦合.在扩张机制方面,Li等使用spatial regimes模型揭示了建设用地规模的空间分异机制[16],Yang等基于spatial lag模型分析了建设用地扩张机制中的空间溢出效应[14],但很少有研究将两种空间机制纳入统一模型进行分析.spatial lag with regimes模型是Anselin院士领衔的GeoDa团队近年开发的空间计量模型[17],其优势在于可将空间分异和溢出效应进行耦合分析,但在建设用地相关研究中鲜有应用.
现有研究中建设用地空间差异与溢出效应耦合分析的缺失,会制约理论分析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并导致政策导向上的偏差.首先,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形态往往同时呈现了空间差异和溢出两种效应.例如,平坦开阔易于开发的地区经常是建设用地规模较大城市的集中区;而受地形等自然条件所限无法大规模开发的地区,往往是建设用地规模较小城市的连片区.两地区间既反映了建设用地规模上的空间差异,也分别呈现了“高-高”和“低-低”两种空间溢出类型.此外,由于溢出效应,中心城市会强烈推动周边地区建设用地的扩张,而对偏远地区的作用较小,从而使建设用地表现出“中心-外围”的空间差异特征[2].可见,建设用地的空间差异和溢出效应是密切关联耦合的,对两者耦合和相互影响的识别、测度与演化的分析是建设用地空间格局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内容的缺失,会影响相关理论分析的完整性和科学性,甚至会导致分析结果的偏差.其次,在建设用地扩张机制的回归分析中,如果缺少对空间差异和溢出效应耦合性的检验、识别与估计,独立使用空间差异模型或者空间溢出模型,就会导致回归结果的偏差,进而形成错误的政策导向[17].综上可见,无论对深入地揭示建设用地空间机制还是对科学地制订建设用地管控政策,建设用地空间差异与溢出效应的耦合分析都是亟待深入探究的科学命题,但目前针对两者耦合特征的研究仍比较缺乏.
有鉴于此,本研究以建设用地空间差异和溢出效应的耦合特征为切入点,以建设用地快速扩张的福建省作为案例开展了如下研究:(1) 采用Theil指数分析了建设用地的空间差异特征,并讨论了空间溢出效应对空间差异的影响;(2) 基于全局和局域两个尺度的Moran指数分析了建设用地的空间溢出效应,并揭示了溢出效应类型的地带性空间差异;(3) 基于spatial lag with regimes模型,通过将空间差异和溢出效应同时纳入到建设用地扩张机制的回归模型中,初步揭示了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要素和扩张机制,并对扩张机制中的空间差异和溢出效应的嵌套耦合结构进行识别.本研究结果可为区域土地利用和城市建设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1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在海峡西岸经济区以及“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推动下,福建省成为城市建设用地快速扩张的典型地区.1995—2015年间,其建设用地由365km2快速扩张至1414km2,扩张了约3倍[18].深入分析其建设用地的空间差异特征与溢出效应,对福建省的土地资源利用优化、城市发展调控都将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研究对象为福建省的9个地级市辖区、13个县级市及45个县(图1).建设用地规模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提供的1∶10万土地利用数据集,通过ArcGIS 10.6提取各县级行政单元的建设用地规模,包括1995、2000、2005、2010和2015 5个年份.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因素的数据均来自于历年《福建统计年鉴》[18],与建设用地数据年份对应一致.

图1 研究区域Fig.1 Study area
1.2 空间差异分析方法
本研究选择可以分解空间差异的Theil指数对福建省建设用地的总体差异、以及“沿海-内陆”和“中心-外围”差异进行分析[19],公式如下:
(1)
(2)
(3)
(4)
式中:T,TI,TB分别为总体、组内、组间的Theil指数,x为建设用地规模,n为行政单元数量,i和j分别为分组之间和分组内部的标记.CB为组间差异贡献率.Theil指数越大,则其表征的建设用地空间差异越大.
为考察福建省建设用地规模的“沿海-内地”差异,将其行政单元分为2组,内陆地区的南平、三明、龙岩3个地级市所辖的行政单元为一组,其余沿海地级市所辖的行政单元为另一组,从而比较“沿海-内地”2组间的差异.此外,为考察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建设用地差异,并分析中心城市溢出效应对建设用地空间差异的影响,将地级市辖区分为一组,其余行政单元分为另一组,从而比较“中心-外围”两组间的差异.
在分析组间差异时,除了分别测算其组内与组间的Theil指数,还基于Rey等提出的Theil指数的permutation检验方法[19],对组间差异进行统计显著性检验.此外,还使用式(4)分别计算了“沿海-内地”、“中心-外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
1.3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被学界广泛应用的Moran’s I指数(包括全局尺度的Moran’s I指数和局域尺度的Moran指数)来分析建设用地规模的空间溢出效应[15,20].
全局Moran’s I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5)
式中:I为全局Moran’s I指数,n为行政单元数量,wij为空间权重矩阵,x为建设用地规模.全局Moran’s I指数的取值一般在-1~1之间,小于0表示负相关,表明高值与低值相邻;如果Moran’s I等于0,则表示随机分布;大于0表示正相关,表明在区域全局尺度上具有高值与高值相邻、低值与低值相邻的整体态势,这表明在全局尺度上各空间单元间存在空间溢出效应[15].
全局Moran’s I指数可揭示建设用地规模在福建省整体的空间自相关性,但不能揭示局部地区的空间分布规律,无法识别建设用地在特定局域的空间关联特征.本研究基于局域Moran指数,用来检验在局域尺度建设用地是否存在空间关联并识别其关联类型[15].计算公式如下:
(6)
(7)
式中:Ii为行政单元i的局域Moran指数,xi和xj分别为i及其相邻行政单元的建设用地规模,Wij为空间权重矩阵,n为行政单元数量.局域Moran指数为正时表示存在局域的空间相关聚集,即建设用地规模较大的行政单元其周围区域也是高值(H-H),或者是低值的周围也是低值(L-L);值为负时表示存在局域的相异特征,即建设用地规模较小的行政单元被规模较大的单元包围(L-H),或者规模较大的单元被规模较低的单元所包围(H-L).通过识别和检验建设用地规模的空间关联类型,可对其局域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
1.4 建设用地扩张机制及其空间效应分析方法
相关研究指出,建设用地扩张机制存在空间效应,包括空间分异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空间分异效应是指建设用地的驱动要素在不同的空间局域对建设用地的驱动强度存在差异[2,16].空间溢出效应是指特定地域的建设用地规模除受到本地的驱动要素的影响外,还受到临近地域的影响[14-15].
建设用地扩张机制的空间分异效应可用spatial regimes模型进行分析[16],两空间地域的模型形式为:
(8)
其中y为因变量,X为自变量,β为回归系数,ε为残差.驱动因素在两个地域的驱动强度的差异可用其在不同地域的回归系数β1和β2的差异来表征,驱动强度差异的显著性可由Chow检验获得.
建设用地扩张机制的空间溢出效应可用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 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进行分析[14-17].空间滞后模型适用于因变量本身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的场景,即特地地域的建设用地规模与临近地域的建设用地规模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其模型形式为:
y=ρWy+Xβ+ε,
(9)
其中W为空间权重矩阵,ρ为W的回归系数,其他同式(8).
空间误差模型可应用于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因素没有全部包含在模型中,模型误差项中可能存在空间溢出的场景.其模型形式为:
y=Xβ+μ,
(10)
μ=λWμ+ε,
(11)
其中λ为W的回归系数,其他同式(8)和(9).在实证分析中使用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可用LM检验(Lagrange Multiplier Test)识别[17].
当建设用地扩张机制中同时存在空间分异和空间溢出效应时可用spatial regimes结合空间滞后或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分析[17],结合空间分异和空间滞后的模型形式为:
(12)
结合空间分异和空间误差的模型形式同式(8),但在残差部分包含了空间项:
(13)
驱动因素的回归系数在不同局域的差异表征了其驱动强度在不同局域的差异,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项的回归系数在不同局域的差异表征了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局域的差异,这些差异的统计显著性可进行Chow检验.最后,模型残差中是否还存在其他空间效应,可进行AK检验(Anselin-Kelejian Test)[17].
2 结果与分析
2.1 建设用地的空间差异分析
福建省建设用地规模的空间差异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波动趋势,其Theil指数从1990年的0.61上升至2005和2010年的0.80,然后在2015年又降至0.74.从分组差异来看,沿海和内地两组间的差异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表现为组间Theil指数从1990年的0.03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0.08,组间差异对整体差异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4.76%上升至2015年的10.75%,其组间差异的统计显著性也在2010年起从不显著转为显著(表1).福建省建设用地日益突出的“沿海-内地”差异可归因为,福建沿海地区位于北接长三角南联珠三角的交通走廊上,是福建省经济最为发达、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在经济增长和居民住房需求的推动下,其建设用地的扩张速度要快于福建其他地区[15].2009年《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出台,临近台湾的沿海城市建设在政策支持下快速推进,使得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建设用地规模差异日益扩大.

表1 福建省建设用地“沿海-内地”差异的Theil指数Tab.1 The Theil index for the coastal-inland differ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land in Fujian Province
福建省建设用地规模在各地级市市辖区和周边县域之间还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差异(表2),分析结果显示两者的组间差异对整体差异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3%以上,而且组间Theil指数在整个研究时段内都在0.0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是由于市辖区在人口和企业数量、基础设施水平等方面远高于其他县域,人口居住、企业运行、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另一方面,市辖区的行政层级也高于其他县域,从而在建设用地指标的获取[10]、开发区的设立上[16],都具有优势.在以上因素的共同驱动下,市辖区的建设用地规模会远大于其他县域.

表2 福建省建设用地“中心-外围”差异的Theil指数Tab.2 The Theil index for the core-periphery differ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land in Fujian Province
从演化趋势上看,中心市辖区和周边县域的组间差异Theil指数从1995年的0.28持续下降至2015年的0.25,组间差异对整体差异的贡献率从1995年的46.15%下降至2015年的33.24%.这说明地级市辖区与周边县域在建设用地规模上的差异在逐步缩小.这与中心市辖区对周边县域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关.具体来看,非市辖区的行政单元中,1995至2015年间建设用地增长速度位于全省前列的闽侯县、龙海市、长泰县、安溪县等均与其所属的市辖区相邻.可见,市辖区对其周边的溢出效应,是中心市辖区与县级地域之间建设用地规模差异缩小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福建省建设用地的空间差异表现为“沿海-内地”和“中心-外围”差异.其中,“中心-外围”差异居于主导地位,一方面表现为整个研究时段内其差异都呈统计显著性,而“沿海-内地”差异只在研究时段末期具有统计显著性;另一方面,其对省域差异的贡献率一直在33%以上,而“沿海-内地”差异的贡献率都处于11%以下.
福建省建设用地空间差异与溢出效应的耦合性体现在,溢出效应对居于空间差异主导地位的“中心-外围”差异有重要影响.由于市辖区对其周边县域的溢出效应,其周边县域的建设用地快速扩大,使得县级行政单元建设用地的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中心-外围”差异对省域差异的贡献率也从46%持续下降至33%,有效缓解了建设用地过于集中于中心城市的失衡问题.
在现有研究中,相关学者大多将建设用地空间差异归结于制度转型,主要包括全球化、市场化以及分权化等制度层面的转变.同时这些学者也指出,影响建设用地空间差异的因素是多元的,现有研究还远未全面揭示建设用地空间差异的机制[2].本研究发现空间溢出效应是建设用地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为全面揭示建设用地空间差异机制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其政策意义在于,揭示了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是缓解建设用地空间分布的失衡的重要抓手,建设用地规模滞后的地区应通过交通设施的建设积极对接中心城市,并着力激发本地中心城市的带动能力.
2.2 建设用地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福建省建设用地规模的全局Moran’s I指数的历年均值仅为0.05,而且在0.05的置信水平不显著;而局域Moran指数结果显示福建省县级单元存在多种空间关联类型,而且多个地区在0.05的置信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图2,见第454页).这说明,福建省建设用地规模的溢出效应具有较强的局域特征,而且不同局域的溢出效应具有多样性;各局域不同类型溢出效应的拮抗作用导致在省域全局尺度的整体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图2 福建省建设用地的空间关联类型Fig.2 Spatial interaction types of the construction land in Fujian Province
福建省建设用地规模的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中心市辖区-外围县域”结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位于福建东南的厦门、漳州、泉州的市辖区,三个市辖区不仅建设用地规模大,并能带动周边县域的建设用地规模也快速增长,形成了空间上连续的“高-高”聚集区,而且聚集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与之相对,东北方向的福州、莆田市辖区和西南方向的龙岩市辖区的溢出效应则较弱.虽然这些市辖区的建设用地规模较大,但这些市辖区对周边县域的带动作用不明显.由此导致这些市辖区的空间关联类型为“高-低”,其周边县域为“低-高”类型,进而在2015年形成了由福建东北蔓延至西南的空间上连续的“低-高”关联类型的廊道.
福建省建设用地规模的溢出效应还具有“沿海-内陆”差异特征.如前所述,东南沿海的厦漳泉地区表现为显著的“高-高”聚集,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该类型沿海岸线由北向南进行扩展,说明东南沿海地区的县级单元不仅自身建设用地规模大,还推动相邻地区的建设用地扩张.而在内陆地区则形成了“低-低”聚集的连片区.在2015年,福建内陆的西北地区完全被“低-低”聚集类型覆盖.这说明该地区的县级单元不仅自身建设用地规模小,还对相邻单元形成了制约.
综合来看,福建省的建设用地规模在局域尺度上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一方面表现为中心城市与其周边城市的相互作用,呈现出了“中心-外围”结构.另一方面空间溢出还存在地带性差异:厦漳泉地区的中心城市溢出效应较强,呈现“高-高”类型的聚集态势;福州、莆田和龙岩地区的中心城市溢出效应较弱,中心城市周边县域形成了“低-高”类型的廊道;而西北内陆地区的中心城市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溢出能力,则形成了“低-低”类型的集中区.
福建省建设用地空间差异与溢出效应的耦合性体现在,空间差异对溢出效应有明显影响.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大,经济水平高,与周边地区的交通联系便利,从而能有效带动周边城市的建设,对周边的溢出能力强;而内陆地区受地形制约,其中心城市的建设用地规模小,经济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水平都较低,难以对周边城市的建设进行强有力的推动,从而对周边的溢出能力弱.中心城市溢出能力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建设用地空间溢出类型的地带性差异.
现有的对建设用地空间溢出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检验是否存在空间溢出,以及识别空间溢出的类型[15],对空间溢出类型的形成机制探讨较少.本研究从空间差异的视角切入,揭示了建设用地的空间溢出类型存在的地带性差异,并指出各地带内中心城市的溢出能力对当地的建设用地空间溢出类型有决定性影响.其政策意义在于,应因地制宜的制订建设用地开发政策,基于当地中心城市溢出能力的高低,对周边城市的建设用地规模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控.
2.3 建设用地扩张机制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研究在参考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建设用地扩张机制的空间计量分析.选取的驱动因素及选取依据包括:(1) 经济总量.为了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地方政府主导了大量开发区建设,通过土地资源的大量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导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建设用地也急速扩张[6].本研究以GDP总量以及各产业的GDP来表征经济总量.(2) 企业发展.对于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其发展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而地方政府为了吸引企业投资,往往以较低的价格向企业出让建设用地,从而成为建设用地扩张的重要推手[7].本研究以企业利润和利税来表征企业发展.(3) 住房需求.住房需求是推动建设用地扩张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以县域人口、各类企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来表征住房需求量及居民购买能力[15].(4) 交通设施.交通设施是建设用地扩张的重要驱动因素,一方面交通设施的建设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另一方面人流物流和商品交易在交通设施沿线的聚集往往催生大量的建设活动[21].本研究以公路里程表征交通设施的规模.
首先,对采用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估计的非空间模型进行LM检验,结果显示1995年和2015年的LM_lag检验都在0.05的置信水平显著,而LM_error在0.05的置信水平均不显著,这说明应使用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分析(表3).

表3 OLS回归结果Tab.3 The result of OLS regression
其次,spatial regimes模型的Chow检验结果显示,将福建分为沿海和内地两个局域,全局和部分因素的检验结果在0.0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福建省建设用地的扩张机制存在“沿海-内陆”空间分异(表4和表5).

表4 1995年空间计量回归结果Tab.4 The result of spatial econometrics(1995)

表5 2015年空间计量回归结果Tab.5 The result of spatial econometrics(2015)
由于建设用地扩张机制同时存在空间分异与空间滞后效应,应采用spatial lag with regimes模型进行分析.对比各模型的调整决定系数(Adjusted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Adjusted R2)发现,spatial regimes和spatial lag with regimes模型的调整决定系数在不同局域存在差异,其中拟合水平较好的局域的调整决定系数都高于OLS估计;而spatial lag with regimes模型的调整决定系数在各局域均高于spatial regimes模型.这说明spatial lag with regimes模型的拟合水平要优于其他模型,所以本研究采用其结果来进行建设用地的扩张机制分析.
spatial lag with regimes模型回归结果的Chow检验显示,1995和2015年的建设用地扩张机制均存在空间分异(表4和表5).首先,两个年份的全局Chow检验都在0.0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福建省建设用地的扩张机制在整体上存在“沿海-内陆”分异.其次,1995年所有驱动因素、2015年企业利税和农民收入的Chow检验也都显著,说明这些因素对建设用地的驱动强度存在显著的“沿海-内陆”差异.最后,两个年份空间滞后项的Chow检验也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沿海-内陆”两个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由此可见,福建省建设用地扩张机制存在系统性的“沿海-内陆”分异,而且多个驱动因素在两局域的驱动强度也存在显著差异;此外,两个局域的空间溢出效应强度也存在显著差异,体现了扩张机制中存在的空间分异和空间溢出的嵌套结构.
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可以判断建设用地的扩张机制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回归结果显示,福建省建设用地扩张机制中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局域性特征,具体表现为1995年的溢出效应局限在内陆地区,而2015年仅存在于沿海地区.
1995和2015年回归结果中的AK检验均不显著,说明回归残差中已没有显著的空间效应,从而表明上述的spatial lag with regimes模型结果较为完整的揭示了福建省建设用地扩张机制中的空间结构.
从驱动要素来看,在1995年,第二产业GDP是沿海地区唯一呈现统计显著性的驱动因素,而且其在内陆地区也显著.第二产业GDP在两个分区的回归系数都为正,体现了工业化在福建全省尺度上对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作用.第二产业GDP的Chow检验显著,而且内陆地区的回归系数高于沿海地区,这说明第二产业GDP在内陆地区的驱动强度要高于沿海地区.这可能与内陆地区此时处于工业化初期,对建设用地的需求量更大有关[22].对于内陆地区,除了第二产业GDP,集体从业人口、农民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回归系数也呈现统计显著性,说明内陆地区建设用地的驱动因素更加多元化.
对于2015年,企业利税是唯一在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回归系数都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因素,而且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表明福建省建设用地普遍受到企业发展的推动[7].企业利税的Chow检验显著,而且内陆地区的回归系数高于沿海地区,说明沿海地区企业用地的效率较高,形成相同的税收需要投放的土地资源较少.除了企业利税,沿海地区具有统计显著性的驱动因素还包括第一产业GDP和农民收入,但这些因素在内陆地区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沿海地区的城乡联系较为紧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对城市扩展的影响较大;而在内陆地区由于城乡分割,农村对城市建设影响较小[11].在内陆地区具有显著性而在沿海地区不显著的因素为公路里程,可能的原因是在此时段内内陆地区的交通设施大规模建设推动了建设用地的扩张;而沿海地区的交通条件此时已经比较完善,对建设用地的驱动较弱.
综上所述,福建省建设用地的扩张机制中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和溢出效应的耦合嵌套结构,而且在不同空间地域和不同的时间发展阶段,驱动要素与空间溢出水平都存在差异.这些结果的理论意义在于现有研究大多局限于建设用地扩张的空间差异或者空间溢出效应的单方面检验和分析[14,16];在后续的研究中应加强空间差异和溢出效应耦合性的检验、识别和分析,从而全面、科学的揭示建设用地的扩张机制.这些结果的政策意义在于,应充分重视不同空间区位的城市间的相互影响存在的差异,依据区域的空间区位特点和发展阶段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
3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Theil指数、Moran指数和spatial lag with regimes模型,对福建省建设用地规模的空间差异和溢出效应进行了耦合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 1995—2015年间,福建省建设用地规模的Theil指数处于0.61~0.80之间,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特征.其中,“沿海-内地”差异及其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呈持续上升态势,组间差异的统计显著性由不显著转为显著.市辖区及其周边县域的“中心-外围”差异在省域差异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其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一直在下降,这可归因于市辖区对周边县域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关结果揭示了建设用地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其空间差异有重要影响.这在理论上为完善建设用地空间差异机制提供了重要补充,在政策上揭示了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溢出效应可作为调控建设用地空间分布失衡的重要抓手.
(2) 福建省建设用地规模呈现空间溢出特征.在东南沿海的厦漳泉市辖区的带动下,其周边县域的建设用地规模也维持在较高水平,形成了“高-高”类型的建设用地热点区域.而福州、莆田和龙岩市辖区的溢出效应较弱,其周边县域的建设用地规模呈现“低-高”类型聚集的特征.而在西北内陆地区,由于缺乏具有强有力带动能力的中心城市,形成了“低-低”类型的连片区.相关结果从空间差异视角揭示了建设用地空间溢出类型的地带性差异,在理论上指出了建设用地空间溢出类型差异的形成原因,在政策上指出了建设用地调控中应基于各地区中心城市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制订调控政策.
(3) spatial lag with regimes模型结果显示,福建省建设用地的扩张机制存在空间差异与空间溢出的嵌套耦合结构:对于沿海和内陆地区,建设用地的驱动要素及其驱动强度存在差异,而且空间溢出效应也局限在两个局域内部.1995年和2015年分别只有一个驱动因素在沿海和内陆地区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分别为第二产业GDP和企业利税,而且这两个因素在内陆地区的驱动强度都强于沿海地区.相关结果在理论上进一步揭示了建设用地扩张机制中复杂的空间结构,在政策上也为福建省土地利用政策工具的选取提供了参考.
基于福建省建设用地空间差异与溢出效应的耦合特征,为推动福建省建设用地的有序和协调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福建省建设用地在“沿海-内地”间的差异呈持续扩大态势;“高-高”聚集的热点地区局限在东南沿海地区,而在西北地区甚至形成了“低-低”聚集的连片区域;在扩张机制上,建设用地规模存在溢出效应,但溢出效应存在沿海和内陆分隔,溢出效应都局限于沿海和内陆地区内部.福建应充分发挥空间溢出效应对空间差异的影响作用,向内陆地区引入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并着力激发内陆中心城市的溢出能力,以实现“沿海-内陆”的均衡发展.
在具体措施上,应重点建设由东向西的3条发展轴:① 福州至武夷山发展轴,在福建北部形成由福州出发,经由闽侯、古田、建瓯、建阳、武夷山等城市的发展轴线,通过重要节点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打破西北地区建设用地的“低-低”连片区.② 泉州、莆田至三明发展轴,横贯福建省中部区域,呈“人”字形格局,连接福建沿海的两个地级市和西部三明地区,并向省外延伸至江西南昌以及长江中游城市群.③ 厦门至龙岩发展轴,横贯福建省南部区域,以厦门为龙头,带动漳州、龙岩、连城、长汀等城市的发展,向省外联系长株潭城市群.
在这些发展轴上以复合型快速交通通道为依托,以城市和产业园区为主体,构筑城镇和产业发展聚合轴,将沿海的辐射动能传导至西部内陆地区,同时在西部打造地区性增长极,适当扩大西部地区城市建设规模,提升福建省城市发展的整体协调水平.
(2) 福建省建设用地呈现“中心-外围”的空间溢出效应:由于市辖区中心对周边县域的带动作用,两者之间的差异不断收窄;以厦漳泉市辖区为中心,并辐射周边县域,形成了福建省最为显著的“高-高”聚集区.但由于各地发展条件的差异,福建省建设用地的空间溢出类型存在明显的地带性差异.福建省应立足因地制宜的政策导向,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实现市辖区及其周边县域的一体化协调发展.
对于西北地区的建设用地连片“低-低”聚集区,应依托上述福州至武夷山发展轴,在轴带上选取区位条件好、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大的城市,培育地域性的增长极,通过建设用地等资源的投入,引导其城市建设率先开展,进而形成地域性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中心,并带动周边发展.
对于福州、莆田、龙岩等溢出效应较低的市辖区,应强化中心市辖区和周边县域的交通建设与联系,以密集的交通产业带为纽带实现两者一体化发展.发展高科技产业集群,借助知识与技术较强的溢出性,提高这些市辖区的聚集、扩散与辐射功能.加强市辖区与周边的城市职能分工与专业化合作机制,形成产业梯度发展与合作互补.以产业差异化合作为基础,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优化建设用地在中心市辖区和周边县域的空间布局.
对于厦漳泉地区,应依托上述厦门至龙岩发展轴,形成“厦门-龙岩”双核结构和贯通福建南部的发展廊道,在扩大经济发展的腹地的同时,也减缓建设用地由于过度集中在东南沿海从而对当地自然生态和城市环境形成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