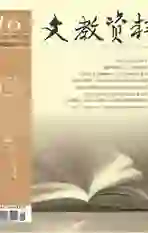苦 难 与 超 越: 论 山 本 的 悲 悯 力 量
2020-08-20王雪薇
王雪薇
摘 要: 贾平凹的小说《山本》,着眼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陕西秦岭上的涡镇为缩影,表现在苦难磨碾下普通百姓苟且偷生的情景。芸芸众生的人性异化,历史的荒诞与苦难的背后,是贾平凹以超越尘世的悲悯之情对于天地万物的观照。涡镇被摧毁之后,象征着秦岭文化精神的剩剩,默默无言地注视着一切,儒道佛融汇的人性光辉照亮了满目疮痍的原始大地。笔者进入已经褪色的秦岭的历史,感受贾平凹如何实现对于人世苦难的救赎,以及对人间大爱的执着探寻。
关键词: 《山本》 贾平凹 苦難 悲悯 民间
《山本》延续了贾平凹一以贯之的救赎美学追求,对一隅之地的观照辐射战乱时代的生存境遇。无论是早期的商州系列以美好憧憬消解苦难,还是痛心疾首于城市文明席卷下凋敝的“废乡”,希冀为传统文明注入蛮力的发声,贾平凹的苦难叙事始终熔铸着以儒家为底色兼以庄禅的深沉关怀。《山本》意为“山的本来”,是“写山的一本书”,也就是秦岭。战乱割据、炮火连天的极境苦难和日常生存性的苦难双重碾压着底层的普罗大众,人性在历史的泥淖里翻腾。多少兴亡事,付诸秦岭中,苍莽之中亘古不变的爱为这芸芸众生的痛楚带来灵魂的荡涤。
一、战争与生活的双重苦难
叔本华认为:“属于生命的痛苦构成了对世界现实的一个标准,世界在苦难中获得最高的强度。”[1](75)苦难是人类无法规避的一种生存困境,作为人类生活和命运的基本存在,对苦难的阐述和思考一直都是哲学、宗教学、文学所探寻和把握生命本质的超越性力量。贾平凹在《山本》的后记里谈道:“那年月是战乱着,如果中国是瓷器,是一地瓷的碎片年代。”[2](404)作为华夏文明的龙脉,秦岭统领着南北方,提携着黄河长江,奇珍异兽和魑魅魍魉氤氲着神秘鬼魅的色彩,更替着腥风血雨的风云传奇。政局混乱,各种势力并峙于涡镇,正义与邪恶的界限被完全打破,革命的初衷发生变化,慢慢演变为嗜血的竞赛。保护涡镇繁荣安康的英雄井宗秀为兄报仇,将仇人三猫剥皮做成人皮鼓,挂在皂角树上;井宗丞为了筹集活动经费,绑架亲生父亲致其淹死粪坑;土匪打砸抢烧,驻扎于镇上,黑河与白河在涡镇村外交汇,岸下的涡潭如磨盘在推动,急速地旋转,手无寸铁的普通人的命运如覆巢危卵走向毁灭。
秦岭万千自然风物下,不仅绵延着亘古的龙脉,而且循环着日复一日的战争与苦难。“无论这历史中有多少血污、暴行和不公正,都由于它是‘通向未来的堂而皇之地谅宥了”[2](523)。历史的合法性一直是叙事讨论的焦点。正规历史性写作是一种语言学构建的对于历史的未来性展望,从整体上看到历史的趋势,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阉割”着边缘的历史叙述。《山本》却没有刻意给历史下一个是非功过的定义,也没有从家国体的维度和伦理纲常肯定绝对的善恶之争,而是原本地复现着历史的本来。人类内部存在难以阻遏的兽性因子,苦难和权力就如同孪生兄弟一样。在封建社会,权力是远离苦难的武器,夺取武器又需要依靠无尽的“暴力武器”,以暴制暴。如今,在这种斗兽场般的角逐中,嗜血成为英雄的标记,暴力戴上“正义”的面纱,权力和暴力相伴而生,战争、鲁迅笔下的“吃人”传统获得蔓延和生长的土壤。
战争又催化着苦难,《山本》中,芸芸众生在历史的漩涡中苦苦挣扎。旱灾和蝗灾一系列自然灾害的侵袭,百姓逃荒要饭维持生存,贫穷与困厄的日常生活更是人性本相的试金石。根深蒂固的农民身份认同感,使贾平凹洞悉了底层民众善良忠厚、勤恳节俭的美德,和与之相伴而生的自私保守、贪婪狭隘的劣根性。《二月杏》中,插队女青年二月杏被人凌辱,村民们却污蔑、谩骂受害人,《带灯》中带灯面对着鸡零狗碎的村镇事务,其他领导却以权谋私,相互攻讦。《山本》中,涡镇村民借骡子去买石灰筹备保安队和预备团之间的交战,没想到被半路截和了,但村民只管骡子不管战况,一心索赔,直至后来对方攻城的时候放出骡子,村民害怕伤到骡子,差点中了对方的奸计。一群本身已身处苦难的小人物,或隐忍度日,争吵不休,相互依赖却倔强地活着,或被革命话语和日常琐屑吞噬,抡起手中的无形之刃,宣判合理的正义,在荒谬的历史进程中制造更多的苦难。
二、超渡苦难的人性光辉
《山本》里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这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在贾平凹看来,“在苦难中,精神并不一定是苦难,这犹如肮脏的泥潭里生出的莲却清洁艳丽”[3](90)。苦难意识与叙事主体的文化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任何苦难都是人的苦难,承受者是个人,但在更深层次上指向的是更宽广的社会空间性,是人类的“集体受难”。余华对于苦难的叙事已臻极致,以零度叙述的口吻无动于衷地咀嚼着苦难盛宴,苦难就像铺天盖地的大网覆盖着普通人,他致力于呈现文学的基本母题:人的本质和命运。“他有意识让苦难主体成为了无意识的自行本体,让他们的苦难终结在苦难中,让他们就在苦难中涅槃”[4](87)。贾平凹的温情之处是在苦难的废墟上开出了救赎的花。涡镇毁灭于无尽的硝烟中,陆菊人和陈先生默默地注视着曾经的绚烂化为灰烬,既没有躲又没有跑,人性的豁达、慈悲、善良为这苦难覆盖的秦岭大地增添了人道主义的光辉。
贾平凹书写过很多女性形象,陆菊人是特别的。年幼丧母的她,后来丈夫和公公相继去世,只有跛脚儿子剩剩与她相依为命,但是在她身上自始至终没有看到怨天尤人和农村妇女的狭隘自私,相反陆菊人端庄大方,主见肯定,精明能干,有着儒家精进入世、宽仁慈爱的精神。雅斯贝尔斯认为:“如果没有面对苦难的真正悲剧意识,缺乏对神祇和命运的抵抗中与人类休戚与共的同情心和道德感,就无法实现救赎,无法抵达存在的澄明境界。”[5](74)陆菊人始终有个念头,她希望井宗秀能“修齐治平”,成为涡镇的英雄,这实际上是贾平凹隐含的儒家理想。她经常去安仁堂和130庙,为这几年镇子上死去的人掏钱立牌位,可以被看作是现世生活在涡镇的一位活菩萨。当日复一日的苦难撑破了涡镇的边界,生存于此地的涡镇人绝大部分化成了尘土,只有陆菊人还在,她始终用悲悯的目光注视着炮火,悲喜,人事。
郎中陈先生和宽展师傅的存在不仅维系和延续着中国农村社会的精神命脉,而且是陆菊人能够在乱世中始终维持着警醒和悲悯的引路人。“他们首先是医生,又都是道家,做身与心的救治,陆菊人的成长,背后就是陈先生”[6](34)。那个年代的医者,医治的不只是肉身,更多的是疲惫枯竭的内心。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7](124)陈先生作为道家的弟子,主张清静无为、追求天人合一,尽管是个盲人,却不为外界乱象所迷惑,治病的同时又以自己的处世之道安抚病人的心结。宽展师傅是个尼姑,又是哑巴,但总是微笑着。土匪在涡镇烧杀抢掠,甚至经常以割舌、殴打等暴力恐吓宽展师傅,并派人看守寺庙,对于宽展师傅来说是心灵的恐慌和灵魂的玷污。然而,130庙大殿和宽展师傅的尺八是涡镇,是整个民族得以绵延的栖息之所和心灵号角,尺八静寂又悠远,穿越了沉重的历史,回荡着袅袅余音在空旷无言的秦岭中。寺庙里的地藏菩萨以佛家的慈悲之心普度众生,无论生前显贵,还是恶贯满盈,死后皆得以超度。
陆菊人、陈先生和宽展师傅始终带着浓重的人道使命,显示了对苦难的超越。别尔嘉耶夫曾说:“超越,是一个蕴含着动力的积极主动的创造过程,是一种深刻的内在体认。具体地说,即在自己的生存中体认地狱、深渊、灭顶之灾、勃生阻绝之感,引发创造之举。”[8](13)超越维系着它被真理所揭示出能给人生存以慰藉的勇气和纯洁的道德价值,由此超越不仅仅是个过程,更像是一种反抗和忍受苦难的姿态和意象。井宗秀曾经看着陆菊人,说:“我看着你身上有一圈光晕,像庙里地藏菩萨的背光。”[2](100)陆菊人如地母般言说着对于这片土地的大爱。而陈先生和哑了的宽展师傅则在欲望、战争、历史的错杂喧响中,践行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至高境界。
三、民间大地的悲悯救赎
陈晓明说:“贾平凹《废都》之后的作品以更朴拙的手法回到乡土,他的小说越写越“土”……而倾笔力于描写乡土生活的原生状态。新世纪以来,贾平凹的叙述手法愈来愈“狠”,以此方式叙述乡村进入现代经历的酷烈冲突。“土”与“狠”构成了美学关联……”[9](69)“土”作为贾平凹写作的审美特质,勾连的是三秦大地苍凉古拙、神秘魅惑的民间文化想象。小说起述于陆菊人她爹的一块三分胭脂地,这块地最后却阴差阳错埋了井宗秀的爹,于是“涡镇的世事全变了”。这种渗入民间、统摄万物的风水文化、灵异称道的神秘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贾平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实践,也是陕西本土巫楚文化所根植在人们内心集体无意识的心理认知,以贾平凹的话来说是:“《山本》打开了一扇天窗,神鬼要进来,灵魂要出去。”[10](90)
隐秘诡谲的原始体验尘封在贾平凹的灵魂里,林林总总的“万物”呼之欲出,碰撞着幽暗的、神秘的火花,浮现出天人合一的生命本相。客观的“象”和主观的“意”所构建的意象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符合对象,借由动物或植物等来寓说作品的隐性结构,使人的本质意义在这些神秘意象中得到写意性的呈现。《山本》中自始至终存在一只黑猫,每当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时,它就会出现。这只黑猫经常卧在瓦槽里,像个幽灵般望着来往的人,安静无息,神出鬼没,冷眼旁观着世间万象。黑猫的大眼睛占了头的一半,始终处在静静观察,双眼睁着的姿态,陪伴着陆菊人带有伤残的儿子剩剩。陆菊人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会“询问”黑猫的意见;在剩剩受伤前骑马的时候,黑猫发出了古怪的声响;剩剩的原名叫“猫剩”;最后炮火轰炸时,这只黑猫依旧在剩剩怀里,一动不动……陈思和言道:“涡镇成为废墟时,炮火中那只猫陪伴着剩剩,暗示了来自某种民间神秘文化的救赎。”[11](85)
同样,植物具有偌大秦岭冥冥之中暗示的力量。涡镇路口前那棵古老的皂角树是德性和神性的捍卫者。这棵皂角树浑身长满了硬刺,德行好的人路过会有皂角落下,然而后期井宗秀将三猫做成人皮鼓挂在树上。树上没有任何动物栖息,只有雨天人皮鼓被雨水拍打的噗噗声,为了盖钟楼,不惜撬动这棵古树,打破了涡镇原有的平衡,一切开始失控。先是皂角树以自焚决绝地做出抵抗暴行的举动,再是搭建的高台压死了人,原本象征着步步高升的高台,被冤魂的戾气所吞噬与掩埋,似真似幻中坍塌成涡镇人的坟冢。
天地不仁,万物为刍狗,狗开始说人话、人能预见未知之事、听懂动物的语言、人和动物的面容难以分辨,煌煌《山本》万言中,太阳底下天地万物皆有灵性。张学军在《中国当代小说流派史》中指出:“神秘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它能给人一种朦胧、含蓄、深邃的美学感受;而它作为一种认识论的范畴,则意味着认识的有限,同时也表达了认识欲望的无限;它能调动读者丰富的想象,产生彼岸世界的追慕,从而超越了小说狭小的时空界限神秘。”[12](266)这与贾平凹的创作是十分契合的。从《废都》中的形而上的“哲学牛”,《高老庄》中的始终扑朔迷离、虚无混沌的白云湫,再到《怀念狼》中野性、生命力的人狼互渗现象,小说中所蕴含的神秘性不是纯粹的超现实世界,而是在虚实相生的美学境界中,扎根在民间底层的文化力量实现渺小生命的自我救赎。
四、结语
贾平凹拂除了覆盖在历史上的层层厚土,将历史更迭投射到天人合一的“大荒”境界中,以中国式的叙述言说着沧海桑田中万物生灵的悲哀,超越了传統正史成王败寇的叙述伦理。《山本》体现了作者来自民间大地的悲悯情怀,是贾平凹全身心浸染于秦岭这片苍茫大地的精神滋养,以历史的悲壮回眸实现“以中国之心诠释当代中国乡土”的写作旨归,站在废墟之上思索和追问,希冀唤醒民间大地上的原生力量,叩问人类存在的本体维度。
参考文献:
[1]黄大军.承受空间之重:贾平凹长篇小说的救赎美学[J].当代文坛,2018(02).
[2]贾平凹.山本[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3]贾平凹.我是农民[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
[4]左文.在苦难中涅槃——余华小说苦难叙事的佛学阐释[J].理论与创作,2004(03).
[5][德]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6]贾平凹,杨辉.究天人之际:历史、自然和人——关于《山本》答杨辉[J].扬子江评论,2018(03).
[7]张文诺.多少兴亡事,都付秦岭中——从《山本》看贾平凹的历史想象[J].小说评论,2018(04).
[8][俄]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和自由[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9]陈晓明.“土”与“狠”的美学——论贾平凹叙述历史的方法[J].文学评论,2018(06).
[10]王尧.关于《山本》的阅读笔记[J].小说评论,2018(04).
[11]陈思和.试论贾平凹《山本》的民间性、传统性和现代性[J].小说评论,2018(04).
[12]张学军.中国当代小说流派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